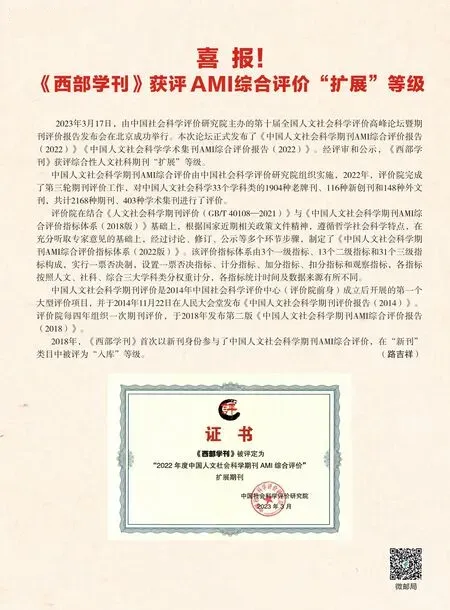环境修复与文化重建:当代青年返乡的双重生态意义
——基于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木皮藏族自治乡关坝村的调研
李承真
(中国传媒大学 国际传媒教育学院,北京 100024)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返乡青年成为新时代乡村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力量,也成为学界乡村研究的重点之一。 当下学者对于返乡青年的关注大概有三个方向:一是探讨青年返乡的动因;二是探讨返乡青年带来的效益;三是探讨青年返乡存在的问题,研究目的主要在于推动返乡青年的精英式治理助力乡村振兴。 虽然少数研究聚焦返乡青年对乡村文化的影响,但总体上看,缺少返乡青年对乡村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影响的研究,缺少将乡村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相结合的研究。 此外,既有研究在分析城市归来青年的乡村融入问题时,内化了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框架与发展主义的历史观,缺乏宏观的、动态的批判视野。
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木皮藏族自治乡的一个小山村——关坝村从生态资源禀赋与保护环境出发,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和文化重建的兼容发展之路,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方案。 在关坝村的建设过程中,返乡青年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本文采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以返乡青年为切入口,对关坝村进行案例研究。 通过线上访谈和文献收集的方式获取素材,在收集整理相关新闻报道与文献材料的基础上,采用线上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的形式,共访谈9 位关坝村村民及其相关成员(下文中以受访者姓名首字母指代受访者信息)。 通过分析关坝村发展的历史、青年在关坝村建设的活动,探讨返乡青年在生态环境修复、文化生态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以期为青年返乡参与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一、青年返乡与生态环境修复
(一)生态修复与生态产业转型
关坝村所在区域是绵阳市重要的生态腹地和水源涵养地。 正是由于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关坝村民的传统生计主要是伐木、打猎、挖药、捕捞等资源消耗型活动。 由于缺乏保护意识,早期的关坝村面临不容忽视的生态问题,比如无序采集导致多种药材被采挖一空,过度放牧导致关坝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植被和水源破坏,毒鱼、炸鱼行为导致当地珍稀冷水鱼类几乎绝迹,水质被污染。
2010 年前后,保护国际基金会的中国分机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公益组织(以下简称“山水”)开始帮助关坝村发展生态产业。 与此同时,平武县林业局为关坝村申请了“平武水基金”综合赠款项目,以扶持其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 这以后,陆续有进城务工的青年返回家乡从事生态保护工作。 在政府、山水、村民特别是返乡青年多主体协作下,关坝村在生态恢复、绿色产业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
1.开展生态保护
一是建立自然保护小区。 2015 年关坝村建立了全国首个由社区主导的保护小区——关坝沟自然保护小区。 小区管理队伍全部由返乡青年组成,保护活动的规划和执行由青年全权负责。 小区下设一个巡护队,向全村招募护林队员,以保护中草药、防止火灾、防范珍贵动物被盗猎等。 2016 年,巡护队招募队员26 人,其中60%的成员都是以前上山打猎挖药的人员。
二是增殖放流淡水鱼。 2012—2016 年间,返乡青年带领村民自发购买了几百条之前消失在关坝沟中的青石爬鮡(属国家二级保护鱼类)、黄石爬鮡、齐口裂腹鱼的幼鱼进行放流增殖。 经过几年的保护,2021年山水机构与关坝巡护队合作进行鱼类调查,结果显示三种鱼类均已得到恢复并开始自主繁殖,不再需要依靠放流来延续种群①《关坝鱼类调查:河流保护的最后一公里》,澎湃新闻,https:/ /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509652。。
2.发展生态产业
一是完善原有养蜂产业。 关坝村的养蜂合作社成立于2009 年,由于缺少销售渠道、资金、管理能力与养蜂技术,2012 年前后濒临破产,返乡青年L 主动担任起合作社整改的重任。 L 接管合作社后,一方面调整管理模式,将集体蜂场改为承包制,降低管理成本;另一方面注册“藏乡土蜜”品牌,创建淘宝店,到北京、成都等地寻找销路,积极开发蜂蜜唇膏、蜂蜜酒等衍生产品,扩展产品样态。 合作社与周边村社实施联合战略,共同推出关坝养蜂标准,以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带动周边蜂农共同致富。 在返乡青年的努力下,合作社在2014—2019 年连续分红,村民股东的现金收益达到投资的200%,被评为平武县优秀合作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
二是创办旅游合作社。 经过几年的努力,关坝的生态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恰逢县政府提出“旅游兴县”发展方针,返乡青年萌发了“生态环境好就应该发展旅游业”的想法。 旅游合作社由此于2017 年成立,由于经营不善经历了两年的空壳期,直至2019年再次将营业执照解冻,合作社才得以正式运行。 受到其他地区自然教育活动的启发,经过实地考察学习,返乡青年L 认为关坝村的下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做有关坝特色的自然教育活动。 通过发展自然友好型的旅游业,将关坝的生态保护成效充分转化成经济效益,改善村民生活。 2019 年,关坝旅游合作社正式开始接待游客,针对公益组织、亲子、青少年、社会企业等团体提供自然教育培训活动,内容包括上山林采风、野营、观摩熊猫、体验养蜂和收蜂蜜等。 截至2021 年,关坝村成功举办了17 次生态教育活动,吸引了大量科研团队和学生群体。
(二)关坝村生态建设的经验
一是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把经济发展变成环境保护一部分,这是关坝生态建设的重要经验。 关坝村生态破坏的源头在于村民的传统生计是生态资源消耗型的,如果生计结构不转变,保护就无从谈起。 因此,返乡青年积极发展生态友好型生计,通过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来解决生态保护问题。 在养蜂的过程中村民们逐渐明白,想要保证蜂蜜的产量和品质,就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包括纯净的水源、多样的蜜源等,因此为了保证生产,必须保护环境。 随着关坝村获得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外界的认可使村民们感受到了生态保护的价值,强化了保护环境的观念。
当然,生态产业的发展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依托当地的生态资源,建立产业和生态保护有机的链接。 比如关坝是依靠原有的养蜂、冷水鱼、草药等资源发展产业,而不是引入全新的产业或发展模式。 只有建立起因地制宜的产业,乡村内部才能形成“生产就是保护”的良性关系,把保护变成发展的应有之意。
二是实施圈层治理,实现理念与行动的涟漪效应。 青年返乡后看似成为村里的治理精英,但治理工作实际上是全村人共同行动和努力的结果。 那么,少数青年的理念和行为,是如何转化为村集体的理念和行为的? 这就需要在治理结构上做出调整。 关坝形成了以村委会为核心,以保护中心、合作社以及非正式组织为外围的圈层治理结构。 这些小团体就是一个个的圆圈,带领各团队的青年是圆圈的圆心,他们在工作中把自身的理念传递、辐射给团队中的成员。最先受影响的是青年的家庭,其次是各个团体成员的家庭。 逐渐地,保护环境的共识像涟漪一般散开,感染到全村人,进而在村落形成共识与合力,转化为集体保护行动。
当然,在行动的过程中要形成良性的参与和利益分配机制,既能让更多人参与到保护行动中来,和更多人产生连接,也要让更多的人都享受到保护环境的红利。 关坝村所有组织都面向全村人进行公开招募,组织负责人经过村民大会演讲、投票选举产生。 同时,合作社每年收入的10%会捐给村中的贫困家庭,使他们共享村庄发展的红利。 在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中,不论是生产材料的获取,还是活动的组织方式,都是集体式的,正是这种平等协作、共同分享的方式解决了关坝保护与发展之间、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
二、青年返乡与文化生态建设
(一)文化复兴与共同体重建
关坝所处的木皮藏族乡是集白马文化、白熊文化、土司文化为一体的融合地带。 平武县地处高寒山区,自古以来有当地人称为“白熊”的大熊猫出没,因而在宗教信仰上,白马族人将白熊视为图腾,在衣帽服饰、节庆习俗、娱乐活动中都有白熊元素的体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水电资源的开发利用,今天平武白马藏区的自然生态环境、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抢救、保护、研究和展示白马人的民族传统文化成为当地政府部门的紧迫任务。 对关坝来说,返乡青年在最初组织村里进行生态保护时,村民们的观念难以扭转,利益冲突严重,集体事务的推进困难重重,甚至出现了巡山队员监守自盗的情况。 青年们认识到,要达成共识,就要在集体内部形成向心力,寻求相互理解。 因此,2017 年青年们开始有意识地组织村里的文化和民俗活动。
一是组织大型集会、妇女舞蹈队。 关坝村的集体活动体现在每年四次的大型社区集会上。 2017 年开始,每逢妇女节、蜂王节、中秋节、重阳节,关坝村都会举行一次大型集体活动,邀请全村男女老少聚餐、跳舞。 渐渐地,这些集体活动变成了村里的常规“团建”活动。 频繁地交往使得村干部和村民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的情感联结愈发深厚,旧矛盾逐渐化解,集体内部越来越容易达成共识。 村民们相互信任,在集体事务中都甘愿无偿贡献力量。
随着集体文化活动的开展,关坝村的妇女们开始自发结成舞蹈队,有意识地排练创作白马藏族的特色歌舞。 她们创作的作品是地道的人民文艺,更是女性文艺。 作为在“离乡潮”中留守在乡村的关坝女性,她们利用女性特有的经验与视角,把关坝村的故事融入舞蹈,传递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通过组织和参与文艺活动,关坝村的女性展示出强大的生活智慧以及主体能动性,她们成了建设家乡的重要力量。
二是举办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活动。 2019 年,关坝村举办了第一届关坝自然文化观察节。 采用摄影竞赛方式面向社会招募自然爱好者,在关坝沟流域开展自然与文化的双元素调查,以科学的方式开展关坝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 文化节不仅实现了关坝生态和文化发展的群策群力,也使得关坝村民凝聚起浓厚的集体归属感和认同感。 更重要的是,对外开放的文化活动成为外界了解关坝的一个入口,旅游合作社的自然教育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白熊部落的传说、神树遗迹、白马文化等,同熊猫、蜂蜜一起成为关坝村自然教育活动的一部分。 关坝的生态资源和文化底蕴由此能够转换为经济发展的潜力,实现了生态、文化和经济的同步良性运转。 这也是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担当新使命的表现。
三是组织大型民俗活动。 每年农历三月三关坝素有祭祀蜂王的习俗。 2021 年4 月,在平武县有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关坝村主办了一场大型“三月三蜂王会”节庆活动。 活动上,关坝村民身穿传统白马服饰,不仅再现了原生态的民族歌舞,展示了当地祭祀蜂王、农耕劳作的场面,还创作了歌舞剧来演绎关坝遇到的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比如村民保护了黑熊,却遭遇黑熊偷吃蜂蜜、破坏蜂箱的矛盾。 此外,蜂王节还设置了特色小吃区、文创体验区以传播关坝文化。这些丰富的巧思构想充分结合关坝的实际情况,既弘扬了传统的民俗文化,又讲出了关坝独特的文化故事,增强了关坝的文化氛围。 关坝所在的木皮藏族乡乃至平武县都共享着蜂王节和白马族的文化传统,举办大型的民俗活动有助于重塑木皮藏族乡的文化认同,有助于关坝同相邻村落“通力合作、协同发展”,通过文化链接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一个村落共同体。
(二)关坝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和反思
一是把家乡建设成活的博物馆。 关于乡村文化重建的形式和方法,用山水负责人F 的话说,就是“把家乡建设成活的博物馆”,让文化传统真正融入到日常的生产和娱乐生活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恢复和保留有形文物。 关坝村通过保留土司遗迹,重现传统的白熊、养蜂歌舞,保护传说中的神树等,让传统的文化重新“活”起来,让人们能够触摸到、感受到历史。 第二,挖掘和传承历史知识。 在现代化与城市化浪潮下,关坝村的老年人大都淡忘了历史传统,年轻人则基本不了解自己族群的传统文化。 为了复兴传统文化,关坝村专门邀请了研究白马族历史文化的老师到村上讲课,让村民了解白熊部落的演化和村落发展的历史,激活“文化之根”。 第三,再现文化,将文化有形化。 关坝制作了一批文创产品来再现自己的文化,比如在蜂王会上推出的传统小吃、纪念品,规划在自然教育项目中设计通关文牒、护牌等文创产品,再现历史上的蜀地通关场景。 在村落人居环境的营造上,关坝突出文化符号,比如用石头拼出大熊猫的形状、用废弃轮胎画鱼塘青蛙等,将文化实体化、有形化。
二是乡村文化建设应遵循适用性、差异性和独特性。 由于受教育水平不足,关坝村民并无自主意识去了解和传承白马文化传统,缺乏文化认同。 对当下的关坝来说,文化更多是一种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 因此,不论是为了形成集体认同,还是把传统文化的要素作为发展旅游业的生产资源,乡村文化的复兴都要围绕现实生活,遵循适用性。 尤其是在如今炙手可热的乡村旅游业中,若是为了迎合经济发展需求而刻意包装、表演文化元素,那这些文化只能沦为空洞的文化商品,难以内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不能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意义和动力。 此外,乡村文化建设要保留差异性和独特性,不能变成千篇一律的、同质化的样板村。 这意味着乡村要思考到底是建设一种迎合外来者的文化,还是根植于自身主体性的、能动的文化。 在这一点上,关坝的返乡青年们明确地认识到,关坝有自己的独特性和珍贵性,不论是养蜂还是发展自然教育,都要坚持自己的特色,不过分迎合市场。
三、结语
“青年与乡村”是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探讨的重要议题。 青年和乡村振兴高度契合,参与乡村振兴是青年作为“强国一代”的应有责任和历史使命。从这一点看,关坝的返乡青年都是“自为”的主体,与外部世界有着能动和积极的主体关系。 他们明确自己家乡的历史和在社会中的位置,明确关坝与社会、国家间的关系,了解关坝面临的处境,并且积极地为关坝争取发展权。 在政府和山水机构等多方力量的协同作用下,关坝村完成了从“靠山吃山”的传统渔猎生计到“生态农业、生态产业”的绿色生计转型,并经由村中青年的回归和集体互惠的共同体营造,实现了传统白马文化的复兴和村庄整体文化生态的重建。
返乡青年这种“自为”的实践,带来的不只是关坝村经济的发展,更在于更广泛、更深刻的村落文化和生态的双重修复。 经由对生态的有意识的保护而发起生计的转型,对现实问题的能动回应和有意识的交往,青年和村民产生了主体间的“互构”——相互激发、相互促进、相互赋权,进而达成关坝村的双重重建——自然生态的回归、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新的共同体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