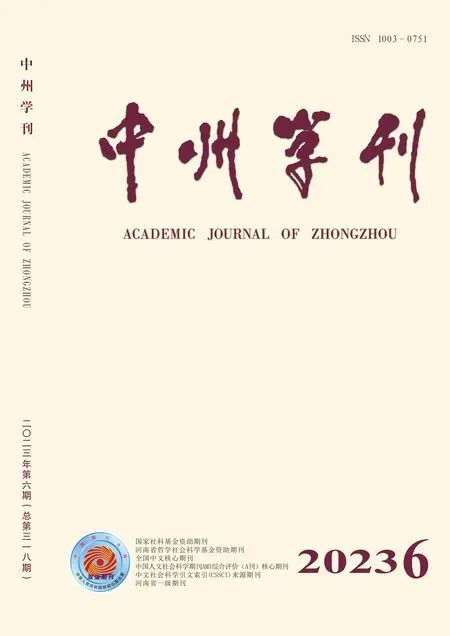“文明境界”:吴趼人《新石头记》的中国叙事与时代价值
晋海学
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国家对清廷的胁迫力度日益增强,知识者们逐渐由此生发出国家即将不保的危机意识。基于对时势的这一认知,他们一方面呼吁人人有救亡之责;另一方面纷纷献计献策,以供清廷参考。考察这一时期知识者们的“救世”之策,我们不难发现,其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呈现出鲜明的未来意识。近代理想小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小说家们与其时的知识者一样,不仅对如何拯救危机这一现实问题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而且以融国家愿景与现实关怀于一身的策略,表现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独特思考。
吴趼人在《新石头记》中对“文明境界”的描绘与憧憬即是小说家们优秀的思考成果之一。“文明境界”思考的核心是文化在将来中国的位置问题,所以,与理想小说中的“立宪”叙事和“革命”叙事相比较,它似乎显得不那么即物;与理想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和“科技”叙事相比较,则又似乎表现得不怎么急切。但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对于中国而言,文化是比政治更为根本的存在,所以对文化之于未来中国的看重,本身就呈现出小说家即物而深邃的思考,再加上小说家对中国元素和中国符号的大量使用,更使得《新石头记》这篇理想小说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基于此,考索《新石头记》中“文明境界”的中国叙事,既有益于对其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也有益于对其时代价值的重新估量。
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明境界”
“文明境界”是吴趼人以儒家大同思想为原型所做出的近代憧憬。作为儒家关于理想社会的典型表述,“大同”一方面寄托了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另一方面则为统治者所致力的社会变革提供了观念力量。近代以后,“大同”理想作为众多“救世”良策中的一种,亦不断地被知识者们所想起,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倡言要破除“九界”,并期待自由制度的出现,“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1]。与康有为关于“大同”思想的政治论述不同,吴趼人则以别开生面的艺术想象来演绎“大同”,不仅为将来中国设计了一个令人神往的理想社会,而且为这个被叫作“文明境界”的理想社会,注入了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
首先,“文明境界”是一个“为公”的社会。这里的人们都有一颗公心,他们并不在意自己的财富如何,反倒常常将公共事务作为其首要的伦理责任。化学博士华必振为一方百姓“制造天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文明境界”创建初期,人们的生活并不富裕,有一年棉花歉收,冬天又“异常寒冷”,为了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华必振散尽“他的一份绝大家财”,研究出了一个令人想象不到的驱寒方法:“使人驾起数十百个气球,分向空中,施放硝磺之类,驱除寒气;又用数十百座大炉蒸出暖气,散布四方,居然酝酿得同春深天气一般,草木也萌动起来。一时穷民大喜。虽然不能遍及境内,然而纵横三百里之内竟然不知道这一年有冬天。”[2]447医学家东方德钻研医道是另一种“为公”的例子。他幼年学习中医,成年之后又攻读西医,可谓融贯中西,但更可贵的是他对于公共事务的热衷之心,正如他自己所说:“能治病的不算是医生,只能算是病人的仆役。是真医生,务要医得通国人都没有病,才算是医国好手。”[2]452将“医得通国人都没有病”作为“真医生”的责任伦理,难道不是“为公”思想的另一种境界?除了华必振与东方德之外,还有许许多多无名的人们,他们也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地实践着“为公”的思想。譬如,这里讲究科学卫生,可以为每家每户提供统一的“食管”供应;这里有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可以为居民提供随时都能乘坐的飞车服务;这里甚至还在全境推广“地火”的使用,以替代传统的煤炭等燃料。如果没有自觉的“为公”意识,上述每一个项目的科学改良何以能进化得如此充分?每一个项目又何以会被推广得如此普及?正所谓“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3]。上有华必振、东方德等人的典型事迹,下有众人在不同岗位上的无私奉献,“文明境地”正是凭借着他们的身体力行而被营造成了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之地。
其次,“文明境界”是一个“道德完善”的社会。从外部视角看,“文明境界”与“孔道”的字体分别被镶刻在入门口牌坊的正面和背面,表达了这里的人们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和信仰。全境的每一个部分都用儒家思想中的核心词汇命名,如用“礼、乐、文、章”四个字代表中央,用“仁、义、礼、智”四个字代表东方,用“刚、强、勇、毅”四个字代表西方,用“友、慈、恭、信”四个字代表南方,用“忠、孝、廉、节”四个字代表北方,尽显对儒家精义的领会与凝练。从内部视角看,这里的人们从小就熟读儒家的经典学说,“那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人烂熟于胸中”[2]489,以至于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有了以“德”为核心的文明的底子。关于个体的修身求仁,孔子曾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4]80这里的人们正是化用孔子所讲的君子求仁功夫,将个体的德性建设当成文明主体生成的基本。可以说,正是因为对个体修身的严格要求,“文明境界”里的人们才会最终成长为具有“性质文明”的人,而经由这些“性质文明”的人所组成的社会,才会是一个真正具备文明内涵的社会,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生活上的不富足而去打别人的主意,更不会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去做不道德的事情。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老少年才说“文明境界”已经做好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取文明字典,把‘盗贼’、‘奸宄’、‘偷窃’等字删去;一件是从京中刑部衙门起,及各区的刑政官、警察官,一齐删除了,衙门都改了仓库。”[2]472《礼记·礼运第九》在述及理想社会的样态时曾云:“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由此来看,不管是“取文明字典”,还是将“衙门都改了仓库”,都是大同思想的某种具体实践,至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等文明之象,更是大同思想在“文明境界”的一种达成或实现。
最后,“文明境界”是一个“上下和谐”的社会。儒家主张社会要有等级秩序,如孔子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时也强调这个有着等级的社会应是一个“上下和谐”的社会,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4]67。然而,考虑到近代统治者在处理诸种事务时进退失据的样态,专制制度还能不能在“文明境界”中得到合法的续延?对此,老少年就专制制度与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究竟孰优孰劣这一问题进行了正面的回答。他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和回答,不能只从知识或语词的层面加以考量,还应该将其放在现实社会之中,从具体政治效果的层面给予客观分析。老少年认为一个社会在还没有达到文明时,采用君主立宪制的效果就会比较好,但是,当人们都普遍具备了良好的德性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采用专制制度或许更为适宜。正所谓“野蛮专制,有百害没有一利;文明专制,有百利没有一害”[2]474。小说更为此安排了一个细节以作进一步的证明。老少年同贾宝玉在南极收获的冰貂、珊瑚,以及绿色山石等奇珍异宝,被有关部门呈献给皇帝,我们可以从皇帝的回应之中看出“文明专制”的优越之处:
本日览某某等启,并进呈冰貂裘一袭,浮珊瑚十枝,寒翠石十座。据称得自南极,冰貂虽于冰地御之亦温,瑚石溽暑置之而凉。朕验之瑚石良然。惟是卿等冒万险而获此,除分置博物、动物两院外,不自置用,而以归之于朕,朕受之亦复何安?使卿等获亿兆京垓之貂,缀为裘以衣被天下,朕亦何妨受此!今天下皆无而使朕独有,岂吾民皆不畏寒而朕独畏寒乎?朕倘受而衣之,更何颜以对诸臣民?瑚石亦然。然竟拒而不纳,未免有负卿等相爱之盛心,爰命玉人截取翠石一角,留朕案头,以为卿等大功之纪念,余均交来使赍还。卿等其仍以分置博物院中,俾与我国民同增闻见。朕亦与有荣幸焉。[2]536
贾宝玉读到了这则被标为“记君德”的新闻之后,不由自主地表达了对“文明专制”的体认:“有这样的皇帝,怪不得他们情愿专制了。而且那上谕的措辞,何等谦抑!除了一个朕字,几乎看不出是上谕来,足见这里是君民一德的盛治了。”[2]536需要注意的是,“文明专制”并非现实社会专制制度的翻版,它的形成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全境的每一位百姓都需“饱受德育”;二是各官僚阶层需要按照“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2]473的伦理行政。这两点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并不妨碍“文明专制”作为一种理想,成为人们为之奋斗和追求的目标。
综上所述,吴趼人用形象的文学语言,将自己心中的“大同”理想惟妙惟肖地叙述出来。这是一个人人“为公”的社会,每个人都能将公共事务当成首要的事情来做;这是一个人人都“饱受了德育”的社会,每个人从小都接受儒家的修身教育,以至于将“不明公理,不修私德”视为“人生第一耻辱的事”[2]543;这是一个等级有序、上下和睦的社会,上至皇帝,下到百姓,每个人都以德为先,他们齐心协力地构建一种叫作“文明专制”的政治制度。“文明境界”的出现并非吴趼人对儒家文化单纯复制的结果,而是小说家融国家危机现实的考量与儒家文化的观察于一体之后所进行的具有创造性思考的结果。它包含着儒家文化的因子,但更重要的是,它从儒家文化中提炼出非常难得的文化自信力,进而形成在当时并不多见的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的小说叙事。
二、作为“真文明国”的“文明境界”
吴趼人在《新石头记》中所描绘的“文明境界”,是一个以“大同”思想为基础的理想社会。它虽然以“文明”来命名,但其中的“文明”之义却与近代社会上流行的西方文明观不是一回事。“文明”一词在周代的文献中就已经出现,如《周易·乾》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5]《周易·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南怀瑾将其释义为“文章与光明两个意思的联合”[6]。汉代之后,基本延续了这一词义,如《史记》曰:“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7]张守节《史记正义》释义云:“乐为德华,故云文明。”[7]但是到了近代,“文明”的含义发生了现代转折,知识者们一般将它与“野蛮”一词对应起来,专门指称人类脱离了“野蛮”之后的发展阶段。近代知识者对于“文明”的重新赋义,其实是一种现代命名的实践,它并非纯粹的知识行为,而是包含了人们对国家未来某种期许的实际内容。当然,也并非所有的知识者都对此表示认同。譬如,有知识者不满于西方国家以文明的借口来掩饰其侵略行为的做法,指出:“国家文明野蛮之公例,乃若点线之相引,而不能于名词上号定之也。文明国与文明国交涉,则彼文明我文明,两文明相交,而文明之祥云出现。野蛮国与文明国交涉,则我野蛮,文明国更野蛮,两野蛮相交,而野蛮之毒雾沛塞。”[8]作为近代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吴趼人以“恢复我固有之道德”的勇气和信心,赋予儒家文化在未来中国的构建设想中当仁不让的核心地位,既是对西方文明观的反驳,也是对它在某种程度上的超越。
西方的文明观不能在将来中国社会的构成中居于主体位置,这在《新石头记》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由于吴趼人不是在语词的意义上去理解“文明”这一概念,而是在语词的意义之外,于生活体验中给予观照和体悟的,所以,他常常能洞察到“文明”这一概念在现实使用中被人们风化的情况:“有两个人在路上行走,一个是赳赳武夫,一个是生痨病的。那赳赳武夫对这生痨病的百般威吓,甚至拳脚交下把他打个半死。你说这赳赳武夫有理么?是文明人的举动么?只怕刑政衙门还要捉他去问罪呢。然而他却自己说是‘我这样办法文明得很呢’。你服不服?此刻动不动讲文明的国,那一国不如此?看着人家的国度弱点,便任意欺凌,甚至割人土地,侵人政权,还说是保护他呢。说起来,真正令人怒也不是,笑也不是。照这样说起来,强盗是人类中最文明的了。”[2]490深而言之,他甚至能洞见那些作为“文明”这一概念的“承载者”,在实际道德行为上的“野蛮”内容,“那报纸上载的公堂案,中国人酒醉闹事的案子,是绝无仅有的。倒是捕房案,常有酒醉闹事的,并且是第一等文明国人”[2]519。可以看到,西方的文明观在具体实践中出现许多问题,而最让人诟病的就是西方国家对其自身不文明行为的讳饰。试想,这样缺乏反省意识的思想观念,如何能成为以“救世”为指归的“文明境界”的核心构架?吴趼人认为,相较西方的文明观,先秦儒家文化才是构建“文明境界”更适合的思想资源。他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量。
第一,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文明开化的程度在周代就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准,即使到了近代,民众依然“知规矩”“守礼法”,保持着较为自觉的伦理意识。老少年在向贾宝玉讲述何以“中国人酒醉闹事的案子,是绝无仅有的”原因时,清晰地指出了这一点:
中国开化得极早,从三皇五帝时,已经开了文化,到了文、武时,礼、乐已经大备。独可惜他守成不化,所以进化极迟。近今自称文明国的,却是开化的极迟,而又进化的极快。中国开化早,所以中国人从未曾出胎的先天时,先就有了知规矩,守礼法的神经。进化虽迟,他本来自有的性质是不消灭的,所以醉后不乱。内中或者有一两个乱的,然而同醉的人,总有不乱的去扶持他,所以就不至于乱了。[2]519
孔子《论语》在很多地方都讲到“仁”,并达到对于“仁”的深刻理解。譬如,孔子《论语·里仁》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4]80钱穆论之曰:“去仁之说,学者尤当深玩。”[4]81孔子强调“仁”之于人们的重要性,尤其指出“去仁”之难,不仅可见先秦民众对于“仁”所理解的程度,而且可见他们将其与个体修身关联的紧密程度。由此来看,老少年所谓“中国开化得极早”这一论断并非虚言,而正因为他们此时既已形成了自觉的伦理意识,才使得中国民众遵守道德的风尚有了远古的传统,一如老少年所说,“中国人从未曾出胎的先天时,先就有了知规矩,守礼法的神经”。正是从这层意义上,吴趼人看到了中国民众在道德实践中“本来自有的性质”。既然中国民众道德意识的形成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那么,以这些民众为社会基础的“文明境界”,就不能不考虑儒家文化的参与程度,所以,他提出“恢复我固有之道德”的文化主张,目的就是要借助“恢复”这一行为,将儒家思想纳入这一宏大理想的建构行动中来。
第二,在战争频仍的近代,儒家文化中的“王道”思想更容易浇开知识者们的胸中块垒。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在与西方国家的交战中屡战屡败,可以说,中国在近代所面临的被诸国殖民瓜分的危机局面,都是因战争上的失败所致。所以,对于志在“救世”的小说家们而言,如何在其所设计的理想社会中处理战争这一要素,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关键问题。
在《新石头记》中,“文明境界”海陆空三军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几乎到了可以在短时间内“吞并各国”的地步,但是东方文明却认为“真文明国”所秉持的宗旨应该是“王道”,而不是以殖民为要义的“霸道”。正是在东方文明的指导下,“文明境界”的军事家们不仅不以炫耀武器装备的先进为荣,反而处处融人道于武器的改良之中,甚至强调即使在战争的过程中也要施以“仁术”:“虽然两国失和便是仇敌,然而总是人类对人类。若只管贪功取胜,恣意杀戮,在临阵时,自然便忘了同类相残的忍心暴动。试问一作局外人想,眼见得因一时之气,伤残同类,岂不是不仁之甚么?”[2]558儒家文化向来都以德为先,尤其在政事方面更是如此,如《论语·为政》所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4]21,《孟子·公孙丑下》所云“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9]65,均将“德”放在众事之首的位置。东方文明对于“真文明国”的执着,其实就是对孟子所说“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一语的坚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靠自己的德行修养,而不是舰船枪炮去影响世界。当然,“文明境界”能否凭此就能做到孟子所说的“仁覆天下”[9]128,我们不得而知,但其中无论是对于“蒙汗药水”“神奇电炮”等战具基于人道的改良,还是对于“不动刀兵”这一军事策略的信守,乃至对于“等他们看了自愧,跟着我们学那真文明”这一处理国家之间关系原则的崇信,均能让人明显地感觉到儒家文化中“王道”思想给予他们的影响。
总之,在国家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势面前,吴趼人洞见了“文明”一词在近代被日益风化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发现使他放弃了从西方文化资源中寻求借鉴的可能。考虑到民众至今尚能保持的道德意识,以及儒家文化中对于“王道”思想的推崇,吴趼人批判性地将儒家文化当成理想社会的构建核心。对此,他曾这样解释道:“各人之眼光不同,即各人之见地不同;各人之见地不同,即各人所期望于所见者不同;各人期望于所见者不同,即各人之思所以达其期望之法不同。”[10]事实上,通过全体民众的“道德普及”以实现国家“文明繁荣”的考量,以及用以“王道”为内涵的“真文明”取代以“霸道”为中心的“假文明”的思虑,都有着较为切实的针对性。从这一点看,吴趼人在“文明境界”的构建中引入儒家文化的做法,是自己基于时势对“文明”做出的崭新理解,其中包含了他基于文化自信所展示出来的对于西方文明观的某种超越性思考。
三、“文明境界”叙事的时代价值
“文明境界”从未来的时间层面,比较理想地预测了国家将来的文明状况。有学者认为,“这也许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只有希望保存国粹的真正爱国者才会有的幻想”[11]。事实上,吴趼人并非不知道西方文化的优点所在,也并非没有看到儒家文化的不足之处,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所思考的出发点和“国粹”的保存与否关系不大,反倒是和国家将因何策略以及用怎样的方法被拯救这一现实问题紧密关联。正是因为“文明境界”所潜含的现实关怀,它才经常被人们提起,经常被人们看作吴趼人为拯救国家危机而献上的“救世”之策。
进一步来说,吴趼人在洞见儒家文化之于未来国家建构的有效性之后,并不拘泥于这种有效性的即时实现,而是将其实现的可能安置在将来。需要辨析的是,他在对“文明境界”的构想中,表现出一种与儒家理想的尊古叙述不尽相同的未来意识。这种未来意识与“幻想”并不同义,因为它是基于强烈的现实关怀而来,所凸显的是因期冀理想实现与现状改变而来的希望精神,而不是为执着于某种观念教条而来的主观“幻想”。
首先,“文明境界”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文化主体的构建机制,这也是它较为突出的现实价值。吴趼人认为“救世”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重建的问题,而任何主体的构建最终涉及的都是主体问题,所以,中国的重建归根结底也是一个主体问题。这正是他所说的“今日之社会,诚岌岌可危,固非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维持之”[10]的深层含义。由于中国的重建必须依靠自己,而儒家文化又是其核心文化的标志,所以,吴趼人强调“固有之道德”之于中国重建的有效性,并坚持在“文明境界”之中赋予儒家文化重要的使命,甚至让这里的人们从小都按照儒家的文化规范进行修身养性。
相比之下,小说中西方文化的价值则在“媒介的意义”上被给予了认可。所谓的“媒介的意义”,不是指对西方文化的照搬,而是对那些可促使文化主体进行自我否定的西方文化的包容,意在达致加速自我实施否定的催化目的。西方文化“之所以在这里被给予充分的展示,并不仅仅是为了片面地凸显西学的价值,而是在尊重西学价值的同时,有意识地展示了它在怎样的层面上促进了中学成长这一路径。这种对于不是‘替代’,而是‘促进’的分寸把握,是在媒介性质的意义上理解西学价值的典范,它不仅表明了有益于未来中国建设的西学内容是什么,而且展示了它们被儒家文化所吸收、所转化的可能性”[12]110。
“文明境界”这一新文化主体向世人展示了它的新特征,到处可见的中国元素,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中国风格,能使人们一下子就能辨识出这是中国的未来,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未来。同时,由于“文明境界”所展示的新特征融合了新要素,所以又表现出与传统儒家文化不一样的内容。例如,同样是专制,“文明专制”就与传统专制有很多不同之处;同样是中医,融合了科学知识之后的中医也与传统的中医有了明显的区别。总而言之,由“文明境界”所代表的新的文化主体,既有过去“中国”的因子,又是经历涤荡之后的“新”的“中国”。吴趼人专注于文化主体建构的这一做法,使得他的“救世”之策显得与众不同,这或许正是他和他的“文明境界”对于现实特有的体悟和关怀。
其次,“文明境界”向人们展现了一种关于未来的时间意识。儒家文化在对理想社会进行描绘时,一般将它与过去的远古时代联系在一起。如孔子在叙述“大同”社会的时候,谈到的就是已经过去的“三代”,“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3]。可是,吴趼人却将“文明境界”得以实现的时间维度放在未来,他要从“未来”而不是从“过去”来思考民族或者国家的改造问题。就前者而言,儒家文化中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有严格的区分,这种区分不仅意味着两者之间在时间上有本质上的差别,而且包含着两者之间彼此无法相交的隔离内涵,所以,对理想社会的赞美,或许并不意味着它就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只不过是代表了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批判罢了。就后者来说,情况则有了很大的不同。吴趼人将“文明境界”放置在未来,意在表明这一理想社会是可以达致的,“现在”与“未来”之间通过一种理性的桥梁被贯穿在一起,以至于依靠两者之间的沟通,国家危机不仅有了可以被拯救的可能,而且使这种拯救有了明确的未来方向。
雷-戈夫曾说:“上帝时间给商人时间让步。这一时期破晓而出的是一种有关未来的观念,它将在人类的塑造潜能面前表明自己是开放的。这是一种自己蕴涵风险的未来,因为只有那些甘愿为赢得机会而不断将其所有拿来冒风险的人才能追求未来取向。”[13]或许,吴趼人还没有体悟到未来意识中的“风险”性质,而只是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对“未来愿景”的呈现上面,其表现就是老少年在给贾宝玉的讲解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文化自信力,很少能见到这一愿景在实现过程中遇到阻碍或者挫折。但即使如此,“文明境界”“追求未来取向”的现代性特点并没有改变,而这正是传统时间观念里所不可能具备的内容。
最后,“文明境界”向人们传递了一种追求理想的希望精神。“文明境界”是吴趼人关于理想社会的总体展望,其中包括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感动的追求梦想的故事。譬如,华必振为了让当地的百姓免于在寒冷的冬天受冻,竟然想出了“设法使天气不寒”的“再造天”办法;东方德为了寻求“氯气炮”的替代品,更研发出了一种“又是利害,又是慈善”的“蒙汗药水”;东方文明为了将“真文明国”推广世界,始终强调“王道”之于“文明境界”的重要性。如果说“四时天气”的制造、“蒙汗药水”的发明,以及“王道”政治的推广就是人们的理想或目标的话,那么构成华必振等人去实现这些目标的内在动力则是“希望”。
或许有人会感到疑问,这些理想虽然足够吸引人,但是它们至今也未能实现,而作为理想社会形态的“文明境界”,更表现出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倾向,那么,由此所展现出来的“希望”的精神值得称赞吗?的确,吴趼人并没有对“文明境界”的实现表示过任何的担忧和怀疑,而是对人们只要通过努力就能顺利地达到目标的想法表示出了确然的相信,这为“文明境界”最终的实现增添了浓郁的乐观主义色彩。但是,正如恩斯特·布洛赫所说,“希望哲学的宗旨就是要预先推定一个更美好生活的梦”,“希望”精神之绝佳体现,即是人们在这一“尚未存在的事物”[14]75方向上所进行的乐观而积极的实践,因此,“乐观主义前景”不仅不会减弱“希望”精神的力量,反而会更有益于这一力量的增强。“如果考虑到目标内容的乐观主义前景,希望和震惊同样拥有强有力的优势,最佳的目标内容同样拥有持续不断的开放性,即拥有迄今从未屈服的历史过程本身。一切白天还都不是夜间,一切夜间还都孕育一个早晨。人类所想望的‘善’难免遭到失败,但这种失败本身包含着自身未来的可能的胜利。”[14]370总而言之,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文明境界”以近乎完美的姿态被小说家放置在了未来,进而成为人们替代危机现实的“乐观主义前景”,而由这种“乐观主义前景”所滋生的“希望”精神,确实能以一种“强有力的优势”,给生存于现实中的人们带来积极的意义。
左鹏军先生在评价“恢复我固有之道德”思想的价值时,认为它是吴趼人努力探求济世之术、设计救国方案的积极用世思想的一种体现方式[15],“文明境界”则是这一“积极用世思想”直接的文学体现。由于“文明境界”既提供了一种可以替代现实社会的远景目标,又提供了未来文化主体如何生成的建构方法,所以,它所呈现出来的未来意识与即物精神,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就前者而言,它所呈现的是包蕴了高度文化自信力的未来意识;就后者而言,它所表达的则是在“既承认西学的昌达,却又拒绝‘崇拜外人’的张力思维”[16]意义上的即物精神。由此,“文明境界”被赋予了虽然尚未形成,但是却可以企及的“希望”性格,由此,它不仅激发了人们心中想要改变世界的潜能,而且为人们亟须变革世界的实践提供了鼓舞的力量。
结 语
在中国近代众多的理想小说之中,吴趼人的《新石头记》虽然在题材上有“理想”之名,但其在叙事上却有明显的特别之处。这种“特别”之处的主要表现,就是对中国元素的大量使用,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中国叙事。在宏观层面,小说触及了“孔道”“大同思想”“文明专制”“文明国”等文化符号;在微观层面,小说叙述了“中医”“文明律例”“蒙汗药水”等文化元素。王尔敏认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思想观念“有一持续不变的新方向,也就是渐趋于西化”[17]。如果以此作为近代中国思想发展背景的话,吴趼人对于时势的理解和回应就显得更加独特。当然,吴趼人关于“文明境界”的中国叙事并不来源于其主观世界,而是基于他对近代时势考量之后的一种理性判断,所以,作为对一种理想社会的构想,这样的叙述既不是虚幻的,也不是空洞的。
尤为关键的是,小说家并不满足于只对理想社会做静态的呈现,而是在其叙述之中融入较多的文化主体构建的内容。也正是因为这后一层因素的存在,“文明境界”的中国叙事才有了更加充实的意义。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正是缘于对中国主体位置的维护,吴趼人才在构建中国想象时,坚决强调儒家文化之‘固有’于未来中国的重要性。”[12]109这是“文明境界”中国叙事的特点,其给予时代的现实价值也因此而凸显出来。由于吴趼人将“文明境界”作为方法,目的就是为“新”的中国建构提供思考,这就意味着,相较其他理想小说的未来叙事,“文明境界”之中的中国叙事为人们提出达致理想社会的办法更加清晰,也更加有效。进而,这一清晰、有效的方法,不仅将人们对于理想社会的想象进行了具体化的处理,而且为人们对于现实的改造提供了确然的路径,让希望精神在人们确然可行的实践中被激发和点燃出来。显然,这既是一种集现实与理想于一体的价值展现,也是一种融方法与精神于一身的意义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