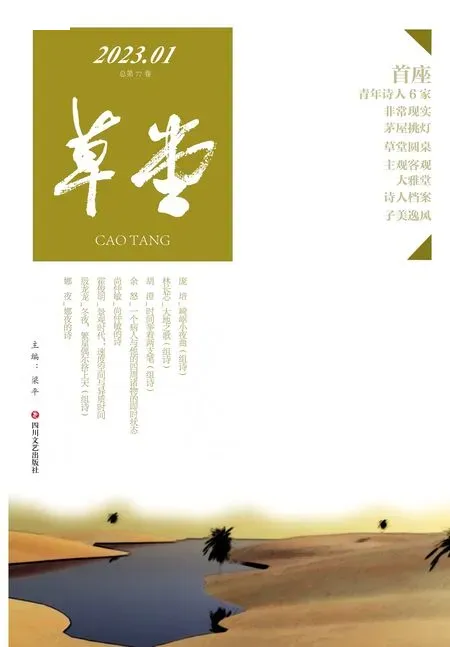景观时代:速度空间与异质时间
◎ 霍俊明
无所不在就是无所在,
谁能证明
一个地方多于另一个地方?
——谢默斯·希尼
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晰而深刻地意识到了随着现代性时间、生产媒介以及交通方式对空间和人的心理意识的飞速渗透,当下的诗歌创作中呈现出了越来越多的速度景观与异质时间,日益复杂甚至分裂的现代性诗歌经验也在景观时代不断地凸显出来。
1
遥想古代,空间距离曾经成为巨大的阻碍,它一再产生的是忧戚满怀的送别诗、思乡诗以及闺怨诗和行旅诗。一旦这一长久的巨大阻碍因为现代交通工具的诞生而被消除,诗人的精神视野和行走空间一下子就被打开了。
1921 年4 月郭沫若写下《沪杭车中》一诗,诗人当时看到的景象是:“紫色的煤烟/ 散成了一朵朵的浮云 / 向空中消去。/ 哦!这清冷的晚风! / 火狱中的上海哟! / 我又弃你而去了。”1923 年10 月20 日下午,徐志摩经硖石探望正在西湖烟霞洞清修寺“养病”的胡适以及曹诚英:“我们第一天游湖,逛了湖心亭——湖心亭看晚霞看湖光是湖上少人注意的一个精品——看初华的芦荻,楼外楼吃蟹,曹女士贪看柳梢头的月,我们把桌子移到窗口,这才是持螯看月了!”(徐志摩《西湖记》)随后,徐志摩邀请胡适、曹诚英等人到自己老家海宁观看钱塘江大潮。10月30 日,徐志摩在由硖石开往杭州的哐当作响的火车上写成一首诗《沪杭车中》(又名《沪杭道中》):
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
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
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
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换作是今天的语境,郭沫若与徐志摩与“速度景观”有关的诗句简直是不折不扣的陈词滥调,但是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显然已经具备了“现代性”和“时代感”。1948 年夏天,风雨飘摇的严峻时刻,又一个诗人在沪杭铁路上写下无比沉痛的诗句:“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 / 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辛笛《风景》)火车天然地成为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界限,而非迅速消解二者之间的差异,反而加深了二者的矛盾。你是否听到了类似于瓷器碎裂的声音?与此同时,几乎是一夜之间修建起来的铁路使得一个个地点被迅速地搬动,旧的时间观念也随之消失了。“滇越铁路运进云南的不仅仅是两条铁轨,也不仅仅是各种洋货,还有医院、车站、咖啡馆以及时间,人们开始看钟表,而不再根据太阳的起落判断时辰”(于坚《暗盒笔记Ⅱ》)。当火车背对着故乡或熟悉的地方远去,这对那些远行者意味着什么呢?年幼的T.S.艾略特对火车怀着深深的恐惧:“我们乘火车旅游,从圣路易斯到东部……我总是害怕火车眼睁睁从我们面前开走,害怕忙着托运行李的爸爸赶不上火车。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灾难让我担忧费神”(约翰·沃森《T.S.艾略特传》)。火车和旷野形成了时代特有的风景,这是张力、拉抻导致的最后撕裂。对于那些生活于故乡而又突然被连根拔起的一代人而言,向前还是向后真正地成了最为现实的生存问题和精神境遇。人们被卷入不可预知的命运旋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个诗人在茫茫戈壁的蚕豆般大小的车站所看到的却是整个星空。
我成为某个人,某间
点着油灯的陋室
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
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
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
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
——西川《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1988 年7 月25 日深夜,海子乘火车经过戈壁中的德令哈,这位青年诗人写下的是:“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确实,汽车、火车、铁轨、车站以及飞机、舷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代表了最为令人心动和憧憬的时代景观。
在徐志摩写完《沪杭车中》九十年之后——2013 年,张执浩在高速路上写下一首《平原夜色》:“平原上有四条路:动车,高速,国道和省道 / 我们从动车上下来,换车在高速路上疾驶 / 平原上有三盏灯:太阳,月亮和日光灯 / 我们从阳光里来到了月光下/ 日光灯在更远的地方照看它的主人 / 平原辽阔,从看见到看清,为了定焦 / 我们不得不一再放慢速度。”这是快速移动的扁平化景观时代的一个疑问重重的寓言,诗人不断调整与车窗外的高速路和事物之间的角度。显然,在高速的时代很多事物都变得模糊甚至发生变形。诗人的凝视与快速的碎片化景观之间的向度刚好是相反的。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他目睹的是时代最恍惚又最真切的日常景观,是往往最容易被抛弃、被忽视的震颤不已的精神现实。这时最需要的就是诗人的取景框和精神能见度。同样是在2013年,孙文波完成了1600 行的长诗《长途汽车上的笔记——感怀、咏物、山水诗之杂合体》。从“六十年代的自行车”到“长途汽车上的笔记”,不仅是孙文波个人的精神成长记录,更是中国当代诗人对工业化、城市化和景观化时代现实的关注,而整体呈现出“无根”“飘荡”的精神状态以及对现代性景观的批判:“譬如面对一座城市、一条街道,暴雨来临,/ 这不是浪漫。情绪完全与下水系统有关,/尤其行驶的汽车在立交桥下的低洼处被淹熄火。”
随着现代交通网络系统的飞速发展,飞机、高铁、游轮、汽车已不再新鲜。在诗人与扁平化的速度景观对视和摩擦中一种崭新的异质化时间观已经诞生并迅速蔓延开来。西方的教堂和中国古代建筑的钟楼以及现代社会的汽车站、火车站和航站楼的钟表都代表了不同时代境遇下的时间法则,这也决定了诗人和哲学家的视点、角度和抒写位置。而随着现代性时间的到来,钟表显然代表了另一个时代的时间法则和生存观念,而这正需要诗人作为观察者和校对者来进行勘问。“路易斯·芒福德就是这些伟大观察者中的一个。他不是那种为了看时间才看钟表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大家关心的钟表本身的分分秒秒不感兴趣,而是他对钟表怎么表现‘分分秒秒’这个概念更感兴趣。他思考钟表的哲学意义和隐喻象征。”(尼尔·波兹曼《媒介即隐喻》)而这正是诗人的工作,他们最后通过观察钟表的内部秘密得出令人震悚的结论,即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生活中便没有了永恒。以往诗人的时间观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语言体系甚至生活方式由此被拦腰截断。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都有登高望远、自比心志的传统,而泛着幽光的新时代的大楼和玻璃幕墙不再制造属于这个新时代的登临者和抒情诗人。在现代性日常生活中登上高楼的人却往往怀有一颗灰暗之心。而当这一情景的主体转换成了诗人,其情势更为严酷。诗人的凝视状态作为一种传统也在此时此刻宣告结束,快速的眩晕的物象使得诗人的眼神茫然无措而飘忽左右,对应于内心体验来说同样是茫然的碎片。一个具备现代经验的诗人必须在诗歌中做出艰难的选择,因为缓慢的、封闭的、节制的古典化的时间观已经在新的现代性时间神话面前土崩瓦解了。这让我想到海德格尔童年时麦氏教堂镇上那座教堂的巨钟。这不只是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和记忆,而是另一个旧时代的最后钟声,一切即将被终止,这代表了以往的时间已经成为历史废墟的一部分。越是在转捩的迷茫时刻,诗人越想登上一个更高的位置来看看周遭环境以及晦暗不明的时刻。
它伸展到郊区的部分已经发灰 一些钢轨翘起在火车站的附近
人类移动的路线 由郊外向城市中心集中 心脏地带危险地高耸
只有在那儿 后工业的玻璃才对落日的光辉有所反映
于坚的《在钟楼上》是旧时间的回光返照。这些铁链般抖动的散文化长句几乎让人窒息,现代性时间的全息面孔令人战栗。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韩东的代表作《有关大雁塔》更多是文化意义上的诗歌实验样本的话,于坚的《在钟楼上》则更像是当年波德莱尔城市里的战栗。“构成城市中心的‘后工业时代玻璃’塔楼的巨大意象象征着现代化和富裕,但代价也随之而来。那些生活在由当代高楼大厦所制造出来的‘阴暗中’的人,正生活在垃圾中,那些垃圾渗透进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对黄昏的经验是那样的相同和不易觉察,他们判断时间的流逝不是凭借日出和日落,而是靠时钟的机械运动和每天必到的晚报。他们自己的语言也走向机械化。”(Jillian Shulman《于坚:一个置身存在的诗人》)
2
新旧交替的时代对于写作者的考验是巨大的,尤其是在新世界和旧世界的理解上往往会发生巨大的分歧,即使是同一个人也会在旋涡中变得矛盾重重,是肯定和怀疑的兼而有之:“这时,我们往往指责这些人是怀古的‘逃避主义’,患上了浪漫的好古癖,缺乏现实态度;我们把他们的那些努力斥为妄图‘倒转时钟’‘无视历史的力量’。”(以赛亚·伯林《现实感》)在速度化的景观时代以及异质化的时间境遇中诗人更多只是看到了各种道路以及道路两旁设定好的“风景”,而普遍忽视了拆除、填补、夷平和碾压的过程,忽视了这一过程之中那些付出了代价的人和物的命运。快速移动的法则使一切成了快速掠过的碎片,整体性的时代不复存在,以往的一切很快成为被迅速遗忘的过去时。所以,一定程度上诗人是倒退着走的人,是具有“逆”“反”和透视心理的特殊群体。失去重心和眩晕成为每一个人在高速运行时代的集体心理症状。
面对快速的碎片化的时代以及异常模糊的碎片景观,能够对此予以整合和澄清的也许只有诗人和优异的摄影家,正如爱默生所指出的:“任何人都不拥有这片风景。在地平线上有一种财产无人可以拥有,除非此人的眼睛可以使所有这些部分整合成一体,这个人就是诗人。”现如今,“远方”和“诗歌”都已经被高度媚俗化和庸俗化了,诗人的凝视能力、行走能力以及感受事物的能力已经被打断并空前弱化和消解,人们对自我以及世界的理解渠道越来越窄化、新闻化和拟像化了:“现在,我们真的很难与真实的土壤产生肌肤之亲了,水泥路面像大地重植的皮肤,蚯蚓爬不出来了,地气升腾不上来了,这简直有些不可思议”(雷平阳《83 路车上的一个乘客》)。尤其是以快速交通网代表的新世界与乡土世界并置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戏剧化的冲突:“人们日后一定会记得,那是一列颜色发黄、沾满尘土,裹在一片令人窒息的烟雾之中的火车。紧挨着铁路,满载着一串串青香蕉的牛车在尘土飞扬的小道上缓慢地行进”(加西亚·马尔克斯《番石榴飘香》)。当年谢默斯·希尼对乡下那个盖屋顶的人处于长时间的凝视之中,而这正是最深切的记忆方式,是童年的乡村经验的一次次现身。当你试图一次次记忆那些永远逝去而无法挽回的事物,现实记忆和诗歌记忆都将因此而变得艰难异常。诗人面对的注定是已经彻底丧失的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将在下一代人那里被彻底中断、抹平。记忆和遗忘是同时进行的,甚至后者的力量更为强大。如果放眼全世界的速度景观,有人早就发现和感受到了无比疯狂而令人惊心的时刻。
在崭新的景观化时间面前,以往的时间结构和记忆载体也一同消失了,随之是一个个废墟和空壳,灵魂没有任何可供寄居或凭吊之所。这是旧时间以及旧空间一同涣散的时刻!在快读移动中,人、物以及风景成为一个个不确定的模糊斑点,时代也是一个个新鲜的碎片:“远处驶过的公共汽车,在一个 / 少年人的眼中,不过是一个 / 移动的风景,或风景的碎片 / 但眼下是我们存在的全部世界 / 或一个载体,把我们推向 / 遥远而陌生的意义,一切 / 都在迅速地失去,或到来。”(张曙光《公共汽车的风景》)
封闭的、固态化的社会已经结束了,液态的、流动的、迅疾的碎片化时代到来!索尔·贝娄说:“过去的人死在亲人怀里,现在的人死在高速路上。”这正在成为世界性的现实。在近乎世界性的新图景与大变革中,在全球化、城市化的国家与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中,速度(快速、加速)成为每一个人日常生活中感受最深的部分。分裂、速度、同化、异化、分化、进化、一体化等等都需要人们重新理解,这一理解关乎自我、现实、历史以及社会机体:“我清楚,自己对内心的更彻底的追问尚未开始,我对于世界的理解,仍停留在知识层面,即使这层面也浅薄不堪。至于偶见的内心追问,也更多是暂时的情绪,而非深沉的情感。我还生活在生活的表层,连接灵魂深处的根还没有生长,它需要真正的恐惧与爱。”(许知远《一个游荡者的世界》)
时至今日,人类旅行时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祖先的想象。快速移动的技术、工具和空间成为达到移动、输送、疏解的重要手段:“移动中的身体所处的状态也加大了身体与空间的隔断。光是速度本身就让人难以留意那些飞逝而过的景致。配合着速度,驾驶汽车,颇耗费心神,轻踩着油门与踩刹车,眼光还要在前方与后视镜之间来回扫视” (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缓慢的时代和快速的时代,那些在路上的人所目睹的情形和感受已经今非昔比。快速的时代使得旋转木马式的生活方式开始了,看似不断快速前进,实则原地打转而没有任何方向感可言。公路、铁路和航线不只是充当了物理空间的搬运功能,而且还导致了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消解,失控的断崖上运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异乡人。从此,我们在诗歌以及小说中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焦虑者、失眠者以及丧家犬般的无家可归者。这些失魂落魄者少眠而多虑,他们凝视着窗外公路和铁轨上那些现代性的钢铁幽灵以及更为来历不明的异质化新事物: “很多时候,‘下落不明’这一个词条总是固执地出现在我的大脑中。火车行驶过的地方,有无数的尘屑飞扬,它们像田野上破碎的昆虫,在光线中打开翅膀。那些窗口上的脸,是水中,蛇的脸,冰冷而迅速,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就像一只蟋蟀嘴中的草叶,从这一亩地搬向另一亩地,最后被带进黑暗的地缝。但是,我一直热爱着这一批批奔跑迅捷的铁器,在我居住的七楼阳台上,就可以看见它们在城市的边缘跑来跑去。它们的叫声,经常将我从睡眠中提起来,我在漏水,我在不知所云地歌唱,它们的叫声把我提起来,提起来,又放下去,让我继续在移动的房子里,把一些难以固定的异乡人的庭院打扫干净。”(雷平阳《火车》)
3
地域和空间区隔曾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视界带来了巨大影响:“从地方的安全性及稳定性,我们感觉到空间的开阔和自由,及空间的恐惧,反之亦然”(段义孚《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相应的“地域性写作”曾是一个比较显豁的文学传统,作为重要的评价尺度在中国诗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米歇尔·福柯看来,二十世纪是一个空间的时代——如今早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而随着空间转向以及“地方性知识”的逐渐弱化,在世界性的命题面前人们不得不将目光越来越多的投注到“地域”和“空间”之上。尤其2000 年以来的二十多年又恰好是“地域性”或“地方性知识”发生了巨大变动的时段,这对诗人的世界观、诗歌写作观念以及整个诗歌生态都带来了不无深刻的影响。
由诗歌的空间和地域性我们总会直接联系少数民族的诗歌写作图景。值得注意的是,“高速公路”以及迅疾的现代化工具(飞机、高铁、汽车)和碎片分割的现代时间景观使得诗人的即时性体验、观察和停留的时间长度以及体验方式都发生了震惊般的变化。在稳定的心理结构以及封闭的时空观念被打破之后,随之而来的感受则是暧昧的、陌生的、撕裂的。这也导致了被快速过山车弄得失去了重心般的眩晕、恍惚、迷离、动荡、无助、不适以及呕吐。这正是现代性的眩晕时刻。而我们放开视野就会发现,于坚、王家新、欧阳江河、梁平、雷平阳、孙文波、翟永明、潘洗尘、汤养宗、张执浩、胡弦、沈浩波、朵渔、哨兵、江非、邰筐、郑小琼、谢湘南、刘年、王单单、张二棍等同时代诗人都将视线投注在高速路的工具理性和速度景观之中。那高速路上出现的兔子、野猪、刺猬、蜗牛、鸽子都被碾压得粉身碎骨或者仓皇而逃。当然,我们并不能如此而成为一个封闭的乡土社会的守旧者和怀念者,也不能由此只是成为一个新时代景观的批判者和道学家,但是这些互相矛盾的情感和经验几乎同时出现在此时代的诗人身上。
新世纪二十多年来少数民族诗歌写作无论是在精神型构、情绪基调、母题意识,还是在语言方式、修辞策略、抒写特征以及想象空间上,它们的基调始终是对生存、生命、文化、历史、宗教、民族、信仰甚至诗歌自身的敬畏态度和探询的精神姿态,很多诗句都通向了遥远的本源性写作的源头。从诗歌空间来看,现在的少数民族诗人越来越呈现出开放的姿态,本土空间、城市空间和异域空间同时在现代性进程中进入诗人的视野,而从精神向度和思想载力来说,这些诗歌也更具有对话性和容留空间。这无疑使得他们的诗歌在共时的阅读参照中更能打动读者,因为这种基本的情绪,关于诗歌的、语言的和经验的都是人类所共有的。这种本源性质的精神象征和相应的语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向民族、传统和母语致敬和持守的意味。这也是一个个少数民族诗人的“梦想”。而任何一个民族和部落以及个体所面对的诸多问题都是共时性的,打开了面向生存、世界、历史、文化、族群和人类的尽可能宽远的文化空间和诗性愿景。随着加速度的城市化进程对原生态地区和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性时间对传统的地方性时间和农耕时间的挤压,少数民族写作也遇到了不小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是现实层面的也是诗学层面的。
每个人都在有形或无形的公路以及铁轨上行走,这是预定好了的旅程,几乎没有重返的机会。一些诗人只能黑着脸、苦着心,竟日枯坐在日渐荒芜的山顶上看着另一种时代景观的崛起,看着空间和事物的震荡和改变,看着暮色中仍然闪亮的铁轨和日夜喧嚣的车站以及郊区。总会有持守土地伦理和地方性契约精神的诗人出现,随之出现的还有文本世界中的“最后一个形象”:“一个地方特殊的精神……是人们体验到一个地方那些超出物质的和感官上的特殊的东西,并且能够感到对这个地区精神的依恋。如果地方的意义超出了那些可见的东西……深入心灵和情感的领域,那么,文学、艺术就成了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它们是人们表达这种情感意义的方式。”(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总是有人对“地域”投注了过多的热情,甚至会言之凿凿地指认地域之间的巨大差异,甚至在“区域文化”“地方主义”的强势口号之下产生了偏狭化和道德化的趋势。由此,我们看到的是“地域性诗歌”的新一轮的信任危机,这一危机的形成既与诗人对地域的浅层描摹和观光化景观的炫耀有关,又与二十一世纪以来现代性和城市化整体情势下地方性知识所遭遇的挑战有关。关于“地域性”写作可能带来的危险,80 后诗人王单单有着深彻的自省和检视:“我的写作状态也从之前的‘阵地’式更换为‘游击’式写作,云南背景下的地域性特征不自觉地有所弱化,诗意的发生也从对自然物景或者个体经验的直接汲取向人性深处的开掘转移”(《让“诗”立起来,让除此之外的一切垮掉》)。质言之,无论是具体的空间还是更为阔大甚至抽象化的地域,已经发生了质变,而这必然深层地影响到同时代人的生活方式、精神视域以及世界观。
有一段时间中国诗坛非常强调所谓的“地方主义”和“地域性写作”,沈苇对此问题的回应则是:“诗人不是用地域来划分的,而是由时间来甄别的”(《西东碎语》。)“地域性”以及我们使用的越来越频繁的“地方性知识”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化的变动空间,更为准确地说,并不只是空间,而是时空体结构,它与整个社会的大动脉以及毛细血管发生着极其复杂的渗透关系。然而,随着“景观社会”的来临,在由“速度”“城市”和“后工业”构成的现代性法则面前,曾经近乎静止的整体化的地域和一个个具体的空间、地点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动。与此相应,“地域性诗歌”的文化功能以及诗人与地域的关系已然与传统诗学迥然有别。
地域和空间就是一个诗人世界观的体现,也是一个人的现实感、生存境遇和精神意志的折射。这正反映出一个写作者与环境和地域之间相互刺激、拉伸、消长以及调整的复杂过程。空间区隔和地域不是符号和元素,也不是仍然被津津乐道的传统和文化遗留,空间在诗人这里只能在成为特殊的精神共时体之后才能获得生命力。随着“新迁徙时代”的到来以及人口在空间的频繁流动,空间和地域的原生文化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携带着异质文化混合和共生的特征。此境遇还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和“异乡人”。“异乡人!行走在两种身份之间 / 他乡的隐形人和故乡的陌生人 // 远方的景物、面影,涌入眼帘 / 多么心爱的大地和寥廓。”(沈苇《异乡人》)。那么,诗人如何能够再次走回记忆中的过去时的“故地”“出生地”?这是可能的吗?而对于很多重新回到故乡的作家而言,面对着与童年期的故乡相去甚远的景观,其感受并不相同,但大多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在不断涣散的“地区精神”面前,我们遇到了讲故事的人,废墟上的无望的自言自语者。我们被讲述者或低沉或悲恸的语气所吸引,被那些古怪难解怪诞分裂的故事所困惑。这一切都大体可归入一个写作者的语言能力和时间观以及世界观。“一个人越是处于忘我的境界,他所听来的东西就越能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中。”(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讲故事的人”本来专属于小说家,但是单一的文体已然很难应付越来越复杂莫名的时间经验了。在速度景观和异质时间面前,诗人几乎和小说家站在了同一个序列里,他们的职责大体相同,都是叙述者,都是讲故事的人,而最终考验他们的则是讲述方式的有效和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