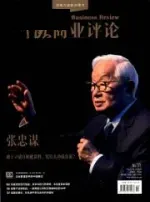上市公司ESG工作如何做:来自一位中集老将的肺腑之言

一直以来,在ESG的舆论场里,缺失一个很重要的声音——那就是来自企业管理者对自身实践的述说。说到底,ESG是一个围绕着企业的故事,企业内部的管理者是承接并将之落地的主角。
今年,在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起成立的第一届ESG专业委员会里,研究者大都是来自科研机构、“四大”、金融机构及咨询公司。只有一位成员来自企业,那就是李柱文。
作为中集集团可持续发展总监,李柱文2018年正式接手集团的ESG事务。他上任以后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集团领导的带领和支持下,牵头撰写集团当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ESG & CSR联合报告)。中集集团是A+H股两地上市公司,较早接受ESG理念,集团董事会和管理层都很支持ESG工作,也对ESG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柱文成了中国第一批汇入ESG大潮的探索者和管理者。如今回想最初的经历,李柱文坦言自己当时是“摸着石头过河,蒙头大胆探索,踩过很多坑,也积攒了不少经验”。而他所经历过的难点,相信很有可能会在很多大型企业管理者的ESG工作中重现。

日前,李柱文就“中国式ESG管理”与《中欧商业评论》分享实干经验,将ESG探索的经验和心路历程予同行者借鉴。以下是他的谈话精选。
ESG让“商业向善”变得很实在。ESG是企业业务走向企业使命的桥梁。
但从实际来看,很多企业的实际运营和ESG愿景还是两张皮。这两年到外面去参会、做分享,听到好的案例不少,但听到企业高层这样的说法也很多:“既然……提了要求,那就做一下吧。”
“做一下吧”“交交作业”,这种态度是很普遍的。大家都知道ESG重要,但它是个“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领导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各项业绩指标的压力也很大,能够有10%留给ESG已经不错了。ESG对很多企业高层来说,是个压力,是个成本,是个负担。
做ESG,首先要灌溉内部土壤。如何向上获得管理层支持,获得各职能部门支持,以及赢得下属子公司支持,这非常重要。在这方面,我觉得自己当时做对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多渠道营造氛围,让管理层对ESG有感知,让管理层“想做”。我准备了很多材料,在不同场合、不同规格的会议上多次讲述ESG内容。我希望让管理层看到:时代变了,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主流,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好的问题。
光自己说没用,我还请我们的高层参与外部峰会、颁奖典礼之类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在场的有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区高管,比如巴斯夫、威立雅、BP、帝斯曼等等。在这些场合,他们能够亲身感受到,巴斯夫、威立雅这样的企业是如何看待ESG的,是如何部署的。我说一百遍,可能不如这些标杆企业向他们说一遍。
还要有专业支持。我也经常请一些知名学者、行业权威来对大家讲课。再比如,我会请头部咨询公司、“四大”来企业内部讲解ESG和企业管理之间的关系。
第二件事,光嘴上说不行,要让内部同事看到实质的东西,要能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务虚。
比如说,要做好研究报告,依托ESG评级和数据对标,展现公司与其他行业头部企业以及行业平均水平的差异。就拿港交所ESG A类环境和B类社会指标来说,一对比,就能看到我们与行业其他企业的差异,比如,“××集团”是每亿元营收排放10吨碳、“××集团”员工培训小时是40小时/年、“××集团”供应商通过质量和环境管理体系比例90%等等运营绩效。这样反映差距的深度研究报告是管理层希望看到的。对职能部门来说,也为他们提供了改善工作的具体指引。得到大家认可,自然愿意参与ESG工作。
我们都知道,写ESG报告的第一步,是要去梳理关键性议题。这是个排摸“家底”的过程。女性董事比例、知识产权,这对中小企业来说,可能不是最迫切的问题。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工伤,不要因为消防安全被停产,不要因为环保问题被世界500强剔出供应商名单。解决工伤问题,解决消防和环保问题,同样也是ESG。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重点地做。
比如,2021年,全国多个省份的企业面临限电、停电问题。这时候,ESG管理者就可以联合部门做深度调研,搞清公司多少家单位受到影响,可能造成的营收损失有多少,多少家单位有条件安装屋顶光伏发电,能够减少多少成本,能降低多少碳排放,能避免多少運营风险。
这样的项目,既是响应“双碳”,同时,也实实在在支持了运营改善。这就是一个ESG策略落地的过程。
第三件事,是学会提交优秀成绩单,让管理层、各部门和各级子公司“有信心做”。ESG工作要积极争取外部支持,包括获得外部奖项,入选外部优秀案例,得到外部ESG提升,获得外部权威媒体的专题报道等。我记忆深刻的是,2018年、2019年,我们陆续获得外部奖项,集团领导很高兴,也有些惊讶。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会觉得,在ESG上投入是值得的。
ESG工作在本质上就是“管长远”。所以,我建议做ESG工作的人把格局打开。不要老想着做自己手头的事情、自己部门的利益。管理者要在各个可持续发展议题上去研究、部署和推动。最终这项任务具体是不是落到自己部门去执行,不那么重要。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烧一把火,然后这把火会转到别人手里,继续燃烧5年、10年。这样思考问题,做ESG管理的人才能越走越远。
在中国内地,正在开展ESG咨询业务的主要有五类机构,一类是“四大”为首的事务所等金融中介机构,也包括“五大行”的戴德梁行等;第二类是检测认证机构,比如SGS、TUV、BV等;第三类是咨询公司、财关公司、资本市场服务机构,比如商道纵横、他山咨询等等;第四类是律师事务所,例如大成、盈科、泰和泰等;第五类是科研机构,例如部分高校、一些研究院等。
我想特别提醒企业管理者:无疑外部专业机构有它们的优势,但是第三方机构和企业内部人自己看ESG,角度是不一样的。如果不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完全听从外部机构的宣讲,其实很容易踩“坑”。尤其是没有实际做过工作的新手,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
常见的第一个问题是,外部机构给我们作讲解,它们会建议“要更全面、更真实的数据,越是全面,相关方对你越满意”。这话没错,但是太理想化,企业很难做到,甚至披露不恰当,最后很容易把好事办成坏事。
企业才是数据的第一负责人。企业需要考虑的是:是否有披露数据的基础?能不能保证准确性?评级机构看企业,看的是这项指标在同行当中的位置。如果你吃不准这个数据在同行当中的位置,应该怎么办?事实上,数据并不是披露得越多越好。也不是披露得多,就说明你工作做得多。
我个人建议,刚刚起步的企业,统计要赶快做起来,同时要清晰这一点:统计≠披露,但统计是为了后续更好地披露。比较妥当的做法是,公司披露范围就跟着监管的要求走,慢慢扩大。
回顾我们自己的实践,我觉得这种方法是对的、稳健的。
我一开始就提出目标——“三年全覆盖”,一步步做数据,务求准确。我们是一家大型跨国产业集团,在境外和大陆有很多子公司,全球有7万名员工。要一下子收集所有的数据,很难保证准确性。同时,各个子公司工作量太大,很难承接。
第一年,我就只搞集团前四大业务板块的A类指标。四大板块占了集团业务量的85%,数据还是有代表性的。最开始,海外企业数据就只有2家,而现在已经覆盖到海外营收75%的企业了。优先要考虑的,不是数据范围,而是收一家准一家,收一个范围准一个范围。另外,就内部协同来说,我们不能让大家感到很累又很彷徨。不然,下一年,工作很难推下去。
常见的第二个问题是,很多外部机构会呼吁企业明确提出ESG战略和愿景,比如“到什么时间点,达成碳中和”,再根据愿景一步步做计划。

说实在话,我一听这话就脑袋冒汗。个人愚见,这样的话,同样是不接地气的。它适合西方上百年历史的大型跨国企业。这些企业已经有很好的基础,内外利益相关方也达成了高度共识,社会责任和商业道德的价值观更深厚一些。但它未必适合中国企业。
ESG战略是融入在企业发展之中的,不是凌驾于集团运营战略上,另起炉灶构建出来的。我认为相对实际的方法是,从企业总体发展战略中提炼出ESG战略,在有了一定基础,有了手感之后,再慢慢丰富。不然,结果就是表里两张皮,上下没共识,很难落地。
关于企业委托外部机构提供报告编制服务,我个人觉得,在起步阶段,企业请咨询机构来写报告,是比较实际的做法。对新手来说,比较快的上路的方法是,在外部机构的带领下先做一回,可以通过与外部机构合作,加深对ESG理念、ESG趋势、ESG披露要求、各类标准、ESG信息表达和报告编制思路等多方面的理解。
随着企业编制报告次数增多和自身水平的提高,企业聘请外部机构编制报告,就要有更高的要求。外部机构的服务内容也会从编制报告走向多元、深入。但外部机构还是一个“扶上马”的角色,如何建立ESG报告编制能力、如何部署ESG工作、怎么落地实施,还是得靠自己。
據我观察,目前,国内ESG刚刚起来,大部分国内机构还在团队组建阶段,起步晚、发展快。最早觉悟到的肯定是靠近资本市场、靠近港交所的机构,比如“四大”一直在服务港交所上市公司,可以说,它们是与港交所共同成长起来的。因而,它们总体上介入更早,研究上也更专业深入。还有就是一批有公信力的全球认证机构,如SGS、BV、TUV等也得到了企业的认同。

对这些机构来说,它们通常把“编制报告”作为切入企业ESG业务的“敲门砖”,从这块可以衍生ESG管理提升、ESG评级提升、ESG鉴证等更多咨询服务。
企业委托外部机构提供的服务中,有一块是报告鉴证服务。目前,鉴证还不是监管层强制推行的,但联交所已经在鼓励鉴证。业界普遍认为,报告强制鉴证是一个明显的趋势。 “四大”、SGS、BV还有中国社科院“责任云”等机构都可以为企业提供报告鉴证服务。
那企业应该请谁来做鉴证?
我认为,实质还是看企业“想让谁来懂你”。比如在港上市公司,可能优先考虑“四大”,毕竟它们在香港资本市场很有公信力;国内的央企、国企,就可能优先考虑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星级评级,它们在政府部门和国内业界有较大认可度;还有的是考虑SGS和BV等有100多年历史的老牌检验检测机构,类似于“全科医生”。这里头的底层逻辑是,各类企业的监管方和利益相关方都不同,情况比较复杂。甚至,有些企业会请两家机构做鉴证,这里头其实也有 “兼顾多方”的考虑。
我常常听到同行有类似的抱怨:“去年自己写报告,评级是B,今年请了‘四大’帮我写报告,评级还是B,怎么回事?”
这是对评级的最大误解——不是报告写得漂亮,评级就会高的。ESG评级体系是一个综合体,企业的ESG报告只是主要载体之一。评级机构会通过各种渠道抓取数据,包括政府官网、权威媒体报道等等。
我的经验是,企业要提升评级,应该组织ESG评级对标和差异分析,建立“涨分计划”,改善ESG管理与信披水平。ESG评级提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评级当然十分重要。评级和资本市场有关,和品牌美誉度有关,与监管层也有关。我听到不少企业实际案例,就是高层不知道评级具体是怎么回事,只关心ESG评级结果,搞得ESG执行层压力很大。
我在各个场合都讲过,但还是要抱着平常心看评级,不要过分关注某一个评级的打分。100个学生里有90个说这个老师好,那这个老师一定是好老师。各家评级的方法和指标体系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一些大企业,某个评级很好,某个评级会很差。
而且,评级是个相对值,是要和同行业横向比,自身纵向比得来的。不是说一家企业工作做得比去年好,评级一定会提高。比如,A企业花了5亿元做研发,比去年提高50%,但是同行业的B、C、D都花了10亿元做研发。同样花钱了,但是A企业评分还是得不到提高,甚至会降低。
客观地说,ESG评级还是西方人在掌握话语权。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大部分投资机构用的还是外国评级,如MSCI和富时罗素等。
说实话,一些外国评级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比如股权集中度问题,部分外国评级一看到国有企业,就可能在G(公司治理)上打低分。这一点从外国评级对中国国企、央企的评分中就能看出。
另外,部分外国ESG评级属于主动评级,需要企业填写资料,整个系统全是英文。这样的操作界面,对中国企业不够友好。虽说全球化的今天,英语是必备能力之一。我曾在外企工作10年,有一定英语基础,但有时还是要借助翻译。
我高度赞成业界公认的观点:中国要有自己的ESG评级,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ESG评级体系。外国评级与中国企业的自身实践,还是有差异,且有些差异是深层次的,很难弥合。中国应该有自己的评价工具,包括源数据、方法论、框架、指标和沟通机制。
比如,中国企业在ESG方面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双碳”,一个是“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今年开始,深交所已经要求企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乡村振兴”方面的举措,但海外评级机构并不是很看重“乡村振兴”。
现在,国内评级体系还在起步阶段,没有达到好的状态,尽管机构很多,但受到各方认可的几乎没有。我也研究过一些国内ESG评级机构的评级工作,发现它们就是在其他ESG评级的工作基础上修修改改,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和评价标准体系,甚至不能提供一份详细的企业评级打分情况。
评级太多,也的确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困扰。不说别的,那么多评级机构要填表、要维护也是一项工程。其次,评级很多,也会造成认知上的混乱。我还是希望评级标准能够统一,形成一个有效的市场信号。
目前,国务院国资委多次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国ESG评级体系建设,深交所也已经在2022年中推出国证ESG评级。这两个举措,还是让我振奋。
回想2018年我接手ESG工作的时候,还是挺感慨。
第一个两年,我从“小白”学起,感到兴奋、惶恐、焦虑。
最初,我对ESG认知不深、专业不够,在内部汇报中表达ESG工作时往往讲不清楚,很担忧无法赢得内部共识。到了年底编写报告的阶段,更是焦虑得不行。做ESG工作之前,我是做HSE(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管理的,安全环保也是ESG的核心内容,两种工作的人有交叉的地方,但是差别也很大。比如,HSE工作更多是管当年的事,守住安全环保运营底线。HSE工作性质更多是对集团内部,而ESG工作是管长远的,是对外的,尤其是对资本市场的,要讲好亮点、讲好未来。

我之前从未接触过资本市场,不懂他们的语言。那时,我在半年内看了大约60份外部可持续发展报告,参加了近20场外部ESG峰会和论坛,认识了很多媒体、资本市场中介和企业负责社会责任工作的朋友。开玩笑地说,我“不是在开峰会,就是在去开峰会的路上”。我也不断学习披露指引、学习ESG标准、学习外部优秀ESG报告、学习搭建ESG报告体系和管理体系。这其实就是一个咿呀学语的过程。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建立ESG数据信息化系统。当年,集团领导考虑到ESG数据范围大、指标多、质量要求高,结合外部专业机构的建议,很早就提出必须建设ESG信息化系统。问题是,当时市场上没有成熟的信息系统可借鉴,也没有比较全面的ESG指标统计系统和手册可借鉴。我们当时联合外部IT公司伙伴做了数据系统,但IT公司也是首次接触ESG。
这里头的关键是,我们自己心里要有一本账。我们要研究各类标准、各ESG指引的指標、同行指标,理解数据来源、制定数据定义、设计数据填报和审核流程并配置数据输出要求,才能告诉IT团队每一步需要的是什么。最初的这个信息系统很简单,只有数据录入,没有分析、看板等功能,它最大的意义在于,把数据定义清楚、把数据责任落实到各级单位各级人员。当时也真的是“蒙头猛搞”,小米加步枪,土法上马。例如统计用电量,那时候没有普及“智慧能源管理系统”,无法自动获取电量数据,但考虑到有据可查,我们就制定电量口径——不看电表,也不看其他统计口径,只看电费单。

回头一看,那时候工作上有很多没来得及做好的地方,特别感谢集团领导的指导、帮助、鼓励和宽容。
第二个两年,是积极探索阶段。我们总结的ESG“三步走”战略,ESG1.0版本是要打造一份高质量的报告,ESG2.0版本是“从报告迈向管理”,ESG3.0版本是将ESG融入业务经营。“从报告迈向管理”,这远比写一份ESG报告难上很多倍。它不是一家企业或者某个人有抱负就能做出来的,要突破既有的管理框架,要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要有顶层设计、要有落地举措等等。
第三个两年,是深入推进阶段。公司的ESG工作在公司高质量发展的情况下也实现稳中有进,呈现出较好的基础。我个人也是不断在“干中学”“学中干”。
在这个阶段,近两年,我开始受邀参加外部活动做分享,开始参加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制定,也开始发表一些ESG文章。我深刻地体会到,ESG不是读两本书、听几次课就能懂的,要真信、真学、真懂、真做、真坚持。所以,我希望把我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与同行们分享交流,共促进步。
我相信,将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形成“中国式的ESG管理模式”。于我个人而言,能为公司、为行业、为国家贡献真知灼见,就是最好的安排。十几年以后,我们这批人也就退休了,对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对于“3060”双碳目标而言,我们就是承接者,是做好起步和开局的角色。作为最早一批ESG探索者,看到ESG生态圈越来越成熟、ESG参与人员越来越多,看到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在践行ESG的大道上,心里欣喜。
唯有追求卓越,方可成就未来。全球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时不我待。ESG是企业要“活下去、活得好、活长久”的必然要求和主动选择。未来,管理者们在这一领域将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