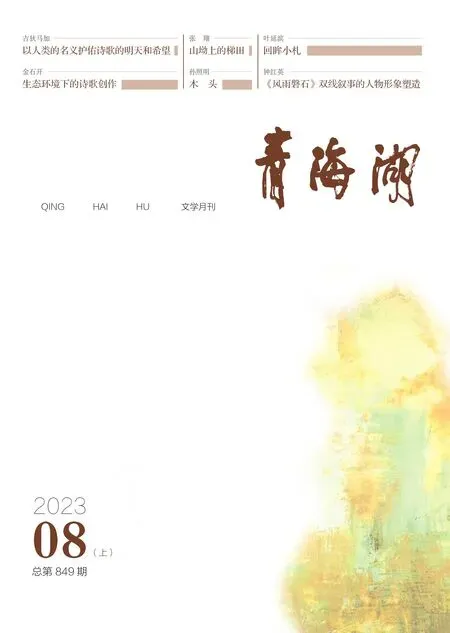倾听物语
阿甲
生态问题已经成为21 世纪的“世纪问题”。
生态问题的凸显说明了人在自然中的定位出现了危机。现代文明中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将人从自然生态的共同体中剥离出来,成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主人,自然也成为了可以无限制地攫取和利用的资源,当工具理性成为解释世界的价值基础,唯一的价值基础的时候,当经济发展成为“硬道理”,唯一的“硬道理”的时候,我们的生存是需要反思的,我们需要问一问,生活世界的“常识”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因为作为被征服对象的自然正在发出反抗并一再警戒着人类:被污染的水源和食品所导致的现代疾病,大气失衡所造成的酷暑和沙尘暴,生态失衡造成的瘟疫,生命优生情结缔造的转基因、克隆人,这一切已经成为现代生活崭新的威胁。这一切正在把人逼向危难的边缘。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非虚构”文学的盛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人的生存状况已经变得紧迫了,现今的生存处境下,直面生活现场,比虚构一个故事更有现实意义,更能触动人心。
我曾在青海海西州生活过十多年,海西整体上是个干旱缺水的地方,不是大面积的农耕区,但只要有河流有水源的地方,被垦荒开拓出来的一些地区的田野里,由于日照时间长,粮食的产量反而是非常高的,海西州的香日德农场,八十年代小麦单产创下过世界之最(每亩地1013 公斤)。因为在铁路工作的原因,我经常坐火车,二十年前,路过海西的时候,在柴达木盆地的东缘,以及许多有水源的农场所在地,种的全是绿油油的庄稼,也形成了许多局部的宜于人居住生活的“小环境”,大约从十多年前开始,这有限的农耕地都改种枸杞了,因为枸杞经济价值更高,是麦子的好多倍,田野里已经看不到庄稼了,我路过外省的时候,情况也差不多,甘肃、内蒙好多地区是大片大片的葵花林,从火车上看,很美,但我还是有一种隐隐的担忧,当一切只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时候,这种“美”可能是个陷阱,当真如果产生粮食危机的时候,这些经济作物是不能当粮食吃的。这些年,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强调生态建设和基本耕地保障,这些地区又恢复了过往,开始种粮食了。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日常场景中的例子,但足以留给我们警醒,就是我们长期以来的认知常识,要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中脱身出来,从一切只以经济利益为重的功利主义思想中脱身出来,生态不仅仅是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而是生存的基本伦理,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古希腊语里“生态(esology)”是由“生存的居所(orkos)”和“持家之道(logos)”两部分组成,而现在许多人只是将“生态”理解为“外部环境”,“一种独立于人类及其他物种之外的外部存在。”这是有失于偏颇的,“生态”更加强调的是符合“自然之道”的生活方式。它不仅仅是要求有纯净的空气纯净的水,反对污染反对浪费,“它还意味着对生存空间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所以在一种更为本源和宽泛的意义上,它还指向一种自律的,合乎自然之道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也类似于我们古典文明中所一再强调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即:人是天道自然的一部分,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自然”这一大的“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人和自然平等相待,和谐相处,才有人自身的出路。
作为文学艺术中最为敏感的群体,诗人们与自然有着天然的亲缘。“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诗可以观,诗可以群,诗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钱穆先生释读说:“举于诗,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此小言之。若大言之,则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可以渐跻于化境,岂止多识其名而已”钱穆《论语新解》。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草木名物琳琅满目,“蒹葭”“黄鸟”,“竹苞”“松茂”,俯拾即是。《楚辞》里香草嘉月,惠风和畅,“江离”“杜衡”“秋兰”“芙蓉”,着手成春。山水诗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伟大传统,陶渊明、谢灵运们在自然中托付身心,王维、孟浩然们在自然中寻得真趣,古典诗人放怀天地之间,寄情山水田园,一代一代形成了与自然共情共处的东方式世界观和自然观。在古典世界,这一切似乎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生态”问题的凸显是个现代命题,是人类社会“现代性危机”的体现。当“天人合一”的世界观,“道法自然”的自然观被“主、客体”意识所取代的时候,被现代主义高扬的“主体”创造性所取代的时候,从知识方法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上,人们看待事物的眼光变了,“山水自然”成为照相机里掠奇的“地理风景”,“梅兰竹菊”成为植物学里的某个科目,在现代文明的观照下,自然是“客体”,是地理学,是植物学,人不再是敬畏天道的那个虔敬之人,而是凌驾于自然造物之上的“主体”,是“空间的强悍占有者”。这种意识主导下的人类生活,以破坏和污染自然环境换取的“进步”和物质积累,已经使人的生活步入窘境。我们被迫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现实的处境也是:现有的文明在交流如此便捷的时空里,谁也无法孤立地生存,但生存也似乎越来越“同质化”,生命经验中那些“细节”正在大量地消失,具体到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古典时代文学里那种细微的“自然描写”越来越少了,这已不仅仅是我们的感受力钝化的问题,而是当下的生活状况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如何“活”,如何“在”,都已经成了问题。《沙乡年鉴》的作者,美国生态思想家奥尔多·利奥波德曾提出“大地伦理学”,倡导一种“生命共同体”意识,法国思想家塞尔日·莫斯科维奇基于“生态运动”的思考,提出“还自然之魅”的说法。我想起国学大家唐君毅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论及人文精神重建时提出的“返本开新”之论,这些深具忧患意识的哲人,都对人类文明的危机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他们都有个共同点,就是要深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活带来的危害,“返本”,是返回“文明”之本,也是返回“人”之本。在与自然的关系中,退回到人正确的“位置”,共生共情的位置,在面对自然万物时,去除“主体化”的自大,让“物”出场,从一个“有理”的世界,返回到“有情”的世界,从“进化论”的世界,返回到“天人合一”的世界。从用种种现代知识“解释”的自然,返回到“倾听”和“沉默”的自然,因为人类过多的解释已经打扰了万物。在天地人神的秩序里,善于“倾听”物之“语”,可能才有真诗的消息,因为诗本身就是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明相互感通的一个场域。
海德格尔曾言及:“自然是先于一切的最老者和晚于一切的最新者”。前段时间曾有朋友问我,你有多长时间没有晚上看过月亮了,我心里一惊,真是好多年了,自从住到现代高楼上之后,我们不是离月亮越近了,而是越远了,许多时候,我都已经忘记晚上有月亮了。夜晚灯火很明亮,没有抬头看过天。大美青海,邀请各位诗人,暂时地返回到自然的“幽暗”“寂静”“无名”中,在青海这个灯火稀疏的地方,看看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