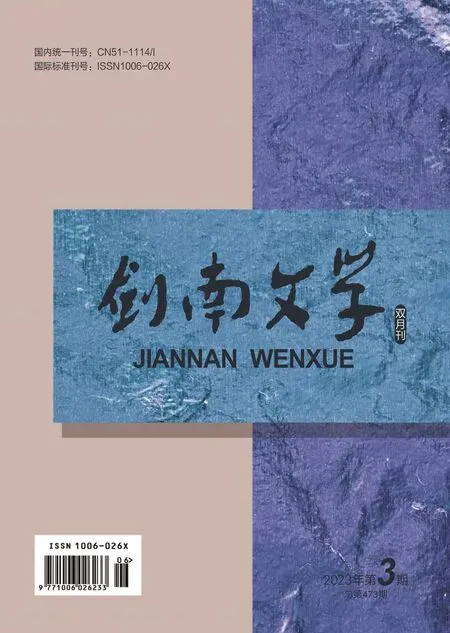龙门山下
□ 郭发仔
古书说,山不过来,我就过去。在龙门山,只要你去,不止山过来了,所有的气息都朝你涌来。
一座山的样子
一朵云落了下来,挂在龙门山逶迤的山峰上,映着日光淡淡的蓝,仿佛邻家年轻的妇人晾晒的褂子。
近处绵延的山体,如同飞奔而来的巨人一点点懈怠,终究无力起来,坐卧在地。山上灌木杂树枝叶茂盛,一律青葱浓郁的深绿。偶尔山花几树,或淡雅白,或梦幻紫,抑或秋熟后的焦红,在流岚中浸润着。山腰处,有骑行绿道盘桓其间,忽隐忽现,一直伸向沟壑曲折的大山深处。
龙门山,古称茶坪山、湔山,又叫龙山,据说是大禹的出生地,因大禹在此“凿龙门,铸九鼎,治水患”而得名。山水行者徐霞客在《江源考》中曾引《尚书·禹贡》说,大禹治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可见龙门山的前世,确有高古迷离的传奇。
其实,龙门山声名在外,是因为此处隐藏着一条巨大的地震断裂带。龙门山地处巴颜喀拉地块东边,西边是巴颜喀拉,东南方向便是四川盆地。巴颜喀拉地块运动频繁,在此受阻后形成龙门山断层。地壳仿佛在此找到了大地的软肋,不时扒开一个缺口,集聚的不良情绪便从岩层的缝隙中喷薄而出,引发天神动怒一般的地震。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对这神秘莫测的龙门山心存敬畏,却又百般好奇。
龙门山安静的时候,依旧是一座山的样子。没有尖峰,舒缓的群山层层叠叠,恍若隔世的隐者,先是浓墨涂抹深不可测的黛绿,随后淡笔皴擦,写意般勾画,远山多飞白,骨架虚幻,轮廓寥寥,天与地的边界都被这山的层次搅得乱了分寸。
龙门山逶迤蛇舞,一律的委婉。山中有一巨大的沟壑,叫蟠龙谷,算是山的最硬处。山体自上而下如熟透的八月炸,被撕裂出一条峡谷,裸露的尖石多青褐色,偶尔巨石横亘,是不守规矩的灰白。沟底溪水哗哗,分不清来处,只顾眼前的畅快,在乱石中穿梭而过,飞溅起银亮的水花。蓝天碎了,阳光碎了,一枝好奇的山雀不合时宜地落在水畔的石子上,惹了一身湿冷,慌忙抖了一下羽毛,扑棱棱又没入浓密的山林深处。
山中林木密集,浓荫遮蔽,不见罅隙,偶尔云雾缭绕,空濛而高远。延伸下来的山体放低身姿,平缓而懒散,植被依旧茂密,湿气氤氲,有阵阵阴凉从枝叶里溢出,沁人心脾。其间有多块不规则的层岩裸露,纹理清晰可见。山下的空隙处,蓬勃的茅草间有人辟了园子,种着丝瓜、南瓜、黄瓜,秧苗或青或黄,藤蔓肆意攀爬,溢出通透的人间烟火气。
与龙门山的沉稳与庄重不同,山下疯长的草地仿佛无所事事的流浪汉。每一株茅草都抬起高傲的头颅,留长了毛发,信誓旦旦要长成一棵树的样子,忽而一簇,忽而成片,高高地出头,在风里招摇。那些先天不足的草蔓,相互缠绕交错,抢占地盘一般,忙着张罗自己的小日子。龙门山下不大的平缓地上,小草层层铺排成一片茵绿的海洋。那种绿,积攒了龙门山上千年的气血,一如人间久旱逢甘霖般饥渴的目光。
深绿的草色中有一条叫湔江的小河。据查,湔江是古蜀文明的发源地,但目前裸露的河面看不出任何前世今生的渊薮。两岸芦苇、丝茅蓬生,枝叶迢迢间,有苍苍芦絮捧出繁华一般的白。枯水季节,小河瘦成一股清流,布满碎石的河滩护着一线天青色,缭绕如散淡的炊烟,透着仿佛从远古漫漶而来的富贵气,教人疑心这便是《诗经》里那条伊人彳亍的无名小河。延续文明气息的湔江原本多产墨玉,多圆润剔透,有通灵之气。不过,大自然的馈赠并非毫无止境,时至今日已无玉可采,倒是盛夏下河踩水的人,一茬又一茬,撩起衣裤涉入,亮晃晃如磨光的新玉。
其实,与龙门山的初遇,总会想起一些东西来。很多时候,哪怕最恶劣的大自然,也从来不会直接亮出自己的獠牙,而总是给自己披上华丽的外衣,让人先瞻仰它最妩媚的一面,例如这龙门山,这山下的郁郁青色。
小鱼洞的海子
龙门山腰有一处小鱼洞,也是古蜀族的发祥地,明亮如龙门山的眼睛。
周围石如刀削,铁青中透出寒气。有山泉自高处跌落,在谷底形成碧绿软润的一潭,雨雾纷飞,清冽之气漫漶。石壁上青苔露出新痕,草芥鲜嫩,幽微的世界里有与世隔绝的精气神。陡转水流盘山而下,龙腾虎跃一般,进入山下那片平坦旷野,虎落平阳却育出一派葱茏生机。下山之后的小鱼洞没有洞,而是一个有更大视域的民间洞天。公元1600 年此地建场,清代康雍年间(公元1662—1734 年)形成集市,取小鱼洞为场镇,人气聚集,渐成气候,其名称沿用至今。
小鱼洞宣泄下来的泉水流经平旷处,放慢了性子,从毫无章法的荆棘丛下穿过,潺潺有声。周围尽是茵茵树木,或翠竹一丛,或杂木参差,高而密,竟不见全景。一抬头,发现身在林中,不过草芥角色,就连日头也应接不暇,只白晃晃四处晃荡。
小道两侧林木掩映,水柳垂垂,桑树茂密,密不透风的杂木林退守后方,形成一道绿色屏障。水沟逐渐扩大,时而隐藏身影,时而漫出路面化作涓涓细流,路边间或有凉亭,水泽处有观赏水磨,如同乡间劳作的情景。溪流尽处,有山石砌就的坎子,各处水流汩汩落下。前方,便是一汪碧绿的海子了。
海子不大,也不规则,碎石围成的堤岸犬齿一般,护着这静静的明镜一般的碧水。海子中央,有鱼凫雕塑一座,扁平的独木舟中,一支鱼鹰独立船头,目光犀利,警惕地盯着无澜的水面。渔夫是一位老者,竹斗笠,棕蓑衣,黑褐色的脸上沟壑纵横。
海子连着更大的海子,碧清的一汪。沿岸曲折,翠柳袅袅,黄葛树和不知名的灌木穿插其中,把大海子围合起来。湖中有一小岛,水草丰茂,有两棵高挑小树立在中央,仿佛在此歇脚的农家女。湖中有三五竹排,宽而长,中央设置了小巧的凉棚。坐上竹排,用竹篙一撑,竹排划开平静的水面,两侧波光粼粼,盛夏的日头碎成了点点银光。水从竹排的缝隙里涌出,在脚底摩挲,清凉彻骨。
在龙门山下,人与自然似乎达成了某种协议。哪怕夏日,阳光是温和的,空气是澄澈的,水洁净而冰凉,野草也无须刻意种植,放在每一块空旷的平地上,一松手就铺展成一片有弹性的茵绿。在一片专为来此休憩的游客准备的帐篷露营区,小草青葱,旱柳点缀。高空的日头有些烈,不过穿不透龙门山下这片浓厚的绿和山泉的清冽,在半空白热着,一重山水一重天,仿佛两个贫富悬殊的邻居。
一条小路在绿地上蜿蜒,不时有藤蔓植物搭成穹形的甬道。烈日进不来,在藤蔓上方吱吱地燃烧,干着急。一侧竹篱笆的空隙里,有风从远方赶来,越过不深的沟渠水,钻进过道的空洞里来回打转。漫步其中,有水的寒、风的凉、草的鲜,还有龙门山体透出来的氤氲之气。
一蓬苇草在远处的水岸泛出青绿。高空中,几朵白云在游走,落下几片,挂在飘拂的柳枝上,贴在大地的草尖上,缠在龙门山伸出来的腿脚上。其实,那不是云,而是山间闲散下来的岚。
时光落在院子里
午间太阳兮白,照亮一片杉树和银杏树,却始终落不下来。
树荫掩映一睹淡红的砖墙,间或有用白灰堆砌的鹅卵石,循着墙根走几步,人便没头没脑地进了院子。院门是没有的,两侧各立了一蓬妖艳的三角梅,一树猩红,一树深紫,在高处枝条,俨然隔着银河相会的牛郎织女。
院子似乎不是想象中的格局,泥巴地面新栽的桃树并不高,细小的一枝,将地面隔成一个个车位。弯腰躲过横斜的秀枝,但见一栋三层楼房,被折成“L”形,白墙,平顶,红色的门窗仿佛画上去的。楼房的一侧全是桌椅,还有四五个灶台,其余,全是银杏树的地盘。银杏树高大挺拔,枝叶在半空里密集,阳光下不来,只在枝叶的缝隙里着急,斑驳的泪光掉在地上,零零落落。老板见有客来,慌忙沏茶,倒水,打开电扇,甜蜜的笑意中又传出一丝清凉。那电扇喷着水汽,随着机械摆动指哪打哪,落在皮肤上,山间的冰凉再次袭来。
老板是一位中年妇女,微胖,本地人,世居于此。老板说,大地震时很多房子都垮了,村里人几乎都搬出去安置了,这房子是大地震后重修的。“千好万好,不如自家老地方好,大地震不多,小打小闹习惯了。这里空气好,每年很多外地人来休养,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老板平静地说,仿佛在唠家常,脸上有怡然自得的满足。院子里客人不多,三三两两,在躺椅里小憩。墙角散养了三五只鸡,母鸡似乎也是来休养的,紧靠墙根,一副懒散的模样。唯一的一只公鸡,拖着黑得发亮的尾羽,围着母鸡踱来踱去,如同在欣赏新创作的一组艺术雕像。一对老年夫妇走出屋来,男的拄着拐杖,女的白发齐耳,二人相扶缓缓抬脚走下台阶,在一棵银杏树下的藤椅里坐定,神情坦然,银丝白发里有夕阳的红光。他们坐下来时依旧紧握对方的手,没有说话,略微浑浊的眼神里有一道明亮的光,或许那是波折生活中练就的色彩,或许是龙门山下清润的空气里颐养出来的气息。岁月静好,是除却凡间杂事,避开无常烦忧时才能体验到的真意。我想,我老的时候,是否也有这般相守时光的笃定与泰然。
中午吃的是柴火鸡。一掀锅盖,热腾腾的雾气中夹着菜肴的香。锅边贴里一圈金黄的玉米糊糊,也叫锅边馍馍,是四川农家一贯的吃法。柴火的烟熏味还在,土鸡的鲜香在锅里回旋,土豆、魔芋、洋葱、辣椒、萝卜,似乎凡是能入锅的,都在柴火的熏烤下与土鸡做了迎合,荤素之间毫无缝隙,米饭反倒成了配角。饭后,习惯性地闭目养神。午后的院子愈发通透,银杏树开始犯困,风在高处摆弄一片片叶子,笨拙得像一只小猴拨弄一方绿手帕。阳光依旧下不来,在枝叶的缝隙里向一张张困顿的脸抛出魅惑的眼神。此刻的龙门山下,仿佛就是一个天然的空调,温湿恰到好处。安然小睡,不觉大半下午已过。一墙之隔的马路上,依旧车如游龙,向往龙门山的人络绎不绝,为了这山间的凉意与景致,不计早晚。
这院子早已住满了,一行人有些不知所措。
“去镇上看看吧。”
一个穿着时尚的姑娘对我们说,一只白嫩的胳膊抬起,指向一片葱茏的玉米地。她所说的镇,就是小鱼洞镇。顺着手指的方向,我们的视线依旧摆脱不了那片玉米地。山间的夜来得快,暮色如同一张大网,撒在玉米地上,也把我们包裹其中。原本灰白色的路面,在玉米林中一点点模糊起来。
不知道这个镇子跟鱼还有多少关系,有怎样的一番风情。玉米地愈发浓厚,如汪洋大海中黑色的深渊。
暮色又重了几层。
青纱帐里的秘密
小鱼洞镇不是想象中常见的镇子。换句话说,玉米林占据了整个镇子。
方圆几里,几十里,到处都是高过人头的玉米地。隐匿在玉米地中几排不高的白色楼房,随着玉米地一起摇曳,仿佛一杯花茶中浮起的几点飘雪。
玉米秸秆粗壮,许多不大不小的玉米棒,披着紫红或淡黄的缨子,兴致盎然,像一个个不肯入睡的娃娃。驻足围观半晌,我的视线无法超越这片作物的长势,不知道这龙门山尖硬的石头为何还能育出这方丰润的土地,也不知道这青纱帐是否稳固地占据了山下充盈的日子。而我们入住的那座孑然的房子,被一张绿色的大网包围着,寂寥得如藏在山林深处小小的鸟窝。
山里的夜来得快,月光仿佛未涉尘世,羞怯如醉,挂在不远的山顶上,很小,但明亮透彻,可以见到若隐若现的筋脉。空气里有玉米茎叶的青涩味,也有夜的清凉。玉米地的空档处,散落着农家的瓜果菜蔬。一侧的山坡上,树木葳蕤,都在月光下默然。龙门山下的夜保持着乡间的静谧和祥和,虫子在暗处歌唱,各种叫声大大小小,相互交织,只有同类才能从嘈杂的声音里捕捉到家长里短的琐屑信息。
咔嚓,咔嚓。
黢黑的玉米地里响起另一种声音,将这恬静的夜色划开一道口子。一个瘦削的身影在掰玉米,在白亮的月光中,像一支跳动的皮影。她裹着青褐色的头巾,衣服也是青褐色的,看不清面容。她的手枯瘦而有力,拨开僵硬的叶子,径直伸向秸秆上藏在夜里的棒子,熟稔而轻巧,如同顺手拿取灶台上的油盐酱醋。
“这么晚了还在收苞谷啊?”同行的友人踩上田埂,靠近了去打招呼。那人一侧身,回应了一句,没听懂。那是一个老妇人。就在那一瞬间,我看清了那张脸,潦草,凌乱,是被太阳和烟火熏黑的颜色。不过,额前散乱的头发青幽幽的。山里人自有山气,土石水木的肌肤掩盖了他们的真实信息。
“这么晚了还在忙,卖一些玉米给我们要得不?”
老妇人叽里咕噜回了一句,过于晦涩的本地方言像一串没有理清的珠子,和着越来越浓稠的夜色,落进深不见底的土里。老人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停下手中的活,一字一顿告诉我们,因为今年干旱,这些苞谷都不饱满,掰下来喂猪的,不能卖。我们内心一阵热,不再说话,继续试探着往前走,踩着自己的影子,仿佛触及龙门山那个神秘莫测的断层。
月色粘在路边的草叶上,发出晶莹的亮光,有淡淡的雾气从山林里弥漫而来,天空愈发高远,而四周的大地,厚重而深沉。
龙门山下,葱茏的青纱帐已经睡熟,只有月光是清醒的,正酝酿一个关于自然色彩的主题。而这片一望无垠的青纱帐,便是那张铺在大地上的画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