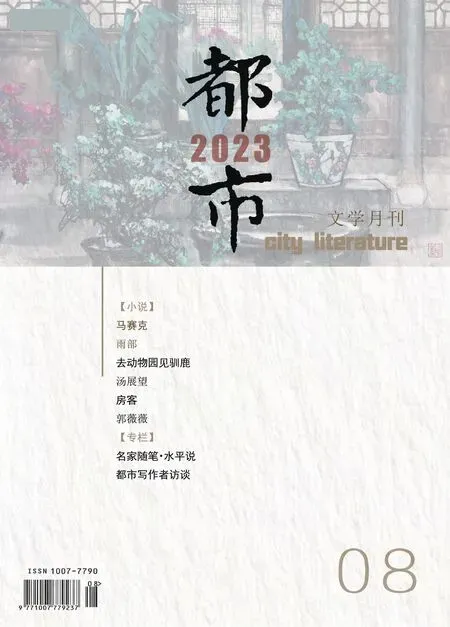大胡子爸爸
文 李世斌
在我七岁要上学的时候,便跟随母亲“随军”了,父亲是驻扎在南方某县部队的营长。紧挨着营区的山脚下有一幢二层的小楼房,这幢小楼房住着营里的几个军官,我们一家住在楼下东头的两间房子里,东边间用薄板隔成了前后两小间,前间用作厨房,摆了一张吃饭用的小方桌。后间安了一张行军床,算是我的个人领地。楼下西头住着副营长一家,副营长的儿子小伟和我同年生,我生于年头,小伟生于年尾。楼下中间的几间房用作营卫生室。营部其他单过的干部都住在二楼,包括战争年代曾经给我父亲当过通信员的营部司务长“大胡子”(平时只要我父亲不在场我就直接喊他“大胡子”)。
一日午间,烈日炎炎,我在屋外杂草地上捉蚂蚱玩儿,一只蚂蚱轻身一蹦,把我吸引到一堆杂草丛跟前,蚂蚱藏进杂草里不见了,我陡然看见了一条手腕般粗的大蛇,我失声尖叫,大蛇倏地“站”了起来,三角形的蛇头忽闪,吐着蛇信子。正在午休的大胡子听到我的尖叫声推门而出,站在楼上的栏杆前朝我喊了一声:“小鬼,别动。”
大胡子平时从来不曾叫我小会,更不会叫我的尊姓大名“易会”,总是习惯叫我小鬼,有时还要顺带着摸一下我的后脑勺或刮一下鼻子。我不愿意他刮我鼻子,会朝他吼一声“你干吗?大胡子!”而大胡子则很有满足感地哈哈大笑几声。这会儿冷不丁遇上吓人的大蛇,我当然会听从大胡子的话,愣愣地忤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大胡子从楼上飞速跑过来,竖起来差不多有半人高的三角蛇头朝大胡子左摆右闪的,我不敢看,生怕大蛇会忽地朝我身上扑来,便掉过身子猛跑了好几步,大胡子注视着大蛇对我说:“小鬼别怕,待我将它手到擒来。”
当我转过身睁大了两眼看时,映入我眼帘的是大胡子不知使出了何种神术,已经把蛇尾捏在了手指间,大蛇被大胡子倒悬在空中甩动,我似乎听到了蛇骨断裂的“拉拉”声响。
过了一会儿,大胡子说:“小鬼,过来吧,不用怕了。”
我战战兢兢地挪着小步,吓人的大蛇像一堆麻绳般被大胡子扔到草地上。大胡子朝我嘿嘿笑道:“小鬼,它的骨头链被我甩断了,已经一命呜呼了。这可是条剧毒的眼镜蛇哟,如果被它咬上一口可不得了。”
我有点不大相信,颤着声问:“它,真的死了吗?”
“那还有假,它的七寸也早被我给捏扁啦。”大胡子说着捡起大蛇朝我脚下一扔,说:“你仔细看看它死了没有吧。”
我跳着脚“妈呀”一声大叫,转身跑开了,躲在远处的一块岩石后面朝大胡子叫道:“大胡子,你是个大坏蛋……”
大胡子发出了哈哈的大笑声。
这一天晚饭时间,父亲回家了,母亲把饭菜刚端上了饭桌,楼上的大胡子端着个砂锅就来了,朝父亲说:“易营长,今晚改善生活喽。”
父亲疑惑地望着大胡子问道:“大胡子你搞啥名堂?不过年不过节的改善啥生活呀?”
大胡子嘿嘿笑着,把放在饭桌上的砂锅盖掀开,砂锅里随之升腾起一股白气,散发出满屋子的鲜香味。大胡子说:“看看,清炖眼镜蛇,天下第一美味。”
父亲问道:“哪弄的?你这个山头人尽爱吃些邪乎东西。”
大胡子说:“我的营长诶,您忘了打仗那会儿靠一条蛇救了我们几个一命吗?那天您怎么说来着?您说蛇肉是天下第一美味。”
“哦,倒是有那码子事,记得,可那是我为了鼓励战士们吃蛇肉嘛。”父亲回忆道。
父亲从砂锅里夹了一筷蛇肉,塞嘴里嚼了几下啧啧道:“还真是鲜美呢,大胡子你还真有两下子呀。”
大胡子往我碗里夹蛇肉,我赶紧把碗端开,头摇得和拨浪鼓似的,只差起身躲开了。母亲笑道:“大胡子,孩子不敢吃就别勉强了。”
父亲看了我一眼,含笑说:“小子没出息。”
砂锅的清汤卧着的两只荷包蛋倒是都被我吃了,感觉跟以前吃的味道不一样,带着腥却又很鲜。
那天晚饭后,我抱着好奇心到大胡子屋里,缠着他给我讲打仗那会儿我爸和战士们吃蛇肉的事。
大胡子卖着关子,慢腾腾地给自己点了一根烟,末了还刮了我一下鼻子。为了听故事,我这回一点儿也不恼,托着下巴急着听他讲。
大胡子吐了一口浓烟,说:“小鬼啊,新中国成立前打仗的时候你爸爸是连长,我是通信员。在一次战斗中我们连打得只剩下不到一个班的兵力,而且已经被敌人围困在山上三天三夜了。如果再这样下去,突不了围,敌人就是不放火烧山,我们几个士兵也得活活饿死。小鬼啊,大胡子叔叔我呢,参加革命队伍前就经常跟我爹上山捕蛇,什么眼镜蛇、五步蛇,当然喽,那些个无毒的草花蛇啥的就更不用说了,连我爹都夸我是捕蛇能手。所以啊,当我们被困在山里没得吃的时候,我就想到在山里捕蛇给大家充饥。记得那天我捕到了一条比今天这条还要粗的草花蛇,但捕到的蛇是不能生火烧的,一旦被敌人发现烟火就完了,所以只能把蛇给脱了皮,用刺刀把蛇切成段分给大家生吃。几个北方兵才咬了一口就哇啦哇啦地吐了,你爸爸自己强忍着作呕,把蛇胆囫囵整个都扔进嘴里吞了下去,还鼓励大家说:“这蛇肉可是天下第一美味,都别吐出来,咽下去,有了力气就能胜利突围。”
我听着大胡子活灵活现地讲生吃蛇肉的故事,觉着好像自己嘴里也渗出了一股血腥味,差点呕了出来。从此,在我的一生中,只要在餐桌上一见到蛇肉就想吐。
一天,大胡子用铁钳夹住一条滑溜溜的,比大拇指还粗的黄色的蛇在我眼前晃悠,那蛇头划着S 形,都快碰到我鼻子尖了,吓得我蹦了起来,惊叫道:“蛇!蛇……”大胡子哈哈笑道:“你这个胆小鬼哟,这不是蛇,是不会咬人的黄鳝呐。”
听大胡子这么说,我觉得自己有点丢面子,憋着通红的脸朝大胡子“哼”了一声说:“是蛇,就是蛇,是……黄鳝蛇!”
“好好,你说是黄鳝蛇就是黄鳝蛇。”大胡子显然是给了我台阶下。
那天是星期天,当天晚上大胡子端着一大盘菜来我家蹭吃喝了。大胡子指着端来的菜盘说:“易营长,韭菜黄鳝丝,我亲手炒的,美味不能没有酒,把您家那瓶大曲贡献出来呗。”
父亲瞪了大胡子一眼说:“真是不怕贼上门,就怕贼惦记。说,黄鳝哪弄的?”
大胡子嘿嘿笑道:“水田里捉的呗,只花劳力不花钱。”
“我这瓶大曲可是花钱买的噢。”父亲笑着说。
母亲笑着把酒瓶往桌上一蹾,说:“大胡子出劳力捉了黄鳝炒给你吃,你就让他喝几口呗。”
大胡子满脸堆笑道:“就是么,还是嫂子大方……”
这时住在楼西头的副营长进屋来了,一见这阵势便“嗬”的一声:“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哈。”
父亲赶紧说:“来来快坐下,否则这瓶酒大半都得被大胡子一人给喝了。”
三个大人把酒盅碰了个响,一仰脖干了,大胡子放下酒盅夹了一筷子韭菜鳝丝,但没往自己嘴里塞,而是夹到了我的碗里。我推开饭碗说:“我不吃你的黄鳝蛇。”
父亲瞅了我一眼,说:“黄鳝蛇?你小子还挺能整词儿。”
母亲一旁说:“小会,大胡子叔叔夹给你的,怎么这么没礼貌,快吃了。”
我装作很不情愿的样子,把韭菜鳝丝扒拉到嘴里,鲜美的黄鳝肉丝一下子便打动了我的味蕾,我终于不顾“面子”,接连夹了好几筷子塞进嘴里。
那个夏天每个周六的晚上,我和副营长的儿子小伟都紧跟在大胡子的屁股后头,去水田或者溪滩里捉黄鳝、泥鳅和溪鱼。我跟大胡子好得形影不离了。
在我十一岁的时候,父亲在训练场上突发脑出血去世。父亲去世后小伟的父亲接任了营长。小伟父母对我们母子很关照。大胡子就更不用说了,那年头还没有自来水,大胡子经常帮我家拎水。母亲说:“大胡子,小会长力气了,叫他拎水去,不能老让你辛苦。”
大胡子跟没听见似的,照样帮我家干这干那,还时不时地送些好吃好喝的。
说来也怪,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我对大胡子突然间产生了一股莫名的抵触情绪。以前他做什么我就喜欢学着他做什么,而现在看见他做什么我就会心生反感和抵触。一次大胡子给我家拎来一桶水,我甚至一脚踢翻了水桶,望着流淌了一地的水,我愤愤地说:“大胡子,以后我家的事不用你管!”
大胡子默默地拎起倒伏的水桶,好像啥事也没发生过,重新给我家拎了一桶水过来。
那天母亲狠狠地骂了我,说我长这么大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事理。
后来大胡子要转业去地方工作了。就在大胡子要搬走的前一天,母亲特意为大胡子包了牛肉韭菜馅的饺子。那天下午放学回家我看着母亲包完了最后一个饺子,牛肉韭菜馅的饺子是父亲生前最爱吃的,也是大胡子特爱吃的,以前只要母亲包了饺子,用不着叫,大胡子总会闻着味儿嘻嘻哈哈过来蹭吃,还会嘬着小酒说些饺子就酒越吃越有之类的话。母亲包完饺子后,一边收拾,一边叫我上楼喊大胡子叔叔过来吃饺子。
我把头一歪说:“我不去。”
母亲操起擀面杖虎着脸说:“你这孩子,你到底去不去?”
我不怕母亲手里的擀面杖,长这么大,母亲啥时候舍得打过我?不过吓唬吓唬我罢了。我突然灵机一动,假装害怕的样子答应去叫大胡子。
我磨蹭到二楼的大胡子的房间门口,门是虚掩着的,我把门推开一半,见大胡子正在埋头打包,他抬头看见我,问道:“小会啊,叔叔包装一下东西,明天得搬走咧,你妈饺子包好啦?”
我听起来觉得哪儿怪怪的,噢,是大胡子今天突然改口不叫我“小鬼”而是叫我“小会”了,是为了讨好我吗?我一边想一边说:“我和我妈都吃过了,我妈叫我过来告诉你一声,我妈有事出门去啦。”
大胡子意外地“哦”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我返回家,母亲问我:“叫大胡子叔叔了吗?”
我眨巴着眼睛说:“叫了,可是他说他已经在营部食堂吃过饭了,营长还加了菜送他,他还说他有事,马上得出门啦。”
母亲一脸的失望,喃喃道:“这个大胡子,昨天跟他说得好好的,叫他过来吃顿饺子的,他也满口答应了的呀,没说营长要送他呀……”
我得意地在心里头暗自发笑,心想你个大胡子还想吃饺子,做你的美梦吧。
母亲从汤锅里捞了满满一碗饺子端到饭桌上,叫我趁着热乎吃。
我夹起一只饺子塞进嘴里,又往灶台上瞟了一眼,发现母亲把锅里的饺子捞进了一只稍大一点的碗里。我估计这碗饺子是母亲特意为大胡子留着的。我狼吞虎咽地把一碗饺子吃完,朝母亲喊:“妈,我没吃饱,我还要吃。”
母亲瞪了我一眼说:“你饿死鬼托生的啊?这么一大碗饺子还填不满你那小鸡嗉子吗?”
我说:“我就是没吃饱嘛,我要吃那一碗里的。”
母亲说:“不饱喝饺子汤,要不把妈那碗稀饭喝了,别想打那碗饺子的主意,那是给你大胡子叔叔留着的。”
我任性地说:“那我再少吃几个。”
“你敢,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母亲又瞪了我一眼,摘下围裙出门往公厕方向去了。
我乘机直接用手抓饺子往嘴里塞,一口一个,硬是把一大碗饺子吃得仅剩几个垫碗底的了。
待母亲回来发现了我的恶作剧后,气得操起擀面杖朝我屁股蛋上狠狠地敲打了几下。
被母亲挥舞的擀面杖软绵绵地敲打几下算不了什么,我还真没啥感觉。问题是没过一会儿,我那圆滚成皮球般的小肚子就胀得受不了啦,我忍不住哇哇叫唤了起来,母亲气得骂我“现世报”,还有“撑死鬼”什么的。但母亲骂归骂,还是硬着头皮敲开了隔壁卫生室的门,卫生员取了两粒消食片让我嚼到了肚子里。
失去了父亲的我就好似断了线的风筝,比我小大半岁的小伟成天跟在我的屁股后头不学好。小伟的母亲曾经朝我母亲埋怨说她家小伟都被我给带坏了。小伟母亲这样说也确实没冤枉我,小伟听我的话远超过听他妈的。哪回兑糖客摇着铃铛来了,小伟就会学我的样,回家翻找牙膏壳、空瓶子、铜质子弹壳、军衣上的铜纽扣什么的,反正是能兑糖吃的都会找出来。山上的番薯熟了或者杨梅红了,我就会叫上小伟一起去偷吃。一次我叫小伟一起上山“挖地雷”,我把偷地里的番薯叫“挖地雷”,方法是先扒拉开泥土,待番薯露出半个身子后再拽番薯秧子,番薯被拔出土后再把番薯秧子插进坑里埋上土,这样就看不出番薯被挖走的痕迹了。那天我和小伟在山腰上的地里偷挖了番薯,用山水洗净,待啃饱了、玩够了,看见西天已是一大片火烧云了,才想起该下山回家了。下山时我在山崖间摔了一跤,一条腿摔伤了,还出了血,不能走道了。小伟害怕了,跑下山报信。因为大胡子在地方上工作的单位离山上近些,小伟就去找了大胡子,才半个多小时大胡子就急匆匆跑上山来了。大胡子要看我的腿伤,我龇牙咧嘴地不让他看,大胡子说:“你这孩子拗什么拗,你想当瘸子啊?有本事你站起来走两步我看看?”
可惜,大胡子使出的激将法也没能使我站起来,我的脚脖子严重扭伤了。
大胡子流露出心疼又生气的表情,说:“小会啊小会,你这孩子也真够皮的,敢偷人家农民种的番薯吃,要是你爸爸在还不敲断你的腿呀。”大胡子数落着我,俯下身打算背我,还叫待在一旁的小伟搭把手。
我本就不想让小伟下山把这事告诉大胡子的,而这会儿大胡子数落我不说,还偏偏提起我父亲,我就更不愿意让他背我了,但大胡子硬是把我给驭到了他的背脊上,我挣脱着,但大胡子那两只铁钳般的大手死死地卡住了我的屁股,我哇啦哇啦叫喊,用两只小拳头不停地擂打大胡子的肩膀……
后山上的杨梅树上才结出绿豆般大的杨梅时,我的口腔内就不时地渗出酸水,我和小伟天天惦记着杨梅粒的变大,终于,我俩发现长成玻璃弹子般大的杨梅已经变幻出了一抹一抹的粉红色。而这时,在进入杨梅林的石阶口处,不失时机地竖立了一块牌子,上面是蚯蚓似的毛笔字:偷杨梅抓到罚款五元。
放学后,我和小伟一路游荡到杨梅山下的石阶口,小伟指着牌子说:“小会,偷杨梅被抓到是要罚款的,五块钱呀,要是我爸知道了,不把我打死。”
我对小伟说:“怕啥?抓着了得罚钱。可是没抓着呢,不就没事了吗?听我的,等杨梅再红点了咱们大胆来摘。”
过了十来天的一个下午,我撺掇小伟一起逃课上山偷摘杨梅,被民兵连长逮了个正着。那天,小伟被他的营长爸爸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我母亲则气到抹泪,还用公用电话给大胡子打了电话。大胡子闻讯后特地赶来我家,随身带着预备罚款的五块钱。见到我之后,大胡子凶巴巴地训了我一顿。这可是大胡子第一次朝我发这么大的火。我怎么也想不到大胡子敢跟我发火,在我少年叛逆的心里,一直朦朦胧胧地认为大胡子对我母亲怀有心思,平时讨好巴结我,帮我家干活送吃的都是有目的的。可这次他竟然把两只眼睛瞪得铜铃般大,嗓音也格外地作响,说我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又是偷又是逃学,送到少管所都够条件了,而且还说这样下去怎么对得起我去世的爸爸。我鼓足气顶了他一句:“不用你管。”我曾经用这句话顶过大胡子好多次,但这次说出的“不用你管”显然比以前软弱无力了好多。我已经从心底里意识到自己真的是做错事了,真的变成个坏孩子了。大胡子一反常态地凶我反倒让我觉他真是出于好意,有点儿“恨铁不成钢”了。因此,当我脱口说出“不用你管”之后,就把头垂了下去。
那天傍晚,大胡子凶完我以后就走了,但过了一会儿他又返了回来,手里捧着卷成喇叭状的黄色草纸,里面装着满满的杨梅。母亲说:“大胡子,你还惯着他呀?”
大胡子把杨梅倒进盘子里,对我说:“小会,叔叔今天骂你是太凶了点,别记仇啊,叔叔相信你一定会改好的。以后想吃什么跟叔叔和你妈说,咱去买。”
我抬头望了一眼大胡子,然后迅速把脸别了过去,我这会儿已经没有勇气再说出“不用你管”的话了。
我有时想,大胡子干吗一直不找个老婆呢?要是他有老婆孩子,说不定我俩仍然还是上下辈的好朋友。我究竟是因为什么对他产生了怨恨呢?他不就是想对我妈好吗?可是,我打心底里抵触,我只有一个爸爸!
十六岁那年,我和小伟一起入伍当了“小兵”。在车站告别时,大胡子也来了,旁边站着不时抹眼泪的母亲。我茫然地看了大胡子一眼,跟母亲挥泪道别。
当兵第二年,母亲来了一封信,说自己得了胆结石,在县医院做了手术,住院期间一直是大胡子叔叔白天黑夜地照顾。母亲在信里特别叮嘱我别担心,手术很成功,她已经痊愈出院了。
我把展开的信放在床头上,痴痴地望着窗外。小伟来到我跟前,问我干吗傻呆呆的。我把信递给小伟看,小伟问:“你的家信也给我看啊?”
我说:“我们之间还有啥好保密的,看吧。”
小伟看完信后“嗳”了一声说:“大胡子叔叔心地真好,不容易啊。”
我没好气地说:“什么心地好,这不明摆着有目的的吗?是有心计好不好。”
小伟瞪了我一眼说:“你说啥呢?我们很难理解大胡子叔叔和你爸我爸他们这些从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战友情呢!你不用把自己放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妈生病住院,人家大胡子叔叔没日没夜地照料,你不感激人家倒算了,还中伤人家,难道你脱下军装回家照料?”
小伟的话击中了我的“七寸”,让我一时无言以对。
当兵第三年我回家探亲,这才知道大胡子和我妈已经住在一起了。
当天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趁他低头旋茅台瓶盖的时候,我用心看了一眼大胡子,发现他脸腮上的刷子般的胡茬子已夹杂了些许白色,头顶也秃了一圈肉色了。
大胡子一边用劲旋瓶盖一边说:“小会啊,这瓶茅台我收藏了好多年,一直没舍得喝咧,另一瓶早就被你爸给喝了,今天咱俩就把它给消灭了吧。”
我赶忙用手推开大胡子旋瓶盖的手说:“别打开,我当兵这几年不碰酒了。”
大胡子用恳切的口气时我说:“小会,这是你回家探亲第一天,就开戒喝几盅吧。”
我把眼神从大胡子脸上游离开,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
母亲在一旁打圆场说:“小会不喝就算了,不喝酒也好。会儿,多吃点菜。”
大胡子无奈地说:“那好吧,这瓶茅台我继续存着吧,来,小会,吃菜。”大胡子说着,特意把一盘韭菜炒鳝丝往我前推了说:“小会,韭菜炒鳝丝可是你愿意吃的,叔叔今天特地为你炒了一盘,尝尝。”
母亲见我不动筷,便夹了一筷子鳝丝放进我碗里。我埋头扒拉着饭,心里想你大胡子又是开茅台又是炒黄鳝的,无非就是想讨好我让我认你这个继父叫你一声爸嘛。
二十来岁的我早已过了“叛逆”期,既然大胡子已经跟我母亲住到了一块,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是十多天的假期我基本不着家,忙着自己会友喝酒去了。
在我探亲假期满的头一天,大胡子终于逮到了个机会跟我说:“小会,找个对象吧,县政府机关有个女孩挺不错,她爸那天在街上看见你后主动找我说起来着……”
我乜了大胡子一眼,不冷不热地说:“我的事不用你管。”
大胡子看我这态度,也就不再言语。母亲在一旁看看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当天晚上,母亲到我房间,慢声细语地对我说:“会儿啊,妈知道你心里不大畅快,怪妈事先没跟你说,但妈也是担心告诉你妈和大胡子叔叔一起住,会影响你在部队上的情绪。妈身子骨一直不好,你当兵后妈住过两次院,多亏你大胡子叔叔照应……”
我倚靠在床头上,打断母亲的话说:“妈,您现在跟我说这些干啥?反正我也管不了,我不反对,只要您觉得好就好吧。”
当兵第十五个年头,我当上了营长。我的任职命令和母亲发来的加急电报是同一天。电报告知大胡子叔叔病危,正在医院抢救。
大胡子毕竟和我母亲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也早已从心底里认可了这个“心地好”的继父,不说别的,如果没有大胡子,就凭我妈那身子骨,这么多年来我能安心在部队服役,还一路当上营长吗?
小伟也和我同时当上了营职军官。得知大胡子病危,小伟特意跑到我办公室,催促我抓紧打报告请假回去。我感到心里十分为难,上级刚下了命令,我都还没来得及走马上任,就请假回去,真有点难开口啊。小伟见我面有难色,叹口气说:“易大营长啊,我还是劝你一天都别耽搁,大胡子叔叔的命可是从战场上捡回来的,他这一辈子是真不容易啊。他的前妻在战乱中被杀害,没给他留下个一儿半女,他自己又在战场上被炸弹炸毁了命根子……”
我一激灵,睁大眼问道:“小伟你说啥?大胡子叔叔他,他下体被炸毁……”
“怎么,你不知道吗?”小伟觉得很意外。
我说:“我怎么会知道这些,可是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听谁说的?”
小伟说:“我爸告诉我的呀,我还以为你一直知道这码子事呢。”
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半晌,才自言自语地说:“我,我这就去找团长政委,我,我明天就坐快列回家……”
坐在回家的列车上,从前有关大胡子的事儿一幕幕在我脑际回闪。我想起孩提时曾经问过父亲,大胡子叔叔为什么老是一个人住啊,他这么老了还没有老婆小孩吗?
父亲瞪了我一眼说:“你个小毛孩子瞎问些啥呢!以后不许乱说。”
比大胡子年长三四岁的母亲在一旁告诉我:“大胡子叔叔以前有过老婆的,被日本鬼子杀害了。”
到达县城后,我顾不得回家放行李,直接往县医院奔。我找到了大胡子的病房,母亲正陪护在大胡子的病床前。看见我后,母亲本想站起身迎我,身子顿了下,转而伏到鼻孔插着吸管,半昏迷的大胡子的耳边轻声地唤道:“大胡子,快睁开眼看谁来了?小会看你来啦……”
大概是听到了“小会”两个字,大胡子睁开了双眼。我扑到床头,一把抓住大胡子焦黄干瘪的手,眼泪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
大胡子憋足一口气说:“小会,你也是营长啦……部队上忙,来,来干吗……快回去……”
我情不自禁地地喊了一声:“爸爸……”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喊大胡子爸爸。
大胡子爸爸嘴角微微一翘,无力地闭上了双眼,两行泪珠从他的眼角滑落。我接过母亲递过来的白纱巾,轻轻地为大胡子爸爸擦去了泪痕……
第二天,我特意炒了一小盘韭菜炒鳝丝,熬了一碗小米粥。我知道大胡子爸爸已经难以进食了,但我必须这么做,在我的记忋里我好像还是第一次专门为他做饭烧菜。
我把装着韭菜鳝丝的盒盖打开,捧到大胡子爸爸的鼻子下,说:“大胡子爸爸,这是我炒的韭菜鳝丝,您闻闻,多鲜,我喂您吃几口吧。”
大胡子爸爸嚅动着嘴,沙哑道:“黄鳝蛇,你爱吃……我吃不动了……”
大胡子爸爸闭上了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