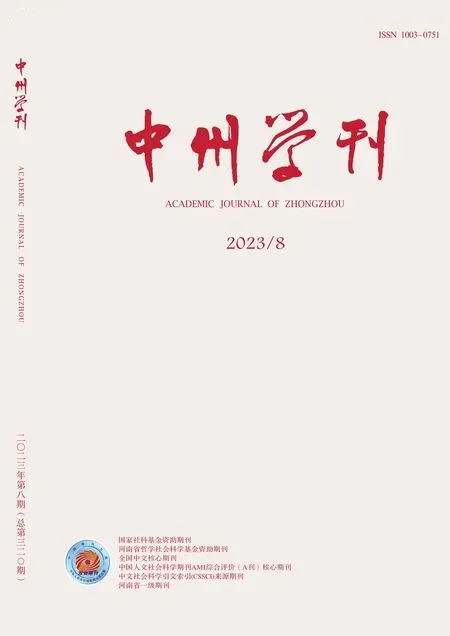制度严苛与皇权调整:清代嘉庆朝王书常案与官员处分研究
孟姝芳
嘉庆十四年(1809年)的“假印案”被称为乾嘉道时期书吏舞弊案的典型,对此案学界有一定研究,如薛刚的《从“假印大案”看清嘉庆朝吏治》[1],倪玉平的《行政失控与政府治理——清嘉庆朝王书常冒领库项案研究》[2],作者分别从“假印案”发生的原因、过程、“假印案”整治的失败等角度探讨了这起案件。也有文章如关文发的《嘉庆吏治评议》[3]等,对案中官员处分予以点及,然未及深论。
本文依据档案资料,尝试探讨当时以吏部为主的制度议处和以嘉庆皇帝为主的皇权调整之间的关系。在制度议处中出现了官员处分的严苛问题;在皇权调整中出现了官员处分从宽轻减的问题。皇权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官员的处分力度,体现了皇权治理对制度治理的完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处分制度本身的效用和导致吏治的愈加腐败。王书常案所揭示的制度治理和皇权治理之间的关系,不独存在于嘉庆朝,乾隆朝和道光朝也同样存在,可见清代对案中官员处分的一贯处置模式已然常态化。
一、王书常案的问题及严重性
这起案件发生在嘉庆十四年十二月,由时任步军统领的禄康将随意捏造工程名目、大胆伪造工部文稿、私刻印信冒领银两的工部堂书王书常和其他一干经承、贴写拿获。经审讯得知,“王书常每次假捏钦派办工事由”[4]778,伙同各部书吏,从嘉庆十一年起,冒领户部银库、颜料库、缎匹库及内务府广储司银两和物料,前后共14次,其“冒领银数共计五万余两,其冒领颜料、缎匹按照例价计值银一万九千余两”[4]777-778。嘉庆对此案尤为震怒,指示迅速查办。
首先是刑部议罪。嘉庆十四年,军机大臣、刑部等奉旨严讯,通过昼夜熬审加以刑吓,案情水落石出,结案治罪上奏。此案治罪依据数款律例:律一,伪造诸衙门印信冒支钱粮者斩立决,为从绞监候。律二,诈传诏旨为首斩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律三,伪造诸衙门印信者斩监候,为从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律四,伪造假印将起意与雕刻之人并以为首论。律五,诈伪六部文书盗用印信者绞监候,诈伪其余衙门印信文书者杖一百徒三年。律六,诈伪六部各司文书者,俱与其余衙门同科。律七,知人盗后分赃者,计所分赃准窃盗为从论。律八,恐吓取财计赃准窃盗论加一等。律九,凡称准者,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4]778。可见,王书常等人所犯不止一项罪状,而是数罪并及,盗库者焉能活命!刑部的治罪轻者发配充军,重者绞斩[4]778-779。
其次是由嘉庆裁决。在刑部拟罪基础之上,嘉庆降旨裁决:“该犯等作奸藐法,情罪重大,实属法无可宽。”对于案中“蔡泳受、王书常、吴玉均著即处斩,蒋得明著即处绞,派侍郎托津、景禄前往监视行刑。”此外,“传集六部、三库、内务府等衙门书吏各数人前往环视,俾共知儆惧。谢兴邦、商曾祺俱著绞监候秋后处决。陶士煜、王嘉鼎、秦浩、钱树堂、祝广平、叶锡嘏均著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宋良辰、万彭俱著发附近充军”[4]775。前后处死者6人,发配充军者8人。
比对刑部治罪和嘉庆定罪,对于所有罪犯的定罪嘉庆全部依从了刑部的制度性议罪,不仅没有从宽,而且还强制性命六部、三库、内务府书吏观看,给予他们心理上的震慑。可见,对于吏役犯罪的处置和对于官员的处分,嘉庆的处置是截然不同的,对吏役,嘉庆的态度是罪无可赦甚至要加重处罚,而对官员,处分可从宽减轻并可以再次被起用。
就此案嘉庆十四年曾有旨:“王书常等胆敢捏造印信,冒领帑银库件竟至十四次之多,酿成巨案,现已按律严办。其失察之堂司各官亦分别降革治罪。”[5]721“牵连、遣戍、降革大小多员。”[4]775嘉庆讲得比较轻松,实际上此案牵涉官员很多。自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以来,一拨又一拨官员受到处分。这些处分从制度的实降实革后转为皇权干预下的虚降虚革,部议处分的效用大打折扣。
二、嘉庆给出对官员处分的初步定性
针对此案需要处分的官员,嘉庆曾就处分官员的程度如何提出初步定性,这是官员处分的第一个环节。吏部便以此定性为基调,进行具体的按例制度性议处。
1.嘉庆针对内务府大臣处分初步定性的“反复”
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吏部尚书庆桂奏请议处失察冒领库银案的内务府堂司各官。嘉庆由此初知案情大发雷霆,立即对内务府大臣苏楞额等6人发难,指出此6人的失职之处:“内务府于伪造工部假印文领,屡次照文给发毫无觉察,此在总管内务府大臣各员怠玩不职,究属咎无可辞。”苏楞额、阿明阿“二人现系工部堂官,各司文稿俱应阅视,使于内务府给发银款时,思及工部衙门并未具奏此件,一加查核何难立破其奸?乃被欺多次”,“岂堪复胜部院之任,苏楞额、阿明阿俱著即行革职,仍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罪”。这是最重的定性。至于英和、常福、和世泰,“俱著先行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对于征瑞,因出差在外,情稍可原,“著交部议处”[6]。除嘉庆以皇帝身份直接处分个别官员外,更多的涉案官员则是按照皇帝的初步定性交由吏部按照制度规定予以议处。
按照嘉庆的治罪处分逻辑,治理失察处分之罪,必须要以精确的失察情况为依据。当时所能提供的精确依据则是大臣们在任期间的失察次数。为更准确地议处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将犯案官员在部年月与失察假印次数进行比对,统计苏楞额在侍郎尚书任内有失察已冒领二次未领一次;英和在内务府任内失察已领一次;阿明阿任内失察已领七次未领一次;常福任内失察已领一次[7]。这项比对核议工作须非常细致,否则稍有差错就会导致后期处分的错误。
军机大臣将此次失察次数清单进呈给嘉庆,使嘉庆看到了实际的失察情况,这与其先前的主观评判“屡次照文给发”有一定出入,嘉庆及时改变定性:“苏楞额在工部、内务府年分俱久,其平素办事尚属细心。”“乃于此等文稿并未寓目疏忽已极,本应仍予治罪,但其失察仅止二次,与阿明阿之失察七次者有间。苏楞额业已革职,著加恩免其治罪。阿明阿仍著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罪。至英和、常福于兼工部侍郎任内各有失察一次,前经降旨将伊二人同和世泰一并严议,此时亦应量予区别。英和、常福、和世泰著分别严加议处。”[5]700此旨将苏楞额的刑部治罪免去。嘉庆以所谓的“一秉至公”[5]700掩饰了自己前期的失误判断,也使得部分内务府大臣的罪状有所减轻。
2.嘉庆针对管理三库大臣失察处分的初步定性
军机大臣又二次上报管理三库大臣的失察次数。档案载:董诰失察二次;恭阿拉失察三次;庆桂、王懿修俱失察一次;费淳兼管工部失察一次;瑚图礼失察一次;禄康、曹振镛俱失察一次[4]765。涉及8位管理三库大臣,其整体失察次数为一到三次之间。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嘉庆依据上述失察次数的不同,对各位管库大臣的失察处分给出初步定性,费淳“著交部严加议处”;董诰、恭阿拉、瑚图礼、曹振镛“均著交部议处”;庆桂、王懿修“著交部察议”;禄康“此次失察之处,毋庸交议”[8]。这是嘉庆针对三库大臣给出的初步定性,各有侧重。
3.嘉庆针对工部堂官失察处分的初步定性
工部堂官的失察处分有两处,一是失察冒领内务府广储司;二是失察冒领户部三库。嘉庆的初步判断程度也有所不同,对于因失察冒领内务府广储司的处分,嘉庆认为:“工部堂官失察书吏铺户舞弊,印由私雕,与盗用堂印者稍有不同。所有工部堂官任事较久者著交部议处,其本年到任者著交部察议。”[6]对工部堂官失察处分的特点是较为平和,只有议处和察议,没有严加议处,这是嘉庆鉴于上次对内务府大臣的初步定性有误而吸取的教训。
为定性准确,军机大臣同样呈报了工部堂官失察冒领三库银两物料次数。大学士费淳和原任尚书缊布都失察五次,苏楞额失察一次;尚书邹炳泰失察一次,曹振镛失察四次,戴衢亨失察一次;侍郎英和失察二次;署侍郎多庆和邵自昌失察一次;侍郎成书失察三次;原任侍郎阿明阿失察二次;侍郎福庆和周兆基失察一次;原任侍郎蒋予蒲失察三次;侍郎陈希曾失察二次;顾德庆失察二次[9]。这次涉及16位大员,失察大致在一次到五次之间不等。
嘉庆同样依据失察次数,给出初步定性。费淳“于本部书吏冒领三库银物失察至五次之多,咎无可辞,著先拔去花翎不必兼管工部事务,再行交部严加议处”;曹振镛、成书、蒋予蒲“均著交部议处”;英和、陈希曾、顾德庆、多庆、周兆基、邵自昌、邹炳泰、戴衢亨、福庆“均著交部察议”[6]。工部堂官的失察处分是嘉庆给出的第三次定性,可见失察次数越多,处分定性越严重,相反则为察议。
4.嘉庆针对户部堂官失察处分的初步定性
同样的,户部堂官失察次数也是他们定罪的依据。大学士禄康失察冒领三库银两物料六次;尚书德瑛失察六次;戴衢亨失察四次;曹振镛失察一次;侍郎托津失察二次;赵秉冲失察五次;英和失察二次;刘镮之失察四次;署侍郎桂芳失察一次;原任侍郎苏楞额失察四次[4]765。涉及10位户部堂官,其失察次数在一到六次之间,嘉庆依此定性:“禄康著革去太子少保衔降补协办大学士补授户部尚书,德瑛著革去太子少保衔降补工部左侍郎,俱仍交部严加议处。戴衢亨、赵秉冲失察较禄康、德瑛俱少,况伊二人供职内廷不能常川到署,著交部议处。刘镮之失察四次又未画稿,著交部议处。曹振镛、托津、英和、桂芳均著交部察议。”[8]嘉庆在直接处分个别官员的同时,又做出初步定性交由吏部按照制度具体议处。
皇帝初步定性,是处分的第一个环节,主要围绕察议、议处和严加议处展开。议处是核心,较轻者察议,较重者严加议处,程度不同。
三、吏部依照制度条例进行严苛议处
在嘉庆初步定性的基础之上,吏部按照制度条例对内务府官员、管理三库大臣、户工部官员予以具体议处,这是处分的第二个环节。吏部议处多为实降实革,因此被视为制度的严苛。实降实革处分对国家行政运转的影响颇大,故而才会有后期嘉庆对严苛制度的调整。
1.吏部对内务府官员的严苛议处
首先议处内务府6位大臣。“苏楞额兼任内失察二次,业经奉旨革职免其治罪,应毋庸议。阿明阿兼任内失察七次,先经革职应请发往军台效力赎罪。英和、常福亦曾兼任各失察一次,应俱请革职。和世泰未曾兼任工部,止于内务府任内失察七次,应请量减为降二级调用。征瑞于内务府任内失察二次,应请降一级调用。”[6]“应……”这是吏部按例议处的套语,因为还需皇帝最后确定,此时表达的是按制处分的内容。此次内务府大员处分议为革职治罪者1位,革职者3位,降调者2位,分别是降二级和降一级调用。吏部议处较为严苛,均为实降实革。
其次议处内务府广储司银库司员和笔帖式。其处分定罪轻重亦与失察次数相关联,郎中德音、员外郎士诚失察八次,员外郎广善失察七次,郎中瑞宁失察五次,库使恩吉、常文、罗汉保失察八次,灵铸失察五次,此8位“均应请旨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郎中文光失察二次,祝麟、穆翰失察一次,此3位“应请即行革职”。当时值日笔帖式保禄、恒启、景椿、裕善、士凤和收文笔帖式达善、郭升阿、石麟、托永武、福泰、重荫,此11位“于假印咨文投到时未能即时查出,亦应一并革职”[6]。司员和笔帖式共有22员,处分较重,8位被议为革职并遣戍乌鲁木齐,14位被议为革职。按制处分总体上严苛,皆为实降实革。
2.吏部对管理三库大臣失察的按制严苛议处
吏部依据嘉庆定罪态度对管理三库大臣进行议处,各官处分具体是:费淳管理三库,“失察冒领物料一次,照例应议降留;又兼管工部未能详加核对漫无觉察,奉旨严加议处,应将大学士费淳即照溺职例革职”。董诰、瑚图礼、曹振镛、恭阿拉“奉旨交部议处,应将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诰,吏部尚书正黄旗汉军都统瑚图礼,户部尚书曹振镛,礼部尚书正蓝旗满洲都统恭阿拉,均照例议以各降一级留任;曹振镛共降二级留任”。庆桂、王懿修“奉旨交部察议。应将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正黄旗满洲都统庆桂、礼部尚书王懿修,均照例减为罚俸一年”[8]。此次制度议处各官处分参差不等,奉旨严加议处的对应制度规定议为革职;奉旨议处的对应制度规定议为降一级留任,奉旨察议的对应制度规定议为罚俸一年。由处分程度可见对管理三库大臣的处分有实革的,有虚降的,甚至有罚俸的,其处分整体轻于内务府官员的处分。缘何如此?从吏部的议处诠释中,可知官员担任本职和兼职,失察都要被处分,只不过本职和兼职被处分轻重有所不同,本职处分往往重于兼职处分。有清一代“一职数官,一官数职”[10]的状况也是导致大员被处分居多的一个原因。
3.吏部对工部堂官失察的按制严苛议处
首先议处工部堂官因失察冒领内务府广储司银库的处分。其所据条例为:“定例书吏舞文弄法侵欺钱粮本管官不行查出降二级调用。又吏部议处事件本管官应降二级调用者,该管上司即议以降一级调用。又官员议处有奉旨交部严加议处者,查照本例酌量加等。其奉旨改为察议者,酌量减等各等语。”[6]
依据以上三条制度规定,吏部议应将工部堂官费淳、前任工部尚书曹振镛、前任工部侍郎成书、前任工部侍郎蒋予蒲、工部侍郎陈希曾、工部侍郎顾德庆,“均照该管上司例议以各降一级调用”。历任未久及本年到任之工部堂官庆惠、工部侍郎福庆、前任工部侍郎周兆基,“于降一级调用上减为降一级留任”[6]。这是吏部将奉旨议处的对应制度条例议为降一级调用,有6位工部堂官;将奉旨察议的对应制度条例减为降一级留任,有3位官员。此次因嘉庆起始就定了从宽的基调,吏部议处,引例确当,处分有实降有虚降,整体已从宽,不需皇权二次调整。
其次议处工部堂官因失察冒领户部三库的处分。此次按制议处结果,费淳因“奉旨交部严议,应照例加等再降二级调用,共降三级调用”,因“任内有革职留任之案无级可降应行革任”。曹振镛、成书、蒋予蒲“均奉旨交部议处,应照例各再降一级调用,共各降二级调用”。英和、陈希曾、顾德庆、多庆、周兆基、邵自昌、邹炳泰、戴衢亨、福庆“均奉旨交部察议,应照例各减为降一级留任”[6]。此次按照处分条例费淳因加等议处议为降三级调用,因无级可降议为革职;曹振镛等3人以议处对应议为降二级调用;英和等9人以察议对应议为降一级留任,此次议处也是有虚降有实降,层次不等。
4.吏部对户部堂官失察的按制严苛议处
吏部议处户部堂官,所引用处分条例有以下四条:条例一,书吏舞文弄法侵欺钱粮,本管官不行查出降二级调用。条例二,三库银缎颜料等项倘有重支冒领等弊,照违制支给例降一级调用。条例三,吏部议处事件本管官应降二级调用者,该管上司即议以降一级调用,本管官应降一级调用者,该管上司即议以降一级留任。条例四,官员议处有奉旨交部严加议处者,查照本例酌量加等;其奉旨改为察议者,酌量减等[8]。按照条例中规定,最重的处分是降二级调用,最轻的处分是降一级留任,所谓的加等和减等,是在这些级别上予以加减。因此户部堂官的处分是:禄康、德瑛因是“奉旨交部严加议处”,应“均照该管上司降一级调用例上加等议以降二级调用”。戴衢亨、赵秉冲、刘镮之因是“奉旨交部议处”,应“均照例议以各降一级调用”。曹振镛、托津、英和、桂芳是“奉旨交部察议”,应“均照例各减为降一级留任”[8]。嘉庆的初步定性对于该处分哪些官员,怎么处分作了指示。吏部遵例议处时,定罪的理由是嘉庆认定的,定罪的程度是嘉庆指示的,可见黜陟大权把握在皇帝之手,部院承担的只是遵旨按例议处。
5.吏部对户工部下属官员的严苛议处
对户工部承办官员的议处,吏议结果为,工部虞衡司掌印郎中英奎在其任内,因失察共有十二次之多,“英奎应请旨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银库给发银两全以户部印札为凭,“福建司三次文札均系已革员外郎刘洋即刘承澍主稿呈画先行……应请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工部笔帖式惠昆“屡被欺蒙,翻稿画押,亦请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工部虞衡司掌印员外郎常安、户部福建司掌印郎中定柱、宽宁,员外郎时敏失察次数一到二次和主事锡礼岱,“均照溺职例即行革职”。颜料、缎匹库司员于假印文领没能查出,即行给发物料,颜料库共计三次,缎匹库共计二次,“应交部查明该管司员等概行革职”[4]779-780。
此番吏议对各官处分以革职和遣戍为主,在几拨处分中,此拨革职官员至少在10位以上,最为严厉。而更重要的是对于这批直接的承办官员,因其职位相对较低,嘉庆给出的定议是依照吏部所议,将以上承办官和司员全部革职,部分遣戍乌鲁木齐[4]775,制度治理与皇权治理实现了难得的趋同,皆为实革。
对户工部其他司员及下属的议处。这些官员包括给发画押的户部监放官、银库司员及工部虞衡司、福建司画押各司员、江南道御史等,嘉庆命“均著照所拟交部查取职名,分别议处”[4]775。随后,便有颜料库郎中宝诚等19位,户部监放官郎中四德保等17位,工部虞衡司失察舞弊司员郎中等24位官员,被议为降一级调用。此为实降,但是所降级数不多,也就无须皇权的再度调整。吏部议处是处分的第二个环节,也是吏部按照定例予以的制度议处,其特点在于以实降实革为主,颇为严苛。
四、嘉庆对制度处分严苛的从宽调整
王书常案中每一次的制度议处之后,凡存在处分严苛实降程度严重的,嘉庆均会进行从宽调整。这种从宽调整的对象不是针对所有官员,主要针对内务府大员以及户部、工部堂官,其他官员即使被议为革职、降调,也很难有从宽的可能,一般都是“照依部议”。嘉庆的调整定议属于官员处分的第三个环节。
1.嘉庆对工部堂官失察处分的调整定议
嘉庆虽然申饬道:“部院各衙门大臣位崇责重,于经管事务分应尽心综核……设于初起时各该管大员等有一二人精明详察,烛破其奸,立时查拿惩办,则罹法者必不至如此之众,而承办各职官亦不至严谴多人。”[5]725但转念又以大员“一时更易多员,乏人简补”[5]725为由,从宽调整大员处分。首先是费淳“前已拔去花翎退出工部,今部议革任,著革去宫衔降为侍郎……兵部右侍郎一缺即著费淳署理”,并没有将费淳革任而是直接降补。其次,曹振镛、成书、蒋予蒲由各降二级调用,“俱著改为降三级留任”,由实降转为虚降。陈希曾、顾德庆由部议各降一级调用,“俱著改为降二级留任”[5]725-726,由实降转为虚降。
2.嘉庆对户部堂官失察处分的从宽定议
部议对户部各堂官处分本来不重,嘉庆却再度从宽,禄康前已降为协办大学士、尚书,“其部议降二级调用著从宽改为降三级留任”。德瑛前已降补工部侍郎,又以其“精力已衰”,“著即以二品顶戴休致”,获得荣归。戴衢亨、赵秉冲、刘镮之部议各降一级调用,“俱著从宽改为降二级留任”[5]725。亦皆由实降转为虚降,一拨拨的处分还没起到效果,便在嘉庆的从宽意旨下消失殆尽,官员不用再予降调。
3.嘉庆对内务府大员的从宽定议
嘉庆十四年嘉庆降旨,阿明阿“原拟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之处,著改发热河”。英和、常福、和世泰、征瑞4人,“分别议以实革实降之处,亦皆咎所应得。惟内务府大臣同时出缺简任乏人,且伊等离任之后转得置身闲散自图安逸,著从宽姑予留任”。英和、常福原议革职,此时“著降为三品顶戴,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和世泰原拟降二级调用,“著从宽改为降三级留任”。征瑞,原拟降一级调用,“著从宽改为降二级留任”[4]755-756。针对这批内务府大员的制度处分是比较重的,实革实降,但是在嘉庆的调整下皆予留任,这是处分的实质性变化。
而上文所论嘉庆对于内务府的管库司员、库使、笔帖式等的处分并没有丝毫的从宽。仅以“职守尤专”[4]756,维护了吏议处分,将内务府中下级官员革职并遣戍。这份谕旨体现出对不同等级官员的最终处分完全不同。针对内务府大臣,嘉庆在吏议基础上按照惯例予以从宽,予以不同的留任等轻处。而对内务府司员及库使、笔帖式等,则完全遵照吏议予以实革。因此,嘉庆的从宽是“有限”从宽,嘉庆的调整也是“有限”调整。
虽然在处分制度的规定中,有由降调、革职到降留、革留的转轻规定。但是,处分制度中却没有规定可以从轻的官员的范围,皇权从宽的对象是有限的大员,而最基层的官员是根本没有从宽机会的,他们的命运就是被“革职”,这也是皇权治理的阶级局限性所在。
五、皇权治理的后续及影响
1.迅速起用大员对处分制度造成的冲击
由上文可知,“因失察或纵容吏役有犯而受到惩处(降调、革职和查办)者,部院大员不乏其人”[11],但从嘉庆的调整来看,嘉庆主要是对大员进行了宽免。此后,又加速对大员的迅速起用。
首先迅速起用的是苏楞额和阿明阿。苏楞额是因案革职,阿明阿亦是革职并发往热河。嘉庆十五年,距离案结不久。嘉庆降旨:“念伊等究系公过,苏楞额于办理工程素为熟悉,尚可录用,苏楞额著加恩赏给圆明园六品苑丞,阿明阿著赏给八品笔帖式。”[12]153其次宽免重用的是禄康和费淳。昭梿曾记载:“宗室相国禄康……才具庸劣,无所建白,又不甚识字,于古今政体毫未寓目。其所操持,率皆以市井毁誉为之趋慕,罔识朝廷大体,故一时丛脞成风,每多苟且之政……夫以天潢贵胄,而不学无术至此,安可以当调羹重任也?”[13]256可见禄康才具一般,却是屡任要职。前论嘉庆十五年,嘉庆从宽处分后禄康改为降三级留任,此时嘉庆以同样理由,“究系失察公过,著加恩仍复还东阁大学士太子少保衔,著管理吏部事务”[14]75。费淳被从宽处分后降补兵部右侍郎,此时“所有工部尚书员缺著加恩即将费淳补授”[14]75。嘉庆恢复了他们的大学士、堂官身份,这些做法都导致“处分无以儆效尤”。但是,嘉庆依然从宽和起用了他们。嘉庆十五年,嘉庆在对此案的回顾中流露出其真实想法。他讲道:“近日各部院衙门因循怠玩相习成风,推原其故,由于各大臣等思避专擅之迹,惟以含容博宽大之誉,推委邀安静之名,虚称办事实则废弛,不肯正色率下综核名实,一切文移奏牍委之司员。而司员中又无实心任事之人,一切委之胥吏,听其播弄画诺施行……试思朝廷政柄操之自上,若大臣盗权坏法,则为太阿倒置。今幸纲纪肃清,大臣等尚无此弊。”[12]6-7
王书常案中,嘉庆认为是大员官权的出让,而不是其皇权的被侵夺。所以,嘉庆认为宽免大臣重新重用他们,重塑各级机构之官威,才能使行政如常,处分仅予“薄惩”即可,这无疑是对处分制度本身的严肃性和处分效用的冲击。“诸部曹夤缘为奸,伺大员谈笑会饮时,将稿文雁行斜进,诸大员不复寓目,仰视屋梁,手画大诺而已……嗟夫!于照常供职之事,尚复泄沓若此,又安望其兴利除弊,致吾民于熙皞之世也哉?”[13]248对于这样的大员不加严惩,而再予重用,嘉庆朝的吏治如何能清明!
2.嘉庆允许中下层官员捐复对吏治的影响
嘉庆十五年正月冒领案结束不久,禄康就奏请将降革司员概予捐复。嘉庆当即批示:“此不可行。该员等甫经部议,若遽令捐复原官,非惟不足示惩,抑且迹涉言利,有此政体乎?”[12]10但随后,便出现了“英奎捐复”事件,从而为案内其他降革官员捐复提供了事实上的可能,禄康的提议捐复在若干时间之后也成为了现实。
英奎是新授内阁大学士勒保之子。嘉庆曾于“十四年四月,以勒保七十生辰,赐御书‘宣勤介景’匾额。十二月,擢武英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15]2213。十九年八月,勒保“目疾增剧,命开大学士缺,仍在家食威勤伯全俸”。嘉庆二十一年,降旨:“勒保之女,著指与四阿哥为福晋。”[15]2214英奎就是这么一个显赫家族的成员。
王书常案中,英奎因案不仅被革职,且被遣戍乌鲁木齐。案结不久,嘉庆十五年,嘉庆念“勒保在外宣力有年,又年逾七旬”,加恩将英奎“仅予革职,免其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12]2。同年,勒保在具折谢恩之际,自认“平素管教不严”,并“恳请罚缴银二万两,稍安卞怀”[16]40。嘉庆默许罚银,但是变通了收银说辞:“朕于臣下功罪惟秉公赏罚,其有身获咎愆者,只照例治以应得之罪,从未开罚锾赎过之端。今勒保此奏虽名为自行认罚,仍系欲代伊子乞恩赎罪……所有此次请罚缴银二万两之处著不准行……现在南河兴举要工需费孔繁,勒保为国重臣,谊难漠视,若恳请捐廉助工尚属可行,著准其缴银一万两分作二年,由川省径解南河备用,俟勒保奏请到日降旨加恩赏收,可也。”[16]40勒保岂有又岂敢不乐请“捐廉助工”?其实质是替代英奎完成了捐复。
嘉庆此时虽然顾忌舆论不承认此“捐复”,但是到十六年就不再否认了。“勒保之子英奎亦系此案革职,前因勒保奏请捐复,业已施恩允准。”[17]因此,嘉庆十六年开春,户工二部奏请捐复因王书常案而分别降调的人员,嘉庆降旨曰:“该员等事同一例,亦著格外施恩,俱照所请准其捐复,仍留该衙门行走分别补用。”[17]官员先前的革职降调处分随着捐纳而消逝,捐纳、捐复对吏治以及处分制度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3.皇权治理亦回归到制度治理
案后嘉庆朝出台相关处分条例,使得皇权治理又回归到制度治理。出台私造印信失察处分的更细致规定,为的是遏制此类恶劣案件的一再发生,但是制度规定太过细致,反而脱离实践,不便于官员引用和掌握,久而久之也会因为太过烦琐而失去制度的本意。
如嘉庆十一年,原处分规定:“本官不行查拿降二级调用。失察奸徒私雕假印未经行用者罚俸一年。已经行用者查明在何处行用,将失察行用之地方官降一级调用……若行用后直至告发始行查拿者减为降一级留任,未能拿获者仍降一级调用。”[18]282本条以“查拿”“行用”为重点,主要针对本官失察,在假印行用与不行用情况下的分别处分,对官员予以降调、降留或罚俸,此条已足够用。
但是,嘉庆十七年,又出台更为细致的规定:“本官失察吏役雕造印信……别经发觉始行查拿降一级留任,别经拿获降一级调用。若已经行用,别经发觉始行查拿或自行访拿者俱降二级留任,别经拿获降二级调用。描摹印信于未经行用之先……别经发觉始行查拿罚俸一年,别经拿获降一级留任。若已经行用,别经发觉始行查拿或自行访拿者俱降一级留任,别经拿获降一级调用。至奸徒雕造印信于未经行用之先……别经发觉始行查拿罚俸一年,别经拿获降一级留任。已经行用,别经发觉始行查拿或自行访拿者俱降一级留任,别经拿获降一级调用。描摹印信于未经行用之先……别经发觉始行查拿罚俸九月,别经拿获罚俸一年。若已经行用,别经发觉始行查拿或自行访拿者俱罚俸一年,别经拿获降一级留任。”[18]282此规定不断重申着“别经发觉”“别经拿获”“自行访拿”等说法,以此对官员予以区别处分。
嘉庆十一年的条例重在本官能否主动发现问题,十七年的条例强调监察御史等对官员失职的监督。然而,这种烦琐的例条,其可操作性几乎为零,可见制度在设计时就已出现问题,才会导致皇权的不断调整,而皇权的调整又带来诸多其他的问题。
六、清前中期皇权治理为主的常态化
“约束之,羁縻之,朝廷一二品之大臣,朝见而免冠,夕见而免冠,议处、察议之谕不绝于邸钞。部臣工于综核,吏部之议群臣,都察院之议吏部也,靡月不有。府州县官,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19]155龚自珍的描述反映出有清一代,尤其是前中期,处分制度造成官员处分苛严的事实,除嘉庆朝之外,乾隆朝和道光朝皇权同样对制度治理中出现的问题予以了调整。
1.乾隆朝对官员严苛处分的调整
第一,皇权调整吏议实降实革为虚降虚革。乾隆一朝六十年,乾隆对吏议处分的从宽,曾屡屡点及。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曾指出:“向来外省失查属员至降革者,往往以事属因公,且人材难得,故加恩留任者多。”[20]110三十四年,又指出:“督抚等向来遇有处分,部议应降应革,皆格外宥原从宽予以留任。”[21]46三十五年,指出:“今大员中革职革任屡犯而从宽留任者,不可屈指数。”[21]671到乾隆后期,同样从宽调整。四十年,指出:“向遇吏部议处司道等降调之案,俱量予从宽留任者多。”[22]47四十一年,提到:“朕于督抚等公过处分,应行降革者,概予从宽留任。”[22]492五十一年,旨曰:“近年各省督抚遇有交部议处降革之案,朕因一时乏人,多有从宽留任者。”[23]不论乾隆的顾虑为何,面对制度造成的严苛处分,乾隆的从宽调整确属事实,限于篇幅本文仅以数例为据。如乾隆十六年,江苏按察使后补河南汝光水利道翁藻因失察民间私铸,吏部议处为降级调用,乾隆降旨:“著照部议带所降之级从宽留任。”[24]272十八年,直隶总督方观承因督饬下属通永道王楷治蝗不力,被交部严加议处,吏议照徇庇例议以降三级调用。旨意:“方观承著革职从宽留任。”[24]757二十年,贵州巡抚定长因疏请原任黔西州知州黄秉忠崇祀名宦祠,乾隆认为定长此举系“瞻徇市恩”,将之交部严加议处。吏部议处定长照徇情例降二级调用。得旨:“定长著革职从宽留任。”[25]101三十年,伊犁将军明瑞、阿桂等因办理新疆乌什事务错误,应照例革职。旨曰:“明瑞、阿桂俱著革职从宽留任。”[26]以上数例是大员被处分的实降实革因皇权的介入调整为虚降虚革。
此外,不同处分案中,亦有官员的实降实革处分被从宽为虚降虚革。如乾隆二十一年,河南南汝光道高照因公科敛财物一案,牵连下属知县张权舆等官,吏部以借送财物将这些官员议为“概行革职”,乾隆认为事属“上司勒索”且“被议多员,其中不无才可办事之人”,因而将张权舆等11位知县的革职处分调整为“革职从宽留任,俟八年无过再请开复”[25]433。四十三年,吏部议处失察高朴家人私玉过境各官分别降革。乾隆降旨:“各省地方官于私玉过境漫无稽查,吏部照例议以降革,均属罪所应得……此案系初次发觉,从前类此者自属不少,难于逐一追究。所有议处大小各员其应革任者,著从宽免其革任仍注册。其应革职降调者,著照部议降级俱从宽留任。”[27]又是数十位官员免除实降实革的命运,乾隆对制度严苛处分的调整,亦被官员“视为泛常”[20]110之模式。
第二,以开复制继续调整官员处分。清代处分法规《吏部处分则例》规定严苛,“自罚俸以至革职,各有专条”[28]548,致使官员“处分多而开复不易”[29]。为此,乾隆五十二年专门针对大员留任处分,出台新的开复制度。乾隆对开复背景予以阐释:“向来内外文武大臣遇有应得处分,该部议以降调革职革任,经朕从宽留任及免其革任者甚多,竟有一人而累至十余案者。盖因该大臣等屡经简擢任事有年,朕念人才难得且因其尚系公过,是以每遇议处之案,酌量案情从宽留任者,不一而足。但愈积愈多,未免视为故常,无所警惕转属有名无实,亦非整饬吏治之意也。”[30]170反映了皇权从宽治理的常态化。乾隆遂降旨:“著交吏兵二部,将内而大学士九卿、八旗都统副都统,外而督抚将军、副都统提镇现任各员,部议降调革职革任,经朕从宽留任及免其革任者,查明每人名下所积之案各若干次数,分别开单进呈,候朕详加察核。其案情较重处分数多者,或酌量议罚再准其开复。其情节尚轻处分数少者,或竟予开复……嗣后并著吏兵二部每届五年,即查明具奏一次请旨办理。著为令。”[30]170此令意味着大员留任处分开复的进一步制度化。
随后,吏兵两部查核大臣原案次数开单呈览,乾隆详加查核后裁定:“在京大臣内如喀宁阿、穆精阿所得降革处分俱已积至七案,姜晟积至九案,处分数多。喀宁阿、穆精阿著将任内应得廉俸分例各罚出二年。姜晟已任湖北巡抚……仍著将侍郎任内应得廉俸分例罚出二年。所有喀宁阿、穆精阿、姜晟从前降革处分,俱准其开复。至各省督抚处分积至六案以上至十案者八人。内如尚书德保、侍郎李封所得降革处分多系从前在巡抚任内之事,德保、李封俱著罚出巡抚养廉二年。刘峨、李世杰、孙士毅、闵鹗元、毕沅俱著照本任罚出督抚养廉二年……雅德现以副都统衔在喀什噶尔办事,所得处分俱在从前督抚任内者,著罚出总督养廉二年。所有德保、刘峨、李世杰、孙士毅、雅德、闵鹗元、毕沅、李封从前降革处分既已议罚,俱著准其开复。”[30]200-201乾隆五十二年的这次制度调整治理再次反映出处分制度的严苛,皇帝不得已出台新的制度予以解决。
2.道光朝对官员处分的调整
第一,道光帝将部议实降实革处分调整为从宽处理。道光五年(1825年),两江总督魏元煜等因漕务办理失当,吏部将之议以降调。道光降旨:“魏元煜、严烺经朕屡次饬谕,均未能筹办妥协,即照部议降调亦属咎有应得。姑念魏元煜甫经简授两江总督,到任未久。严烺职司河务,此次漕运迟延,非尽关河工办理未妥,尚可少从末减。”因此将二人处分调整为留任:“魏元煜著加恩改为降四级从宽留任,严烺著加恩改为降三级从宽留任。”[31]335道光七年,因战事问题处理不妥,长龄等被部议革职。道光又予以从宽:“长龄等办理不善咎无可辞,本应照部议革职,姑念道路辽远,一时难以更换,长龄、杨遇春、杨芳、武隆阿俱著从宽改为革职留任。”[31]1066
以上都是个别性的,还有群体性的。如道光十三年,户部捐纳房贴写蔡绳祖等私办假照一案,各部司员因“毫无觉察漫不经心”,有被革职永不叙用的,有被降调停其升转的。若干年后,道光又予以从宽处理,“本属咎所应得,姑念事隔数年,人数众多,此中不乏人材,若概予废弃尚觉可惜,因令将降革各员开单呈览”。最终,将“奉天府府尹乌尔恭额著加恩开复顶戴;原任翰林院修撰朱昌颐著加恩准其捐复主事;其革职之陆以烜等五员,降四级调用之呈麟一员,升三级调用之李韫英等三员,降二级调用之重谦等三十七员,降一级调用之恒景等十四员,国子监降一级调用之荣第等二员,降一级留任之瑞庆一员,俱著加恩准其捐复,补缺后并准其一体升转”[32]。从而将此前规定永不叙用的、停其升转的官员,以捐复的形式予以从宽。
道光十九年,济克默特参奏紫禁城内值班之王大臣公永康、内大臣常喜、文职全庆、武职常恒、散秩大臣侯张淳,庆郡王奕彩、侍郎溥治、副都统连贵、内大臣肃亲王敬敏、散秩大臣书桂,于出班进班之际,“不遵定例,任意迟早”,道光降旨将所涉王大臣等交各该衙门分别严议议处。各衙门根据道光初步定性,议“请将该王大臣等爵、职,一并斥革”。道光对于各衙门的严议处分,认为“实属各所应得”。但笔锋一转,“惟念年岁久远,积习相沿,恐以前旷班者尚不止此数人。若但将永康等惩治,转不足以昭平允,姑从宽免其斥革予以薄惩”。在此理念下,定议:“永康著罚公俸六年;觉罗常喜著革去副将统并一切差使,仍罚世职俸四年;张淳著革去散秩大臣,仍罚侯俸四年;庆郡王奕彩著退出内廷行走,仍罚王俸六年;肃亲王敬敏著革去宗令、内大臣,仍罚王俸六年;书桂著革去散秩大臣,仍罚侯俸四年。常恒、全庆、溥治、连贵、中山俱著降二级调用;济克默特著加恩改为降四级留任不准抵销。”[33]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诸王大臣的处分,保留了其爵位和一定职位。
第二,更改法规与条例以调整制度处分的严苛。“有清一代,二百数十年间,各部署无虑数十,各有则例,即各有处分。”[34]68“处分则例之设,最为严厉,一切惩戒以此为准则……而吏部每拘泥成例,轻重倒置,以致处分失平者日多。”[34]70-71王钟翰阐明了以则例为主的制度规定,也会导致“处分”的种种“失平”。道咸时期大员胡林翼亦曾言:“大清律易遵,例难尽悉;刑律易悉,吏部处分律难尽悉,此不过专为吏部生财耳,于实政无丝毫之益。”[35]提及了制度治理的弊端所在亦有“于实政”无益之处。贺长龄也曾指出处分制度带来的深层危害,“今则科条繁多,惟簿书期会之为急,少有龃龉,即干吏议,虽有愿治之心不能自行其意,亦莫不苟且其心思,为自全之计”[28]400。鉴于此,道光朝对处分制度进行了两个调整。
首先,道光四年,全面从宽处理《吏部处分则例》中之例条。道光继位后,吏部尚书那彦成奏请续修《吏部处分则例》,于道光四年完成,是对当时处分制度之具体调整。此次重修意见始于军机大臣曹振镛于嘉庆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所上条陈,奏“为军机大臣会同六部堂官议覆整饬部务条陈事”,其意大致为:“今欲去其弊,必须删节例案,以数条并一条,去其烦碎而存其大旨。至删减例条,吏兵二部删减无多,今条陈内复以删节例条为请……量宽公罪,实为救弊之急务。应请于吏兵两部处分则例内各条下,皆注明公罪私罪字样,除私罪毋庸置议外,其公罪有至降调、革职者逐条细核,非实事关重大者酌改从宽,由吏部兵部将公罪内共存降调、革职处分若干条,其中情节较轻应改降留革留之处悉心核办,陆续奏明请旨。其造册舛错迟延等处分,应列明何项册籍,非实有关系不可少者,即应裁撤。其余繁文以此类推。”[36]曹振镛提出具体修订意见,意在“从宽”。道光阅后接受,郑重颁布上谕:
军机大臣六部议覆整饬部务条陈一折,所议甚是。六部律令务在持其大纲,则政清而易理……部中多立科条,州县无日不奉行具文,转荒其教养本务,于事何益。而公罪繁多,贤吏或因此废黜,不肖者巧于规避,部书得以舞文纳贿,皆由于此。嘉庆十八年曾敕吏兵二部删减处分例条,该部未能实力遵行。又谕题调要缺,不计因公处分,而该部续议章程仍复牵混。殊不知公罪从严,则中材以下之官益多巧避。严其经征处分则多垫欠,而那新掩旧即成亏空。严其承缉处分则多讳盗,而纵恶养奸转贻大患。故曰:徒法不能以自行。著吏兵二部各将处分则例悉心确核,于各条下皆注明公罪私罪字样。其公罪有至降调革职,非事关重大者酌改从宽。各部烦苛无当处分例文,互商裁汰,务归简明。其公罪处分,除盗案及正项钱粮停升外,余皆不碍推升。至题调要缺,则一切因公处分皆无庸计算,各纂成例册呈览。[37]
道光基本采纳军机诸臣之意,这份上谕给重修处分则例定了基调,即从制度上彻底放宽因公处分,避免制度严苛再度造成处分的加重。有宗人府府丞毛式郇曾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奏为军机大臣等率议将吏兵二部则例改重就轻罔顾废弛致流弊事”一折,驳斥军机大臣的此种提议,“今军机大臣等忽又持宽减之议,于京外文武各官诚为甚便,但恐便于官,而不便于国,不便于民,此实不可不虑”[38]。从侧面反映出道光四年所修之处分则例,是制度治理的由严苛转为从宽。道光皇帝如此关注与调节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官员实际处分。道光朝后期皇帝的直接改实为虚大为减少,就有这一原因在内,这是皇权治理的深度体现。
其次,道光十年,废除定期修纂处分则例之制。处分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因时代的局限有偏颇不适之处,因此它也是一项需要不断完善与时俱进的制度。有清一代,曾规定,各部则例是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然而,道光十年,御史王玮庆就则例修纂的时限予以上奏,从而改变了这一历史的修纂传统。道光十年二月初六日,朝廷有旨:
御史王玮庆奏六部重修则例,宜率由旧章,如有更改,应专折奏明通行一折。各衙门颁行律令,原期垂诸久远,其有今昔异宜者,固应随时酌改,然不必定限十年,即开馆重修一次。若如该御史所称各部则例十年一修,往往不能依限告成,每迟至六七年始刊刻完竣。又未能及时颁发,其间数年之久,各省官员既无新例可遵。又谓旧例已改,茫无所措,而书吏得以高下其手。及至刊改颁行将届,则例重修之时,新例又成废本,无所遵循……嗣后各部已颁成例无得轻易更张,如有因时制宜,必应更正之处随时专折奏明改定,立即通行各省一体遵照,以免书吏影射弊混,不必定限十年开馆重修,致滋流弊。[39]
这份谕旨意味着定期修例之制由此取消,作为则例之一的处分则例,其修纂由此也变得减少,这也是我们看到清后期所修处分则例不多之原因。修纂次数的减少,版本的减少,从客观上对严苛的处分制度予以了调整。
余 论
以王书常案为例,处分的环节包括三个方面,处分的最初交议、吏部的具体议处、皇帝的最后定议。三个环节中,属于制度层面的只有中间环节,属于以皇帝为代表的皇权治理调整的有首尾两个环节。可以说,官员处分始终处于皇权的控制之下,皇权治理要远远凌驾于制度之上。嘉庆朝对案中官员处分的这种处理模式,不独只存在于嘉庆朝,乾隆朝和道光朝同样存在,反映出至少在清中期这种处理模式的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