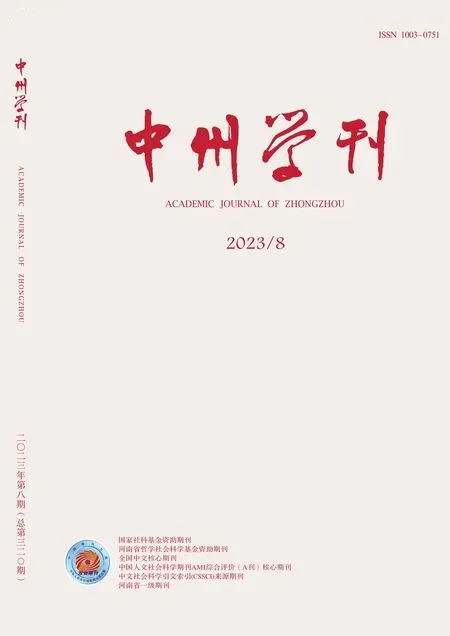大众文化视域下的海派话剧图景
尹 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海派话剧①即使以今天眼光来看,其繁荣景象也是异常耀眼的。它以市民性的彰显与解放区、大后方话剧区别开来,在百年话剧发展史上留下了市民图景的印痕。以海派话剧和大众文化的关系作为文学史研究的线索,通过对20世纪上海市民文化的回眸,重新思考一些文学史问题,不仅可以加深人们对海派话剧的了解,而且可以强化话剧史中一些被人忽视的因素。如海派话剧隐含着怎样的文学经验,传递着怎样的大众文化生产信息,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这一文化奇观,所有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一、海派话剧生产的大众文化语境
海派话剧和海派小说、海派散文一道组成了海派文学的大致图景,呈现出媒介、市场合力下的大众文化景观。长期以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被认为是“小市民”文艺。如茅盾曾言:“一种是完全按照个人的趣味而采集些都市生活的小镜头,编成故事,既无主题的积极意义,亦无明确的内容。这种纯粹以趣味为中心的作品,显然是对小市民的趣味投降,而失去了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众的基本立场。”[1]此言论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左翼对这一时期上海市民文学的态度,凸现了对市民文学的排斥,影响可谓深远。而实际上,海派文学的多重面相被遮蔽了,从大众文化、都市文学等生产环境加以观照,可以逐渐看清海派话剧的真实面貌。
大众文化是和现代都市相生相伴的现象,在本质上也属于都市文化。话剧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里移植成功,绝非偶然。从开埠直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现代化都市发展成型,“成为了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工商业中心,积累了成为现代型商业消费城市的物质基础”[2]。以商业消费取向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兴起,为娱乐业的繁盛提供了土壤。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的商业消费日渐兴盛,大新公司和中国银行大楼于同年落成,百老汇大厦与号称“远东第一楼”的24层四行储蓄会大楼开始屹立在外滩和南京路上。1933年革新后的“大光明”开张,配备美国RCA实音式有声放映机和空调设施,有1900个沙发软座,其豪华魅力首屈一指。“跳舞场以1932年开办的百乐门为代表,地处静安寺,有远东第一乐府的美称。”[3]此外,还有跑狗场、回力球场、现代剧院等现代娱乐场所的兴建,以及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馆、公园、动物园、植物园等文化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话剧作为现代社会的文化娱乐形式,正是在上海都市的土壤中滋生和成长起来的。
“市场经济、技术文明、全球时代造就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口味,即公共的审美追求、文化趣味。”[4]市场经济是大众文化兴起的前提,话剧的发展自然离不开成熟的话剧市场。沪上的话剧为何迟迟走不进一般市民阶层呢?主要因为话剧市场薄弱,成熟比较晚。1936年,《雷雨》在卡尔登剧院上演成功,标志着中上层市民观众对话剧的接受(愿意买票进剧场观看)。话剧最初作为文明思想的代名词由外国引进过来,但其只说不唱不舞的表演方式不符合中国大众观戏的习惯,以至于在“文明戏”阶段需要以加唱加舞的方式来吸引市民。为了吸引更多市民走进剧场,话剧历经了多次改良,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化的尝试。文明戏、新剧、白话新剧、改良新剧、男女新剧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名字变化,实则折射出话剧的荣辱兴衰。此外,编演剧人才的缺乏,也制约着话剧艺术的发展,使得文明戏不得不频频向传统戏剧求援,但一味追求通俗甚至低俗无法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而像春柳社那样追求话剧的纯粹的做法,终不免在风雨飘摇中宣告失败。但这些做法都不失为话剧市场化进程中的有益探索。
历经起伏变迁的海派话剧在商业大潮中逐渐完善自身的生产体制,到1941年前后,在人才、资金、场地、制度等方面都有了基本保障。“大约从1941年起,‘演剧职业化’运动在上海和大后方同时开花结果,四五年间先后有20多个职业剧团问世。剧本创作、舞台艺术、演剧活动持续高涨,达到空前的活跃与协调。”[5]这一时期,除了姚克、顾仲彝等一批剧作家留沪之外,众多话剧专门人才积聚于上海,为海派话剧的长足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话剧演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一批有着较高学识水平的导演,如黄佐临、吴仭之、胡导等,为观众奉献了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市民作品。上海话剧演员基本上都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相当一部分是经过招考成为职业话剧演员的。剧坛繁荣背后还有大资本的投入,这是沦陷时期特殊形势下的经济行为。评论称一批“有投资眼光的‘后台老板’们,认定这事业在现阶段有抬头发展的机会,而且说不定会和电影事业争一日之短长,所以纷纷投资,向话剧新市场发展”②。此外,版权意识的增强、演出税等制度的形成,亦保证了话剧的良好从业环境。从报刊新闻史料可以看到,20世纪40年代,上海经常演出话剧的剧场已有“卡尔登、金都、巴黎、金城、兰心、美华、绿宝、丽华等八家”③。
报纸、杂志和书籍见证了海派话剧的繁盛景象,形成一道独特的媒介景观。虽然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多样的新媒介,但笔者能查阅到的涉及话剧的大众报刊不下百种。其中既有专业刊物《戏剧杂志》《剧艺》《话剧界》《舞台艺术》,也有具有影响力的报刊如《申报》《万象》《半月影剧》《大众影讯》《良友》《杂志》《天下》,还包括众多的都市小报如《社会日报》《力报》《海报》《大上海报》《平报》《中国艺坛日报》《娱乐》《铁报》等。市民阶层的兴起为话剧接受传播群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评剧者往往是话剧爱好者、报刊编辑,或是话剧活动的实践者,多重身份使得他们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践融入媒介传播活动中,产生消息、报道、演出手记、广告、座谈会纪要等各种形式的剧评。一般认为,大众文化“是工业化的——其商品的生产与销售,通过受利润驱动的产业进行,而该产业只遵从自身的经济利益”[6]28。海派话剧利用大众传媒牢牢地把握住观众的审美趣味,商业化的功利性的文学观念要求它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消费者趣味为目标。正是现代大众传媒的参与,使海派话剧实现文化、艺术与商业消费的合流,发展成为批量化、商品化和标准化的娱乐消费品。
为了吸引观众,每个剧团也都格外注重宣传效应。他们经常会在话剧首演前夕组织招待会,邀请新闻界人士参加,充分运用媒介的力量来宣传剧目。海派话剧的宣传花招多种多样、层出不穷,当时常见的话剧宣传刊物即“演出特刊”。各剧场频频推出“演出特刊”,刊印内容除了应有的本事与演员表外,还可载入编剧人的意见、导演的自白、演员演技的研究,以及一切有关剧目的各项问题。这如同今日大片上映之前的宣传花絮,将作品的亮点优势集中展现。另外,还有“剧透”预告类报道、话剧内幕和演出花絮、演出广告、明星选举的新闻等娱乐化的宣传方式,像有些剧团的“道歉声明”被评论界认为是广告手段。费穆导演《梅花梦》时,报上刊登了原作者谭正璧保留著者权利的抗议广告,这被人看穿了把戏:其实这是上艺的宣传手法④。话剧在报刊的推动下,表现为一种社会化、媒介化的文化生产形态。如果忽略话剧的传播途径和方式,忽略报刊印刷媒介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就无法真正认识市民文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无法触摸到话剧发展的生动脉络。
二、海派话剧的大众文化特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通常被认为“彻底摆脱了传统贵族社会的文化认同,自寻目标地发展起独自的近乎当时世界标准的大众文化”[7]。这和今天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的定义不谋而合: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8]。海派话剧以明星制、打对台、流行风、娱乐化等表征书写了大众文化的众声喧哗。
高额的演剧报酬使得一批话剧明星应运而生,成为大众文化的象征。中国旅行剧团的唐若青实行“包销前十排”⑤的做法,李绮年在绿宝上演《潘金莲》,实行每座抽一元的办法,花样不一而足。主角与明星制相连,这是商业化演剧的必由之路。每个剧团都会注重用明星的公众影响力提高产品的号召力,分级别的演剧报酬制度也在客观上具有“造星”的效用。报刊是现代上海明星文化滋生的温床,通过媒体的大肆宣传,孙景路、上官云珠、沈敏、石挥、陆露明等明星成为公众追捧的对象。明星的演艺活动、兴趣爱好甚至饮食起居都成了大众关注的热点。如《拉角风潮》一文曾言:“乔奇的退出‘上艺’加入‘光明’,也是拉角家乘他和石挥闹意见的当儿,从中拉拢所得。石挥似乎已成了‘红伶’,更多的拉角家企图重金礼聘。”⑥关于明星的各种消息和流言成为都市里最有声有色的风景。通俗期刊里各种夸张性的批评与褒奖共存,它所带来的休闲趣味是单纯阅读纯文学评论很难体会到的。媒体在诸如此类的报道中扮演了“捧角”“造星”的角色,将演员、明星以更加立体生动的形象展露出来,满足了社会大众以明星为谈资的窥视欲。为了扩大影戏、吸引观众,各剧团还会在剧本的分量或名演员、名导演的号召力等方面与竞争对手形成“对垒”之势,评论界将此类现象称为“打对台”。1942年12月24日卡尔登推出《秋海棠》之时,艺光剧团公演《甜姐儿》(魏于潜编剧,胡导导演),中中剧团上演叫座戏《欲魔》,由话剧卖座明星孙景路主演。三部作品制作阵容强大,各有所长,由此可见当时剧坛竞争的激烈态势。海派话剧努力将观众视为上帝,在追逐时代潮流的同时,亦能变换不同的风格适应观众多变的口味。
海派话剧具有释放都市生活快节奏的功能,将娱乐的消遣休憩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符合大众文化的本质属性:“偏重感性愉悦,它不以提供对世界的理性反思为目的,而主要倾向于创造娱乐大众的文化形式,达到‘捕获’大量受众、获取商业利润的目的。”[9]因此,感性层面上的快乐成为大众文化的运作核心。海派话剧中,夸张性的闹剧如《八仙过海》旨在给人们带来放松和愉悦,《梁上君子》在演出时,观众始终不停地开怀大笑。外国改编作品则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异域风情,适应了上海观众追新逐异的欣赏需求。才子佳人之类的民间题材剧目,则赚足了旧式观众的眼泪。历史剧如《杨贵妃》布景壮观华丽,配以古典优雅的音乐,使得观众沉浸在缠绵悱恻的帝妃恋里。《倾城之恋》《清宫怨》等表现爱恨情感的剧作,满足了观众追求热闹好看的心理需求。悬疑破案剧如《天罗地网》也是百姓爱看的一类剧作,破案的趣味性很能吸引民众的好奇心。20世纪40年代,在国破家碎的沦陷区上海,话剧工作者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愁米愁煤愁得太苦”的上海人带来了笑声,使他们在对娱乐的追求中使生命紧张之后的倦怠与失落得到暂时的放松和弥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海派话剧为观众打造出一个特殊的文化领域,发挥了建立民族认同、慰藉精神的巨大能量。
由市民观众和都市媒介共同参与形成的潮流风是海派话剧的另一表征。“潮流风”即某个剧目的卖座会引发此类作品的流行。1942年上半年恋爱剧《香笺泪》《茶花女》《水仙花》《红楼梦》《花花世界》走红沪上,随着年底《秋海棠》的轰动演出,现代通俗派剧作争相出炉;1943年古装戏流行一时,7月《武则天》开启风气,8月《杨贵妃》《清宫怨》紧随其后,《香妃》《钗头凤》《浮生六记》《李香君》等持续上演到岁尾;《潘金莲》的上演引起一波民间剧的热潮,《梁山伯与祝英台》紧随其后;到了1944年,闹剧又成了上海剧坛一条主要的线路⑦。潮流风的形成标志着话剧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这是之前的话剧所不具有的。
海派话剧、左翼话剧以及电影、戏剧、通俗小说在媒介营造的公共空间互相影响。在世俗大众中占主流的市民剧评,以大众趣味的培养和满足为基本导向,以鲜明的商业娱乐性凸显市民观众的审美趣味。市民剧评之外的左翼剧评、自由派剧评,以坚守政治立场和艺术性为主要特征。但无一例外,它们也都处于大众文化的浸染之中,并且相互影响、彼此促进。市场化在推动左翼话剧扩张观众市场、促进演剧职业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商业竞争在促进剧团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精英思想的引领能有效避免话剧误入过度商业化的泥淖。左翼剧评提出话剧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服务的目标,阿英的《碧血花》、于伶的《大明英烈传》等将抗战与民主的现实要求寓含其中,对剧坛商业化起到了一定的纠偏、制衡作用。此外,“反映现实的程度和是否有利于改进人生理应成为评价作品艺术的标准”⑧之类的言论,对于防止话剧低俗化也有着积极的意义。各种流派的文学观念在话剧里交汇融合,带来话剧现代意义的演变和审美艺术的革新。
三、大众文化对于话剧审美经验的特殊开发
海派话剧以民间性的坚守开辟了广阔的演剧市场,逐步赢得了市民大众的喜爱。传统文化不会创建大众文化,但却是大众文化发展的土壤。“通俗性到了现代,常常要由民间文学与旧文学这样两方面来输送营养。”[10]作为都市文化日常生活的参与者,世俗大众为自己发声,从某个程度而言,这确实翻转了传统主流社会“由上而下”的规训文化。而民众发声最常用的工具就是民间文化,经过改良创新的民间戏剧或者小说与话剧实现了有机结合,在戏剧形象的塑造、戏剧冲突的营造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功效。直到1944年的话剧舞台上,还有传统戏曲改编剧《春阿氏》。至于20世纪30年代的舞台上,《赵五娘》《珍珠塔》《玉堂春》等剧目就更为常见了。名剧《秋海棠》更是离不开京戏的功劳。话剧导演费穆跟周信芳、梅兰芳都是很好的朋友,石挥为演好名伶“秋海棠”,专门拜访黄桂秋、梅兰芳、程砚秋等演员[11]12。
大众文化对于民间传统文化加以改良创造,使其更为现代化、更富于美感。如《秋海棠》开头和结尾以“戏中戏”的手法将京戏《苏三起解》穿插到话剧舞台上,这成为该剧的最大看点。深受海派京戏影响的导演、演员亦将戏曲的唱念做打手法运用到话剧中。胡导在《陈圆圆》中出演算命先生时,运用“老鼠胡须、弯腰驼背”[11]8等京剧丑角的表现手法,强化了人物的喜剧效果。
传统戏曲、通俗小说在与话剧的交融中,创造出了独特的艺术美感。话剧中的“伶人戏”可以看作青楼文学的延续,但表现范围已从妓女扩展到了歌舞明星、舞女、京戏名角儿,由此联结起娱乐业、商界、家庭之间的情感利益纠葛。这不仅投合了市民喜好明星的独特心理,而且使剧作的主旨指向对艺术从业者的同情,以人物最终难逃灭亡的悲剧命运控诉社会。由此可见,海派话剧内容社会涉及面之广、批判性之深刻,显然不是以往的通俗小说所能达到的。
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出现了历史剧演出热潮,《文天祥》《明末遗恨》《岳飞》《葛嫩娘》《杨娥传》等剧传达了上海市民的爱国情绪和民族气节,隐晦曲折地表达了抗议外族侵略的心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大众文化理解为“通过对霸权力量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抵抗,而在社会的意义上运作”[6]68。一方面,历史改编剧的盛行适应了大众喜爱谈古论今的心态;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环境下,尤其是孤岛时期,直接谈论抗战是不行的,历史剧搬出古代衣冠较易避开当局检查。因此,这种历史改编剧是对时代主题回应的爱国剧,剧场成为观众曲折表达爱国情怀的特殊空间,亡国之痛和爱国情怀在观剧过程中得以释放和表露。面对日本侵略者入侵、国土分裂的现实,民众对统一国家的期盼与想象不只包含在对历史传奇的向往中,更是通过历史剧对“中国文化”的强调,表达对侵略者反抗的心声。这样,历史被赋予了舒缓焦虑、抒发民族大义的拯救性意义。无论是英雄传奇人物剧目《文天祥》《李香君》,还是传唱至今的爱情剧目《杨贵妃》《梁山伯与祝英台》,都被涂抹上了“精神性家园”的虚化色彩。李香君、葛嫩娘更是成为抗战历史剧中经常出现的主角,她们都具有聪明果敢、率真纯情、蔑视权贵的性格特征,以及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不惜献身的崇高精神。
家国情怀历来是民间文化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在这一点上,海派话剧和当时进步的左翼话剧是相通的。“大众文化的政治是日常生活的政治。这意味着大众文化在微观政治的层面,而非宏观政治的层面,进行运作,而且它是循序渐进式的,而非激进式的”[6]68,但却是“日复一日与不平等权力关系所进行的协商”[6]68。海派话剧在写实和想象交织中构建的家国形象,不断激荡、影响着市民的爱国情怀,在异族统治的孤岛这一特殊的环境下,这不啻一剂殖民地子民心灵疗伤的良药。民间爱国热情裹挟着反抗侵略的快感,使得历史剧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一种重要力量。
海派话剧对民间文学的创新式传承体现了改良的功用。改良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生产方式,贯穿海派话剧的发展历程。话剧能够克服传入初期的“水土不服”而在中国大地上生存下来,归功于不断的改良。改良使其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不断调适,兼容并蓄,有了不断更新、持续精进的机会。无论是话剧初期与通俗小说和传统戏曲的联姻,还是电影兴起后大量电影改编剧的出现,都体现了话剧向传统和创新双面出击的能力——改良。在改编外来剧时,海派话剧十分注意题材的择取。黄宗英主演的《甜姐儿》等“流线型喜剧”成为首选,因为与悲剧相比,喜剧能够减少审美距离带给观众的陌生感。顾仲彝改编《简爱》时,特意将剧名改为《水仙花》,故事中的地名和人名也都进行中国化处理,这些本土化的改编方式使得外国剧作逐渐收获了更多的中国观众。
改良还包括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互动交流。话剧和电影、京戏、越剧等艺术形式之间的改编比比皆是,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曾演过朱端钧导演的《雷雨》里的一场戏[11]87。在海派话剧中,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开放交流异常活跃,这固然离不开商业利益的驱使,但较为成熟的、市场化的演出环境更是基本保证。话剧在20世纪40年代兴盛时期,夏佩珍、宣景琳、王雪朋、白虹、顾梦鹤等人都曾登上话剧舞台。1941年,天风剧团在推出姚克编剧的《清宫怨》时,邀电影明星舒适参演,增加不少票房。费穆创造性地把电影手法引入话剧舞台艺术,使话剧的场面调度更具视觉冲击力。如《浮生六记》最后一场,芸娘说完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春天不远了”之后,病榻后面的绿幔掀起,露出窗外暮春三月的景象⑨,这种画面切入的手法显然来自电影。
海派话剧在不断的改良中汲取各种艺术的精华,在上海话剧舞台上始终占据重要一席。在与左翼话剧共存的时代,左翼注重社会意义与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塑造等艺术特性在海派话剧里都有体现。海派话剧曾演出左翼剧作《龙凤花烛》(改编自《一年间》)。海派话剧的经营者深谙人们的观剧心理,通过改良使不同流派风格的剧目适应观众多样的欣赏口味。在成熟的话剧市场上,呈现的是雅俗结合、新旧交融、中西结合的图景。各流派的互动共生不仅促使精英文化、意识形态文化成为市民大众文化的构成要素,而且使大众文化的品位获得空前的提高。话剧艺术在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交流中不断提升,呈现出市场与审美、政治与商业、抗战与娱乐之间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海派话剧注重变换风格保持演剧的“新鲜感”,悲剧和喜剧、古装戏和现代剧、闹剧和抒情剧、改编剧和国产剧等各种名目的剧目次第上演。这种做法适应了观众不同欣赏心理的需求,是趋新求变的市民品性使然。
海派话剧参与建构了城市生活的公众休闲与流行风尚,这是大众文化在都市日常生活层面的显现。演剧及观剧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的一种方式,话剧中现代生活理念传输渗透也变得无处不在。在海派话剧中,推崇物质文明、多元生活方式的现代思想理念和价值立场,多以旅游、出国留学、蜜月旅行等现代生活方式加以展现。而其中诸如女性意识的觉醒、新型家庭关系等也成为引领现代都市生活的重要面向。各种刊登在戏剧专业期刊、休闲杂志、都市小报上的剧评不拘一格、蔚为大观。观众体验都市的欢乐喧哗和悲欢离合,借助现代媒体发声评戏,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种流行风尚,话剧由此成为大众文化蔓延至整个都市生活中的重要艺术形式。
“受众同文化工业一起,成为大众文化的共同创造者。”[12]有剧作者和演员以及观众的参与,才能成就作为观演艺术的话剧。观众推动着话剧前行,话剧影响大众生活,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建构。受市民关注的影星也会被写进剧本,以拉近剧作与观众的距离。《春闺风月》里,编剧王兆墀加进了许多现代生活的例子,“例如二加二等于五,杨梅冰淇淋,桃拉塞拉摩之类”⑩,桃拉塞拉摩即为当时的国际影星。话剧剧场作为传输新型价值的空间,折射了人们对于都市、现代生活的理解与想象。
结 语
对于海派话剧的大众文化生产,我们不仅要看到其商业化、娱乐化的特征,更要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学的大环境来看待。“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基调是乡村,城市文学不能算作主流,都市文学往往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如果我们将观察话剧的目光从传统的立场转向“市民观众”的角度,也许会有新的发现。以大众文化、市民文化的视角考察海派话剧,揭示商业、都市对文学的渗透以及都市文学呈现的特色,可以为话剧史发展经验提供有益的补充。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透视多元、立体的都市文学景观,而且能够发现市民通俗文学、现代文学史的多重脉络。对于文学和商业的关系,我们不能像以往那样,简单地划分阵营,下个对错结论,而是要结合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从文学自身的生存环境,来理解文化市场、大众媒介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学生产场域对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除了海派话剧,海派小说、海派散文、都市期刊也都是大众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它们与此前、此后文学史上的作品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海派话剧对于当今剧坛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也正在于此。
注释
①这里所说的“海派话剧”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产生的带有商业性的、以市民观念为主的通俗大众剧。“海派话剧”的说法由来已久,最常见的理解是泛指在上海演出的所有海味话剧,包括当今正在上海演出的海味话剧。这成了一个包括现、当代文学在内的现象。而实际上,先厘清现代文学中的“海派话剧”,然后再用历史的眼光来打量今日上海话剧的情况,才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态度。详情可参看尹诗的文章《文明戏改良和海派话剧的产生》与《1940年代海派话剧的璀璨绽放》,分别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1期、第12期。②⑥参见雷诺:《剧坛秘话》,《太平洋周报》1943年第55期。③参见慧星、王林:《剧坛崩溃的秘密:蓬勃也,衰落也》,《剧艺》1944年9月4日第4期。④参见重逢:《费穆的梅花梦》,《太平洋周报》1942年第1卷第23期。⑤参见洛西:《上海各剧团经营内幕》,《太平洋周报》1942年第1卷第44期。⑦参见《申报》1942—1944年的部分话剧广告。⑧参见万里浪:《剧评及其他》,《剧艺》1944年第1卷第2期。⑨参见王希尧:《浮生六记观感》,《太平》1943年第2卷第12期。⑩参见春理:《观“春闺风月”》,《中华周报》1943年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