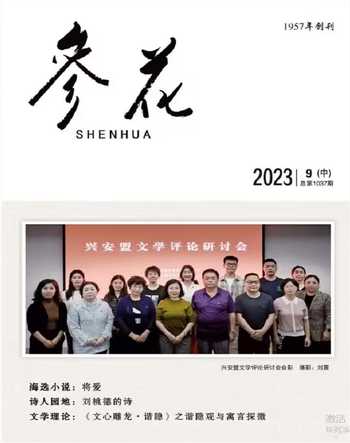九歌散文:新乡土文学的书写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的生活离不开泥土,我们民族的历史是从土里面长出来的。以农业谋生的人依赖土地,乡村的人附着在土地上。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其后,诸多作家用带有现代理性色彩的笔触,描摹了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乡村文化和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以揭示古老的乡村文明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人们对于乡村静谧美好的痛惜,以及对乡村根深蒂固的落后思想的惶惑与哀愁,并对其进行现实性的批判和文化反思。
自二十世纪末,中国乡土文学进入了特殊的文化生存背景,这给乡土文学的创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商业文明和都市文明的崛起,大量消费文学充斥市场,乡土文学也逐渐处于边缘地位。于是,越来越多的作者对乡土文明进行反思,不再凭吊乡土文明的历史,而是将视角聚焦于当下,形成了新乡土文学的书写方式。在新乡土文学的创作中,尤以小说为体裁的作品层出不穷,散文作品却始终寥寥可数。在九歌的散文作品中,我感受到了乡土文学的“变”与“不变”,看到了乡间人的“定居”与“迁徙”。本文择取九歌散文诸篇,作为乡土世界的切入点,溯至当代新乡土文学的创作源泉。
一、乡土文学的“变”与“不变”
长期以来,中国乡土叙事大多数都以描写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变迁以及乡土社会结构演变规律为核心,作品更多追求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史诗性的品格,当然,也有少数作家关注民间小人物的品质以及命运。但归根结底,无非是作为乡土社会历史演变规律的一种例证或附庸,丧失了其成为独立审美对象的权力,也鲜有特殊个体意识的流露。
当下,乡土文学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变,这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同构的。所以,面对高速发展的中国,如何讲述关于“新乡土”的故事,关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乡土文学”的发展趋势,便成为学界探讨“新乡土书写”的基点。
九歌在散文创作上另辟蹊径,将视角从旁观的时代旋律中抽离出来,聚焦于“沉浸式”的乡村书写,对乡村生活进行细腻刻画,呈现出带有华北平原地方性的文化传统:
“三伯家的大哥是小队会计,背着三伯用绳子丈地,三伯见了就骂:‘没记性的东西,没告诉你吗?还用绳子打。地跟人一样,上绳子没了性子,粮食打不出数……”
——节选自《母亲的哲学》
“暮色降临了,村子里的喧闹声渐渐消歇远去,我和舅舅乘月色坐在垄台上。我一边看舅舅慢慢悠悠地吸烟,一边听蛙喊虫嚷,湿漉漉的田园空气洇湿了我的身心。”
“赶上月亏星明之夜,我和舅舅就早早地走进菜园子的窝棚,躲在板铺上,目光越过矮矮的柴门,对着神秘莫测的满天星斗久久凝视。
“夜深了。菜园子里万籁俱静,我也于静谧之中悄悄地溜向了无忧无虑的梦乡……”
——节选自《遥远的乡村》
语言风格上的成熟老练以及细微的捕捉使其文章简洁质朴、自然浑成。其文章特质兼具节奏感、旋律美和素朴的意蕴。这都与其创作中的地域性的语言特色,以及巧妙穿插的具象化语言密不可分。同时,正是這种正向的、微观的聚焦,使北方农村原生态生活的面貌跃然纸上,琐碎而不失真切的艺术表达,不啻新乡土书写上的一种全新探索。
二、乡间人的“定居”与“迁徙”
在乡土文学的叙事中,通常都是以“离乡”和“返乡”的书写形式交汇着乡村与时代更迭中乡间人新的生活状态与人生目标。以往绝大多数作家的乡土经验已经无法继续建构日常乡土生活的经验主体,在他们不断返乡观察和思考新时代乡村变迁的过程中,某种程度上也与“乡村现实”存在一定的片断性。
在《洗澡》(2017年发表于《海外文摘》9期)中,便是以“离乡”为基点,回溯作者年少时在乡间生活的点点滴滴。但作者在处理上似乎更加周全,先以和母亲的一些生活作为切口,使文章始终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同时加深了乡村现实生活的体验感。而在《母亲的哲学》第三、四节中,则是以“返乡”为肇始,引出华山诸葛所赠的手杖和母亲的“哲学”。文章中说:“我坐在他面前的矮凳上,问了几个问题,老者一一作答,滴水不漏。掏卦钱,老者执意不要,回身将一手杖递给我说:‘此杖可扶三代,带回去吧。我坚持给钱,只收了十元。回到家,我把华山诸葛的手杖孝敬了母亲,平时母亲扶它走路,忙时用它撵鸡烧火。”
相较于“离乡”,“返乡”在一定程度上因中华文化的乡土情怀,更能引发读者的共鸣,所以九歌在对于“返乡”的描写上一笔带过,笔墨更多用以引导如何在现代文明和固有传统中寻求一个契合点,进而葆有乡间人生活中个体意识的主体性,重新找回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
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曾提道:“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深思。”在下文中,或许我们更能找到作为土生土长在这片土地的劳动人民人生的“哲学”,那便是在这乡土之上砥砺出的智慧,充溢着静水流深的不朽光芒。
“有人儿一生下来是根儿绳子,有人儿呢,生下来是根儿棍子,没人儿提拎,绳子伸不开腰儿,没人儿扶帮,棍子站不住脚儿!”“别心高,好好过。”
——节选自《母亲的哲学》
“土豆栽子杵泥地,埯到哪儿都要梃秧儿活啊。”
——节选自《土豆花开》
乡土文化历来都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乡土文学的浩瀚之中,我所能看见的亦十分有限,终究只是历史须臾的佐证。即使在时代变换的今日,“新”乡土文化的创作形式、鉴赏角度、艺术特色无论怎样发生变化,乡土文学最深远的源头依旧未曾挪移。相反,惟余一箭之地。
山本玄绛说:“一切诸经,皆不过是敲门砖,是要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是你自己。”读者的角色与作品同样重要,我们作为和作者对位的读者,自应凭借九歌简短而不失饱满的文字,寻觅自己遗失在时代洪流中新时代乡土文学的根之所在。
作者简介:朱艳波,笔名卷耳,系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兴安盟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多篇文章发表在《芒种》《中国教育报》《内蒙古日报》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