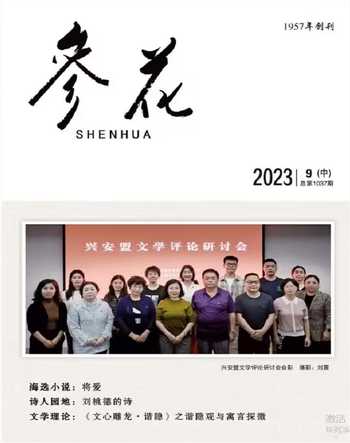语言、技艺、思想
为积极践行新时期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推动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日前,参花杂志社受邀参加了由兴安盟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兴安盟文艺评论家协会承办的兴安盟文学评论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集中展示了近年来兴安盟文学评论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时也加强了作家、评论家与编辑之间的互动。本刊对研讨会期间征集的评论文章进行了细致的遴选、系统的评点,将其一并刊发在专栏中,以飨读者。
日前,应兴安盟文联、兴安盟文艺评论家协会之邀,我有幸参加了兴安盟文学评论研讨会。接下来,我将结合几篇文学评论,以及它们所对应的原始文本,粗略地谈一下我对文学评论的理解。
张彩华的文章从社会进步、文化发展、个人奋斗三个层次去解读《衣裳》这篇散文,精准地洞悉了“衣裳”这一文化符号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可以说,一部穿衣史就是一部社会发展史,一部民族振兴史。朱艳波的文章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较强的统筹材料的能力,她并未对某一篇具体作品进行评价,而是对作家九歌的散文创作进行了总括式的评价,她以文明演进、文学观念嬗变为背景,引出了“新乡土文学”这一概念,并以此为理论框架对九歌的散文书写进行观照,具备高度的理论自觉。张芳的文章从人物、叙事、时代记忆几个角度为我们还原了文本的书写现场,评论的调性跟文本一样,是明丽的、热闹的。漠耕和温智慧写的是诗评,这两篇评论文章文笔优美又不乏哲思,本身就是两篇十分出色的散文。总的来看,兴安盟文艺评论家协会可谓人才济济。刚才提到的几篇文章具备宏观的视野,又有理论的自觉,各具特色,各有优长。接下来,我将结合这几篇评论文章和与之对应的原始文本,从语言、技艺、思想三个维度谈一下我对文学评论的理解。
一、语言层面
九歌的散文多用口语化的短句写成,里面大量使用了方言、乡谚、俚语,是一种没有被驯化的语言。我们都知道,白话文运动至今,我们的现代汉语仍未发展成熟,语法规则多效法西语。随着西方典籍的譯介、传入,在文化接受的过程中,我国的知识分子习染了他们的书写方式、表达方式。白话文运动早期的作家尤为明显。我们看鲁迅、巴金的作品就会发现这种现象。这种潜移默化的习惯至今仍影响着汉语写作。但是也有一些优秀的作家跳出了它的束缚,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比如金宇澄的《繁花》。方言在文学创作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生长在泥土里的语言。它以一种强大的地域文化力量影响着文学的主题、灵魂,决定着文学的讲述方式、叙述腔调,它全面渗透到人物的行为、生存方式、精神状态中,最接近人类生存的本真。有人甚至说,语言即风格,这话有一定道理。经过逻辑、技术严密修正过的书面语则会造成本真的遮蔽,则不具备这一功能。我们都知道,很多优秀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学故乡,比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乔伊斯的都柏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香椿树街。而地方性语言正是构筑文学故乡,形成创作辨识度的最重要材料。九歌散文的创作语言就具备这一特质——琳琅满目的乡谚俚语、生动恰切的口语以及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表达方式,一下就能把我们带到他土生土长的故乡,带到属于他自己的文学现场,我认为针对九歌的创作语言,仍然需要更加深入地挖掘、阐释。
二、技艺层面
文学评论可以大而化之地谈感受、谈概念,谈宏观层面的东西,但也不能忽视对技巧、方法的分析。文学让人更好地理解生活,文学评论则让人更好地理解文学。拿九歌的《衣裳》举例,这篇文章表面上以“我”为观察视角——“我”去看母亲,去看我自己的变化,去看时代的变迁。而在另一个侧面,母亲也在看我。在时代变迁的舞台上,我和母亲互为镜像,照见彼此,既看到了“变”,也看到了“不变”。很多人会忽略母亲这个视角,跟随“我”的体验、感受,重温我的成长经历,回溯时代发展进程。但从母亲的视角出发,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不变”——一如既往地节俭,绵延不绝的对儿子的疼爱,面对生活、甚至生死的那种淡定和潇洒。正是因为这些“不变”的品质,我的人生航向有了坚强的锚定,整篇文章也有了稳固的根基。再拿北琪的《托起幸福》举例,这首诗运用了三组蒙太奇镜头——清晨草叶上翻滚的朝露,黄昏山峰上不肯下落的太阳,以及被托起的、父亲后背上的我,诗人将它们按照心理顺序进行组合、拼接,巧妙地凸显了诗歌主题。前面已经说过,文学评论可以宏观地写,可以按照写思想史的方法将它写成《艺术哲学》《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这样的鸿篇巨著,也可以巧妙地选取角度,让它见微知著。如何选取合适的角度,是考验评论家功力的一件事。好的评论文章能够挖掘文本背后的价值。文学作品不只有文学一种属性,它的价值是丰富的、多元的。在高明的评论家眼中,文本就像一颗钻石,评论家总能独具慧眼,找到合适的角度,将它的不同侧面进行切割、打磨,最终显露出光芒。我们拿《乡村土宴》这篇文章举例,文章细描了内蒙古东北部一户乡村人家的婚礼,尤其对整个流水席的制作过程刻画得相当精细,这就让文本有了民俗学意义。所以可以从民俗的角度切入去考证研究当地的婚俗。用丹纳的“民族、环境、时代”的理论模型,去分析它背后的历史源流和社会成因。我们还可以对一部作品中出现的山川、大地、动物、植物、生态系统等进行归纳分类,从博物学角度为它编纂一部自然志、博物志,《诗经中的草木》等作品就是其中的代表。我们还可以对文本中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人际交往方式,对他们日常的伦理规范、心理结构、观念秩序、审美趣味等等,进行揭示、论述、阐发。通过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的选取评论,文章就有了知识性、趣味性。就有了理论深度、文化底蕴。
三、思想层面
文学评论还要有思想高度,要尝试去凝练、升华作品的主题。《乡村土宴》这篇散文没有对主人公大马勺进行人物小传式的描写,而是截取了大马勺一生当中的一天,讲了他作为我二哥婚宴的掌勺厨师制作流水席的全部过程。由于对象的远近关系,作者对情感态度进行了一定的克制,作者躲在故事背后一言不发,让人物自己说话。于是,我们看到了周旋于砧板、灶台前的大马勺,看到了为弟弟回勺婚事发愁的大马勺,看到了人走茶凉后才被簇拥到桌前的大马勺,看到了因为经年疲累落下一身毛病,不得不告别职业生涯的大马勺。他一个人待在家里,偶尔看看烹饪节目,才能咂摸出生活中唯一不多的一点意思。更多时候则是觉得心里少了抓挠,他时常看向窗外,望望蓝天,然后骂上一句,妈的,生的不是时候,不是地儿。换个,躲开这脚踏地界活一回,咱也能在大饭店子里弄个厨主还是主厨当当。我认为这是这篇文章最令人动容的部分。虽然文章大半笔墨只写了一生中的一天,但这一天又何尝不是他的一生?它是大马勺,也是一种职业、一类人的群像——他们被命运牢牢地按在生活的砧板上,拘囿于方寸之地。他们是一群疲惫不堪的人,气喘吁吁的人,在落下一身毛病,不得不停止生计的时候,才能稍作喘息,才能偶尔朝天外一瞥。这个时候的大马勺是空虚的,无所适从的,但也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才会生发出理想、憧憬,才会有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意识的自觉。通常情况下,他只具备工具属性。时间在他的生命里似乎没有多余的意义,他生命里的每一天都好像被复制粘贴成同一张面孔。大马勺一天的历史,就是他这个厨子一生的微观史,这就是我为这篇文章提炼的主题。
以上是我结合几篇评论文章产生的几点关于文学评论写作的体会。时间仓促,难免顾此失彼、挂一漏万。总的来讲,文学评论应该有思想、有温度、有个性、有创见。既能讨论一部作品的优长,也能坦率接受其中的缺憾。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评论事业应该紧贴时代脉搏,致力于和作家、读者一道,共同建构一个珍贵的审美共同体。
作者简介:陈增禹,系参花杂志社编辑部主任。
(本栏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