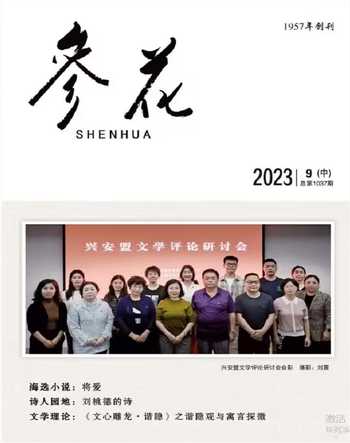温暖淳朴的乡情表述
散文的妙处,因人而异。九歌的散文《乡村土宴》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时代色彩,展示了一幅原汁原味的北方乡村生活画卷。
文贵有情,真情实感是作家创作的动力。《乡村土宴》饱含九歌对家乡的深情厚谊,围绕二哥的娶亲婚宴展开,筹备采买、送亲迎亲、喝酒吃菜,写出了乡村土宴喜庆热闹的氛围,乡情、乡俗、乡音,构成了其散文的审美特质。
北方民俗文化、乡土气息是《乡村土宴》的叙事底色。
所谓乡村土宴,就是乡村的流水酒席,它不同于城市宴席的豪华排场,也不仅仅是把一群亲朋好友请来吃个饭那么简单。主家宾客、大人孩子、酒肉菜谱,处处有讲究,每一处细节都透露着乡民为人处世的世俗哲学,也折射出乡民朴素的智慧和邻里间的人情百态。
乡村土宴是父母为二哥娶亲而准备的一场隆重热闹的结婚盛宴,买酒买菜、杀猪宰鸡,掌勺的、落忙的、烧火的、做饭的、端盘子的,准备齐整,喜气洋洋,披红挂彩的二哥迎来了披红挂彩的二嫂,按照婚礼仪程:坐福、点烟、开席,全屯子的老老少少热热闹闹地赴一场乡村土宴。
乡村土宴的特点是场面大、人多、热闹。场地是自己家开放的院子,家里的桌椅板凳、杯碗瓢盆当然不够用,所以都是借来的,款式不一、五花八门;条桌、炕桌、四仙桌、八仙桌,各具形态,所有桌子“是从东西两院前后街临时借的,带着各家的饭味菜汤水儿”;盅盘碟碗也是借来的,大小不一、杂花样儿,各家的“盘子们”和主人们一样待遇,“也能凑到一个桌上”,全屯子人随礼凑份子,一悠、两悠、三悠,流水席,吃完一拨人,再来一拨人。流水席虽然简单,但是其中的传统仪式和礼数还一直在,人们热闹着,也默默遵循着这些礼仪,如婚礼的过程“坐福”,红布裹着的斧子塞进被褥里,巧妙借用“斧子”——福字的谐音,新娘子坐一坐,沾了福气,幸福一辈子,这种习俗流传至今,仍代代沿用;“清蒸白条鸡压在桌心,成了压桌菜。桌长不发话不能吃,年老的不动筷不能吃,不到最后不能吃”。婚姻是人生大事,乡民们一起见证着二哥二嫂的幸福时刻,连长生天也“罩着这属于人间贫俗小民难得的喜乐”。在作者的审美观念中,在平凡的叙述中,北方婚宴的习俗文化、乡村淳朴的民风展现了一定的优良传统文化意蕴。
乡村土宴的菜系说不上归属,但婚宴上的标准规格是不能简省的。菜单子早就“划拉”好了,四六八碟、煎炒烹炸、焖熘汆炖,南北荟萃,鸡是整鸡,鱼是全鱼,清蒸白条鸡压桌,然后红烧鲤鱼、狮子头、红烧肉、过油炸馃、挂浆苹果一一上桌。狮子头本是淮扬名菜,是将有肥有瘦的猪肉剁碎,配上荸荠、香菇等材料做成丸子,然后先炸后煮,配上翠绿青菜掩映,色彩诱人、香味扑鼻,是无法抵挡的美食。
但是在北方,狮子头却不叫狮子头,叫肉丸子,“汆丸子,炸丸子,四喜丸子”。在大马勺的工序里,“丸子出锅,掌勺的拿筷子中间来一下,大小不管,人人有份儿就得。丸子馅赶上啥算啥,遇上材料不足,豆腐渣芡粉面子,倒油抟和,炸出来一模样。”这完全是改良版的“狮子头”,透着当地人随机应变的灵活与淳朴的智慧。乡村土宴上,红烧肉也不叫红烧肉,叫老虎肉上席,非常具有地域性特色,之所以叫“老虎肉”,并不是字面的意思,而是有引申含义,说明这是一道硬菜,全是肉,肉多,扛吃。乡村土宴上多美食,这里有南北饮食文化的交融,更有乡土風俗文化的底蕴滋养,雅俗共存、魅力无穷。
品读《乡村土宴》,有时代记忆,也有生活气息。
好的散文是发自内心、真实平淡的。汪曾祺曾说:“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乡村土宴》记录了真实平淡的现实生活,是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的缩影创作。
乡村土宴流行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九歌熟悉热爱这一片土地、山水、人情,截取乡村生活的一个侧面,真实反映环境的发展变迁。他描写了一场乡村土宴中的流水席,乡里乡亲、猪肉老酒、土生土长、原汁原味,院子里支起铁锅,煎炒烹炸炖,香飘十里八村,让人不禁重温旧日往事。
《乡村土宴》开场就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大马勺,是二哥婚宴上帮衬做菜的,他的故事贯穿全文始终。大马勺并不姓马,真实的姓名不待考证,作者用了最具有职业特点的名字。大马勺即“屯子里摆席掌勺的”,他们一家子都和餐饮有点瓜葛,回勺是大马勺的兄弟,是他哥的帮手,小勺子是大马勺的儿子,后来接了他爸的班。
岁月流逝,大马勺老了,儿子小勺子接了他的班。小勺子脑袋瓜机灵,接过家传手艺,与时俱进,“想着法变着样地捯饬”,招兵买马壮大了父亲的事业,专门做起了婚宴生意。两千多一场,雇了一个上灶师傅、两个配菜的小工、三个服务员,置办了喜棚桌凳、盘子碗,大马勺做了知宾,全家组成一套班子,乡村土宴“升级”了。时过境迁,世事变化,从大马勺亲自上灶掌勺,到小勺子当上小老板,乡村土宴的经营理念已经悄然发生改变,乡人的生活也越来越富裕,曾经的“乡村土宴”早已不能与“升级”的婚宴相比,此例足以看出时代的发展进步。情由心生,笔随意驰,作者关注现实、关注乡村生活,生活与艺术合而为一,从琐碎平常的世俗生活中,自然流露出作者的乡土情结和家国情怀。
如今的大马勺不愁吃喝、安闲自在,“街上走走,暖地坐坐”。电视里美食烹饪节目的新鲜玩意“沙爹酱烤培根”让他觉着有意思,也是他生活里不多的那一点意思了。大马勺时常自言自语、颠来倒去地感慨“生的不是时候不是地儿”,否则“也能在大饭店子里弄个厨主还是主厨当当”,这成了他活下去的理由。冬去春来,日复一日,对着北方的风雪,对着高蓝的春天,对着一日三餐,对着空了的酒杯和满了的茶杯,自然的轮回与生命的逝去如此沉重感伤,支撑大马勺晚年生活的那些话,炽热真诚,烘烤着日月,烘烤着他的余生,那是大马勺一生的执着,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和悲悯情怀。
《乡村土宴》凸显出了鲜活的人物形象,也显露了作者的语言功底。
多年来,九歌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独特个性的创作之路,形成了适合自己的叙述方法和创作风格。《乡村土宴》直抒胸臆,开头即写人物,语言流畅简练,绝不拖泥带水。从审美感性视角出发,描写了勤劳俭朴的父母,帮衬做菜的大马勺,落头忙的刘铁嘴儿,碎嘴的西院王大娘,热情的卖菜老张头,还有掌勺的、烧火的、做饭的、端盘子的、送亲的、迎亲的、车老板子、接暖壶的、端洗脸盆的、绷大镜子的……这些人物纷纷亮相,既呈现了乡村婚礼上的热闹场面,也彰显了乡民们的质朴热情以及邻里间友好相助的和谐关系。
作者描写人物有独特的视角,善于用白描的手法刻画形象,选用极为简练朴素的文字,不重渲染烘托,也不重辞藻修饰,而是依据人物出身、环境、地位,三言两语地描摹出人物的外貌、神态及心理活动,使读者如见其人。如写大马勺,“小个儿,像个瘦猴儿”,与人们心里肥头大耳、脖颈子流油式的厨师偏差太远,他一边“跳马猴似的忙活着”,一边嘴里也不闲着,和他一个拐弯儿亲家调侃打着嘴架。写他弟弟,“回勺的个子不高,横粗,车轴汉子。”抓住人物外貌、语言、动作,惟妙惟肖,简单几笔,特征显露,尽传神态。乡村土宴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串联起一个个性格迥异的人物,展现了北方乡村人民热情善良、乐观幽默的性格。
作者写人叙事,言简意赅、线条明晰,展现了北方乡村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写喜宴上的人们,喜宴上的菜谱,甚至写到桌子底下的猪儿、狗儿、鸡儿、猫儿,浓厚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猪喝着槽子里的油泔水,狗站在墙角啃骨头,猫趴在炕脚底下嚼鱼刺,大公鸡也领一群母鸡在当院里撒着欢找食儿。”这是在乡村生活才能看得见的真实场景,画面淳朴、动态十足,充满温情脉脉的烟火气。
散文语言是较能表现作家个性的因素之一,作家审美情趣不同,语言风格亦不同。“散文的语言,以清楚、明畅、自然有致为其本来面目。”(李广田)在多年的散文创作实践中,九歌追求散文语言的通俗晓畅之美、朴素自然之美,使外在语言与内心情感相契合,呈现出一种通俗质朴、自然淡远的语言风格。他描写北方淳朴民风,描写亲情乡情,彰显着生命的真实与顽强,温暖蕴藉、自然生动。
九歌善于使用东北方言,呈现鲜明地域特色。如作品中另一个人物——落头忙的刘铁嘴儿。“落头忙”是东北方言,指村子里帮忙张罗事的人,能说会道,颇懂人情世故、礼尚往来,在北方乡村里被人们戏称为“大明白”“小诸葛”或“屯不错”。这些名字、俗语方言,自有东北黑土地的诙谐幽默。作家乡音难改情切切,方言俗语信手拈来,如“踅摸个笔头儿”“划拉菜单子”,踅摸、划拉都是动词,指寻找、潦草书写等动作;“日头儿冒嘴”指太阳从地平线上露出头,充满动态感和画面感;还有“笋鸡上不了架”“二伏萝卜球蛋蛋”“窗户外头连天遍野的大烟儿炮”,都是人们日常中的俚俗用语,弥漫着淳朴的乡土气息,呈现了口语话、通俗化、形象化的语言特质。
九歌善于锤炼语言,巧妙使用修辞手法,抓住准确的词语,反映人物性格和事物特征。文字看似平淡质朴,但淡而有味,于平淡中寄予真情理趣。如文中结尾写劳碌了一辈子的大马勺,老了之后还是有苦恼遗憾,念念不忘如果能够重新活一回,也能再次人生辉煌:弄个主厨当当。在永恒的时间面前,人的生命无法回头,大马勺的人生感叹正是芸芸众生的迷茫困惑,文思含蓄、耐人寻味。
梁实秋说,“文调的美纯粹是作者的性格的流露,所以有一種不可形容的妙处。”《乡村土宴》书写北方淳朴的乡风民俗,书写乡村普通人的生活状态,融入了作者对故乡土地的深情眷恋,融入了对时代变迁和人们命运的关注,字里行间流露出生命的思考和生存的智慧,也让读者在平凡的岁月中,对平凡的生活抱有温情与想念。
作者简介:张芳,女,有多篇小说评论、散文评论、诗歌评论及戏剧评论文章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