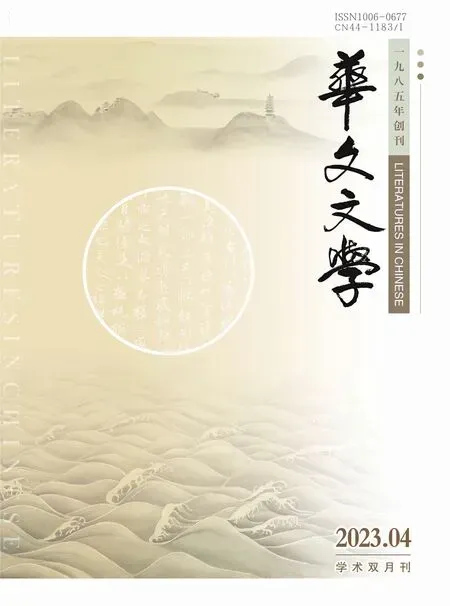抗战时期《大风》的香港叙说
操乐鹏
1940 年,《今日评论》刊载了一篇“香港通讯”,题为《香港的文艺界》。该文对香港文艺发展史作了一番简明的描述与扼要的论断。就香港文化而言,“香港住的‘华民’读不通英文,但似乎也读不通中文”,“这类智识分子对于英国文化,不曾窥到门径;对于中国学问,亦未登堂入室,遑论从事文化工作”?①于是,香港的汉文报纸、文艺副刊,便都离奇古怪,多是“梁山伯复祝英台书”、“麻雀经”、“恋爱经”一类的东西。而香港文艺真正的开端,则要留待全面抗战的爆发:“如果说香港有文坛,那就是抗战发生后由国内迁移去一批文化人所造成的文坛”②。作者“马耳”(即叶君健)依次列举了《大公报》《星岛日报》《大风》《天下》等报纸杂志,认为这些刊物“登载之作品,大多数是由住在国内各地方的作家寄去的。因之这些刊物还相当地保存中国新文艺的传说”,影响所及,“有许多香港的中学生,即因此起了对文学有好倾向的兴趣”,“这种国内移去新文艺的影响是无形的,但是很广大,星加坡南洋各地据说都波及到了”③。
不难发现,《香港的文艺界》一文对香港文艺发生、发展的聚焦和关照,与后世史家的描述在诸多关键点上若合符节。一方面,南来文人被视为香港文化建设的主导力量,“这些报刊都是由大陆南下香港的文人所办,服务于中国抗战现实的,它们虽然创建于香港,但与香港本地并不大,这些刊物的编辑、稿源甚至发行都在内地”④。另一方面,尽管南来文人的文化活动以排山倒海之势,确乎为香港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活力与动力,但是,内地作家多“以‘君临’姿态来港”⑤,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对港岛本地作者造成了压抑乃至压制。《香港的文艺界》对香港本土文化的淡漠与轻蔑,便鲜明呈现出“内地—香港”文化互动间不平衡与不平等的症候性特质。可以说,南来文人的诸多刊物,无不或多或少沾染着居高临下“俯视”香港的傲慢姿态。
在如是1940 年代文学现场的实况与目下香港文学史叙述的定见之下,值得进一步追勘覆按的是,在香港空间中创生与兴盛的报刊,其对香港的观感与态度:轻蔑与漠然,确然有之;对香港文化认同性的体贴与关怀,亦属可能。究其原由:镶嵌于香港语境的文艺刊物,虽说编辑或稿源大都与内地休戚与共,但往往也有个别香港在地文人或平等认同香港文化者的参与。编辑同人文化取向的驳杂性与流动性遂带来了多方观点的聚合,导致在“君临”与对抗的姿态之外或许存有众声喧哗之罅隙。于是,有别于对作家个体香港行旅与香港书写的微观考察⑥,亦不同于文学史“内地—香港”二分的宏观分野,将香港刊物作为“中观”的勘察维度,自有其裨补之益。秉此理路,本文择取《香港的文艺界》文中所标举的《大风》杂志为切入口,寻绎《大风》香港叙述的演绎轨辙及其呈露香港形象的衍化踪迹,将刊物内不同话语中的香港书写重新脉络化,探勘其如何交织着对香港的发现与不见,又何以掺杂着抗战时期香港文化主体性生发的袅袅杂音与可贵契机。
一、“吾道其南”:《大风》基本史实钩沉
1930 年代的上海愚园路愚谷村,可谓是“风”字辈杂志的大本营,《宇宙风》《逸经》《谈风》《西风》月刊等,均汇聚于此地。然而,“八一三”战事一起,这些刊物或夭折、或停刊。据孔远之回忆,“大家觉得困守孤岛,听天由命不是办法,乃有图南之议”,“由逸经社振臂一呼,宇宙风社附和于后,两社乃共同合办大风于香港”,“当时两社的陶陆两位编者,均在上海,正于夏历的岁尾年首,他们准备束装南行”⑦。此处的“陶陆”,即《大风》的编者陶亢德、陆丹林。在《大风》两周年之际,编辑部也回溯了这一创刊缘起:“逸经社同人为着上海的空气和环境,都使说话行动不能够自由,而我们的职责又绝不肯卸弃。在全民族努力抵抗侵略者的时候,凡是不甘心做卖国贼与汉奸的坏分子,都该奋起一致和日阀斗争,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站在本位,认定文章报国的责任,自然感到责任的逼切,于是就和宇宙风社合作,来港合办大风旬刊。廿七年三月五日,创刊号就在香港出世了。”⑧
《大风》于1938 年3 月5 日创刊于香港。初为旬刊,自第59 期始改为半月刊⑨,直至终刊。1938 年10 月中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大风》出至第23 期时曾停刊两月,直到1938年12 月25 日《大风》第24 期的复刊。此外,《大风》第30 期和第44 期都曾因故延期⑩。《大风》最初由《宇宙风》社、《逸经》社联合创办,在第1至9 期封面刊名之上,都书有“宇宙风社逸经社联合主办”的字样。《逸经》创刊于1936 年3 月5 日,发刊至第36 期(1937 年8 月20 日)之时,“为着淞沪战事发生,交通梗塞,文友星散,就中途暂停”[11]。《大风》创办不久,因《宇宙风》迁移到广州出版,《大风》即完全归属《逸经》社创办。《大风》自第10 期始,封面开始署明“逸经社在港主办”。该期还刊布了《宇宙风》社和《逸经》社的联合启事:
本社原由宇宙风社逸经社合办出版《大风》十日刊。今以宇宙风社本身由沪迁粤,无暇兼顾,因从第十期起,《大风》编辑、出版、发行、经济全部事权,改由逸经社单独负责,继续办理。此不过经济与责任之分离,精神上两社仍本友谊而互助也。[12]
1940 年,中国文化协进会“在四月间会员大会时,通过一条‘发刊适应青年读物’的议案。理事同人为执行这一决议案,立定了原则,指拨了经费,并公推了几位出来负责商定实施的计划和办法。但是在香港出版刊物,有许多困难,大家感觉得重新办刊物很不容易,在经济和人事的条件之下,简直是无可能的事”,与此同时,“《大风》因欧战发生,纸价飞涨,成本过巨,而且内地运输及汇兑皆极困难,逸经社同人感觉独立继续维持下去,甚为棘手,所以愿意将《大风》化私为公,把全部基础贡献给中国文化协进会主持办理”,之后,“经双方磋商,决定共同合办,一切责任平均担负,由‘管理委员会’主持其事,另行组织新大风社。本期——六十七期——即是这新组织的宁馨儿”[13]。自第67 期,《大风》封面上的“逸经社在港主办”,随之改为“中国文化协进会逸经社合办”。新《大风》社“管理委员会”公决了《大风》以后的计划:仍旧半月刊发一次,每期篇幅比前增加;在保留原有文艺、特写和史料的内容之外,“加多时代文化的作品,以及清雅有趣的文章,务使本刊能成为抗建期间,青年人和一般人士,既足怡情又能养性,复可加增知识点的最高尚的精神粮食”;在约稿和作家队伍方面,“现已邀请中国文化协进会全体会员,旅居港澳的文艺界人士,以及全国各地的著名作家,撰述文章,充实内容”。[14]
综上,就《大风》的编辑队伍而论,他们在由沪赴港的“图南之议”中发出了所谓“吾道其南”的悲壮之音[15],无论社长简又文、主编陆丹林,还是编辑陶亢德[16]等,无不是南下香港的内地作家。同时,《大风》亦吸纳了在港文人如许地山者的参与。就刊物归属层面来看,如陆丹林所言:《大风》的“面貌形质,虽然受了时代的熏陶,变换了一些,但从它的性质上来说,还是保持着它的姊姊一点风格”[17]。《大风》历经“《宇宙风》社、《逸经》社合办——《逸经》社独办——中国文化协进会、《逸经》社合办”的三个阶段。从与上海文学圈的藕断丝连,到被香港协进会承包,应当说,《大风》历经了与香港文化场域从游离到深嵌的过渡。除停刊外,《大风》持续时间较为长久,正可借此一窥南来文人香港观感的变化。因此,以《大风》为核心勘察其香港叙述以及香港文化主体性议题,可行性与合理性也自兹而显。
二、“外江佬”眼中的香港形象
《大风》作为南下文人所创办的刊物,其最初的香港书写多汇聚于内地作家初次赴港的纪行文章中。《大风》第3 期专门辟出“作家离沪琐记”的专栏,收入诸作家的同题散文。严谔声于1937 年11 月15 日下午5 时乘“维多利亚”号意大利邮轮离开上海赴香港,同行者有萨空了、翁达藻等。至香港,住宿成了首要问题,严谔声详尽记录了一行人的寻宿经历。多亏了谢六逸的学生,帮助他们在陆海通饭店觅得两间客房。谢六逸携家眷居一间,严与萨、翁三人共住另一间。第二天,严与萨空了另抢得了六国饭店的一间房间。此时的“六国饭店,全给上海人的空气笼罩了,差不多全饭店旅客十分之七八,都自上海来的。”[18]而萨空了却后悔不已,他认为离沪赴港是“一桩大错事”,“到香港下了船住到旅馆里半个月后,如果不是茶房的语言不懂,广东菜吃不惯,我简直会疑心自己是还留在上海,在上海未陷前常常可以见到的朋友已而今在香港全遇到了”,“这一切都叫我后悔我不该离开上海,甚至想到重回上海去。同时觉得我们这一群人‘自己恐吓自己’,是太可羞了”[19]。萨、严等人由上海逃难至香港,而署名“纪难”的《厦门失陷日记》一文,叙说着由福建赴港的真实境况。众人“群趋香港。安庆轮开港,余送友人行。赴港者群集,顿成闹市”,“余等以五元代价雇小艇往,又以两元代价倩轮上水手以巨索缒上,以四十二元代价购得最后一张房舱票。轮上凡有空隙之处,均已填满,而后至者尚不绝。友人竟愿以百元向人转让一原价十一元之统舱票”[20]。
正如谭子浓所译的《一个外国记者眼中的香港》所述:“在数月之前,香港仍是一个保守色彩甚浓的殖民地城市”,“现在什么事情都改变了。因为远东战争,香港已立即变为一个重要的城市,一个世界中心”[21]。面对四方杂处的国际性香港,这位记者敏锐地关注到了民生和物价问题,“现在,香港挤满了欧洲人,美洲人,与及从上海,南京,汉口,广州来中国难民,他们以这个英国商港为天堂了,据说这些难民数达三十万,而且不断增加的。这大批的来自中国内地的难民,因其购买力不衰,另到物价腾贵,尤其是屋租飞涨”,同时,大量难民的涌入,也可能导致瘟疫,“由于这一大批难民的逃亡海外,传染病发生的危险,大有可能。从今年正月一日到四月底,香港为天花痘症而死者数达八百人,在三月中旬,港政府于是厉行种痘运动了。这种难民的苦况,只有亲历难民者群中才知道”[22]。这种情况之下,贫富差距愈加明显,“的确,香港从来没有目前的繁荣的。难民堆中,不少富贵华人,他们挟着资产逃到香港来作寓公。战争爆发后,这个自由港,一跃而为远东商业和航运的中心了”,而腐败的问题更是如影随形,“各地的人民都乐闻香港百万富翁的种种,整千整百的华贵汽车,停在通衢大道。高贵的酒店与餐厅老是座无虚席”,“女人穿着巴黎的新装,珠宝饰物,炫人眼目;有钱人家的窗牖饰物,也时时更新——这就是商业繁荣的象征”。[23]
应当说,这位外国记者眼中的香港,并非刻意抹黑或丑化。主编陆丹林就曾多次抨击香港的腐败丛生。《大风》第8 期“风雨谈”栏目刊载了《做国难的官发救国的财》一文,陆丹林乘汽车带友人游览香港一周,在途中,“司机频频的指说,这是某部长的别墅,那是某主席的大厦,左边一家是某军长的新屋,右边一所是某厅长与某局长的洋楼;不久,又说这是某委员第几姨太的港寓,这是某行长的儿子最新式的私家汽车;说来说去,指东指西,无非是那些要人们的享用的物业”,“每天在晚间六时以后,一时以前,到那些酒楼旅馆舞场俱乐部等巡视一下,则当中赌钱的吹大烟的跳舞的人物,属于现在或过去的公务员与其家属等成分最火,他们纵情声色,起居阔绰,用钱如泥沙,挥霍若浪子。际此,春末夏初季节,安居在绝不闻枪炮声,飞机轰炸声,伤兵呻吟声,与夫难民逃亡惨象的另一角落里,穿了簇新的夏装,无挂无碍地过他们表面上所谓避难而实在是享舒适生活,可说是及时行乐了”[24]。陆丹林的《愧煞富豪》则是赞美义卖筹赈活动中的底层百姓,讽刺富豪们的不作为。“香港的工商界,在八一三周年纪念以后,分地举行义卖筹赈,尤以鲜鱼果菜等小贩,奔走呼号,夜以继日的热烈筹措,情况的优美,为内地各省市所未有,这一种爱国热诚惊天动地,实在使人钦佩”,陆丹林“看见一张一张的白布横幅,写上一两句惊心动魄的词句,满贴了花花绿绿的钞票,由一元至万元,每张钞票,都是表示某一人或某家的商店工厂等救国的一种伟大热诚”。然而,这种义卖的筹赈运动,不是发起于长衫(或西装)阶级,而是由短衫的朋友们任劳任怨舌敝唇焦般办理,“各方面所捐输的款项,大宗的收入,除了一部分商店工厂之外,其他的许多富商巨贾的个人名字,都没有见着,不知什么原故”[25]。
可以看出,在纪行话语中,香港作为逃难之所,自身生存作为第一要务,这都使得作家们似乎尚无暇展开对香港的细致体察。同时,香港往往也只是战时行旅之中转站,而非最终目的地所在。即如萨空了的“后悔”,画家冼玉清也觉得返回内地远较奔赴香港为佳[26]。而对香港为数不多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对战时香港的腐败社会状况和骄奢淫逸的文化风气的批判性讨论。主编陆丹林嫉恶如仇的姿态已如上文所引述,编辑陶亢德也曾有言,“若香港,更是‘世外桃源’,居斯境而忘国家安危任情作乐,或犹可说是环境使然乐不容辞”[27]。
颇有意味的是,《大风》社长简又文的态度却又稍显暧昧。在以“大华烈士”为笔名主持的“耳边风”栏目中,简又文有《家丑外扬》一文,谈及“在香港屡见到一件可憎可厌——但谈不到可痛——的事”,即“有些男女——不知其头脑心肠是用甚么原料制造的,每因对于个人或政府,或团体有些牢骚,或愤恨,便用英文投函去英文报纸尽量暴露,或攻讦对方”[28]。简又文在下文例举数端,如暴露和攻击“国难官”在港之奢侈淫靡的腐化生活等行径。在简又文看来,“这等举动,大言之,确可以坐以‘不爱国’之罪——向外国人暴露同胞,祖国和政府之短,而使民族国家失去光荣,丢了名誉,更足使外人之同情于我民族之努力抗战者心灰胆寒”,“我不能不说,这些男女,纵然所暴露的恶事是真,呼吁的理由是足,申诉的委曲是直的,然而,实在是太没常识了”,最终,简又文发出呼吁,“有血性的人不要甘为‘害群之马’啊”![29]同出《大风》这份刊物场域,作为右翼文化人的简又文面对香港腐败状况的姿态,与陆丹林、陶亢德等人呈现出鲜明的不同。
三、文学与漫画视野中的香港书写
在上海等地陆续失陷后,当地的文艺工作者先后奔赴香港,在陆丹林看来,“他们好像是‘外江派’,和香港本地原有的文人,因为言语或其他关系,大家很少往来”,故而,旅港文艺界,是有派别的,“从大体来说,是分本地和外江两派”[30]。按此分类,上文引及的纪行话语及其中的香港书写,发语者均为“外江佬”。在“外江佬”们的纪行文章中,主人公常常在逃难与惶惑中行色匆匆,或注目于衣食住行的生存根基,或抨击香港过分商业化的文化环境。这其中,怀恋上海、嫌恶香港的沪港对照,成为“外江派”香港纪行的基本心理构型。典型的例子还有柳存仁。柳初至香港,顿感“街道并不很好,最热闹的,像德辅道中,皇后大道中,有点儿貌似,但都不及上海的外滩马路,南京路,福州路,和霞飞路。然而一切的商业,金融,文化中心,多半集中在这里”,“这里的先施等大公司,建筑,营业,外表上都不及上海的热闹”[31]。
画家赵含英与诗人徐迟的笔墨,将香港剥离开商业批判的先入之见,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香港风景之发现。赵含英在回上海的前夕,饱含眷恋地追忆在港时光:“栖迟在香港七个多月,在人生的生活过程中,的确使人没能够忘怀,这里有幽美的山峦,碧绿的海水,菁葱的花木,斑斓的鱼鸟,夜里很像一座晶碧玉盘上;这种美丽的都市,确实使人沉醉和留恋”,“这是南方的香岛啊,也是中日战争中的边区的一个安全地带,而今和它暂别,不免有点凄怆”[32]。文章作于归沪的邮轮中,尽管文字多少有些新文艺腔,但确是难得的对港岛的诗化书写。
相形之下,徐迟的笔触更加成熟且冷峻,“在华南的蓝色的海波里,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岛上,现在真是如此美丽的夜风景。横陈在人家窗前的山峰,渐渐消失入夕暮里”,“在海波上,渔火虽已因这个中日战争而改少,巨大的邮轮,与巨大的保护这个军港的英国的兵舰却停泊在海港里,一球一球的灯光灿烂地在水上燃烧”,“而在舞场里,酒家里,咖啡店里,电影院里,是有这末多的人,拥挤着。香港真成了电光管构成的晶耀小的都会。这里拥塞着许多人:到内地去的行客,到这个和平的岛上来的高等难民。这里的一个夜,是寻常的岁月里的夜,被上帝祝福着的。为难民筹赈是这些人的愉快,冬天来了,可喜的是这里并不寒冷,而圣诞节的习气确实如此之普遍”[33]。在诗人徐迟的笔下,蓝色海岸、英国军舰、内地难民、冬日圣诞……种种香港的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季节与节日汇于一炉。徐迟显然更懂文章之节制:圣诞节习气的普遍,暗示着英国文化对殖民地的渗入;“高等难民”以筹赈为乐,既是反语,也平添一股战争语境下的悲凉和哀矜。
《大风》在栏目安排上设置有“漫画”专栏,百余期的刊物中附有近百幅漫画。其中,只有五幅漫画关涉香港;极低的比例,在在昭显出对香港的漠然之态。这五幅漫画分别是《香港所见之难民》(《大风》第7 期,见图一)、《香港路景无理要求》(《大风》第11 期,见图二)、《香江闲写》(《大风》第89 期,见图三、图四),《香江闲写》(《大风》第90 期,见图五),兹截录如下: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香港所见之难民》由丁聪绘制,署名“小丁”。画中的贵妇人衣着时尚、发型时髦,右手拎着购物袋,左臂将所购服装夹在腋下。身后的男士抱着一大摞已经超出他头顶的包裹。纵深处的背景则是挂着华美裙饰的商店。在漫画标题的“难民”与漫画中的“富人”形象之间,构成了反讽的张力。陈宪錡《香港路景 无理要求》的构思与构图与丁聪的漫画大同小异,画中一男一女也是热衷于购物且满载而归,同样也是贵妇人在前,满手提着购物袋的男性角色在后。陈宪錡为香港街景增添了路边蹲坐擦鞋童的形象,画旁还有方言对话:“叫乜野呀!”与“擦鞋”[34]。
因泉所画的《香江闲写》共三幅,都附有署名“布衣”的题诗和解说文字。第一幅图(见图三)正中央为两位身着旗袍(其中一位上身着有短款夹克)、脚踏高跟鞋的时髦女郎,画面右下方是赤脚、赤膊坐在路边捉虱子、晒太阳的苦力。该画的题诗为:“美人换季试新装,扪虱乘时亦向阳;裸退何如能赤背,一般皮肉且同方。”[35]《香江闲写》之二聚焦的事件背景是:“香江护林之政甚善,奈近来柴贵,偷伐山林者日多;偶行山间,见畴昔密林,或竟疏落有致矣。”[36]此种疏落的林间景致,正是画中儿童偷偷砍伐树木以作柴火之用所致,百姓日用之匮乏与生活之疾苦,可见一斑。《香江闲写》之三的关注点由柴价转向米价:“香江米贵,近日飞贵,中等以下之家,买米用纸包,已为常惯之事。试立米肆门口细观,当知纸角顾客之激增也。”画中即是以小纸包买米的荒诞场景。“布衣”的题诗云:“不提米价如珠贵,买米何惭纸角包。顾客莫嫌多碎屑,间中沙粒见掺淆。”[37]
五幅漫画作品无不表达着画家(包括题诗者)对香港社会状况尤其底层民众生活的敏锐观察,蕴藏着哀民生之多艰的人道主义情怀,表达着对香港商业化、消费化的警惕与批判。当然,这些漫画也不断形塑着香港作为消费天堂的刻板印象。在主题观念上,这类漫画既是对纪行话语中香港书写的赓续,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大风》中“香港”之文学书写的匮乏有所增益。此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画作有意无意间都把“消费”与“女性”划等号,凸显出男性漫画家与生俱来的狭隘性别意识与偏见。
《大风》的漫画聚焦香港的物价等民生议题;反过来,窘迫的经济状况,也直接波及《大风》的编辑、发行等事宜。陆丹林在《到港一年》的总结中,提及港币汇率对刊物发行及销量的制约,“国币折合港币由九四跌到五六左右;一切刊物的销路,跟着国土日蹙而低减,而国内难民的数目与民众生活的指数,却又跟着时间而增加,这一年头,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阶段,不可掩饰的事实,是无可讳言。”[38]为了节约成本,《大风》编辑部在邮票的使用和花费上,也是“斤斤计较”。投稿者假如想要索回未被录用的投稿,《大风》编辑部愿意办理,不过,却需要投稿人附寄上回件的邮票(露封的附寄四分,封口的每封最少附寄一角)。
香港语境对《大风》的制约,除了经济因素,尚有文网密布的政治审查。陆丹林在《大风》第24 期的《复版赘言》中直陈:“我们目下,香港,是寄人篱下的侨民,一切言论行动,都要遵守当地政府的法令,因之文字上有许多便受了相当的限制,和国内是两样的”,这类限制最典型的不外是刊物的“开天窗”,“固然,香港是属于中日关系的第三者,他为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不愿意中日双方的刊物文字上有特殊的字句与描写,因之刊物上空白的字句便要天天发现尤其是日报了”[39]。陆丹林也提醒着内地来稿的文友们,如“敌”“倭寇”“兽性”“兽行”等字眼都不能在文章中使用。
四、学术话语中的香港文史
因与《逸经》《宇宙风》之渊源,《大风》的内容与风格较为庞杂丰富,其中即有关涉香港文史研究的部分。一般来说,学界对香港文史研究的总体判断是:“1949 年以前之香港史学,尚处于草创阶段,可述者不多。”[40]许地山及其香港研究,自然是其中最可述的部分。有关许氏的香港研究,诸多论家言之详矣,此处不赘。值得补注的是,许地山正是《大风》作者队伍中的关键一员;他的《香港与九龙租借地史地探略》一文发表于《广东文物》,后者正是中国文化协进会在港举办的“广东文物展览会”之成果汇集。《大风》除了不遗余力地为“广东文物展览会”作广告宣传,也从第65 期始,陆续发表相关研究成果[41]。除此之外,综览《大风》杂志在学术话语中的香港文史研究,尚有两处史料,值得打捞与补充。
其一是《大风》同人未竟的香港文史纂修计划,见于《大风》第12 期的一则“文艺消息”补白。兹录于下:
五月廿八日中午,文艺座谈会“香港”编委会开会,出席人有许地山,陆丹林,樊仲云,李圣五,杨纪,简又文(临时主席)叶恭绰(因病告假)结果如下:
一、定名:“香港”子目内“附九龙租界”
二、内容:一、纵的——历史地理的叙述,
三、横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之特写。各个人印象与感想之随笔。特[]之图片。(引者按:原文该处有阕文)
四、作者及文体:撰稿人除文艺座谈会各作家分任写稿外,并公开征求文稿。文体:文言语体不限定。
五、集稿期:六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
六、分工编辑:
历史地理:叶恭绰、许地山
政治经济:樊仲云、简又文
文化社会:李圣五、杨纪
杂感随笔:陆丹林
编辑主任:叶恭绰(引者按:原文即序号有误,无“六”)
七、出版处所:俟收稿整理后再定
八、稿费:所有稿件,作者均尽义务,本书出版时,所得稿费或版税,用全体名义捐入儿童保育金。
九、通讯处:大风社陆丹林
十、杂用:在筹备期间,所需杂费由大风社捐助。[22]
从这则编委会简短的纪要中可以见出:其分工详尽可行,关涉香港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的各层面。“香港”子目内“附九龙租界”,也正意味着编委会同人对香港斯时历史状况的谙熟与体贴。各项承担人也可谓一时之选,既有许地山、叶恭绰等热心于香港文化的学人牵头,又得到《大风》社的组织筹划与资金赞助之便。这都显示出《大风》同人日益见涨的对香港文史的浓重兴味。然而遍览之后各期《大风》,此事并无下文,该计划想必也就不了了之。
其二是陈公达的《成都的招额》(《大风》第67 期)一文。陈公达,即陈炳权。作为广州大学校长,抗战期间,陈随学校一起迁九龙、开平,设分教处。1940 年,陈炳权开始倡导举办“广州大学书画展览会”。同时,麦广达曾协助陈炳权组织“香港书法座谈会”,使得港中各中小学纷纷响应,书法比赛及书法讲座蔚然成风,且与叶恭绰、沈演公等联合举办的“广东文物展览会”交相辉映[43]。《成都的招额》即是陈炳权对香港、成都两地招牌书法的描述与评判。陈赞同沧阁《名家所书的招额在香港》(《国民日报》1940 年2 月26 日)的论说:“香港各商店之招牌,多是写近体字或所谓美术字,十足表现近代文化的色彩”,继而论定“整个香港就是商场,在光怪陆离的商店招牌中,其文字大都出自俗手。局促之态,令人欲呕,求能稍带书法意味的已难,遑论高逸气息”。相比之下,“四川是天府之国,成都亦是古都,有小北平之称。街道整齐,屋宇宏敞,招额一项,亦带古色古香的意味”,“且成都招额之字体,尤不只意味深长已也,尚有各种特点,活跃于吾人之眼前”[44]。陈对香港招额书法的文化审视,其实并不脱对香港商业环境的鄙薄与厌恶。
五、结语
陆丹林曾在《香港的文艺界》中自陈对于香港文化的认识:“香港属于华南出入口的枢纽,吸收外来的文化,或输出本国的文化,按理应该比较其他商埠来得活跃和成绩好,然而事实上却相反。从前有人描写香港的心脏,只写一个算盘和一根扁担。无疑地是说它是商业和运货工人,就可以代表香港,其他可以推想了。”[45]这里陆丹林所引的香港文化“算盘”说和“扁担”说,其实来自简又文的同题文章《香港的文艺界》[46]。正如陆丹林所说:“‘七七’抗战以前,香港文艺界的情形怎样,我不知道”,不止陆丹林,连同简又文以及前文引及的诸多南来文人或者说“外江派”(许地山自然除外),均与香港文史有着不同程度的隔膜。这也可以解释缘何当陆丹林、“马耳”、简又文们尝试缕述香港文艺时,抗战以前的香港文史常付之阙如。本文所梳理的《大风》刊物场域内纪行、文学、漫画与学术诸种话语中的香港叙说,均非完全立足于香港文化的本土性与在地性,于是,在力图呈现香港的同时,亦不无遮蔽与简化。有鉴于此,前文引及的《大风》“香港”编委会的撰写计划,其所提供的历史讯息便变得尤为重要,它所蕴藏着的香港文史研究的可能性也极为醒豁,至今仍不失其价值。然而,这份香港文史研究与撰修计划未能得到贯彻施行。时至1941 年,随着许地山逝世、香港沦陷,编委会同人遂星散,《大风》继而停刊。香港文化主体性生成与浮现的幽微杂音与可贵契机,至少在《大风》场域中,就此寂灭。
①②③马耳:《香港的文艺界》,《今日评论》第4 卷第15、16 期,第239 页,第239 页,第239、240 页。
④赵稀方:《报刊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19 年版,第133 页。
⑤卢玮銮:《香港文纵——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7 年版,第16 页。
⑥相关研究有:卢玮銮:《香港文纵——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7 年版;赵雨乐:《近代南来文人的香港印象与国族意识》,香港三联书店2016 年版等。
⑦[15]孔远之:《大风一年》,《大风》第30 期,第934 页,第934 页。孔远之等人在福州路大鸿酒楼和大东酒楼替大风编者践行,大家“都很感伤,觉得这一去好像没有重行聚首机会似的。后来不知是谁说出一句‘吾道其南’的话,总算把感伤的情绪压低下去”。见孔远之:《大风一年》,《大风》第30 期,第934 页。
⑧编者:《大风两周年》,《大风》第63 期,第1914 页。
⑨《大风》第59 期刊有“大风社紧要启事”:“大风旬刊从廿九年一月起,改为半月刊,月出两册,以五日廿日为出版期。扩充篇幅,而定价亦略为增加。所有订户,按照未完期数,折合新旧价格寄发。特此通告,诸维亮察。大风社启”,见《大风》第59 期,目录页。
⑩《大风》第29 期刊登“读者注意”:原定2 月25 日出版的第30 期,“因印刷所整理字房机器,停刊一期。三月五日出版周年纪念特大号,内容丰富,特此预告。”见《大风》第29 期,第912 页。《大风》第43 期刊有“大风社紧要启事”:“香港排字工友,昨因事罢工,本刊连受影响,廿五日出版之一期,只得停刊。四十四期,顺延八月五日出版。特此奉告。”见《大风》第43 期,第1368 页。
[11][17]陆丹林:《〈大风〉一周年》,《大风》第30 期,第933 页,第933 页。
[12]《大风社改组启事》,《大风》第10 期,第330 页。
[13][14]《大风——以前和以后》,《大风》第67 期,第2041 页,第2041 页。此外,“管理委员会”还表示:在发行方面,除了“内地各处的推销,同时另想运输的迅速办法”;在办刊宗旨上,“本刊一向及以后皆本着‘拥护中央,抗战到底,’的大原则,以促进大时代的文化运动”(引者按:原文标点如此)。
[16]在《宇宙风》迁移广州后,陶亢德也脱离了《大风》编辑群体。
[18]严谔声:《作家离沪琐记》,《大风》第3 期,第70、71 页。
[19]萨空了:《作家离沪琐记》,《大风》第3 期,第73、74 页。
[20]纪难:《厦门失陷日记》,《大风》第11 期,第334 页。
[21][22][23]谭子浓:《一个外国记者眼中的香港》,《大风》第21 期,第656 页、第656 页,第657 页。该文由谭子浓译自“伦敦出版之派力杂志九月号”。
[24]陆丹林:《做国难的官发救国的财》,《大风》第8 期,第225 页。
[25]陆丹林:《愧煞富豪》,《大风》第19 期,第577 页。
[26]冼玉清文中有言:“果老云:‘香港虽有门生亲串,曾允招待。然家口繁多,彼地又米珠薪桂,何以图存?仍以返内地为长久。’”参见冼玉清:《万苦千辛离危城》,《大风》第24 期,第739 页。该文于1938 年10 月25 日写于澳门。
[27]亢德:《伟大的国民》,《大风》第1 期,第3 页。“亢德”即陶亢德。
[28][29]大华烈士:《家丑外扬》,《大风》第25 期,第799 页,第800 页。
[30][45]陆丹林:《香港的文艺界》,《黄河》创刊号,第18 页,第18 页。
[31]柳存仁:《我从上海回来了(续)》,《大风》第77 期,第2471 页。
[32]赵含英:《舟中杂感》,《大风》第28 期,第893 页。
[33]徐迟:《烽火篇》,《大风》第29 期,第898 页。
[34]陈宪錡:《香港路景 无理要求》,《大风》第11 期,第328 页。
[35][36]因泉画、布衣题:《香江闲写》,《大风》第89 期,第2974 页,第2974 页。
[37]因泉画、布衣题:《香江闲写》,《大风》第90 期,第3018 页。
[38]陆丹林:《到港一年》,《大风》第28 期,第865 页。
[39]陆丹林:《复版赘言》,《大风》第24 期,第737 页。
[40]郭少棠、邹重华、董群:《香港的史学研究》,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98》,三联书店2000 年版,第12 页。
[41]《大风》第56 期刊有叶恭绰的《广东文物展览之缘起》。简又文在《研究文化》中说及中国文化协进会在港主办“广东文物展览会”,“本期开始发表研究这题目的文章”。参加《大风》第65 期,第1977 页。
[42]《文艺消息》,《大风》第12 期,第364 页。
[43]1937 年至1941 年是香港书法发展的重要阶段之一:“以广东文物展览会为主体的书画圈,在中国文化协进会的推动下,粤沪书家齐聚香港,与本地书家一道,带动香港书法活动的高潮,其中广东文物展览会标志着广东学者文人在香港艺术界的全面立足”。参见陈雅飞:《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香港书法》,《新美术》2021 年第2 期,第214 页。
[44]陈公达的《成都的招额》,《大风》第67 期,第2104 页。
[46]参见简又文:《香港的文艺界》,《抗战文艺》1939 年第1 期,第23-2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