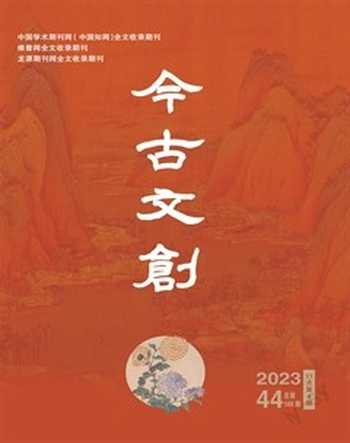尘埃中绽放的花
【摘要】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大淖世界。在这里,小人物虽然面对着沉重的生活压力,但依然追求着自由,展现出生生不息、坚韧不拔的生命力。从结构到审美内涵,小说浸透着浓厚的生命美学意蕴,又包含了作者对文明与生命关系的反思。
【关键词】汪曾祺;《大淖记事》 ;生命美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3)44-0054-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4.017
《大淖记事》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值中国新时期文学起步之际,发表之初就以独树一帜的风格吸引了众多关注。作品描述了大淖优美的自然环境,讲述了锡匠十一子与巧云的爱情故事,刻画了一批生动鲜活的大淖居民形象,歌颂了健康向上的人性之美。从结构设计到审美内涵,它以诗意的语言创造了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间世界,处处浸透着浓厚的生命美学意蕴,又暗含着对文明发展的反思。
一、美的“留白”:环境塑造
汪曾祺说过:“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1] 《大淖记事》可谓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
《大淖记事》全篇分为六节,开篇便花费笔墨交代“大淖”之名的由来,接下来的三节全部用来描绘大淖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直到第四节主要人物才正式出场。
自由和自然是大淖之美的核心。大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2],春天“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夏天“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秋天,人们把茅草“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大淖指的是这片水,也指水边的陆地”。除了湖中诸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像大淖的四季一样自然地生活着,这些形形色色的居民组成了大淖的人文景观:卖紫萝卜的、卖风菱的、卖山里红的、卖熟藕的,“像一些候鸟,来去都有定时”,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还有挑着锡匠担子,走街串巷的锡匠们,“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靠肩膀吃饭”的挑夫。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一切都在按自然的方式自由生长。
虽然文字间充满了对自然之美的向往,但作品并没有走向脱离现实的境地,相反,大淖的人文环境塑造带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小贩们“大都不是本地人”,他们每天早出晚归,点着“半干不湿”的柴草,还要随着季节的变换迁移,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锡匠们恪守着严格的纪律,甚至需要习武防身。挑夫吃着粗糙的饭菜:“青菜小鱼、臭豆腐、腌辣椒”;而他们淘气的孩子们则收集芦柴,“从乡下人的草担上猛力拽出一把,拔腿就溜”,这是多么有童趣的场景,但看似轻松愉快的他们也早早走出了童年:“十三四岁的孩子就开始挑了”;女人们“像男人一样的挣钱,走相、坐相也像男人”,甚至“也用男人骂人的话骂人”。大淖居民做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可以说生活在社会边缘,如诗的风景也并不能减轻他们沉重的生活。倘若用文明的眼光去审视这里的生活,甚至能够看到野蛮和粗俗的影子。作品并没有因为对和谐的追求而淡化这份真实的沉重,也没有美化普通劳动者的卑微生活;相反,他细致入微地刻画出这些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唯恐读者不能形成一个明白的印象。
美的塑造正是在真实的生活背景之下展开的:这里的女人“发髻的一侧总要插一点什么东西”,或者是“清明插一个柳球”,或者是“端午插一丛艾叶”“一朵栀子”“一朵夹竹桃”,没有鲜花时插“一朵大红剪绒花”;她们“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摇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的很”。在生活的压力之下,处在社会下层的大淖人每日为生计奔波,但在这样的生活中,他们也没忘记追求美好。他们对生活抱持着本能的热爱,充满了健康的活力,在生活的尘土中处处显露出高贵的人性之美。
海德格尔说过:“我们是植物,不管我们愿意承认与否,我们这种植物必须连根从大地中成长起来,方能在天穹中开花结果。”[3]大淖居民身处卑微却不忘美好,在生活的重担下仍保持着热爱,时时刻刻以微小的“美”追求着一种无意的诗意。小说的自然环境正是在“自然——生活——美(自然)”的往而复返中塑造完成的:真实生活的沉重不会消解生命之美。
這一部分在全文之中作为主要情节的“留白”存在着。宗白华认为美的塑造“在于能空,对物象造成距离,使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孤立绝缘,自成境界。”在这部作品中,环境描写所占篇幅与主要情节所占的篇幅几乎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说,大量的环境描写正是主要情节部分的“留白”。作者所要建构的,与其说是一个限定在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框架中的传统故事,毋宁说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世界”。结构上的松散恰恰保证了审美所需的距离感。
在阅读过程中,大家也能清楚地感受到这样的设计带来的结果:故事和人物似乎都是由层层递进的环境描写所推演出来的。在这里,环境塑造不再是隶属于人物和情节的棋子,二者成了相互渗透,不可分离的整体;结构换句话说,人物是扎根在世界之中的。对于这样的设计,作者在《〈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一文中提到:“我这样写,自己是意识到的。所以一开头着重写环境,是因为‘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从这里可以看出,松散的结构正是作者是有意识安排的结果,其目的正是为了构建一个独特的“世界”,无所谓失衡。人物是活动在世界中的,情节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为这一切赋予合理性,读者在阅读中随时可以意识到这样一点:“大淖”这个虚构的世界活生生地存在着,包容着一切,在人物和情节的面前也并不处于从属地位。这就是如前所说的“留白”的效果,它使小说别有一种空灵之美,在主要情节之外仿佛还有无限的空间、无限的故事。正是“留白”让这个世界拥有了无限丰富的生命力,这种丰富性在主要情节展开后依然作为一种情节外的“空白”持续在场。“‘空’可以使对象呈现为孤立绝缘的‘美’的对象,而且能显现对象的本来面目。”在背景的无限空间和真实生命力之中,主要情节作为这个世界中的一件事发生了,这样的安排在一开始便具有赋予真实性和吸引读者审美注意的双重意义。
二、美的追求:自由解放
十一子与巧云的爱情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其审美的核心正是美的终极理想:自由解放。
大淖人的爱情观是自由的。作者在第三节结尾处特地拿出一整段来描写大淖人对待男女爱情的态度:婚嫁“极少明媒正娶”,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而“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
婚嫁“极少明媒正娶”,爱情似乎只有一个标准:“情愿”。对于礼法教条来说,这是背离,难怪街里的人要说这里“风气不好”了。不过作者还不满足于此,他立刻反问一句:“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大淖就是这样一个不为世俗所容的地方,它因为自然而“原始”,因为自由而“野蛮”,又因为自然和自由而富有生命力。
这种自由寄托在两位主人公身上,可以说,他们是审美理想的化身。十一子长得“挺拔厮称,肩宽腰细,唇红齿白,浓眉大眼,头戴这遮阳草帽,青鞋净袜,全身衣服整齐合体”,“天热的时候,敞开衣扣,露出扇面也似的胸膛,五寸宽的雪白的板带煞得很紧”,“走起路来,高台脚,轻着地,麻溜利索”,不愧为一表人才。每逢十一子唱戏,“附近的姑娘媳妇都挤过来看——听”。巧云则是“瓜子脸,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眼睛有点吊,是一双凤眼”。每逢她去看戏,人们都“不是在看戏,是看她”。
十一子与巧云可谓是天作地设的一对。巧云落水,十一子救了她。接着,没有海誓山盟,也没有物质考量,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开始信号,两人的爱情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萌发了,真诚又朴素。彼时,封建礼教依然控制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自由的爱情难能可贵。追求自由的人不是付出生命的代价,就是曲终人散,空留一场遗憾。但在大淖,十一子和巧云的爱情却生长开来。究其根本,这里的人们认为你情我愿的爱是理所应当的。
审美理想正是借由十一子和巧云的爱情故事集中展现的。摆脱束缚、追求自由的情结贯穿了巧云和十一子爱情的全程。他们一个是锡匠里的“金凤凰”,另一个是挑夫黄海蛟家的一朵花,两人情投意合,后来遭到保安队刘号长的阻挠:十一子被打成重伤。在这样一个悲剧里,小说歌颂的人性的光辉得到了升华。巧云没有抛弃十一子,而是“没有经过太多考虑”,拿起扁担“就去挑担挣‘活钱’去了”。在巧云看来,这是无须多虑的选择,而我们却能够从巧云的坚守上看到一种光辉的生命力,那是一种未经雕琢的,甚至近乎原始的健康与活力。作者以这个远离礼教束缚的纯净乡野,向我们展示了自然人性那自由自在又无比坚强的本色。
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是生命中的自由和解放的集中展现。只有大淖能孕生出这样的爱情,虽然结局并不美满:十一子重伤,巧云的父亲卧病在床,巧云不得不去当挑夫,扛起整个家。这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结局,但作者却留下了这样的结尾为整个故事收尾:
十一子的伤会好吗?
会。
也许是觉得一个“会”不足以承担他心中对于人性之美的赞叹,作者又以极为肯定的语气强调道:“当然会”。
在主要情节中,除了十一子和巧云两位主人公,作者还塑造了一批自觉帮助主人公的平凡居民。悲剧发生后,他们迫使县政府惩罚了造成悲劇的刘号长。可以说,居民的存在正是对自由追求的侧面肯定:他们团结起来保卫十一子和巧云,保卫大淖的生活。不过,真的是悲剧唤醒了大淖居民吗?通读全篇后,不难发现,也许悲剧只是给他们提供了机会,而真正驱动这一切的是他们身上与主人公一样的追求自由和解放的生命活力。这种生命力没受道德律令的教化,没有子曰诗云的支撑,大淖人只是觉得应该伸出援手,只是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有同情和关心,只是觉得追求自由的十一子和巧云理应追求,就像他们认为爱情该以“情愿”为标准,是不需要解释的。追求自由、捍卫自由的崇高斗争只是在作者淡淡的文字中自然而然地进行着,却展现了生命不竭,追求不止的美的理想。宗白华认为,中国传统美学不同于西方美学之处就在于其“往复、来回、周而复始、无往不复”[4]的观念,生命的推移随着宇宙的律动展现不竭的美。小说从大淖出发,经过主要情节的渲染,又回到大淖的居民、回到大淖的生活之中,在结尾处完成了整篇小说的生命之美的升华。
在大淖,苦难没有扭曲人性,因此也没有塑造人性,它更像一面镜子,把平日埋藏在平凡生活中的美好人性照了出来。这种独特的表现方式,也许正是作者“恬静、淡泊”的美学追求在小说细节上的展现。不在平凡中泯灭,也不畏惧苦难的威吓,始终保有健康、健全的、活力四射的人性,这样的大淖住民,也许正是作者理想人性的例子。究其根本,健康人性的本质正是追求自由,不受约束,热爱美好,人与人之间保持真诚和善良。
“《大淖记事》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它不是一般的爱情悲剧,没有一把泪,一滴血。”[5]大淖的生活是残酷的,作者不否定,但有意不去写它的血和泪,而是在悲剧的泥沼中留下了一个肯定的呼唤作为结尾,这正是对生生不息的自由的强调:虽然身处尘埃依然追求着开出美丽的花。
三、美的内涵:生生不息
作者曾说:“《大淖记事》等几篇东西就是摆脱长期捆绑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从这几篇小说里可以感觉出我鸢飞鱼跃似的快乐”[6]。鸢飞鱼跃的快乐是一种没有外在的压抑、自由随意的快乐。大淖正是这种 “快乐”的结晶,一个理想化的世界。
生活在大淖的人们是平凡的:挑夫、锡匠、小贩……但这些卑微的人却以他们普通的日子进行着一场纯净的远征,在无意中展现着不屈的生命活力。小说以舒缓优美的文字点染出明丽的人情:这里没有苦大仇深的斗争,也没有海誓山盟的爱情,一切都在平白如水的文字中前进。摆脱拘束,崇尚自然,追求自由,这些巨大的主题在小说中并没有伴随着刻骨铭心的战斗和流血,而是以某种自然而然的状态融入了大淖人的生活中。自由是本应如此的,爱情是应该追求的,个性就是自然,是从来如此的。作者曾说过:“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但“我的作品不是”,“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7]。
这种“健康的人性”体现在贯穿整部小说的生命力中。大淖的居民不是哲学家,不是知识分子,他们只是普通的下层人物,他们追求自由与解放也不是经受扭曲、压迫后的觉醒,而是一种自然状态的保持。他们的生活与作为自然环境的大淖紧密相连,富有天人合一的活力与生命力。诚然,大淖并非没有斗争和压迫,只是那种生生不息的东西并不是历经磨难的灵魂,而是一个个平凡的人;他们也不是为了明确的目标和未曾拥有的东西而战,只是在保卫自然而然的生活状态。比起崇高的话题,这种斗争也许只能说是一种不自觉的追求,却在不经意间展现出不屈的生命力。大淖人没有血海深仇,生生不息的意志与自由的追求早已是自然状态,是不需要特意提及的。“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风俗, 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他们也许说不出道理,但已深得精髓。
不息的生命力又表现在大淖居民的生活状态里。宗白华提到生命观念时说过:“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却不是正视的抗衡,紧张的对立,而是纵身大化,与物推移”[4]。大淖居民的生活态度可以概括为平淡。他们顺应自然变迁的节奏,没有过多的欲望。但这并非麻木,恰如小说给出的解释:这只能归结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而在这种自然的生活状态之下的正是坚韧不屈的生命力:他们尊重自由爱情,不看重制度化的伦理道德,为了保卫自己的生活能赶走保安队,甚至能迫使县政府讲和。斗争是突发的,不会扼杀生命的力量,平淡才会。斗争能激发人们追求美好的决心,塑造出崇高和伟大;平淡是长久的,会逐渐消磨人性,让旺盛的活力变成冷漠。大淖人的生活恰恰是平淡的,连沉重也是,但他们以他们的行动证明,平淡从来没有消磨掉他们的力量。在琐碎和卑微中保持着乐观纯真的活力,又能迸发出追求美好的坚韧力量,这正是不息的生命之美的内涵。
四、文明与生命的反思
作品以其诗意的语言和巧妙的结构塑造了富有生命力的大淖。大淖的居民尊重大淖,远离“文明”的他们过着几乎自在自为的生活,展现着生生不息,坚韧顽强,纯真朴素的生命之美。但大淖也是原始而粗糙的,在这里,无论人们的生活态度还是生活方式都透露出一种难为世俗所容的色彩。显然,作者塑造出这样一个理想的世界或多或少是为了与所谓“文明”世界相对照的。虽然作品平淡如水,但它背后所体现的问题却值得深思:文明是否该引起更多的怀疑和反思,生命在文明之前究竟应该局于何处?
文明是以“人”为基础的,尽管它的前进伴随着人的扭曲;文明还是一种约束,但这种约束是不为人所控制的:它可以既阻挡愚昧的利剑,又捆绑人性的高贵。
通读作品不难看出,作者所说的健康人性可以等同于某种理想的人性,或者说纯粹的人性,它没有被文明戴上犹豫的枷锁,是自由而美好的。大淖居民,他们没有对于自由的深入思考,甚至没有这种能力,也不觉得有必要;他们的真纯和善良不是源自修养,而是一种天生携带的“照例”的想法。追求自由,追求美,追求善良已经融化到了他们的生活中,变成了无须多虑的行动。就像这篇小说,人物与背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无法分离。
作品成功地塑造出十一子、巧云和一大批普通人的形象,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中展现出对自由健康的人性的追求,同时隐含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反思:文明在遮盖所谓的“野蛮”的同时,是否也遮盖了“人” ?面对大淖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态度,初看之下有些难以理解,甚至有些厌恶:这不是赤裸裸的原始吗,这不是纯粹的落后吗?但细读起来,它却引人反思,到底什么是文明,文明又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没有文明的地方却保留了更加纯粹的人性,为什么大淖人在枯淡的生活中却活力十足?是否过快的前进扭曲了人本来拥有的东西,而那种东西本来是“文明”应该带来的?
这样的思考不可避免地要带上某种“反文明”的色彩,或者全盘反对文明进步,神化古代生活,或者不假思索地歌颂文明,接受文明所带来的一切:这两种倾向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的危害。文明的前进保障了人类生命的延续,同时又扭曲自然的人,迫使个体的人丧失生命活力。
作品在那个时代给了跑步前进的人们一记柔软的针刺,它所提出的问题现在看来犹有余威:生命与文明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大淖具有“街里”所没有的生命力,这里的一切都是自然的,是美的,是自由蓬勃的。孰优孰劣,至少作者的观点不言而喻。如今,在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数字技术日新月异,以人为本、为了人民的观念也在不断健全,重新思考上世纪末所提出的这一问题,对深刻认识发展与人的关系,乃至对社会未来的走向似乎依然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
[2]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2.
[3](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讲话与生平证词(1910—1976)[M].孙周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4]宗白華.宗白华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5]凌宇.是诗?是画?——读汪曾祺的《大淖记事》[J]. 读书,1981,(11).
[6]汪曾祺.汪曾祺小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7]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8.
作者简介:
孙小凡,男,山东济南人,山东师范大学20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