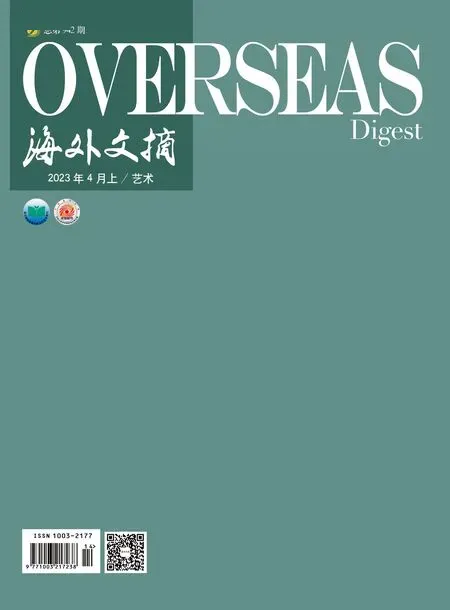《无声告白》中美籍华裔跨族裔家庭的家文化
□赖琦琳/文
作为以“家”为重的民族,国内对于华裔美国文学中家文化的研究早已有之。2006年薛玉凤著有专著《美国华裔文学之文化研究》,其以2000年之前的华裔美国文学为历史文本进行家文化意蕴型研究,文本大多涉及20世纪的一代及二代移民,对象主要是华裔与华裔结合的家庭。目前国内关于美国跨族裔家文化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大多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而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文本作为历史书写具有文化研究价值,本文将以此为基础进行探讨。
小说中的家文化有着特殊的表征。目前,国内对该作品的相关研究集中于族裔文化身份认同、性别、叙事和人物心理分析,鲜有将其作为历史文本,从文化的角度,对美籍华裔家庭家文化进行的研究。本文从跨族裔婚姻的动因、夫妻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父母与孩子关系的窘境、兄弟姊妹之间的间隙与共契四个方面,探讨家文化的杂糅与流变。
1 婚姻的动因
跨族裔婚姻本身标志着血缘意识的淡化。“血源性是中国人家族意识的本质特征”[1],其源始可追溯到氏族社会,家庭成员的关系以血缘为纽带,而作品对二代华裔血缘意识的淡化的过程进行了叙述。1882年美国颁布的《排华法案》是第一个规定某一特定民族集团不得入境的全国法,它禁止华工及其亲属进入美国,迫使早期的华人街成为单身汉聚集地,但该法案允许有华人祖先的美国公民入境,这使得很多冒名顶替的华人有空可钻。《无声告白》一书中,詹姆斯的父亲也是受到了所谓“兄弟”的帮助才得到学校的差事让詹姆斯有书可读。莫里森·G·黄和黄兆群在讨论华裔美国人家庭形式的演变时,大致将其分为五个历史时期,其中第二阶段为“1850—1920年间的‘残缺的’或‘破裂的’华人家庭”[2]。而童年的詹姆斯,周围都是这样残缺、破裂的华人家庭,这样的成长环境深刻影响了詹姆斯的家庭观。早期华裔由于法律限制,被迫淡化了血缘意识。此外,詹姆斯从小接受美国教育,为了融入集体,他一直拥抱美国文化。上大学后父母去世,更是斩断了他与母国血缘上唯一的联系,也影响了他对家文化的认同。
通常二代华裔知识分子融入美国社会的途径有两个:一是通过“美国梦”,靠财富积累赢得尊重。如《典型的美国佬》中的拉尔夫;二是通过异族通婚和白人建立契约伦理关系。相较于华裔与华裔的婚姻的“联合对外”,跨族裔婚姻本身标志着中国传统血缘意识的淡化。与此同时,跨族裔结合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把族裔问题带入了双方的婚姻关系中。在这样的环境下,跨族裔婚姻成为有目的的交易,象征征服与被接受。“这正是他爱上她的最初原因,因为她能够完美地融入人群”,这是詹姆斯对玛丽琳的第一印象,玛丽琳能带给他融入美国社会的机会。对此,杨微用“交换理论”分析指出,“少数族裔与主流社会成员通婚是为了获取后者的高等社会和族裔地位,所以詹姆斯与玛丽琳结合是因为玛丽琳是白人女孩。[3]”而詹姆斯的自白也表明他从玛丽琳身上获得的是族裔身份被接受的安全感和征服的快感。“他恍然觉得,是美利坚这个国家对他敞开了怀抱”[4],玛丽琳是美利坚的化身,娶她意味着被接受,征服玛丽琳是文化身份上的反击。“在中国儒家家庭文化里,‘人伦’关系大体分为两类:父子、兄弟是‘天属’;夫妇、君臣、朋友是‘人合’,显然在以血缘为大的中国文化中,夫妇关系以嗣续为重。”而对二代移民来说,“子嗣”就是一种文化身份博弈。
综上所述,二代美籍华裔血缘关系的淡化主要有两个动因。第一,《排华法案》导致的华人街组合家庭对二代移民的影响;第二,二代移民对美国文化的拥抱。由此,促成子嗣和夫妻关系观念的转变,跨族裔婚姻成为获取文化身份认同的筹码,导致家庭的核心变为文化身份博弈。
2 夫妻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在20世纪60、70年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华裔的跨族裔婚姻夹带着族裔文化身份和新女性身份认同的目的,夫妻关系展现了双方身份转化与认同的过程。相较于以“夫妻,人之始也”“夫为妻纲”的传统中国家文化为基础的华裔家庭,跨族裔婚姻夫妻双方之间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相较于华裔婚姻的联合对外,跨族裔婚姻把族裔冲突带入了双方的婚姻关系中。詹姆斯作为二代移民,中国文化的影响内化为他的性格。“詹姆斯是他见过最严肃认真和保守的人”,相对于大多数的美国白人,詹姆斯拥有着更偏向于华人的性格特质,他内敛而严肃。与此同时,詹姆斯又有点缺乏安全感。当然这也与从小被当成文化“他者”的成长环境有关。詹姆斯对于族裔身份不安全感的来源在文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凝视”。跨族裔婚姻在当时是被当做异类的,夫妻要共同面对社会的质疑,在质疑中双方对自己的婚姻选择产生焦虑。二是法律。《反异族通婚法》(Antimiscegenation Laws)最早产生于1661年,禁止黑人与白人通婚,后来也波及华裔。詹姆斯与玛丽琳结婚的时期是该法案快要被废除的时候,此时跨族裔婚姻在法律上的争议增加了夫妻双方的不确定,而族裔身份的焦虑转为对妻子的控制,通过控制来获得家应给他的稳定感。而被束缚的玛丽琳无法实现自我,新女性身份梦想破灭最终爆发为对丈夫文化身份的攻击。“我知道怎样独立思考,你知道,不像某些人,我不会对着警察叩头。”玛丽琳的爆发反过来加深了詹姆斯的自卑,“叩头——他仿佛看到一群头戴尖顶帽、留着大辫子的苦力趴在地上。唯唯诺诺,奴性十足。”而詹姆斯与中国助教的婚外恋是他融入美国社会无果后的回归,在路易莎那里他获得了族裔身份的安全感,“你是我应该娶的那种女孩”,可以看到他对中美两种文化的矛盾心理表现为了对夫妻关系的摇摆。
综上所述,相较于以中国传统家文化为纲的华裔家庭,由于跨族裔婚姻将族裔身份问题和中西文化中关于家庭伦理观的碰撞直接带入了夫妻关系内部,夫妻关系充斥着不稳定因素,在协商过程中跨族裔家庭的家庭伦理观处于中西文化杂糅的动态变化中。
3 父母与子女关系的窘境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父子关系处于一个很高的地位。自先秦儒家便把人伦关系归结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五伦’”[5],仅次于君臣的父子关系在早期华裔家庭中对家的关系和氛围起决定性作用。然而随着华裔家庭物质环境的改变,父子之间的尊卑和孝悌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从詹姆斯接受美国教育开始,他对父亲的尊崇变得很淡。获取文化身份认同是高于中国家文化中的父子伦常的,在融入美国社会这件事上詹姆斯比父亲更具优势,这导致了父子关系的隔阂。而对于二代移民家庭,受到美国文化影响的詹姆斯一家对于孩子在性别上一视同仁,因此该部分论述将父子关系扩大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为虚位。中国人却从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体与团体这两端。[6]”
相较于以家庭身份对外的社交方式,在美国化的跨族裔婚姻践行者詹姆斯的眼里,混血子女更像美国人,他们应以个人身份在白人社群中发展。“詹姆斯觉得,到了高中,内斯就会成为游泳队明星、奖牌的包揽者、游泳比赛的王牌。赢得比赛之后,他将开车请大家吃饭——或者去做20世纪70年代孩子们喜欢做的事情来庆祝。[4]”然而内斯和莉迪亚无法融入,却因害怕让父亲失望而对此闭口不提。作为二代移民的詹姆斯内化了美国以个体为单位的社交模式,认为自己提供的物质条件和孩子的混血身份是他们融入白人社会的通行证,而这与孩子在学校已久被当做东方人而无法融入的现实相矛盾,孩子处于无法融入社群又无法拥有亲密的家庭联结的尴尬境地。
除此以外,与中国传统家庭类似,二代跨族裔家庭也十分看重孝悌之道。然而影响孩子性格的不仅于此,跨族裔婚姻中夫妻关系问题也影响到了孩子。玛丽琳的离家出走,让孩子和父亲遭受了来自白人社会的非议,莉迪亚认为母亲的出走是因为自己不够听话,所以母亲回来之后她对母亲言听计从,但这与她的个人诉求产生了矛盾。对于传统中国家庭,子女对父母的孝悌观会弱化这种矛盾,但作为从小出生于美国的三代华裔,他们受到美国个人主义的影响,个人意志和父母意志之间的矛盾也就更加尖锐。
总的来说,相较于“子以父为纲”的家文化,跨族裔华裔家庭中文化身份认同成为家庭的核心,影响甚至颠覆着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而孝悌观与个人主义的冲突也直接地表现在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中。
4 兄弟姊妹关系的间隙和共契
完全是东方人长相的华裔家庭子女通常而言较为团结,为了在美国立足而共同抵抗外部的歧视,体现着手足之情。而“手足情深”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兄弟姊妹间因血缘联结而构成的亲密无间的关系。然而对于混血三代华裔情况就不一样了,外貌让他们产生焦虑。“莉迪亚却公然违抗遗传规律,不知怎么,她继承了母亲的蓝眼睛。他们知道,这是莉迪亚成为母亲宠儿的原因之一,当然,她也是父亲的宠儿”,内斯和汉娜认为莉迪亚因为更像白人而获得了优待,族裔问题成为横亘在兄弟姊妹间的障碍。混血家庭的兄弟姊妹之间,存在着族裔阶级概念。正如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所言:“东西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关系。[7]”而根据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知识—话语体系,混血兄弟姊妹的外貌差异变成优劣之分。然而在白人面前,他们又变成“一根绳上的蚂蚱”,经受着所有华裔都会经受的“他者”的孤独,“她是就读于米德伍德高中的两位东方学生之一——另一位是她哥哥,内森——在学校里非常显眼。”在外,他们互相照顾,互相为对方打掩护让父母觉得在学校一切顺利。由于受到权力话语的影响,在跨族裔华裔家庭中,第三代混血华裔兄弟姊妹之间,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关系,对外时的共契与对内时的间隙。
5 结语
跨族裔婚姻动因的目的性、夫妻之间的不确定性、父母与孩子两代人之间社群观的差异和兄弟姊妹之间的“东方主义”影响展现出中美文化杂糅的家文化导致的家庭成员关系的破碎、断裂的景观,在二代移民混血家庭中,不管是美国文化还是传统中国家文化的影响都不再是以浅显的方式出现,更多的内化成为家庭成员的性格和无法言说的创伤。而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始终处在华裔家庭的核心位置,影响着夫妻、父子、兄弟姊妹间的权力话语关系,与中国传统家庭纲常和美国个人主义不断协商。■
引用
[1] 薛玉凤.美国华裔文学之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 莫里森·G·黄,黄兆群.美国华人家庭[J].民族译丛,1993(04):19-31+64.
[3] 杨微.《无声告白》中的跨族裔家庭伦理关系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7.
[4] 伍绮诗.无声告白[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5] 汝信,马振铎,徐远等.儒家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49.
[7] 萨义德,爱德华·W.东方学[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