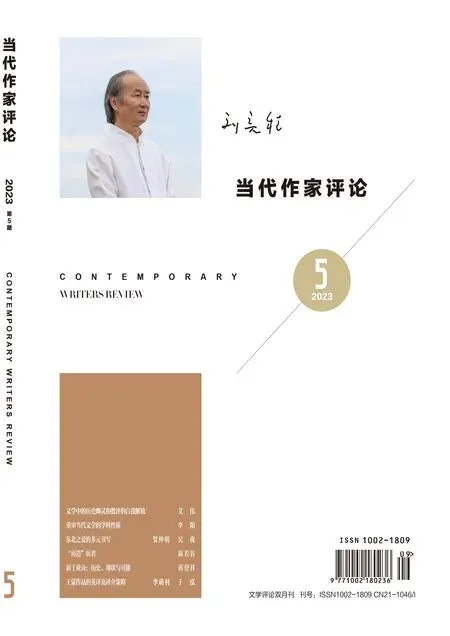汪曾祺的多重镜像与自我建构
迟晓旭 徐 强
汪曾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具有独特精神气质的作家,高邮历史悠久的乡土文化传承和善于变通、维新的儒商家庭作为其文艺创作的初始场景,奠定了他在颠簸起伏的生命历程中朴素精致的诗与思。时至今日,汪曾祺的精神风骨仍旧彰显着强大的凝聚力量,不同时代的人都能在他身上找寻到灵魂“共振”的气息和余韵。自汪曾祺1997年5月16日逝世至今,单篇的回忆文章多不胜数,仅结集出版的初步统计就有十余种,我们能在此间感受到不同“镜像”折射出的生命律动,“汪曾祺热”也由此成为文化史、思想史中永恒的“风景”。人们以多重“镜像”构建汪曾祺形象,使带有真实生命体温的“老头儿”形象愈来愈丰满清晰,而他的自我定位则别具独特的精神丰仪。考察多重“镜像”与他自我定位间的微妙关系,应为接近汪曾祺诗性灵魂的窄门,也可以发现作家形象生成的普遍规律。
一
目前,汪曾祺相关研究日臻丰富,正有条不紊地行进在“经典化”的学理道路上,研究者不断阐释其文学作品的内在精神价值,透过文字表象洞察主体生命内核,在感知“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的形象交汇与碰撞中,建构生成了汪曾祺的艺术形象。综观汪曾祺的全部生命历程,虽然身处革命战争动荡与急剧转折的历史时段,置身于政治旋涡的中心,花甲之年重操小说旧业时却自甘于边缘,摒弃宏大叙事的小说写作范式,重归笔记体,在人伦常情中复原消逝的文化史风貌,呈现出散淡、文雅的传统士人气质。但他在新时期的悄然登场带给文坛的震动却是巨大的,批评家以基本一致的文学史坐标为其定位。1988年,“北大年轻学者黄子平、陈平原诸位,评论汪曾祺有一句话,大意是:士大夫文化熏陶出来的最后一位作家”。(1)林斤澜:《〈纪终年〉补》,金实秋编:《永远的汪曾祺》,第123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孙郁对此持认同态度,直接将研究汪曾祺的论著命名为《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2)孙郁:《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对社会上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和官吏的统称,他们深受儒家思想浸润,心系江山社稷,具有感时忧国情怀的宏伟理想抱负。汪曾祺自认为,相较佛、释、道思想而言,自己更多地接受儒家思想,但“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3)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4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由此观之,汪曾祺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和接受,并非传统意义上宏大的经世济民理念,而是侧重于其中的人道主义情怀和美的生活态度,这种美学倾向在小说《钓鱼的医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主人公王淡人是作家以父亲汪菊生为原型塑造的人物,他在治病救人中秉持人道主义思想,对生疮长疖子等小病症免收诊费,如遇到家境困难者,还会白送药材;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他抛却个人安危在洪水中奔波救治病患;即便病人身无长物,也定会竭尽所能,以尊重、平等的姿态挽救个体生命,村民合赠的“急公好义”牌匾便是他人道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日常生活中,王淡人追求美的生活态度,钓鱼时随身携带白泥小炭炉子,葱姜作料和酒水一应俱全,尽情享受及时烹制鲫鱼的鲜美滋味;家中小院除种植鸡冠、凤仙等草花,还刻意从外地寻来瓢菜种子,与院中原有的扁豆相配,以此呼应医室内悬挂的木刻对子:“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汪曾祺从情感角度接受儒家思想,内化为“以人为本”的现代意识,且追求和谐的人伦理念。在文学创作中,他塑造的王淡人身上既饱有儒家思想的人道主义,也蕴含着士大夫敢于担当的品格和淡泊的高雅情怀。因此,批评者将汪曾祺定位为“士大夫”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历史合理性。
汪曾祺与传统士大夫文人雅趣相投,自幼受琴棋书画的熏陶,不仅精通笔墨,借书画自娱,而且对饮食文化兴趣浓厚,以美食饮誉海内外文友,可以说,书画和饮食构成了他的部分生活艺术。中国古代的文人画和写意画是士大夫表达“与自然为友”的最直接的艺术载体,他们多借花草、树木、山水等自然风物表情达意,恰到好处的题词则补充强化了画作的主体意蕴。汪曾祺亦然,他的画作简洁明快,以写意为主,善于将丰富的情感融入浓淡相宜的墨色间,所绘花鸟皆为寻常品类,用简单舒朗的线条勾勒物体形态,偶尔就地取材,用菠菜汁呈现初春野树的新绿,以白牙膏代替梅花花蕊,将笔墨情趣自然呈现于纸上。“题画”则是以补白形式提示强调创作的意图,他的边款文字既有诸如“明日将往成都”的平淡记叙,抑或“故园有金银花一株,自我记事,从不开花。小时不知此为何种植物。一年夏,忽开繁花无数,令人警骇,亦不见其主何灾祥。此后每年开花,但花稍稀少耳。一九八四年六月偶忆往事,捉笔写此。高邮汪曾祺记于北京”的绵绵乡愁;但更多的则是“凌霄不附树 独立自凌霄”“残荷不为雨声留”的主观抒情。写字和作画于汪曾祺而言虽属文章余事,却意义非凡,他的题字与画面相映成趣、精神相通,画作整体呈现的意境与主体情绪具有内在一致性,确有士大夫的文雅气息。
在饮食层面,汪曾祺爱“吃”,自称是“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4)汪曾祺:《豆汁儿》,《汪曾祺全集》第6卷,第3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的杂食者,敢于挑战生牛肉、炸蝗虫、牛肝菌、炒青苔等地方特色吃食,甚至晚年仍对在江阴读书时没有勇气吃河豚的往事感到遗憾懊悔。而且汪曾祺懂“吃”,他在系列散文中畅谈四方食事,既有对故乡食物的品评,如杨花萝卜水分充足,微甜极脆,除了生嚼也可以拌萝卜丝,“萝卜斜切为薄片,再切为细丝,加酱油、醋、香油略拌,撒一点青蒜,极开胃”。(5)汪曾祺:《萝卜》,《汪曾祺全集》第5卷,第24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也不乏对旅途特色吃食的记录,昆明的汽锅鸡、火腿、牛肉、炒鸡蛋,内蒙古的手把肉都使他直至暮年仍难以忘怀。他还乐于实践,发明了“夹馅回锅油条”这道“专利菜品”。据袁敏回忆:“早餐剩下的那两根油条,被老头塞了用荸荠、虾皮和小油菜拌的肉馅,切段回锅油炸,外焦里嫩,油条嘎嘣脆,肉馅口感有层次,有嚼头,鲜香极了。”(6)袁敏:《淡泊杏花图》,《文汇报》2015年6月7日。汪曾祺谈论和烹饪的食物与他的审美趣味相契合,从家常小菜着手,制作过程中,极大程度地保留食材本味,即便煮干丝也不宜用螃蟹等辅料“喧宾夺主”,他制作的美食具有清纯、本味、中和的鲜明特色。事实上,“汪曾祺谈吃,只是表达‘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对文化的态度’——对生活的热爱,对天地厚赠的感激——不是暴发户的摆阔、饕餮之徒的痴迷、风雅之士的自标格调”。(7)郜元宝:《与“恶食者”游——汪曾祺小说怎样写“吃”》,《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5期。他热爱世俗生活中的艺术,以“雅”的方式对待饮食,将“吃”艺术化,视“吃”为生活的情趣,超越口腹之欲的味蕾满足,是精神上的寄托与享受,朴素寻常的食物也潜隐着作家的日常生活美学和高山流水般的名士雅趣。
二
友人以更加日常化的生活场景和细节细致入微地还原了汪曾祺淳朴可爱而独具个性的生命形态,这显然是以人伦常情为光谱的人物“镜像”。他们抛却附着于主体的文学成就和作家光环,以作家为认识对象,跨越由文学史产生的“镜像”阻碍,从汪曾祺的生活实际出发,让他的喜怒哀乐跃然纸上,回忆建构出汪曾祺作为普通人的日常形象。
汪曾祺交友广泛,就读西南联大时期,与朱德熙因戏曲结缘,患难与共,直至晚年依旧保持密切交往。两人专业相近,互相激赏扶持,常于往来书信中交流学术意见,“他们的友谊,是君子之交,平淡持久,堪称当代的伯牙子期”,(8)徐强:《浊酒一杯天过午——汪曾祺与朱德熙》,《同舟共进》2020年第7期。当属知音。何孔敬在《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中,以回忆视角讲述了汪曾祺吹笛子、喝酒、送干巴菌等细琐往事,间或提及朱德熙评价汪曾祺的文字:“曾祺将来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作家”“曾祺喝酒很少喝醉,就由曾祺喝吧”“曾祺烧的菜,是馆子里吃不到的”。(9)何孔敬:《长相思:朱德熙其人》,第67、194、19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朱德熙从创作能力、生活趣味等诸多维度充分肯定了汪曾祺的超群技艺和人格魅力,当汪曾祺得知好友因病离世的消息后,深夜作画遥寄相思,以致放声大哭,泪不能禁,两人的友情在此可见一斑。20世纪50年代初,汪曾祺与刚调入文联工作的林斤澜和邓友梅过从甚密,“文革”结束后,正是在这些老友的鼓励下,才重拾信心,再次提笔进行小说创作。林斤澜用“我行我素小葱拌豆腐,若即若离下笔如有神”概述了汪曾祺创作的心路历程,“若即若离”指作家在不同时期与文学主潮的关系,“我行我素”则意在强调他在曲折人生道路上的精神坚守。他们交往多年,是文友亦是酒友,林斤澜曾在文章中追忆两人最后一次饮酒的经历:90年代初,两人乘飞机到黄山脚下的屯溪,伴随着夜晚昏黄的灯火和迷蒙细雨,“一人一碗螺蛳,一个口杯温上一瓶黄酒,自斟自饮自说自话。两天三夜,不上黄山,也没有醉。说不上‘豪饮’,略略渗着点‘豪情’吧”。(10)林斤澜:《〈纪终年〉补》,金实秋编:《永远的汪曾祺》,第125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在邓友梅的记忆中,汪曾祺文学创作呈现出“大俗大雅”的鲜明特质,他的“大俗”涉及丰富的人间生活场景,“大雅”则独具打捞消逝的文化史记忆功能。汪曾祺工作中沉稳内敛,担任《说说唱唱》编辑时,对人谦虚有礼,朴素实在,“他申请入党时支部曾责成我与他保持联系,进行‘帮助’,结果发现他的政治觉悟比我还强,个人主义不说比我少也要比我隐蔽点”。(11)邓友梅:《漫忆汪曾祺》,《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5期。汪曾祺对待朋友热忱直爽,得知邓友梅的《烟壶》发表后,他欣然接受为此写评论文章的邀约,当好友向他表达谢意时,他却直言道:“先别高兴,我还有话没写上呢,你那个库兵不行,是个多余的人物,这篇小说没他什么事也碍不着,只因为你对这种人物有兴趣就写上了。这不行!破坏了结构的严谨。我只在文章中说你九爷写得好,没提这写得不好的库兵,给你留点面子,当面这一件还得告诉你!”(12)邓友梅:《再说汪曾祺》,《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6期。对文学的共同热爱缔造了汪曾祺与好友间的真挚情谊,朋友以同辈人的立场漫忆往昔,涉及作家创作、饮食、工作、生活等诸多领域,显然概括了他精神世界的重要面影,友人的视角无疑为我们呈现出带有鲜活生命力的汪曾祺“镜像”。
汪曾祺待人宽厚,乐于扶持后辈学人,家中常有青年作家、学者到访,从汪曾祺与陆翀、宋志强等人的书信往来以及新发现的致曹乃谦的五通书信中,可见他竭力帮助文坛新秀,并与之保持密切交往。被誉为“第一汪迷”的苏北是汪曾祺在鲁迅文学院的受业学子,对先生的学识才情饱含崇敬之意,他视汪曾祺为“精神上的父亲”,(13)苏北、徐芳:《汪曾祺为什么这么迷人?——苏北、徐芳对谈录》,《文艺评论》2017年第7期。为学习汪老的写作技巧曾手抄《晚饭花集》,在不断的阅读与走访中收集大量资料,为深入研究汪曾祺奠定现实基础。苏北认为汪曾祺的作品虽然短小,但生气盎然,他冲淡平和的文字为青年作家提供了丰厚的养料。龙冬夫妇亦是汪曾祺家中常客,在龙冬意识深处,汪曾祺平易近人,给予他亲人般的无声滋润。藏族作家央珍与汪老情同父女,“先生那和悦舒展的脸庞同炯炯发光的眼睛,表达出来的豁达、善良、恬淡、儒雅,给我们一种难得的享受”。(14)央珍:《来自一个西藏人的纪念》,《作家通讯》1997年夏季卷。每次辞别汪先生,央珍总会顿觉精神得以净化,内心充实,仿佛朝圣归来。后辈友人对汪曾祺高山仰止,汪老既是他们文学创作上的引路人,又是慈祥和蔼的父亲形象。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五种关系准则,分别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由于朋友的特殊性,对君臣、父子、兄弟不可言者,皆可与朋友分享。因此,友人眼中的汪曾祺相较文学史中的作家“镜像”更为平易可亲和真实可感。
三
汪朗、汪明、汪朝三人合力撰写的回忆录《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极具史料和研究价值,子女们以细腻的笔触回溯了父亲生前的生活片段,用零散的记忆拼贴出作家的生命轨迹,为研究者提供了诸多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真实资料,在对父亲的深切缅怀中建构了家庭血亲伦理语境中的汪曾祺“镜像”。
在子女的记忆中,汪曾祺爱烟嗜酒,即使晚年在家人的严格监管下也要偷偷饮酒,虽然被外界誉为“美食家”,但厨艺并不算过人,只是懂得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纵使在文坛上声名显赫,被人尊称为“汪先生”“汪老”,可在家人眼中,父亲只是亲切温和的“老头儿”。他对于自己知之甚少的领域总是虚心求教,认真听取他人意见,作品初稿完成后,必然需要经过家庭成员的审阅,家人可以提出意见或在作品上涂改,即使读小学的孙女们也可以对他的得意之作随意指摘。
爸在一篇文章里谈到知识的积累,说一个人知识的积累就像冰山一样,往往只有四分之一漂浮在水面上,而多达四分之三的只是平时是淹没在水下,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文章发表后,颇得评论赞赏,但在我们家里,却引发了一场“炮轰”。妈说爸是“科盲”,告诉他冰山淹在水下的部分远不止四分之三……于是,一家大小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向老头儿发起“攻势”……爸缩在沙发上,听任我们疾风暴雨般地一通攻击,满脸愧色,真的像做错了一件什么要紧的事儿。后来这篇文章再版时,爸认真更改了这个被我们定性为“老头儿特没文化”的错误。(15)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第345-346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
由此观之,汪曾祺在家庭话语空间中,从未将自我思维禁锢于长幼尊卑的封建纲常伦理桎梏中,他能够以朋友的相处模式对待子女,为他们营造自由宽松的成长环境,他尊重每个孩子的言论及人生选择,给予子女充分的理解、肯定和关爱,用自己豁达坚韧的生命哲学引导他们在困境中成长。这种思想的形成得益于汪曾祺的个人成长经历,他身为家中的“惯宝宝”,自幼备受宠爱。祖父汪嘉勋亲自指导他读书、习字、作文,为其文学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出身书香门第的祖母谈氏和二伯母等家中女性长辈,对他关怀备至,填补了母亲早逝的情感欠缺;父亲的人生态度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汪曾祺的情感表达和个性生成,“多年父子成兄弟”的平等教育理念也为汪曾祺与子女的相处模式提供了有效借鉴。在此基础上,汪曾祺主张:“一个现代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16)汪曾祺:《多年父子成兄弟》,《汪曾祺全集》第5卷,第26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与孙女的相处过程中,汪曾祺以平等的姿态真心实意地和她们交流,允许孙女们在他稀疏的白发上缀满花色鲜艳的发卡,认真听取孩子稚嫩的“审稿”意见,虚心接受“批评指正”。据孙女汪卉回忆:“我和表妹自觉应为提高作画之人的艺术水平做些贡献。……决定以‘禽、兽’为目标进行‘打击’……我翻出老人颇为自满的一幅新作,指着图中雀儿呆滞外凸的眼珠,笑道:‘这鸟儿的眼睛都赶上死鱼眼了,木呆呆一点灵气都没有。看看我买的鸟儿多可爱,就当模特送给爷爷您,以后画鸟时多学着点吧。’爷爷先是怔然,随即呵呵一乐,大呼我批评的是,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改进,那只鸟窝便被他收进了书柜中最接近画案的位置,直至他离世也没挪过地方。”(17)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第449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汪曾祺没有旧式大家长的作风,深爱家人并以包容的心态接纳家人建议,是性情温和的“好老头儿”。
汪朗亦曾坦言,父亲看似随和其实相当自负,年轻时表现出莫名的傲骨,在文学上绝对自信和挑剔。他对待文学创作有着超乎常人的严谨和执拗,作品文字甚至标点符号都需要反复推敲,在他1981年致《人民文学》杂志编辑涂光群的书信中可见一斑:“前寄一信,请代为把《晚饭后的故事》中‘倒呛’的‘呛’字改成‘仓’字;郭庆春细看了科长一眼,‘发现她是个女人’一句删去。”(18)汪曾祺:《810722致涂光群》,《汪曾祺全集》第12卷,第8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汪曾祺重视汉语的使用,对语言要求严苛,落笔前习惯先打腹稿,待腹稿成熟再秉笔直书,在此心理流变过程中,强调“不管叙述也好,描写也好,每句话都应从你的肺腑中流出,也就是从人物的肺腑中流出”。(19)汪曾祺:《小说创作随谈》,《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23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落笔后认真修改,力求语言精准无误,从现存手稿的修改痕迹中不难发现,“其修改文章的过程,大致有以下的特点:多余的话删,露骨的话删,刺人的话删,忌讳的话删,这样的结果是朴素、自然”。(20)孙郁、姬学友:《汪曾祺片影》,《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4期。在子女笔端,汪曾祺完成了从“作家”到“父亲”的身份转换,这种阐释视野更易于触及他鲜为人知的日常往事。
汪曾祺自20世纪30年代末走出童年“伊甸园”,告别无忧的少年时光,相继辗转于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等多重文化地理空间,50年代末期,历经群众诉议、组织检验,终于成功摘帽,在杨毓珉的帮助下调到北京京剧团工作,这一选择使他再次走向风口浪尖,开始了与京剧福祸相依的生命旅程。“1963年汪曾祺开始参与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由此揭开了他与‘样板戏’、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葛,构成他一生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21)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第40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即使汪曾祺时刻小心谨慎,终日诚惶诚恐,将全部情感、才华都投入剧本创作中,心理上远离一切纷争,但他出众的才情迅速得到江青赏识,指派他加入现代京剧创作,继而被动地卷入前所未有的文化运动中。这一人生经历对汪曾祺来说难以言喻,既让他尽快走出“牛棚”不曾遭受身体上的摧残,不明就里地登上天安门享受无上荣光;但也为他后来被“挂起来”的境遇埋下祸根。生活的磨难重塑了汪曾祺的筋骨,也锻造了他的性情。从天真隽永的心境到沉静内敛的气质,其中蕴含着难以言说的苦楚,长时间的谨慎、恐惧使汪曾祺在心理上备受煎熬,多重情绪的叠加让其深陷痛苦的深渊,精神上时常处于愁苦、压抑、孤独、无助的状态,以致于接受审查时,“天天喝酒,喝完酒就骂小人,还经常说要把手指剁下来以‘明志’”。(22)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第140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家庭为汪曾祺提供了心灵休憩的隐秘空间,能够让他卸下防备和伪装,展露真实的内心世界和情绪起伏。亲人所建构的汪曾祺“镜像”相较文学史及朋友视域,喜怒哀乐更加丰富,性格的立体呈现补充了学者和朋友“镜像”中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的面相。
四
在汪曾祺的生命系统中,既有源自童年的家庭温暖,也有成年后饱经时代变革和历史跃迁的沧桑,外在形象随之悄然发生改变,从童年时代的无忧无虑到青年阶段的恣意洒脱,由中年的困顿迷惘到晚年的随遇而安,受外部环境熏染,他在文艺思想转变及作品风格确立中完成自我形象的生成。
童年时期,汪曾祺在亲人呵护下快乐成长,时常流连于老宅花园,在独属自己的空间内自由狂欢。他充分调动一切知觉系统,感受自然生命的脉搏,走出家门后,对寻常巷陌的市井风俗兴趣盎然,街市见闻为他带来了全新的生命体验。《昙花、鹤和鬼火》中的李小龙是童年汪曾祺的化身,他对故乡满怀热爱和深情,上下学途中洞悉生活肌理,目光所及皆为“风景”,粪船、菜地、农田、牌坊、晚饭花等寻常景物在他眼中别具光彩,甚至苇荡子里的小蝌蚪也富有生命力。真挚纯净的童心促使他在夜晚敏锐察觉到昙花绽放时醉人的芳香,一睹其淡雅之美;在大雪后欣赏到雪白原野上流淌玫瑰红色河流的奇特景色;深秋清晨在淡蓝如水的天际发现孤鹤的踪影,惊诧于它的孤傲和凄清之美;也曾在阴云密布中领略鬼火的异彩,纵横交错的碧绿光芒正是自然的伟大杰作。总之,汪曾祺在这此时期自由欢愉,怀揣未被浸染的童心和诗心,俨然一副逍遥自在的“顽童”模样。
外出求学后,连绵的战火打破了原有的宁静,汪曾祺的生活急转直下,只能以混杂着沙子、木屑和老鼠屎的“八宝饭”勉强果腹。文学创作上,他吸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作品带有明显的意识流色彩,至40年代末期,他的生活和创作都陷入艰难境地,不得不开始探寻文学创作的新路径。于是,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希望增加人生阅历,改变当下的苦闷境地,但“由于就读于南菁中学时误入‘复兴社’的历史问题,汪曾祺被革命主流淘汰出局,他被搁置在了武汉。更让他忧虑的是,同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联大文学圈几乎都被挡在门外,无一人受邀参加”。(23)赵坤:《“如何通俗”:50年代汪曾祺文艺思想的转捩》,《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3期。汪曾祺在文艺思想转捩的关键时期,曾试图竭力靠近时代话语,他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积极响应时代主旋律,希冀与主流话语同频共振,《怀念一个朝鲜族驾驶员同志》《从国防战士到文艺战士》《一切都准备好了》等作品应运而生,集中讴歌了普通人的革命精神,与前期作品形成鲜明对照。“下放”时近距离地接触农村和农民,在“样板团”工作期间,依照上层标准高呼了十几年的豪言壮语。但右派的特殊身份如同悬置在汪曾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禁锢他思想和灵魂的无形枷锁,无论置身于何种境地始终惶恐不安,心理和精神时常处于崩溃的边缘,由此形成了疲惫窘迫且急于寻求出路的中年迷惘者形象。
80年代,在历史烟云的迷雾退散后,汪曾祺迅速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艺观念,并坦诚宣示是“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在艺术创作上,他则以后撤的姿态将娴熟的意识流写作技巧深藏于作品的隐秘角落,转而高举“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的旗帜。他曾在不同场合反复阐明:“我所说的现实主义是能容纳一切流派的现实主义;我所说的民族文化传统是不排斥外来影响的文化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可以融合的;民族文化和外来影响也并不矛盾,它们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作家也不必不归杨则归墨,在一棵树上吊死。”(24)汪曾祺:《910617致范泉》,《汪曾祺全集》第12卷,第2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汪曾祺探求的是西化与传统相融通的美学原则,他对自己的艺术才能颇有自知之明:“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25)汪曾祺:《门前流水尚能西》,《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3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他作品中呈现的创作意图明显表现为“人间送小温”的教化功能,其中既传承着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又内在性接续着席勒所谓“素朴的诗”的美学范畴。晚年他在创作上进行“衰年变法”,将现代意识与传统文化融会贯通,明确提出:“一个人要使自己的作品有风格,要能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并且,应该毫不客气地说,欣赏自己。‘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26)汪曾祺:《谈风格》,《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3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这无疑是本真生命的回归和坚守。
从本质上讲,汪曾祺文艺思想转型时期,确乎饱有“积极入世”的态度,并未以闲适散淡的心境独善其身,但由于他“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殆矣”,(27)汪曾祺:《泰山片石》,《汪曾祺全集》第5卷,第32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故唯有以美食、美酒排解心中郁结,士大夫的散淡与闲适既为个性使然,也属无奈之举。汪曾祺将“美食”和“美酒”作为躲避现实困境与协调自身生命状态的有效手段,在酒酣时,方能让紧绷的神经得以片刻松弛,他借谈吃忘却烦忧,弥合精神创伤。汪曾祺所执着的“美食”和“美酒”都承载着他特殊的心理逻辑,“吃是中国传统高明的解脱法,口腹之欲可以使思想活动得到最充分的休息,《红楼梦》中贾府那些精美绝伦的食谱无非是应付政治高压的镇静剂”。(28)胡河清:《汪曾祺论》,《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于汪曾祺亦是如此,“美食家”和“酒仙”的形象是汪老雅趣的外化,更是他智性生存的“外衣”。迄今为止,汪曾祺在文学史上独占一隅,随着图书出版以及“汪迷部落”等自媒体的广泛传播,汪曾祺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作家的形象建构不仅是对个体生命历程的简单回溯,同时也呈现出对特殊历史时期的关切与反思。不同文化身份的阐释者在记忆中追寻作家远去的身影,以多重话语体系建构的汪曾祺“镜像”再现了作家鲜活的生命历程和主体形象。遗憾的是我们永远无法重新折返历史现场,唯有在回忆者的语言文化“镜像”中无限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