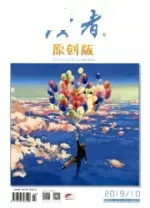我在德国打过的工
文 | 几 时

一
因受了毛姆的蛊惑,我在学生时代一直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是件既浪漫又充满哲理的事。每当读到他笔下的主人公放弃优越的生活去工厂做工,去巴黎住阁楼、啃干面包,做水手出海、满世界跑时,我都心生羡慕,常幻想着自己白天与朴实的工友并肩干活,晚上回来吃两口面包,打开幽黄的台灯看书思考。我总是可惜自己只顾贪图享乐,不敢放肆拥有这样单纯的人生。
直到我毕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不堪忍受办公室生活,辞了职继续读书,但坐吃山空,迫在眉睫的生存需求让我不得不找兼职时,我才终于有机会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现在我写出“体验生活”这样的字眼好似很轻巧,实际上当时因为没有存款,签证、保险和房租样样都成问题,就算不吃不喝每个月也得有几百欧元的硬性开销,青黄不接,十分窘迫。
因痛恨看电脑的日子,所以我坚决将坐班的工作排除在外,简历只投给要跑、要跳、要动的岗位。毛姆对我的影响实在不浅,在看到某仓库的招聘广告时,我浪漫朴素的情怀又蹦了出来,激动地打电话应聘。电话里对方问我能不能搬动20千克的货物,我满口答应,又夸张地描述了我如何热爱运动。
可等到现场面试时,两个男主管看了几眼我细细的胳膊,对视一番,还没叫我试工,就已经没戏了。确实,我除了一腔热血,什么都搬不动。面试碰了壁,但缺钱的人没时间气馁,我得继续找工作。
那段时间不少公司都在裁员或者倒闭,奇怪的是,唯独有一家零售公司,反而大力扩张折扣店,在德国的中小城市不停开新店、招员工,不久也开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也终于应聘成功。
这家店店面200多平方米,商品品类极多,仓库里货物堆成山,不上货的时候,我们这些售货员也要全场跑。说是售货员,其实根本不用推销,只管上货和整理,有时也当收银员。工作内容听起来令我很满意,好在我也让面试经理满意,便得到了这份工作。
有工作便意味着有进账,饭钱有了着落。我吃饱了饭,又开始胡思乱想,希望和同事结下深厚情谊。尽管工作氛围一团和气,但一起工作多时,并未生出我想象中的同志情谊。同事中年轻人居多,有在异乡的外国人,有做做兼职、观望人生的本地青年,也有携家带口的中年人。
有一次,我和一位本地同事一起改装货架,她大概也想与我增进感情,便问我现在在干什么。我说在念硕士。又问我念完硕士要干什么,有什么人生理想。我说念完后要继续念“Promotion(授予博士学位)”。她听了茫然地应一声“OK”,就没了下文,两个人沉默地把活干完,她没再问过我什么。
在家吃饭时随口和室友说起这事,他责备道:“你可以说以后想在大学工作,可以说继续读博士学位,但说‘Promotion’并不是人人都懂。以后你跟他们说话要挑常用的词。”
“但‘Promotion’是最常用不过的词啊。”我不以为然。
“那只是在你的象牙塔里常用。”室友说道。
二
既然和同事没有彼此联结的情谊,我便将这份无处安放的感情寄托在了工作上。最开始的几个月,在我把一箱箱的货物从仓库里轰隆隆地拉出来一件一件地摆放在货架上时;或在我奔走于货架之间整理被顾客放乱的商品时,我常愉快地想:这就是最普通的劳动人民的日子。想至此,常被自己感动。
念书时,我的交际圈子十分狭小,社会经验几乎为零,加上洞察力薄弱,导致从不知道别人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从没有想过,在周六我舒舒服服购物、吃饭时,那些在商店和饭馆为我服务的人是没有周六的;也没有意识到,我在节假日外出享乐时,为我服务的这些人是没有节假日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也实在想象不出来。

打工的店铺
现在不用想象了。因为每周有20小时的时间,让我可以真真切切地体验“别人的生活”。周六的晚上,在顾客开开心心拉着购物车结账时,我是那个手忙脚乱地扫码、装包、收款的人;在商店打烊、顾客回家后,我是那个留下来把乱成一团的货架收拾整齐的人。我成了那个没有星期六的人。
我终于过上了求之不得的劳动生活。但是我只有理想中的劳动生活的第一部分,没有秉灯夜读的第二部分。要工作的日子,虽然工作时间只有7小时,但强度太大,来回的路程有6千米,除了中间休息的半小时,一刻也不能坐,手也不能停。偶尔遇见不讲理的顾客,还要受一肚子气。一忙起来,时间过得飞快,有时感觉才刚来上班,却听到同事在收银台对顾客说“祝您傍晚愉快”或“祝您周末愉快”时,才会猛地一惊:已经傍晚了吗?又到周末了吗?店面在商场的地下一层,一排排白炽灯将店里照得通亮,我们不知天日。看见许多人买伞,才知道外面下雨了;要是顾客寥寥无几,才知道,外面是晒太阳的好天气。晚上下班回家已疲惫不堪,洗漱之后倒头便睡……
就这样,我每周3天上班、3天上课。研究生课程繁重,我被必读的文献追着跑,上一周的文献还没读完,下一周的又铺天盖地而来。有时下班后会勉强自己坐在书桌前,但累得背都挺不直,翻开文献头脑发涨,白纸黑字跳来跳去怎么也看不明白。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只想象了勤奋劳动的浪漫,却忘了劳动给身体带来的苦累。几次逼迫自己学习不成,终于妥协,让身体坦然地躺在床上。虽然入睡前依旧会迷迷糊糊地想:明天,明天下班后一定要学习。但每天的工作都差不多,哪一个下班后的明天都是一样的累,哪天才能读完那些成山的文献?
有一次,我蹲在地上整理最底层的货架,起身时眼前发黑,赶紧扶住旁边的一摞箱子。在小说家那里得来的天真,让我搭建起浪漫的布景。在那幅布景里,我是来体验别人的生活的好奇的知识分子,随时可以全身而退,所以才有勇气去打工,才能日复一日地上班下班。然而,我忽然意识到,每天上货、理货、收银,我并不是在体验—这就是我的生活啊。尤其是当我点开银行流水,看到每个月收支相等,没有几分余额时,我不得不承认,这不仅是我的生活,且毫无退路。
浪漫的布景“呼啦”一下坍塌,我脑子里长久绷着的那根弦,吱吱呀呀,马上就要断掉了。没有社会需要我观察,也没有生活需要我体验,我来上班,是因为我要交房租和医疗保险,要吃饭,不得不上。我不是劳动人民的观察者,我就是劳动人民。镜花水月散去之后,这份售货员的工作仅仅成了“jobs that pay rent(为交房租的工作)”。上班从此成了一件面目可憎的事。

打工的商场
那段时间我不合时宜地看起《我在底层的生活》(Nickel and Dimed),专栏作家为了写作,化身服务员、超市售货员和清洁工,深入体察美国底层人民的日常。他们隐身在咖啡店、快餐店、超市,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但又从未被人注意。他们的生活只有无尽的黯淡,微薄的收入又都回到了资本家的腰包。
5月的德国,冷得像深秋,天总是阴的。骑车去上班,风吹在脸上,总有一种被迫去接受什么的悲凉。
上班时看着顾客来来往往,拿起一件件花哨而无用的商品爱不释手,我有时会忍不住默默地骂着这些不开眼的同是劳动者的人们,白白地把血汗钱拱手送出去。我也在痛骂老板,就算把钱发到员工手上,也要变着法子拿回来。所谓员工购物打8折的“福利”,好像给了员工多少甜头似的,实则不过是机关算尽罢了。
店里有一个大柜子专门给员工用,我们上货时要是碰到喜欢的东西,可以把东西放在柜子里,下了班买回去。有一个女同事,每次上班的第一个小时,至少要放四五件衣服在柜子里,下了班不走,留在店里继续逛,不买走几件不行。每当看见这位同事,《我在底层的生活》里的字句就会萦绕在我脑子里,我想她这班算是白上了。
三
在一个不用上班、不用上课的星期天,我看完了这本书,有气无力地躺在沙发上,对室友说实在干不下去这份剥削人的工作了。
他一惊,拉我起来,和我面对面坐着,问:“这工作哪里剥削你了?”
我指了指这本书,讲了书里人物的生活,又和自己做了比较,怨恨地说:“哪里都在剥削。”
他说:“你一周只工作20小时,挣的钱虽然不多,但足以让你在这座小城里住着舒适的公寓,交完房租,剩余的钱也完全能够支付你的生活费和书钱。另外,雇主还给你交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护理保险,这些算下来可是一大笔钱。”
我环顾我们的公寓,多肉植物静静生长,白玉兰花开得强劲,阳台上一片绿色,窗外蓝天白云。比起书中住集装箱和拖车的人,我们的公寓确实很舒适。室友把我的阴霾心情归为“冬季忧郁症”,都怪德国该死的天气。末了,他说:“最重要的是,你一年有36天的带薪假期。下周我们就去克罗地亚晒太阳了。真的没有人在剥削你。”
又过了一周,凌晨4点,我收拾完匆忙下楼,室友早在车里等候。我跳上车,启程出发。行至静谧的乡间,我将窗户摇下来,空气微凉,远处淡淡几抹朝霞。在曙光中,我们开过奥地利云雾缭绕的群山和斯洛文尼亚幽深的峡谷,一路向南。太阳越升越高,土地也越来越干,植被稀松,尘土飞扬。
我睡了又醒,醒了又睡,直到室友叫醒了我,说“到了”。我打开车门,走到一片白皑皑的岩石边上,湛蓝的亚得里亚海一直延展到天边,阳光像一层薄纱,温柔地将我包裹。心瞬间静了下来。人类被世间琐事搅得心烦意乱,只有站在大自然跟前,才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才恢复些许理智。那一片海,我看了好久好久。
原来我既不是小说家笔下体验生活的浪漫人物,也不是被资本家剥削的劳动者。我只是一个平淡真实的普通人,边念书边做着一份简单的兼职,这份兼职的薪酬能担负我现在的生活,也让我能在初夏时节静静地看着地中海。度假结束后回去,同事们和气地跟我问好,顾客依然络绎不绝,音响里循环播放着流行歌曲。我把一箱箱的商品从仓库里拉出来,开始一天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