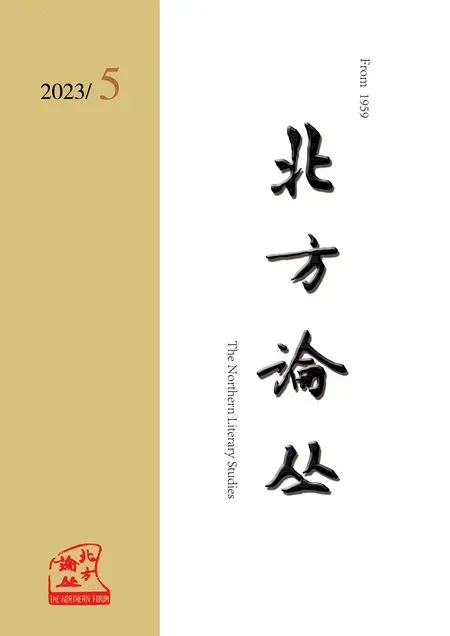郑玄笺《诗》的家国情怀及其现实意义
孙永娟
清代戴震曾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1]140这段话,明确了解释经文训诂与义理两者不可偏废,也明确指出了经传的关系。古人对经典的神圣性的膜拜,致使在经传关系、疏注关系中都在强调不可破。在汉代丰富、精审的字句训诂与章句解释过程中,无论怎样注释者都要坚持对经典的纯粹性,但“因事而发,借经传而注我之意,也注家一例。这是墨守不住的”[2]23,郑玄也是如此。郑玄在笺诗过程中,坚持字斟句酌、实事求是,他宏通博大、无所不包地百科全书式地解读《诗经》,但是他是汉代的人,汉代的政治和生活环境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郑玄身处汉末,外戚和宦官集团交替擅权且互相倾轧,党锢之祸触目惊心。古人之意与现实情境的对照之下,郑玄会不自觉地隐曲表达对乱世的无奈、对时政的讽刺,也希冀用这种方式能唤醒世人,尤其是振奋士人的信心,重建道德秩序、重建理想的清明世界。郑玄在《诗经》注释中字里行间流溢出对现实世界的思考与反思,主要表现在笺释中流露出的悼国伤己之情、对现实政治的怨刺之情、对当下生活细微的体察。
一、“悔仕之辞”与郑玄的感伤时事之语
汉末的第一次党锢之祸,郑玄未被牵连其中。第二次党祸一开始,郑玄与同乡孙嵩等四十余人都被禁锢,这一禁锢就是十四年,而这十四年郑玄“隐修经业,杜门不出”[3]1657。众所周知,孔子不遇,退而作《春秋》,因史见意。郑玄追寻孔子之志,立下向志——“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3]1209,这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当时社会情形之下,作为一代大儒于笺诗中关切家国天下,寄寓伤己之情,实在情理之中。
清代学者陈澧《东塾读书记》中引《小雅·桑扈》《小雅·小宛》《小雅·雨无正》三首诗中笺注指出:
《郑笺》有感伤时事之语。《桑扈》“不戢不难,受福不那”,笺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敛以先王之法,不自难以亡国之戒,则其受福禄亦不多也”,此盖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笺云:“喻有万民不能治,则能治者将得之”,此盖痛汉室将亡而曹氏将得之也;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笺云:“衰乱之世,贤人君子,虽无罪,犹恐惧”,此盖伤党锢之祸也;《雨无正》“维曰于仕,孔棘且殆”,笺云:“居今衰乱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迮且危”,此郑君所以屡被征而不仕乎?郑君居衰乱之世,其感伤之语有自然流露者,但笺注之体谨严,不溢出于经文之外耳。[4]276
陈澧的评说可谓确切。《小雅·桑扈》笺:“衰乱之世,贤人君子,虽无罪,犹恐惧。”[5]970此郑玄伤悼士人无罪却被禁锢,身如浮萍,内心充满忧惧之情,可见王政暴虐至极。《小雅·小宛》笺:“蒲卢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煦育养之,以成其子,喻有万民不能治,则能治者将得之。”[5]969此句是郑玄感慨汉室将亡,深含忧愁之情。《小雅·雨无正》笺:“居今衰乱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迮且危急。”写世道衰乱,欲隐也。陈澧还指出:“郑君启告昭烈治乱之道,其语惜乎不传,然诸经郑注言治乱之道亦备矣。启告昭烈之语,必有其在内矣。”[4]276郑玄在笺诗之中,贯穿对家国兴衰、治乱的关切之语。《郑笺》在笺诗中悼国伤己之情也见于其他篇章:
《小雅·都人士》“我不见兮,言从之迈”,《笺》:“言亦我也。迈,行也。我今不见士女此饰,心思之,欲从之行。言己忧闷,欲自杀,求从古人。”[5]1062这句诗,《毛传》并未做注,《郑笺》从服饰的古之有仪、今之奢淫的区别,欲追慕古者的仪容有法度。清代邓翔进一步阐发:“不知者以为其饰也,而知者以为其礼也,且世必太平乃为此容饰也。”[6]607可谓揭示了郑玄的深意:古之好,不仅有仪度,更在于天下太平。接下来的“言己忧闷,欲自杀,求从古人”为评说之语,也是郑玄的内心剖白——忧郁苦楚至极,甚至到了自杀地步,此也为禁锢之下士人的真实状态,隐微地揭示当时党锢之祸对士人内心的迫害至深。“伤今不如古”是《郑笺》常见之意,古今之对比,就是影射汉代政治的衰败。
《小雅·苕之华》“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笺》:“我,我王也。知王之为政如此,则己之生不如不生也。自伤逢今世之难,忧闵之甚。”[5]1076此句解释中,“伤逢今世之难,忧闵之甚”也是评说之语,郑玄曾无限感叹地说:“汉世之事,谁与正之。”[3]2006由此可见,此评说之语,更多是郑玄对所处时代的忧心忡忡,是对现实的影射。清代郝懿行《诗说》评价这两句“极为深痛”[7]445,也是缘于“乙巳、丙午三四年,数百里赤地不毛,人皆相食,鬻卖男女者,廉其价不得售,率枕藉而死,景象目所亲睹”[7]445,可见,解诗者多会由诗思及现实之境。
《小雅·小明》“心之忧矣,自诒伊戚”,《笺》:“诒,遗也。我冒乱世而仕,自遗此忧。悔仕之辞。”[5]997郑玄用“悔仕之辞”紧扣《诗序》之“大夫悔仕于乱世也”[5]997,此为重申,可见郑玄对这四个字的深刻理解。郑玄对汉末政治,始终采取的是回避态度,这是智者回应黑暗复杂政局的最好方式。“悔仕之辞”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学术态度的最早体现,也可以说是郑玄一生拒不做官的清醒态度的再现。但作为儒学大师,他的信念和对人世的关怀,却又使他并不能置身事外。于是才有了对家国、对同时代人的关切之心,这点也恰恰验证了他在笺诗之中所寄予的家国、时事及自身之感慨。刘成德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说明,在此不再赘述[8]127。
二、“曲笔微言”与郑笺的政治讽谕
孔子的春秋笔法,也是源于《诗》中所蕴藏的讽语,“孔子秉承诗学之讽语,运用属辞比事的春秋笔法而得出相关褒贬义例,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9]54。郑玄也说:“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5]554可见,儒家传统的曲笔微言也是从《诗》开始的。
郑玄“以政立教”思想贯穿于所注群经之间,从政教的角度解说诗义也是汉代诗说的一大特色。皮锡瑞《经学历史》中评价汉儒:“以《禹贡》治河,以《洪范》查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10]90当然,这与《诗》最初的功用密切相关。《诗》之始是用于礼乐的场合,就是主文明教化的。到了汉代,在阐释《诗经》的过程中“将这种‘讽谏’扩大、增强了,这差不多已成为对《诗经》的一种再创作”[11]112。郑玄在《诗谱序》中鲜明地指出:“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5]555诗具有颂美与刺恶的政治作用,也可以说是基本职能。诗必须或美或刺,从而达到崇善戒恶的教化作用。
而郑玄又亲见东汉末年朝廷衰微、宦党倾轧的政治形势,也感受到政治迫害的残酷。“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往车虽折,而来軫方遒”[3]2043,对于士人来说,生死已经是基本需求。因此郑玄笺诗“并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而是要表达“对重建以礼制为框架的社会秩序的向往”[12]351。
鉴于以上原因,郑玄在笺诗中会借题发挥,与现实社会相联系,隐曲表达对所处时代政治的讽刺是难免的。
(一)借助《诗》中自然现象隐喻时政,表达讽刺
《邶风·柏舟》:“日居月诸,胡迭而微。”《笺》:“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谓亏伤也。君道当常明如日,而月有亏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专恣,则日如月然。”[5]625此笺释之语,用日月比兴君王,应和诗序之意。“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专恣”讽刺君王失道,“今”既是诗中之时,也让人联想到汉末君王的昏庸。
《邺风·北风》:“北风其凉,雨雪其秀。”《笺》:“寒凉之风,病害万物。兴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乱。”[5]654“惠而好我,携手同行”,《笺》:“性仁爱而又好我者,与我相携持同道而去。疾时政也。”[5]654在郑玄看来,风与雨雪肆虐的恶劣天气,是兴喻君主“政教酷暴”。郑笺没有涉及具体的君主,而是讲“疾时政”,用了较宽泛的阐释,曲笔写尽汉代之政的酷虐。此类情况比较多,如下三首也是如此。
《小雅·正月》:“瞻彼中林,侯薪侯蒸。”《郑笺》:“林中大木之处,而维有薪蒸尔。喻朝廷宜有贤者,而但聚小人。”[5]948郑玄进一步解释了林中树木杂芜,是比喻朝廷平庸无能,对贤臣得不到重用的而感到惋惜。
《小雅·四月》:“冬日烈烈,飘风发发。”《笺》云:“言王为酷虐惨毒之政如冬日之烈烈矣,其亟急行于天下如飘风之疾也。”[5]992诗句写冬天的景象,《传》未做解释,郑玄则是重复诗句的解释,意在强调“王为酷虐惨毒之政”。对政治的暴虐的强调,也是对当下的一种揭示。
(二)点明《诗》中时政之语,语用双关,直指当下
《大雅·民劳》:“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笺》:“谨,犹慎也。良,善。式,用。遏,止也。王无政听于诡人之善不肯行而随人之恶者,以此敕慎无善之人,又用此止为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疾时有之。”[5]280-281此句的笺释之语,与《毛传》注说相类似,单单只在篇末增加了“疾时有之”的评语,可见郑玄是着重点出此语。“疾时有之”是可有可无之句,但放在最后点出,可见出郑玄用语有双关之意,即针对古代社会,也曲折反映现实,表达自己对当时社会统治者的不满情绪。
《小雅·节南山》:“君子如届,俾民心阕。君子如夷,恶怒是违。”《笺》:“届,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诚之道,则民鞠讻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则民乖争之情去。言民之失,由于上可反复也。”[5]945君子,是指在位者。此句原意是,在位者如行至诚之道,则民心知止息。在位者如果行平易之道,则民不平之气亦去矣。点出君王决策是否正确,决定百姓是否依附。这些也从另一面表明与郑玄的“正变说”相通,以“正”寄托理想于往古,以“变”借历史讽刺当今社会。
《小雅·十月之交》:“今此下民,亦孔之哀。”《笺》:“君臣失道,灾害将起,故下民亦甚可哀……臣不事君,乱之阶也。”[5]955君臣如果不遵守秩序,灾祸就会来临。专断用事的大臣、祸国殃民的小人造成了乱世衰微的局面,这也是郑玄所处乱世的情形,他以此刺寓当时的政治现象。《郑笺》屡次提到“避小人之害”,这是为政者基本的操守,也是各个时代政治清明必备的条件。
《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笺》:“兴者,蝇之为虫,污白使黑;污白使黑,喻佞人变乱善恶。”[5]1039此句是郑玄在《毛传》基础上做进一步阐释,这种虫子变乱黑白,不能近之,用此来兴谗佞之人变乱善恶,混乱朝政。以此告诫当今统治者不要亲近此类人,可以见出郑玄对时政的关切,此乃儒家风范的体现。
(三)用《诗》中所涉及历史现实,隐喻当下
《诗经》大小雅、颂中的一些篇章与西周历史、文明的兴衰过程是一致的。《毛诗序》会叙写所对应的历史人物及历史现象,《毛传》几乎不在具体诗句阐释中提及史实与人物,郑玄在笺释中却在叙述史实中,讽喻当下。
《小雅·节南山》:“琐琐姻亚,则无膴仕”,《笺》:“婿之父曰姻。琐琐昏姻,妻党之小人,无厚任用之。置之大位,重其禄也。”[5]945汉代社会多是少儿称帝,尤其是东汉从和帝开始,每个皇帝都年少,甚至是幼儿时候登基。比如,和帝1岁登基,顺帝11岁登基,冲帝2岁登基,质帝8岁登基,献帝9岁登基。小儿称帝,必然是母后当政,母后自然依靠外戚。郑玄历经东汉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少帝,对外戚当道的王朝统治的弊端体会至深。
《大雅·抑》:“彼童而角,实虹小子。”《传》:“童,羊之角者。”《笺》则解释为:“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喻与政事有害也。”[5]1039郑玄在《毛传》的基础上把童羊进一步比喻为皇后,角者则比喻于与政事有害者,这是直接指向皇后的。这是郑玄所处时代的事实:桓帝时期共三位皇后,第一位梁皇后嫉妒嫔妃,凡是妊娠者都堕其胎,行为卑劣,被废;第二位邓皇后,也自恃位尊,骄横嫉妒,被废;汉桓帝死于第三位窦皇后之前,汉桓帝死后,窦皇后立即对桓帝生前宠爱的嫔妃发难。《郑笺》的比喻直接点出皇后,为影射当时三朝皇后。
《大雅·瞻仰》:“哲夫成城,哲妇倾城。”《笺》:“丈夫,阳也。阳动故多谋虑则成国。妇人,阴也。阴静故多谋虑乃乱国。”[5]1244郑玄这一观点,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以阴阳动静来兴比男女的行为职责。最后一句“阴静故多谋虑乱国”,也是汉代妇人谋虑过多,参与国政的现实情况。
(四)用表达怨望的情绪之语,彰显爱憎
《郑笺》笺释用疾、斥、忧、恨、责等词语,表达怨刺之意,这表明《郑笺》的训释,由字词句发展到带有主观意识的评论。这些情绪和讽谏词语的运用,传递自己对现实的讽喻,彰显爱憎。所刺内容多为君主淫于美色,不理朝政,亲近任用小人等,从笺释的字里行间读者就能够感受到义愤之气、不平之情。
《邶风·北风》:“惠而好我,携手同行。”《笺》:“性仁爱而又好我者,与我相携持同道而去。疾时政也。”[5]654此诗的诗旨,《毛传》说为“刺乱”之作,今人多从于省吾先生的婚变说。在此不论述篇章主旨,只看《郑笺》“疾时政”,愤恨之情,溢出笔端,此为曲笔之言,隐喻当下。且同行之人“归有德”(下一章“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毛传》注),这也是控诉君政暴酷一种方式。
《王风·黍离》:“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笺》:“远乎,苍天!仰诉其察己言也。此亡国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5]689《黍离》篇三章,章尾皆是:“此何人哉。”诗人怨之深切,抒发得淋漓尽致。郑玄在笺释中,用一“疾”字,进一步申说强烈情绪。既是郑玄对诗中情景的体会,也是对现实社会的反应,用强烈的语气和情感表达出自己所处时代的执政者的不满。
《大雅·瞻卬》:“天何以刺,何神不富。”《笺》:“介,甲也。王之为政,既无过恶,天何以责王见变异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灾害也?王不念此而改修德,乃舍女被甲夷狄来侵犯中国者,反与我相怨。谓其疾怨群臣叛违也。”[5]1246此篇是周的大臣对现实的哀叹之诗。此句明显是反问:神为什么不赐福给我们?郑玄在解释这句之后,又进一步揭示作诗者的控诉与愤懑:王不知道改修德教,不应该舍弃的舍弃了,反过来却怨恨我。只因为我不阿谀奉承王的旨意,不与群臣同流合污。然后郑玄直接点明,这句话作者是“疾怨群臣叛违”,郑玄也借此表达对时政中权臣的“疾怨”。
《大雅·板》:“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笺》:“天斥王也。王方欲艰难天下之民,又方变更先王之道。臣乎,女无宪宪然,无沓沓然为之制法度,达其意,以成其恶。”[5]1183《笺》一开始就亮出评价之语“天斥王”,足见对王之为政昏聩的愤懑之情。接下来,解释诗句:王想变化先王之道,行邪僻之政,你等臣子,通达王意,从而助之,使王成恶。郑玄的这一解释,影响了孔颖达疏及至今人的阐释。
《小雅·裳裳者华》:“我觏之子,我心冩兮,我心冩兮,是以有誉处兮。”《笺》:“覯,见也。之子,是子也,谓古之明王也。言我得见古之明王,则我心所忧,写而去矣。我心所忧既写,是则君臣相与,声誉常处也。忧者,忧谗谄并进。”[5]1030诗句是写诗人遇谗绝世,伤古思今。郑玄也进一步阐释诗句:我得见古之是子,即古之明王,那我心所忧伤的谗谄之事,写除而去。我心的忧愁既然已经卸除,君臣是以有声誉之美而处之。接下来,郑玄揭示出诗人作诗之旨:自己由谗见绝,因此忧而思之。以古之讽今之意可见。
《小雅·雨无正》:“昔尔出居,谁从作尔室。”《笺》:“往始离居之时,谁随为女作室?女犹自作之耳。今反以无室家距我。恨之辞。”[5]961-962此篇作者抨击了自己的同僚及当时王共大臣不尽王事、自私误国。郑玄用“恨之辞”传递出强烈的愤怒。
《邶风·旄丘》:“何其处也,必有与也。”《笺》:“我君何以处于此乎,必以卫有仁义之道故也,责卫今不行仁义。”“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笺》:“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必以卫有功德故也。又责卫今不务功德也。”[5]644《旄丘》篇是黎国的臣子责备卫伯不救助之诗。此两句诗是整首诗的第二章,诗者自问自答,郑玄在解释诗句之意后,分别点明诗句的言外之意“责卫今不行仁义”“又责卫今不务功德也”。
(五)揭示诗中古今不同,厚古薄今以警当下执政者
郑玄经常揭示诗中作者对比古今之不同,向往古之醇厚,今之薄情,以此来劝诫在位者。《郑笺》中多用“今不然”来点明此种情况,以下三则,皆是。
《郑风·萚兮》:“萚兮萚兮,风其吹女。”《笺》:“槁谓木叶也,木叶槁待风乃落,兴者,风喻号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5]721郑玄此处沿用毛传所指出的兴意,点明君行明政,则臣跟随,用“刺今不然”,指明现在是君不明,臣不随。
《小雅·菀柳》:“有菀者柳,不尚息焉。”《笺》:“尚庶几也,有菀然枝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岂有不庶几欲就之止息乎,兴者,喻王有盛德则天下皆庶几愿往朝焉,忧今不然。”[5]1056此处,郑玄点明为兴,所兴是用古之君王有德的行为,能引得众望所归。用“忧今不然”,来对比当今的执政者无德之行。
《小雅·都人士》:“行归于周,万民所望”,《笺》:“于,于也,都人之士所行要归于忠信,其余万民寡识者咸瞻望而法效之,又疾今不然。”[5]1060“疾今不然”,是郑玄对诗意的进一步挖掘,点明上行下效之意。
当然,也有不出现“今不然”的,如前面所讲《小雅·裳裳者华》“我觏之子,我心冩兮”句,下面再举一例:
《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笺》:“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时,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则衣狐裘,黄黄然取温裕而已。其动作容貌既有常,吐口言语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责以过差。”[5]1060郑玄在解释诗句之后,总结“疾今奢淫,不自责以过差”,思古人之善,以刺今人之恶。
《郑笺》强调美刺,关注现实,主要目的是要通过笺释,引导为政者、百姓崇善,戒恶,以伦理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就如郑玄所尊崇的“文武之德,光熙前绪”[5]555,由此可见《郑笺》极力推崇君王的德行,也向往明君贤人。乱世思贤君,这是《郑笺》纡曲的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也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讽刺。
1.不断强调德在为政中的重要。如《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笺》:“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无常家也,勤于德者则得之。”[5]969《笺》紧承《毛传》之意,申发此句是喻指域中之有王位,有德能勤治之者则得处之。郑玄借对此诗句的解释,表明王一定要修德以固位。
《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笺》:“文王应天之命,度始灵台之基址,营表其位。众民则筑作,不设期日而成之。言说文王之德,劝其事,忘己劳也。观台而曰灵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5]1129郑玄对这句诗的笺释,用字较多,极力赞美文王之美德感染百姓,忘记自己的劳苦,很快建成灵台。接着《郑笺》又解释了灵台名字的由来,也因文王之功德而名。
在这类笺释中,郑玄强调了为政之德,关于此点刘伟《郑玄“以德笺诗”文学思想研究》[13]有所阐释,不再赘述。
2.贤君名臣,国兴之根本。在此类笺释中,郑玄首先表达了对贤人的渴求,表达了思贤之心强烈。如《邶风·简兮》“云谁之思?西方美人。”《笺》:“我谁思乎?思周室之贤者,以其宜荐硕人,与在王位。”[5]651关于此诗之主旨,在此不探讨。郑玄进一步指出,美人为贤者。《小雅·白驹》“所谓伊人,于焉逍遥”,《笺》:“所谓是乘白驹而去之贤人,今于何游息乎?思之甚也。”[5]928笺中直接点明,“伊人”为贤人。除了单纯表达对贤者的向往之外,也对贤臣的表率有了进一步的阐释。
在郑玄的内心建构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如《小雅·南山有台》,郑笺在《序》后曰:“人君得贤,则其德广大坚固,如南山之有基趾。”[5]897“南山有台,北山有莱”,《笺》:“兴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盖 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贤臣,以自尊显。”[5]897指出太平政治的实现来自任贤使能,国君得贤臣,国家就会像南山一样具有坚实的根基,牢不可破。表达了对贤人政治理想的渴望。
《大雅·思齐》:“不显亦临,无射亦保。”《传》解释句意,《笺》云:“临,视也。保,犹居也。文王之在辟廱也,有贤才之质而不明者,亦得观于礼;于六艺无射才者,亦得居于位,言养善使之积小致高大。”[5]1112其中除去对字词的解释之外,都为《笺》所生发之语,点明文王识才,又能养才,赞叹文王任贤之胸襟。《郑笺》在对大雅和颂的笺释中,依据诗意,无数次着重强调了成就圣王的重要条件是对贤能之士的培养、尊重与任用。
《周颂· 维天之命》:“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笺》 “……文王之施德教之无倦已,美其与天同功也。以嘉美之道饶衍与我,我其聚敛之以制法度,以大顺我文王之意,谓为《周礼》六官之职也……”[5]1258郑玄在此所作的笺注就包含着他的政治蓝图:德教与法度合一。这个蓝图最终的落脚点在礼制上,也是郑玄以礼制垂世立教的呈现。郑玄也想借此“收拾士人的心灵,导之于执中履常之道”。[14]134、596-618
从上述笺释可见,《郑笺》中刻画明君贤人的形象是君王要勤于德,教令行于四方,身先士卒;臣子要行君政令,与王一心等。《郑笺》的政治理想的构建,是图景般的描绘,是美好的憧憬。无论是对世代兴衰的总结,还是对往古的向往,郑玄都表现出对明君贤臣的赞美,借以影射现实政治,也是对现实的不满,“人心不古”则思古。
总之,郑玄身处末世,对政治的黑暗、腐朽感受深切,他是以更为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来理解诗之怨刺功能和笺释刺诗的。对政治的怨刺之情,《郑笺》在阐发时,注重挖掘诗中的微义,显其隐略,彰其意蕴,寄寓现实的之境况、之情绪,寄寓对现实政治的讽谏。
三、“尽己之情”与郑笺的现实生活带入
男女爱恋、诸多情义、家庭生活是《诗经》的重要内容之一,《郑笺》在笺释此类诗歌中,饱含情感,所传递出的生活态度和对生命的深情体验,令人动容。此类例子很多,几乎《国风》每首诗的笺释,《郑笺》能够依据诗的风格进行诠释,能够较为恰当的表达自己的理解与体悟。
(一)人间至情的体察
《周南·汝坟》:“虽则如燬,父母孔迩”,《传》中只解释了具体的字义,《笺》则云:“辟此勤劳之处,或时得罪,父母甚近,当念之,以免于害,不能为疏远者计也。”[5]594虽然王室之事酷烈如火,也得尽力做好王室之事,不能逃避;如果逃避,就会获罪,连累父母,只能黾勉从之。对父母之爱,必护父母周全,不能逃脱王室繁重之务,《郑笺》体察出诗中人物的内心纠结和于现实无奈之情。
《祈父》:“胡转予于恤,有母之尸饔!”《传》:“尸,陈也。熟食曰饔。”《笺》:己从军,而母为父陈馔饮食之具,自伤不得供养也。”[5]928诗人叙说自己的忧虑,无定居之所,朝不保夕;关键是还挂念母亲炊食劳作之苦。郑玄接着直接点明,诗人伤感不得奉养父母。
《小雅·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笺》:“哀哀者,恨不得终养父母,报其生长己之苦。”[5]986父母之情,是人生最根本的情感之源。不能终养父母,此哀哀之恨,为人之常情。这既与郑玄对汉末社会现实的感受密切相关,也同古诗及建安诗歌普遍具有的悲伤情调有着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
以上两则,郑玄的解读,使得诗人爱父母、意深长的情感跃然纸上。
(二)夫妻大义,婚姻观的传递
《礼记·昏义》:“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14]3647可见中国早期就把男女、夫妇礼教纳入至高的层面。娴于礼法的郑玄自然也是如此,对夫妻之道特别重视。
《邶风·绿衣》:“我思古人,实获我心”,《传》:“古之君子,实得我之心也。”《笺》:“古之圣人制礼者,使夫妇有道,妻妾贵贱各有次序。”[5]627可见传笺的所解释的重点不同,传重在解释句意,笺重在对夫妇之道的阐释,“妻妾贵贱各有次序”,强调一家之内秩序的重要。
《邶风·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笺》:“此二菜者,蔓菁与葍之类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时,有恶时,采之者不可以根恶时并弃其叶,喻夫妇以礼义合,颜色相亲,亦不可以颜色衰,弃其相与之礼。”[5]639此处郑玄点明喻义,强调了夫妇之间,不能重美色,而是要以礼义合。
《齐风·南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传》:“必告父母庙。”《笺》:“取妻之礼,议于生者,卜于死者,此之谓告。”[5]746《笺》比《传》多一层“卜于死者”,足见《笺》对婚姻的重视程度。这也符合郑玄重视礼的一贯态度,夫妇始合要以礼正之,不仅要告知父母,还要卜于死者,六礼备,然后得娶。
至于《唐风· 葛生》“ 夏之日,冬之夜”,《笺》:“ 思者于昼夜之长时尤甚,故极之以尽情。”[5]778及“ 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笺》:“ 居,坟墓也。言此者,妇人专一,义之。至,情之尽。”[5]778郑玄的笺释则是对夫妻至情的体察,从中可以体察到建安诗歌般忧伤情调。这应该与汉末的社会现实的感受紧密相连。
(三)朋友之谊
郑玄论述友情的重要。如《郑风·子衿》“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传》:“言礼乐不可一日而废。”《笺》:“君子之学,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故思之甚。”《传》《笺》释义迥异,郑玄在此处强调了朋友的重要,与《论语》开篇第一章完全相合。
郑玄看待友情重点放在志向相同上。如《周南·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传》:“宜以琴瑟友乐之。”《笺》:“同志为友。言贤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与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时,乐必作。”[5]572《传》并没有强调“友”,《笺》则一开始就说“同志为友”,后面的解释诗意也围绕着“志同”。
《谷风》:“习习谷风,维风及雨。”《笺》:“习习,和调之貌。东风谓之谷风。兴者,风而有雨则润泽行,喻朋友同志则恩爱成。”[5]985郑玄点出喻义“朋友同志则恩爱成”,孔颖达认为郑玄的比喻是因为“风雨相感故润泽德行,以兴良朋相亲于善友,以成其恩爱”。其实,郑玄在这里强调的还是朋友的“同志”,朋友间的友爱,前提是“同志”。
对于友情,郑玄也有自己见解。如《常棣》“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笺》云:“平犹正也。安宁之时,以礼义相琢磨,则友生急。”[5]872这里郑玄强调朋友要以“礼义相琢磨”,朋友之交有礼、有义,相互切磋勉励。
《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笺》云:“丁丁、嘤,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农之时,与友生於山岩,伐木为勤苦之事,犹以道德相切正也。嘤,两鸟声也。其鸣之志,似于有友道然,故连言之。”[5]877这里强调朋友要以“道德”相切。
《谷风》:“将安将乐,女转弃予。”《传》:“言朋友趋利,穷达相弃。”《笺》:“朋友无大故则不相遗弃。今女以志达而安乐,弃恩忘旧,薄之甚。”[5]985其中“朋友无大故则不相遗弃”,这应是郑玄处友的原则之一。朋友或穷或达,无原则问题,不能相背弃的。
(四)揣摩人意,感同身受
如《邶风·燕燕》“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笺》:“妇人之礼,送迎不出门。今我送是子,乃至于野者,舒己愤,尽己情。”[5]627这首诗的背景是卫庄公无子,庄姜以戴妫的儿子完为自己儿子。庄公死后,完即位,却被州吁所杀。按照当时的礼制,戴妫必须返回母国陈国,庄姜远送戴妫于野,并写了这首诗。郑玄先指出庄姜送戴妫是冲破礼法的,然后郑玄解释为什么庄姜破坏礼法,也要这样做,是“舒己愤,尽己情”,庄姜是为了全“姐妹”情义,更是为了抒发内心的愤怒之情。郑玄的这六个字,饱含着对庄姜失去儿子的哀伤和对戴妨的安慰、同情、惜别与同病相怜等多种情感。
如《卫风·氓》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笺》:“说,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过相除。至于妇人无外事,维以贞信为节。”[5]685男人有事业,即使做错了事情,也可以功过相抵;女人除了守在家之外,没有其他可做之事,只能以贞信为节,这是唯一的选择。郑玄在此对当时男女所处社会的情境做了特别现实的分析。
(五)重视女性德行、礼仪之教
郑玄对于女子德行、礼仪更为重视。在《邶风·日月》“日居月诸”下,郑玄笺释:“日月喻国君与夫人也,当同德其意以治国者,常道也。”[5]628-629又在“日居月诸,出自东方”,笺释:“……言夫人当盛时,与君同位。”可见郑玄对于女子是极为重视的,把后妃地位于与国君置于同等的高度。他对女子地位的重视,更多是把因为女子对君王的德教负有责任。这在很多章节的注释中都有不同角度的阐释。
如《邶风·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裳”,《笺》:“妇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黄,喻乱嫡妾之礼。”[5]626嫡妾秩序,古有定制,而今黄里降为裳,嫡妾易位。郑玄很敏锐的把握到这一点,可见诗人因思古人,整篇以衣言妇人,其实是所有指。国之兴亡,首先看伦理秩序,而微末之间的妾宠而骄,已见国家有失道之败。郑玄《礼记》中注释:“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不使君妾,适妾有敌义,不相亵以劳辱事也。”[5]3182可见在古代嫡妾之间诸多细节皆有定制。
《邶风·泉水》“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笺》:“道也。妇人有出嫁之道,远于亲亲,故礼缘人情,使得归宁。”[5]651《周易·渐》曰:“女归吉,利贞。”[16]130女子出嫁循礼,可获吉祥,利于守持正固。郑玄在此指明妇人的出嫁首先要遵礼法。
《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洵美且都”,《笺》:“洵,信也。言孟姜信美好,且闲习妇礼。”[5]721郑玄在解诗句之后,对孟姜又赞叹道:闲习妇礼。《周官·天官》中提到郑玄的注释:“九嫔、世妇、女御,皆统于冢宰,则王所以治内,可谓至公而尽正矣。郑氏曰:不列夫人于此官者,夫人之于后,犹三公之于王,坐而论妇礼,无官职。”[17]1381于此可见,妇礼于国、于家是多么的重要。
(六)关心民生、民俗
郑玄对百姓的生活极为关切,且能感同身受。《邶风·终风》“寤言不寐,原言则嚏”,《笺》:“言我原思也。嚏读当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忧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5]629这应该是民间传承下来的古语,“人道我”的说法是在今天仍然存在,多是表达是思念之意。《郑笺》对当时所遗留下来的语言的留意,对民风民俗的关注。
《鄘风·载驰》“我行其野,芃芃其麦”[5]676,《毛诗》认为诗人欲行于卫国郊野,且视麦之盛长,《郑笺》言“芃芃”暗指麦未收而民将困,许穆夫人卫国之行应该是在麦盛的春夏之交。《郑笺》从麦子无人来收这一景象,点明了卫国当下国破家亡、百姓流离失所的状况。
由上可见,郑笺之中,大到百姓安康,小到父母之情、夫妻之道、朋友之意等等,无不一一体察。
作为一代大儒郑玄,一生无意于政事,但笺注《毛诗》时蕴藏着强烈的现实寄托。无论是“文王之化”“后妃之德”“美文公”还是“刺奔”“刺时”“刺平王”等等,都是对当下社会的关切。“《郑笺》几乎调动了一切可能的文化资源,将《诗经》转换为非美即刺的史鉴文本,以及承担儒学教化的话语系统”[18]15。由此可见关注现实对于郑玄来说,不仅是倾注自己的情感,融合自己的人生感受,更是对儒家文化立场的坚守与发扬。诚如陈澧所说:“盖自汉季而后,篡弑相仍,攻战日作,夷狄乱中国,佛老蚀圣教,然而经学不衰,仪礼尤重,其源皆出于郑学。”
但需要注意的是,《郑笺》对现实的关注,或伤悼,或怨刺,说体察进行“怨而不怒”式的中和处理,大多是以委婉托讽的形式进行阐释,从而将其纳入了温柔敦厚的规范。因此,《郑笺》对现实关注的感伤之语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没有破坏笺注的谨严体例,没有溢于经文之外,表现出郑玄注经的谨慎态度。正如焦循《毛诗补注》所说:“《毛传》精简,得诗意为多。郑生东汉,是时士大夫重气节,而温柔敦厚之教疏,故其《笺》多迂拙,不如毛氏。”[19]44正如孔颖达所说:“探意太过,得无诬乎!”[5]1350足见郑玄的庄严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