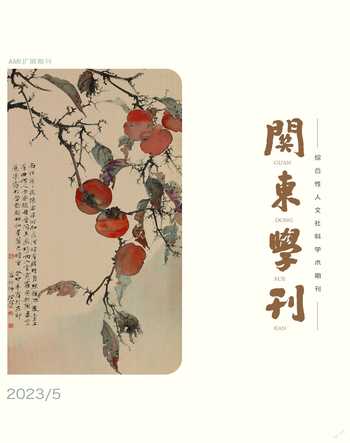社会学视野中的个体化研究:中国议题与本土化思考
杨君 蒋佳妮

[摘 要]从社会学视域看,个体化理论从西方传入中国已有40年之久,个体化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学术界研究得到应用并取得发展,与其所反映的社会变迁背景密切相关。中国的个体化蕴含着个体与国家、个体与社会、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变迁。城乡结构的个体化、家庭领域的脱嵌现象、群体个体化的多样化成为个体化的中国重要议题。本土学者从家庭的伦理与家庭私人领域开展研究,推进个体的生命历程、家庭的代际关系和婚姻关系、个体与国家关系的研究。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生活单位,仍是中国个体化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社会并未出现彻底的个体化现象。除此之外,应同时开展对技术与个体、社会网络与个体、文化与个体的相关研究。中国的个体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何塑造经济上独立、政治上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个体仍然是继续研究的重要主题。
[关键词]中国个体化;国家制度;城乡体制;家庭;本土化
[作者简介]杨君(1987-),男,社会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蒋佳妮(1998-),女,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237)。
在第二现代性语境下,工业主义被资本所裹挟,促使“全球化”势头不可阻挡;互联网技术与交通网络的发展实现了信息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自由市场为女性走出家庭提供机会;“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不知不觉笼罩了整个社会。(解彩霞:《个体化:理论谱系及国家实践——兼论现代性进程中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青海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在反思现代性思潮下,“个体化”越来越成为作为人的独特性、主体性得到展示的代名词,但在社会学领域所蕴含的不仅是自我意识的崛起,更是一种描述社会机制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的重要概念。一些社会团体,如国家、阶级、核心家庭开始消退,个体不再能够从第一现代性中的集体挣脱出来,进行自我选择,而是走上了另一条被社会要求“强制性独立选择”的道路。这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是个体在第二现代性下新的社会生活形式的展现:个体越来越渴望控制自己的生活,打破传统的标准化生活方式,成为生活的原创者,塑造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但这也意味着,个体成为“游荡”的状态,在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之时,也面临难以掌控的后果。这种现象冲击着工业社会的基础,重构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个体化”并不表示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强调一种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理念的价值观,而个体化侧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性;前者所展现的是个体与客观的分离,而后者更坚持一种个体与客观的多重复杂关系。在社会学领域,对个体化研究较为著名的学者包括贝克、鲍曼、吉登斯、埃利亚斯等。在贝克眼里,个体化是高度工业化的福利社会的主要特征,它标志着大团体社会的终结,个人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直接关联,这是一种对个体化含义最鲜明的表达。个体化一方面意味着原有旧的社会形式弱化了对个体的束缚,另一方面新的社会规范重新缠绕在个体身上,无法解脱,这是一个长期贯穿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化过程。([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0页。)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个体化”是人们的身份发生了从“承受者”到“责任者”的转变,表明不仅要自己承担完成任务的责任,也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体现了个体的“自足性”。([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0-26页。.)吉登斯则从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中以及在新型媒体所传递的经验背景下,透视出个体化表现为一种去传统化:个体的日常生活被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辩证影响所重构,同时个体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得以增加,传统的控制性减弱。([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0-130页。)贝克、鲍曼与吉登斯三位学者的论述都表明了现代性反思中个体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但贝克与他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强调的是一种个体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张力:一方面,个体对自由与个性的需求与向往越发强烈;另一方面,个体无法完全实现“自由”,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制度产生依赖。([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等译,第40-50页。)对于现代社会的这一变化,贝克所秉持的是一种乐观的态度,并且认为个体化既是社会高度分化产生的结果,也是实现社会整合的有效条件。在他看来,要经过“脱嵌—去传统—再嵌入”这样一个过程才能够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等译,第40-50页。)贝克的个体化理论较为完备地向我们展示了现代社会的变迁中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把握当前这一个体化阶段的特征。
以上对于个体化的探讨主要是基于一种西方社会语境的研究。个体化理论,尤其是贝克的个体化理论在近四十年的研究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与社会制度使得个体化在中国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贝克的个体化理论对我们理解中国的个体化现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本文重点关注贝克个体化理论在中国的应用以及中国本土研究的拓展,笔者将其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相结合,从宏观层面的城乡个体化、中观层面的家庭个体化与微观层面的群体个体化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国的个体化议题。基于以上论述,笔者试图从现有的研究中展现中国个体化研究的基本议题和基本特征,以此讨论中国本土研究与个体化议题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
一、个体化理论在中国的研究状况
个体化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阎云翔教授是较早运用贝克的个体化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之一。他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描述了以东北下岬村为调查对象所发现的乡村私人生活的变革,这部乡村民族志探讨了此前从未被谈论过的议题。可以说,中国的个体化研究是以关注农村社会的私人生活变迁为开端的。随着现代化和市场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冲击,个体化现象在中国的表现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相关研究逐渐深化与扩展。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个体化”为主题词,并选择社会学及统计学学科来进行相关研究成果的搜索,以此来进一步探析个体化理论与研究在中国的发展。通过计量可视化分析可以看到,至2023年3月其公开发表的文章总数为487篇,其中有368篇为学术期刊,128篇为学位论文,其余为非学术类研究,将其数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从文献数量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个体化方面的研究呈现较为空缺的状态。从2000开始至今,在知网上发布的文章数量呈逐步增长趋势,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0年到2007年,增长幅度较小;第二阶段,在2007年到2013年間,增长速度十分明显,但在2008年到2010年期间稍有回落,而后逐渐大幅上升,2012年到2013年的增幅最大,达到66.7%的增长率;第三阶段,从2013年到2021年,总体趋势仍然呈现上升状态,在2021年到达顶峰,发表文章数量最高为35篇,但增幅相对缓慢,并且有较大的上下波动。从总体情况来看,中国个体化研究的热度逐渐增加,但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仍然十分稀少。
从文献质量来看,期刊来源为北大核心或“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文章数量的增长趋势与所发表的文章总数增长趋势较为相似。如图1所示,在2007年到2013年增幅较为明显,从2013年到2018年,总体浮动趋势相对平稳,其中2015年降幅较大,从20篇减少到14篇。在2019年有回落,随后呈现上升趋势,在2022年达到顶峰,数量为32篇。总体上来看,在发表的文章总数中,北大核心与CSSCI所占比例相对较小,高质量的个体化研究较为缺乏。
二、个体化的中国议题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首先是从农村社会的公共性衰落与家庭空间的私人化中折射出来的,其中蕴含着个体与国家、个体与社会、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变迁。中国社会的个体不仅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同样经历了社会制度变革所带来的环境变化。个体从旧有的形式与束缚中解放之后,呈现出多种状态的个体化表现,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发生改变。本文将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讨论中国的个体化议题,并以此从城乡结构的个体化、家庭领域的脱嵌现象、微观群体个体化的多种表现形式阐述学者的研究成果。
(一)宏观层面的个体化议题
1.中国的城乡结构与社会流动。
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具有上千年的历史。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将公民的户籍分为城市户籍与农村户籍,城乡由此被割裂开来。城市和农村成为封闭性的单位,生产要素受到了十分严格的限制(厉以宁:《走向城乡一体化:建国60年城乡体制的变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并且个体在国家权力的掌控之下形成了强烈的集体与国家意识,可以说行政力量是不同个体之间捆绑在一起的纽带。集体化的国家建设使得整个中国社会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的私人伦理关系经历严重收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带有政治性色彩的“同志”关系所替代。一系列制度的建构将个体深深植根于集体,城市的单位体制承包了居民的生老病死,工作与生活都受到单位的管理与控制,个体很难离开单位而独立生存,对于组织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关系;而农村在国家权力与传统社会规范的双重笼罩之下衍生出了一套新的农民行动指南,很大程度上依靠自治,并且具有较强的封闭性(杨君、徐选国、徐永祥:《迈向服务型社区治理:整体性治理与社会再组织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可以说每个村庄都是一个小社会。由于国家制度的变迁,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与改革开放以后的城市化加大了城乡的发展差距。个体化浪潮首先是在城市中发生的。对于城市来说,资源的集中能够让市民比农民优先获取技术发展带来的福利与各种思想文化的洗礼,追求自我与恋爱自由等。劳动力市场与工业化同时为农民提供了多元化的生存空间,打破了乡村社会的封闭,开放了边界。人口的流动性加快了各种要素的传播,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文化通过流动人口作为媒介渐渐在农村得到扎根与生长。城与乡之间的界限不再分明,二元分割开始走向一体与融合。这是从宏观角度上来探究中国的个体化所发生的社会情境,城乡体制与社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个体的状态改变。
2.城乡个体化表现。
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促进了社会政策的变迁,加强了城乡之间的紧密联系,推动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机制形成,但其造成的最显著后果是乡村社会结构的空心化。一方面,人口流失导致建立在血缘与地缘关系上的社会网络格局发生了改变,流动性不利于稳固社会关系,残存在农村熟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脆弱。因市场经济观念的渗入,利益最大化成为个体之间的交往原则,社会关系逐渐体现出工具性的特征,并且个体之间的关联性减弱,犹如一个个独立的原子,其命运被分割开来,互不相关。另一方面,村民与集体的联结逐渐式微,在“外出务工型村庄”中,村级组织缺乏能力对乡村社会中的成员进行管理与整合,乡村社会内部结构松散。对于脱离农村的个体来说,集体认同感减弱,呈现“去组织化”的状态。(张良:《论乡村社会关系的个体化——“外出务工型村庄”社会关系的特征概括》,《江汉论坛》2017年5期。)市场化的利益导向强化农民的个体意识与理性主义,公共领域中的自我身份逐渐衰落,个体身份逐渐凸显。家庭空间的私人化与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娱乐方式的私人化,将个体与集体更加“割裂”开来,乡土社会中的公共生活逐渐失去了“公共性”(杨君、周自恒:《治理过密化:理解乡村社会中国家联结个人的一种方式》,《公共管理评论》2022年第2期。)。与此同时,村民之间具有的共同历史文化记忆也在逐渐消退。乡村的社会边界虽然在开放和更新,但现代性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冲击着熟人社会的信任环境,乡村空间中的情感边界在逐渐收缩。(杨慧、吕哲臻:《个体化视域下乡村社会情感共同体重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传统的伦理不再是指导个体的行为准则,面临着被冲淡与被遗忘的风险。
(二)中观层面的家庭个体化研究
1.家庭内部个人与个人的关系。
中国学者主要基于家庭与个人的关系和家庭内部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两个视角进行研究。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包括纵向的代际关系和横向的婚姻关系。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最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传统大家庭的瓦解使得小家庭摆脱了父系家族的控制,随之而来的是家庭内部关系的简单化。代际关系的转变是中国家庭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最关键的特征。父辈与子辈之间减少服从的关系,出现一种新型的代际关系,表征为“孝而不顺”的代际亲密关系。(阎云翔、杨雯琦:《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有学者认识到这种代际亲密关系逐渐体现为亲代与子代之间的权责更加明确,也使得代际关系越来越具有建设性,从权威-服从向亲密-协作的模式转变,但转变并未改变“父子同一”的家庭价值。(王海娟:《农民家庭代际关系脱嵌化诱因与效应分析》,《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同时在作为亲属的关系网络中,与亲属的交往成为可选择的互惠关系而不是责无旁贷的义务,个体依然能够发展和保持自身的自主性,可视为一种选择性亲密关系。(张广利、马子琪、赵云亭:《个体化视域下的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演化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4期。)横向婚姻关系的核心是夫妻关系。在传统社会,婚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联结的模式,是一种由传统大家庭或者宗教所规定的形式,自主权很少掌控在自我的手中,夫妻双方不仅是生活共同体,也是经济共同体。但是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趋势表现在家庭从经济领域和工作中分离出来,夫妻双方组成的经济单位开始破裂。现代婚姻虽然逐渐減弱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但是以个体化意志为主,依然受制于制度性的法令,因此,婚姻不仅是一种个体秩序,也是一种“有赖于制度的个体情况”。近年来,中国的婚姻状况发生了很大转变,主要体现为初婚年龄推迟、离婚率攀升、结婚率下滑。一种贝克所谓的“自我文化”在中国社会同样可以看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加注重分离的价值,这些现象折射出人们对“属于自我的空间和时间”的强烈需求。
2.家庭与个人的关系。
“制度化的个人主义”(Kyung-Sup,Chang and Song Min-Young,“The stranded individualizer under compressed modernity:South Korean women in individualization without individualism”,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61,no.3,2010,pp.539-564.)代表着现代社会的核心制度是为个体而配备的,并且这种格局摧毁了原有的社会生存基础,劳动力市场、教育系统等是现代社会生活所必备的构造,为了适应与生存,个体必须被迫重构他们自己的人生轨迹,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个体—家庭的关系重构,改变了家庭的模式属性。由家庭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抉择产生的个人本位还是家庭本位问题在中国家庭研究中引起了热烈的探讨。现代青年人在家庭认同和自我价值之间形成了弹性选择,家庭和个人并非是简单的两极对立关系,(康岚:《代差与代同:新家庭主义价值的兴起》,《青年研究》2012年第3期。)但即使子代在代际关系中有了更多的自由与更多的选择,对于家庭的不可割舍的依赖仍然是其家庭关系的主要特征。(张爱华、岳少华:《个体化抑或家庭主义:河北上村代际关系的实证调查》,《学海》2018年第6期。)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新家庭中心主义不同于传统的家庭主义,它赞扬个人的价值,同时强调家庭利益的优先地位,它将家庭生活的重心从祖辈转移到孙辈身上,从而重新定义了家庭生活的意义。(Yan Yunxiang,“Neo-Familism And The State In Contemporary China”,Urban Anthropology and Studies of Cultural Systems and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vol.47,no.3/4,2018,pp.181-224.)可以看出家庭对于中国的个体而言是很难完全脱离的。当个体难以抵御社会的风险并且受制于社会条件时,甚至会出现与家庭形成更加紧密的代际关系,这一家庭模式被称为“个体家庭”。(沈奕斐:《个体化视角下的城市家庭认同变迁和女性崛起》,《学海》2013年第2期。)通过对近年来中国家庭个体化的研究,多数学者达成一种基本共识:中国家庭并未表现出彻底的个体化倾向,个体在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环境和全球化的风险时,“回归家庭”成为当下中国人最有“保障”的选择,因此家文化也依旧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钥匙。(金文龙:《代际合作理论视野下的隔代照料——兼議中国家庭的个体化》,《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三)微观层面群体个体化的多样化
1.自反性的个体化。
中国的个体化研究立足于个体的生活处境与生命历程,展现个体生活境遇的复杂性,包括自反性的个体化、抵抗性的个体化与默认性的个体化三种状态。(杨君:《个体化的类型学及道德底蕴》,《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11期。)自反性表现为一种被迫性与不确定性,表现为个体在传统生活轨迹破裂的同时,面对选择多样化的世界,为了生存的适应性要求而被迫不断地建立一种更利于自我发展的机制([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等译,第31页。)。从私人领域来说,在个体与家庭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个体利益与家庭利益所产生的张力正通过一种“为自己而活”的心态所体现出来。这种主体性表明个体越来越注重自身的选择和价值,在一些女性、青年和老年人身上尤为明显。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个体化进程中的女性境遇:“女性不再是家庭的‘核心’,她必须像个体一般生活下去;不仅被允许有‘自己的行为’,而且被要求‘有自己的行为’。”([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等译,第73页。)生存和发展资源不再倚重于家庭,社会分工和市场化允许女性通过职业劳动来获取自我价值。她们能够在流动的个体选择中获得积极的身份认同和自主的人生;(吴小英:《主妇化的兴衰——来自个体化视角的阐释》,《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生育层面减少了传统的规范束缚,并越来越成为女性自主规划的一部分。(朱安新、翟学伟:《家庭社会学视角下的女性生育——个体、组织关系转变与女性生育》,《河北学刊》2022年第1期。)老年群体则受到传统观念与个体化思想的冲击与碰撞,在晚年更加注重自我,并更多依赖自我养老,体现了自我需求的实现与代际责任的冲突两者之间的协调。(徐依婷、沈毅:《城市“新老人”的群体特征与代际责任研究》,《中州学刊》2022年第4期。)对于青年来说,个体的自反性不仅仅表现在社会制度和体系之下自我适应性机制中的主体性策略,伴随着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实践弱化,个人意志独立于他人和社会的可能性也逐渐增加,一种自我取向的价值正在强化。独立的人格促进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互动原则的形成,同时对待爱情表现出消极的情感态度导致了越来越多不婚女性的出现。(高夏丽:《个体化视角下不婚女性的情感态度及情感调适研究》,《青年探索》2019年第4期。)“孤立化”的生活态度也同样表现在一部分“空巢青年”身上。他们从群体性的生活状态中脱嵌而出,将“为自己而活”视为一种生存策略和生存智慧,呈现出一种个体化的私人生活方式。(张艳斌:《自由抑或风险:个体化视角下“空巢青年”的双重面向》,《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2.抵抗性的个体化。
中国社会是一个压缩的、仓促的和过渡的风险社会。(Kyung Sup Chang,“China as a Complex Risk Society:Risk Components of Post-Socialist Compressed Modernity”,Temporalités,vol.26,2017.)个体化趋势加剧了个体生存的不确定性和安全感的匮乏,人们在对确定性和秩序化的追求中再次转向共同体。(磨胤伶、王坤:《个体化社会的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马克思共同体视阈下的社会秩序建构》,《广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同时,社会分化与日益显著的差异性会带来个体化时代的自我认同危机,寻找社会身份归属成为了个体的重要精神需求,拥抱集体可视为在这个时代的“抵抗性生存”。正如鲍曼所说,自我身份表现为一种个体化的形式,它实际上是一种实现归属感和拯救共同体意识的尝试。([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第20-26页。)中国文化将集体置于个人之上,集体一直以来是个人创造归属感和归属感强大的和最终的实体。(Yan,Yunxiang,“The Chinese path to individualization”,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61,no.3,2010,pp.489-512.)在广场舞这样的公共生活形式中,很好地凸显了个体对于集体归属的渴求。(杨君:《私人生活的公共转向——基于个体化视角的广场舞分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虽然多数研究表明个体已经部分地从家庭的私人领域中脱嵌出来,但是家庭仍然是中国个体规避风险的“港湾”,对于个体整合与代际团结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子代经济不能独立时,父代所呈现出的资源向下流动的这样一种不平衡的代际关系状态被称为“啃老”现象,特别是在独生子女家庭,两代之间会出现代际经济混合。家庭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情感乃至经济的一体化在新的社会风险条件下,可以成为个体对抗不确定的命运的一种选择。(郑丹丹:《个体化与一体化:三代视域下的代际关系》,《青年研究》2018年第1期。)这种个体的“联合”不仅表现在熟人之间,同样也在陌生人中有所体现。社会团体和组织的力量弱化导致个体身份产生“游离”,也就是脱嵌之后所产生的“无根性”,脱离了集体之后的个体很难获得自我认同。在一个充满变化的外部环境中,个体对于独自承担风险的忧虑或由此产生的孤独感需要通过与人的交往来缓解,因此可能会寻求“融入环境”来维持自己的“本体性安全”(王阳、张攀:《个体化存在与圈群化生活:青年群体的网络社交与圈群现象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2期。)。青年在网络中的圈群化生活体现出这一重要特征。有学者发现“养老式追星”就是这样一种青年在消费社会中参与社会交往的途径,他们重构了基于一定的共认价值的想象共同体来作为集体生活的方式和自我认同的来源,同时也代表着他们对于个体化进程的抵抗性符号表达(Koo Anita,“Negotiating individualisation in neoliberal China:youth transitions amo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rural migrants”,Children's Geographies,vol.19,no.6,2021.)。
3.默认性的个体化。
生活中的个体每天都要面临解决系统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矛盾,风险渗透了个体生活的每个角落。为了逃避风险,选择一种对社会制度的依赖路径,以此形成一种标准化和一致性的生活模式不失为个体化的另一种适应机制。在现代化语境之下,将看似独立和差异的个体放置于社会群体中来看,其实是更趋于一致性的存在。减少思考和自我抉择,在大众文化中寻求新的社会团结体现了现代“单向度的人”([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20-30页。)的特征。因此,个体面对机会的多样性与风险的不确定性,不仅具有自反性的特征,同样也具有“顺从”和“默认”的自我抉择,也是重新整合的体现。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和阶层固化为个体的向上流动制造了更大的阻碍。在中国社会,“考公热”和“考研熱”一时间成为数百万应届高校毕业生所追随的潮流。这种制度性的个人主义实际上已经将众多个体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标准化与平均化,并且“吸引”更多缺乏自主性的盲从者,社会的成功指标变得单一;同时表明了有无数个相同的个体在为了他们同样的理想生活而奔波与奋斗。这种一致性也通过网络空间的无限扩张渗透到了不同个体的自我意识形态之中。网络社群的形成强化了个体的信息吸收的同质化,弹幕和评论对于个人的价值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会产生影响,从而促进一种个体的单向度默从式的行为形成。这是个体意志的外在呈现,同时又是社会环境在个体心中的内化,由此出现了此种默认性的个体化的新型团结形式(吴真:《转向、重构与余问——当代法国个体社会学的进路》,《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1期。)。
三、中国式个体化研究的多重面孔与本土化议题
个体化理论在中国的应用与拓展呈现出了一些中国特色的个体化现象,不论是在家庭层面、社区层面或网络空间等领域都体现了多重面孔。在进行本土化推进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明确中国的个体化状态与西方有何不同。笔者将试图总结中国式个体化多重面孔的体现,并从中国学者所提出的与个体化相关的本土概念与研究议题方面来阐述中国个体化研究的特征。
(一)中国式个体化具有多重面孔
中国特殊的现代化路径和制度环境,决定了中国个体化的复杂性和多重面孔。从家庭层面来看,中国家庭结构呈现核心化现象,规模逐渐缩小,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但同样存在个体更加依靠家庭、拥抱家庭,以此规避外界风险,因此体现出新家庭的代际团结模式。在社区层面,中国的制度变迁虽然促进了个体流动的自由,但同时也改变了社区秩序,导致乡村社会的原子化和空心化,并且由于国家控制下的单位集体制的生活方式消解,城市社区的公共性衰弱也同样面临困境。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国家权力的控制与主导作用。从个体角度来看,既脱离了传统束缚,也在新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嵌入,但中国个体根植于传统的集体文化,不仅追求自我,同样试图寻找身份认同,因此重塑了一种回归集体的公共生活。贝克认为个体在经历“脱嵌”以后,并非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和自由,而是被重新控制和束缚在了新的社会形式中。(张爱华:《贝克的个体化理论以及对研究中国社会的启示》,《理论界》2011年10期。)中国也同样存在一种个体化的悖论。熊万胜等人(熊万胜、李宽、戴纯青:《个体化时代的中国式悖论及其出路——来自一个大都市的经验》,《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发现尽管个体的自由权利扩大了,但兑现这种自由权利的能力却缩小了,他们将其称为“自主性的衰落”,并主张从关系本位和从家庭出发来思考中国个体自主性的建构,强调要把“我”理论化。王建民(王建民:《作为文化转型过程的社会转型——以“差序格局”为例的讨论》,《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9期。)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个体化的本土特征由传统思想文化和市场化改革、制度变革与网络兴起等现实时空情境因素所共同塑造,但中国个体没有经历过生活个体化时代的考验,并且社会保障制度不足以支撑个体应对风险,因此出现了一种矛盾:在越需要个体自我依靠时,个体往往只能通过家庭主义和关系主义来化解“危机”,这进一步限制了独立自主的个体性形成。
为何中国的个体化具有复杂的表现呢?我们又能够在何种意义上理解中国独特的个体化现象呢?中国的个体化叙事体现的不仅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个体与国家在历史变迁中所产生的影响。第一,中国具有独特的现代化路径。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现代化进程,这决定了中国个体化的内涵与西方具有显著的不同,在注重个性的发展与集体发展的统一下,并不鼓励极端的个人主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使得国家权力趋于集中化,因而助长了个体的国家意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城乡体制下的社会生产单位都建立了一种集体意识,特别是在国营企业中,单位制巩固了工人服从于集体与国家的心理;而后,市场化改革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型,权界意识逐渐萌发,个体化的生产方式被重新组织,农村社会得以秩序化,个体的权利与义务开始被逐渐定义与明晰。对于国家来说,治理的对象不再是家族或者单位,而是公民个人。(陈周旺:《权界意识的生长: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形成与国家转型》,《人文杂志》2009年第1期。)由此看来,中国的个体化社会的形成经历了从家族式统治到单位式控制,最终实现对公民个人的法治型管理这样一个过程。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个体化发展方向起到关键的规制作用。从社会思想层面来讲,个体化早在西方个人主义传入中国之际被仅仅理解为功利性取向,这种不全面甚至可以说失衡的理解扩大了其负面影响。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思想价值观念所注入的是凌驾于个体之上的集体本位,中华文化强调“和”的概念,这种思想的根深蒂固与西方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发育不良意味着个体必须面对心理层面上独立自我的建构与传统约束力之间的张力,因而这种矛盾造就了一种既不是个人主义的,也不是集体主义的,在拥有大局观念的同时却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体系。与强调个人特性的西方社会不同,中国是强社会关联性的,不管个体能够如何突破组织形式的限制,但在本质上,其行动仍然受制于网络化的社会关系。第三,中国独特的公共性构造影响了个体化的形成。当单位社会结构逐渐转变为公共社会时,个体与公共体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个体在公共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也更加多元化。契约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一些社会互助团体、市场组织等对个体之间的关联进行了重塑。在充满选择的关系网络中,公共性在一些更为私密化的生活因素中得以体现,例如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保等权利约束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方式,进一步体现为利益关系的组织化(周庆智:《改革与转型:中国基层治理四十年》,《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1期。)。
(二)本土化关键概念的提出
个体化理论在逐渐成为考察中国社会变迁分析工具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一直在做概念化的努力。家庭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个体化时代的中国家庭处在了现代与传统的张力之中,以儒学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家庭观念与礼仪规范在中国人心底仍根深蒂固。与此同时,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潮不断冲击着个体对于家庭的固有认知。因此,中国家庭在第二现代性下走向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中可以发现,家庭领域的本土概念化成果较为显著。笔者在此主要围绕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这一话题来阐述相关学者的观点。从最早的阎云翔教授的研究来说,他启发了众多学者从个体化视角来构建新的分析框架。他观察到由国家主导“私人生活变革”的后果是“无公德个人”的出现,表明在社会变迁中没有产生出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新道德;(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00-250頁。)在后来的研究中,阎云翔又将中国家庭的特殊性纳入了个体化的分析框架,提出“中国社会自我主义”,表明中国的个体化进程使得追求幸福成为新的家庭理想的一部分,但是个人生活的意义深深扎根于人际关系之中,只能以一种“大我”的名义来实现自我利益的追求。(阎云翔、杨雯琦:《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沈奕斐明确将个体化概念与中国家庭的研究案例进行了理论对话。为了体现当代中国的个体面对风险所选择的更加依赖家人的一种家庭模式,她提出了“个体家庭(ifamily)”的概念。(沈奕斐:《个体化视角下的城市家庭认同变迁和女性崛起》,《学海》2013年第2期。)钟晓慧等人对西方的“亲密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的拓展,提出代表中国家庭特点的“协商式亲密关系”概念,包含着与西方所强调的存在于夫妻之间、去物质化的关系不同的一种不脱离物质利益的共同决策与情感寄托的纵向关系。(钟晓慧、何式凝:《协商式亲密关系:独生子女父母对家庭关系和孝道的期待》,《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也有学者从传统文化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家庭的转型。杨善华等人提出了“责任伦理”来分析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方式,老年人对于子女不计回报的付出是其能够实现家庭养老的基础。狄金华等人进一步发现,在个体化时代下,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并未呈现“伦理沦丧”的特征,而是出现一种“伦理转向”的资源下沉的代际支持现象。(狄金华、郑丹丹:《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社会》2016年第1期。)李永萍提出家庭伦理的重构体现为父代单向度付出的实践,让更多老年人陷入了一种“伦理陷阱”,表明老年人在伦理的束缚下面临着一系列养老危机(李永萍:《家庭转型的“伦理陷阱”——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一种阐释路径》,《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2期。)。
(三)研究议题的本土化推进
中国的个体化研究绝不是西方视角的简单复制,从理论反思现实,是中国社会学研究所需要突破的现实瓶颈。从微观层面来看,在研究一些类群体的行动时,中国学者倾向于将其个体化的生命历程作为整体的分析视角,对个体的自主性崛起与所遭遇的困境做出阐述和深入挖掘。周永康(周永康、王荆川:《大流动时代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化生命历程》,《江汉学术》2020年第6期。)等人探究了个体化现象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指出其如何管理和构建自身的生活。这种将个体化理论引入个体生命历程的研究,反映了宏观的社会环境与微观个体之间的互动,有利于深化对社会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思考。同时,在研究中国的个体行动中,中国传统思想的引入成为了本土化的关键。周飞舟曾提出,“要理解中国人的行动意义和精神世界,就不能简单站在‘局外人’的立场,而是要回到中国文明的传统中来”。(周飞舟:《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他进一步强调中国历史中“伦理”的概念,并主张从行动伦理层面切入来解释行动意义与中国传统理念的联系。汪和建提出了一个“自我行动”的分析概念,来表现中国人所特有的以“自我”为中心,且以“关系”为运作空间及手段的行动方式,以此来理解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汪和建:《自我行动的逻辑理解“新传统主义”与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社会》2006年第3期。)
从中观层面来看,家庭仍然是中国学者研究的主要领域,其中的代际关系、婚姻关系是学者较为关注的议题。家庭的伦理价值对于中国个体来说难以割舍。尽管中国社会具有不同的个体化表现形式,我们在一些关于类群体的个体化研究论述中仍然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是行动者所进行生活实践的基础。例如于志强提出了一个关系主义的分析框架,说明了“空巢青年”所呈现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家庭主义与个体意识崛起相互交织的结果,不同于传统的家庭主义而牺牲个体诉求,他们在秉持着婚姻家庭观念的同时,又试图突破世俗化的血缘与伦理联系。(于志强:《关系主义实践:“空巢青年”家庭再生产的机制分析》,《宁夏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金一虹基于个体化理论中的传统化面向研究了流动农民家庭中父权制的延续与重建,流动农民在国家制度的约束和市场主导交互作用下,选择了一种最经济务实、最能适应严酷环境的家庭制度。可以看出,家庭的转型并非呈现了现代化社会变迁冲击下的消极结果,而是一个积极适应变化和抵抗变化的组织。(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于中国具有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国情,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同样是中国学者看待个体化的重要维度。陈周旺(陈周旺:《权界意识的生长: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形成与国家转型》,《人文杂志》2009年第1期。)从国家的视角来阐述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形成历程。他采用严复先生从密尔的《论自由》中所翻译而来的“权界意识”作为关键的分析概念,探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微观社会心理之间的互动。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的是国家的统治方式对于个体意识的影响:从传统的中央集权下的家族观念到国家政权建设所形成的国家意识,再到单位制庇护下让个体与集体更加紧密团结,直至市场化改革推动产权意识的生成,社会利益进一步分化到个体身上,产生了个体与个体之间权利不可侵害的界限。因此,国家作为重要的行动者,其作用对个体化社会的形成是不可忽视的。也有学者在探究个体化时结合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基础,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层面入手来把握中国的个体化进程。王建民(王建民:《作为文化转型过程的社会转型——以“差序格局”为例的讨论》,《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9期。)提出“差序格局”这种社会结构及其背后的自我主义构成了阻滞社会转型的因素,中国的社会转型在根本上受到文化中相对稳定因素的影响,要塑造独立人格的个体,平衡个体性与社会团结之间的平衡,需要进行中国社会思想层面的转变。
四、结论与讨论
如果用西方的个体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必然要对其原有的理论内涵进行深度剖析。贝克所论述的个体化是基于西方社会内部一种嵌入式的民主与福利国家的体系所获得的认识,其具有四项基本特征:第一,它意味着个体首先所面临的是去传统化的束缚;第二,在制度方面产生抽离,原有的一些社会形式消失,但同时产生的新制度使得个体面临再嵌入情境;第三,个体失去了私人领域的庇护后,在主流大众的影响之下被迫追求为自己而活,但缺乏个性的彰显;第四,面对需要独自承担的一系列风险与不确定性容易形成内在化的社会心理问题。([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等译,第7页。)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首先是从农村社会的公共性衰落与家庭空间的私人化中折射出来的,其中蕴含着个体与国家、个体与社会、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变迁。中国社会的个体不仅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同样经历了社会制度变革所带来的环境变化。个体从旧有的形式与束缚中解放之后,呈现出多种状态的个体化表现,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发生改变。本文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讨论中国的个体化议题,并以此从城乡结构的个体化、家庭领域的脱嵌现象、微观群体个体化的多种表现形式阐述学者的研究成果。
个体化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学术界得到应用并取得发展,与其所反映的社会变迁的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在西方社会,二战后福利国家的兴起为社会成员能够脱离家庭,从而获得“独立”状态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生存条件;劳动力市场的繁荣促进了流动,并且成为人们生活个体化背后的动力源泉。这一切所带来的是女性地位的提高、阶层的流动性增加与竞争压力增长等社会变化。贝克认为,教育、流动与竞争相互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其相互补充、强化并共同构成一股力量推动着西方过去几十年的个体化进程。中国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同样也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与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与个体化息息相关。由于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农民的生产方式选择更加自由;随着市场化与城市化的推进,农民获得进城的就业机会,城乡之间的流动大大增加,并且乡村社会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因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确实发生了,高度集中的生活共同体瓦解,人们从私人领域“脱嵌”出来,个人的生活方式呈现更加多元化的状态。对于西方学者的著作中所描述的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迁在中国也同样可以看到,但独特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与文化底蕴决定了中国的个体化是多元性与复杂性相统一的。
自个体化理论引入中国,学术界一直对其争论不断。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十分复杂,并不能用个体化来解释其中所蕴含的本质。贝克通过个体化理论向我们阐明了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变动,同时充分阐释了在其变迁过程中行动者的表现,但并未明确如何能够达到个体化发生所具有的条件,这就导致了对社会文化重要性与社會关联层面所发挥作用的忽视。有学者选择从传统思想切入,进一步拓展研究议题,提出了中国本土化的新概念,将个体化理论的解释维度进行了深化,因此在个体化的本土研究中纳入中国历史文化与制度变迁的视角是十分关键的。基于目前的研究成果,从方法上看,中国的个体化研究在定性层面较为丰富,多数是以剖析西方个体化为主的理论研究和以访谈法为主的实证研究,但所运用的定量研究方法较为缺乏,鲜有用大量的实证数据来论证观点,在个体化研究的统计学意义上需要增强说服力。从研究视角与议题方面来说,由于中国特殊的城乡体制,学者在社会结构层面较为关注城乡关系的制度背景,致力于探究乡村社会的变迁;而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生活单位,仍是中国个体化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家庭在社会变迁的历程中发展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轨迹,传统的家文化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制度环境的变革催生出很多新兴群体,学者更加关注对于不同类群体行动逻辑的个案研究,使我们能够看到个体的具体境遇,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有重要的意义,这与帮助个体更好地生活与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也紧密关联。
通过对现有相关文献的梳理与思考,笔者认为,个体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何塑造出经济上独立、政治上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个体仍然是当前的迫切任务。在未来的研究中,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推进。第一,社会网络与个体化之间的关系。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关系与权力反映了个体的社会资本积累、信息获取与社会支持等方面的个体化差异,进一步投射出的是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第二,技术与个体化之间的关系。中国的个体化是伴随着国家制度的改革、市场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互联网技术的提升而产生的,我们所关注到的更多是生活方式层面的转变,网络空间已经成为我们生存空间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在生产领域,数字化更是催生出了多种新兴产业与职业,其中蕴含着个体与宏观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第三,文化与个体化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的是,第二现代性下的个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被消费主义所深深笼罩,其消费行为的变化反映了个体的价值追求与情感体现,最终形成一种在大众生活层面流动与传播的文化形态。消费不仅是一种符号,更是风险社会中获取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以个人为导向的消费成为现代较为显著的个体化表现。第四,更加微观的个体化群体研究。目前中国学者主要将农民工、青年群体、女性群体和老年群体置于个体化特征的主要分析框架中,但对于新消费群体的研究较少,徐颖(徐颖、范和生:《新型消费模式的蔓延:个体化视角下“一人式”消费的产生与发展》,《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等人所关注到的“一人式”消费正反映了个体化时代的消费形态,为了促进消费的正确与可持续发展,用个体化视角来解释宏观背景与微观个人的心理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我们除了要发现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现象,同样也要关注个体化的悖论,社会学学者要更加致力于探究如何塑造出既具有独立权利意识的个体,又能够促进新的社会团结,以此助推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