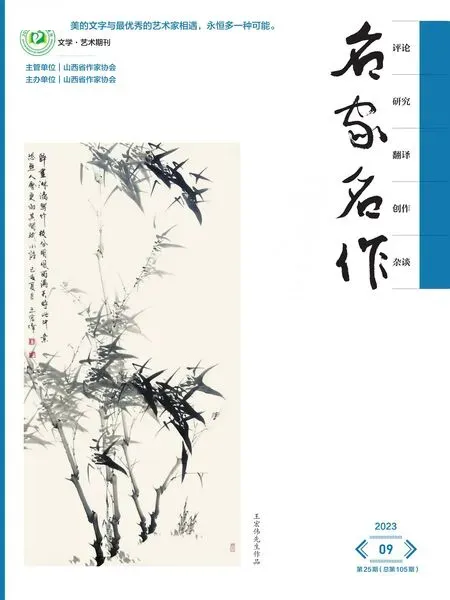对志贺直哉“调和”之路形成过程的研究
——以志贺直哉作品中的“死亡”为线索
孙 可
志贺直哉以白桦派代表作家之一而闻名,活跃于日本大正、昭和时期。他的代表作有《在城崎》《学徒的神》《和解》《暗夜行路》等。其中《在城崎》被公认为日本私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在文学界拥有重要的地位。志贺直哉在《在城崎》中通过对蜜蜂、老鼠、蝾螈三个小动物死亡的描写,表达了自己疗养时期对于死亡的感悟。《在城崎》让大正时期的教养主义在文学界开始流行,同时也开创了调和型私小说(又被称为心境小说)这一新类型。有关死亡的描写在志贺直哉的小说中并不少见,本文尝试从志贺直哉几部作品中对死亡的刻画及思考,解析志贺文学调和之路的形成。
一、对死亡的恐惧与反抗
《为了祖母》与《某个早晨》《母亲的死与新的母亲》都为志贺直哉自身生活的早期作品,三部作品中都包含一个人面对亲人即将去世和去世后的复杂情感。其中《为了祖母》里对死亡的心理活动描写最为丰富,可以说在志贺早期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高桥敏夫(1987)认为《为了祖母》是一个对正在衰弱、崩坏的内部导入来自外部否定的契机,然后为了确保内部的稳定,将外部契机排除的故事。从小说开头的部分可以看出,祖母是“我”的依靠,祖母病倒后,“我”对祖母的死亡产生恐惧,就是高桥所说的来自外部的危机。《为了祖母》中在祖父病逝十五分钟内,患了白化病的殡仪馆员工“羊白头”就赶到现场,高桥认为他是虚构的外部契机。在文中,他“经常揣着两手在路上晃晃悠悠地走动。在我看来,那就像饥饿的肉食动物在搜寻猎物一般”。祖母感冒病危后,“我一定会拼命盯着房间里黑暗的角落,在那里,其实并不能看到羊白头那灰色的眼睛,但我却臆想着——并且尽量——用尽全力紧紧盯着那眼睛”。我认为羊白头这个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象征了死亡,在祖母痊愈,“我”准备带祖母到鹄沼休养时,路过殡仪馆门前没有看到准备办丧事,“‘说不定是羊白头死了!’——仅仅只是猜想就让我胸中悸动不已。……从后面望着前方车里微微露出的矮小的祖母那戴了头巾的脑袋,我很想怒吼一声‘看啊’,但极力克制住了。”“羊白头确实是死了。——关于这件事的含义我丝毫没有怀疑。”从文中“我”强烈的情感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战胜死亡的喜悦。根据高桥的理论,“我”与祖母同属内部整体,而死亡是外部因素,因此《为了祖母》表现出的是“我”与死亡的对峙,即自我与外部的强烈对立。
二、对死亡的胜利
《范的犯罪》是志贺直哉虚构的作品,灵感来源于一位亲戚的遭遇,那位亲戚因妻子出轨而自杀,作者试图在小说中表现出相反的结局。在虚构的情节中,也强烈反映出作者本人的心境。下冈友加(2010)认为,《范的犯罪》通过种种手法让读者代入范某的视角,讲述范某从压抑中解放的故事。现实中亲戚因没能摆脱被背叛的心境而自杀,所以志贺直哉很可能想要将范塑造成一个战胜压抑的具有强烈自我主义的角色。
范某的助手回答法官对夫妻两人品行的询问时答道:“她是个正派的人”“他俩待人都极为和善”。法官问范某:“你此前丝毫没有爱过你的妻子吗?”范某回答:“从结婚那天起直到孩子出生时,我曾经真心爱着她。”法官问妻子是否爱着范某时,妻子回答“不爱”。“我越发觉得,这样瞻前顾后,成天愁眉苦脸,又不敢正视自己内心的愿望,对无比厌恶的事也没有勇气拒绝,这半死不活、窝窝囊囊的日子都是与妻子的关系害的。对自己的未来我看不到一丝光亮。但自己心里还燃烧着寻找光亮的愿望,我要让它燃尽,妨碍这种燃烧的正是我与妻子的关系。而那团火总也不熄灭,还在那里冒着烟勉强地燃烧着。那种不快和煎熬简直就要让自己中毒,彻底中毒时自己就死了。虽然现在活着却成了死人。”从以上描述可以推测出,文中范某的妻子形象来自现实里亲戚的妻子,但除了真正意义上的“妻子”,也象征着范某无法自我原谅的一面,范某与“妻子”都是“正派”且“极为和善”的,彼此都无法爱对方,说明两者有同一性。下冈也在论文中说到,使整个“从压抑中解放”的故事更加坚固地完结的“装置”,就是法官的“无罪”判决。“我想着,终于杀了她。”“此话怎讲?是故意为之的意思吗?”“是的。无意间做了仿佛是故意的事。”“我突然兴奋起来,兴奋到坐立难安的程度。我感到无比愉快,甚至有种想要大喊大叫的冲动。”“对现在的我来说,被判无罪就是一切。我绝不断言这是过失所致,另一方面,我也绝不会说这是故意所为。”“‘可是你对妻子的死,丝毫没有感到悲伤吗?’……‘完全没有。即使是从前对妻子万般憎恶时,也想象不到自己竟然能以如此快活的心情谈论她的死’……法官感到内心涌起了莫名的亢奋。他立刻拿起了笔,接着当场写下了‘无罪’二字。”以上法官对范某下达无罪的描述,看上去是不符合常理的,范某杀害了妻子是不争的事实,而他杀人后的态度是过失还是故意又模棱两可,却使法官亢奋地给出“无罪”判决,这就说明了《范的犯罪》并不是真实地记录针对范某杀妻的审判,而是通过范某的直白,讲述了其战胜自己压抑面的故事。
在《范的犯罪》中,妻子的死亡同样代表胜利,是自己与自己过失的斗争的胜利,对范某“杀死”了自己过失的一面并感到无比愉快的“无罪”判决,是志贺直哉表达战胜过去的强烈自我意识,但是范某本人的纠结与痛苦同时也是志贺本人的梦魇。近代文学研究者红野敏郎评价《范的犯罪》为“志贺文学初期自我扩张的巅峰之作”,而《在城崎:志贺直哉短篇小说集》译者吴菲评论:“这种与周遭激烈对峙的心态,在作者经过数年的沉默与挣扎之后,才找到通往自我调和的出口。”
三、死亡的答案
《在城崎》作为志贺直哉最知名的作品,一直是志贺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而围绕《在城崎》中三种动物:蜜蜂、老鼠、蝾螈的死的解读不计其数。山田伸代(2017)在《志賀直哉の『城の崎にて』をよむ:静かなる生と死》中阐述了对《在城崎》中生与死的理解。山田认为蜜蜂的死对于志贺来说是“独自一人的、孤独的、寂静的”,“只我一人,连个说话的对象也没有”,此时“我”假设了如果因电车事故而死,“现在大约已仰躺在青山墓地的土里了。……身畔是祖父和母亲的尸骸,且相互之间已没有任何交涉。”这里志贺提到了祖父和母亲,志贺其他作品里对两人的描写,《为了祖母》里写祖父“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很了不起。祖父是整个家族的顶梁柱,对祖母而言几乎就是一个偶像”,可以看出祖父是一个被包括作者在内的所有人所敬佩的存在,并且《为了祖母》中的“我”第一次对“羊白头”产生敌意就是因为祖父的死,那样有本事、健壮、被人所敬佩的祖父一死去,病态的“羊白头”仿佛等候多时,令“我”感到可疑,仿佛觉得他在期待着别人的死。而在《母亲的死与新的母亲》中,“我”的生母在病逝时,志贺通过几个侧面描写使读者感受到当时的悲伤,比如“大家都议论说,潮汐退去的时候,人也会随之逝去。听了这个说法,我跑去母亲最初养病的房间,一个人扑在那里哭泣。学仆进来安慰,我问他:‘退潮是几点钟?’学仆回答:‘再过大约一个小时。’我想,母亲再过一个小时就会死吗?‘再过一个小时就会死吗?’不知为何那之后也时常回忆起当时曾这样想过”。不难看出,在志贺早期的作品里,亲人的死令人悲伤,尤其是《为了祖母》里的祖父,即使有本事、身体健康,在死亡面前也是无力的,这使当时的“我”对“羊白头”、对死亡的对抗意识开始觉醒,并在早期作品中逐渐达到巅峰。《在城崎》里则是说到,如有闪失,自己可能已经和祖父、生母一样死去了。因电车事故受伤时,志贺说“如果发展成脊椎骨疡难保不会变成致命伤”,在此担忧下,此刻志贺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始思考死亡的本质,“虽然凄凉,但这想法并未令自己感到多么恐惧,总有一天将会如此。……总是不知不觉地把‘总有一天’当作遥远未来的事,而现在却越发感到那真的是不知何时。……奇特的是,我心里一片宁静。我心中对死亡产生了某种亲近感”,就像《母亲的死与新的母亲》里所说,“‘再过一个小时就会死吗?’不知为何那之后也时常回忆起当时曾这样想过”。而《在城崎》中作者对蜜蜂的描写,真实地说明了这一过程。《在城崎》中也提到之前写的《范的犯罪》,并说:“作品主要描写了范的心情,但现在,我感觉自己更想以范妻的心情为主,描写她被杀后在坟墓中的那种静谧。”上文我分析《范的犯罪》中的范某与妻子的对立可能象征着对立的自我与自我斗争的胜利,而《在城崎》中作者产生了与彼时不同的想法,死亡如此接近,无论是胜利的范某,还是身死的祖父、生母、范妻,等待众生的最后都是静谧。
对于老鼠的死,“老鼠为了不被残杀,虽身负死期已至的命运,依然竭尽全力四处奔逃的情景奇特地刻印在脑海里。我感到凄惨且心生厌倦。我想那才是真实的。”而后又通过描写自己受伤时就医的情形,表达真正面临死亡时的反应,这是人之常情,诉说自己与前文认为死亡很“静谧”“亲切”不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志贺也许认为老鼠的死是还没有认识到死亡本质的阶段,所以“感到心生厌倦”,就像当初还无法和解的自我的挣扎。之后的登山及蝾螈之死的部分,就像众多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志贺感受到生命的无常,生与死的间隔如此之近,用一句“它们并非两个极端”作为《在城崎》思考的结束。
《在城崎》与志贺直哉之前的作品比起来,是一篇颇为温和的小说,文中充满了动与静的对比,劳碌的蜜蜂、挣扎的老鼠、被砸中时跃起的蝾螈,它们是动的,而无论是以自然的方式死去,还是以意外的方式死去,它们最后都归于宁静。对登山时桑叶随风抖动的部分的解释是《在城崎》研究的难题,一直众说纷纭。志贺在《创作余谈》中多次解释了写这段的缘由,其中在《生命》(《在城崎》的初稿)中的解释较为合理,他说:“由于其方向和植物叶柄软硬程度的缘故,只有那片叶子才可以感觉到其他物体所感觉不到的微弱的风。这就好比时钟的秒针精密地不停跳动一样。其他物体也能感受到的那种程度的风刮起来的时候,这片叶子反而会停止抖动。”(肖书文,2006)但就像《范的犯罪》中对杀人行为宣判“无罪”的不合理一样,这里也不必过分追求物理学上的合理性,不妨从文艺的角度去解读。在登山时,拐过几个弯后,“景物都显得苍白,空气凉飕飕的,‘寂静’反而让我有种心神不宁的感觉。”如果把“静”与死亡联系起来,可以解读为还没感悟时对死亡的不安,而那片桑叶先在风中翻动,其他树叶随风而动时它却停止不动,是代表了生前的动到死亡的静的变化,“我”因为观看了忙碌的蜜蜂融入泥土的过程,所以说“自己应该明白其中缘由”。
总之,在《在城崎》中,死亡代表无常、宁静、和谐、万物的最终归宿,也是和自己命运的和解,正如孟子云,“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四、结语
志贺直哉因《在城崎》《暗夜行路》等作品被称为心境小说的代表作家,但他的心境历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早期作品中与死亡的对立,到被称为心境小说的作品中对死亡静谧、纠结、无常的认识,是逐渐发展的。在动荡的昭和时期,人们即使生活还算安定,也会经历众多变故,尤其是以自己的生活为模板进行创作的作家。日本近代史上众多私小说作家为了创作出别具一格的作品,大多过着不同寻常的生活。志贺直哉的心境小说也被称为“调和型”私小说,与之相对的是“破灭型”私小说,代表作家是太宰治。太宰治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以厌世著称的芥川龙之介同样也是自杀,志贺直哉与两位作家都有所交集,芥川龙之介死后,志贺直哉在《沓掛にて—芥川君の事—》中提到,芥川说自己不是适合写小说的人,志贺回道:“谁都有那样的时候,就那样接受不也挺好的吗?抱着冬眠一样的心情休息一两年试试如何,以我的经验,那之后就能写出来了。”
白桦派文豪们经常因为出身较好而遭受非议。包括太宰治在内的许多人评价志贺直哉的作品不够接近平民,芥川龙之介在《文芸的な、余りに文芸的な》里评价志贺直哉,“也许是像神一样活着的人物”。志贺本人的一生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经历过和父亲的不和与决裂、电车事故、自己的两个孩子死去,但他没有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最终破灭,而是对抗死亡、理解死亡并自我和解地活着,就像成为佛一样的神明,但这一切也是有一定的过程的,志贺直哉最终也在暗夜的路中找到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