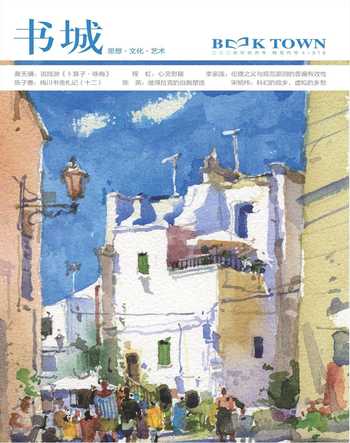在真与美之间
郁隽
“一件事物,非但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皆无碍于其为真,并且正是因为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以才为真;这实在是一项日常智慧。”一百多年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面对慕尼黑的大学生时,说出了上面这句话(《学术与政治》,钱永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这句话一方面展现了一种对现代文明冷峻而清醒的分析,另一方面也流露出些许无奈—人们从内心深处渴望一个整全的世界,能够将真善美这三个基本价值域聚拢乃至统合起来。然而,我们身处的时代不仅仅将个人的职业切碎细分,还将世界区隔为若干个互不相干甚至彼此冲突的领域:在这样一幅未经反思的图景中,求真的任务大致被交托给了“科学”,往日的形而上学和哲学日益隐退幕后;求美的任务好像交付给了“艺术”,然而艺术却常常被其他力量所牵引;而求善的使命则尴尬地“落空”。在越来越多元化、相对化甚至虚无的价值观纷争中,几乎没有哪个学科或者机构敢于承认自己愿意或者能够承担求善的责任。
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对个人而言最为方便的选择就是凸显自己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坚守或者说“退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于是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中均呈现出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的分工。“专业主义”一词既成了对职业人的恭维,但又同时蕴含了某种整体性的盲目。人们将各类事无巨细的问题交托给各学科和专家。然而在看似无所不包的专业领域之外,其实还有更为广阔的“未勘之域”。在专业与专业的空隙处,需要无数的人来穿针引线,互通有无。如今在学院派的研究计划与专著中,“跨学科”几近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而语义空洞的陈词滥调,少有人尝试更遑论真正做到。
这本《一点五维的巴赫》恰是在上述图景中逆流而动的一个“异类”。作者马慧元多年来在这样一片未堪之域中遨游,努力试图沟通“真”与“美”这两大价值域。事情虽然宏大,但她的切入点却是极为具体而精微的—音乐(史)与科学、技术。她的教育和职业背景—既是资深乐迷,又具备相当的科学素养,加之经年累月的阅读和思考,使得她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两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此书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可能性和质朴的希望—真的东西可以是美的,而美的东西也需要真之基础与担保。
人们头脑中通常有一些朴素而未经反思的“图式”(schema)。它们虽然足以应付日常生活,却往往禁不起追问。音乐属于文科还是理科呢?笔者在某搜索引擎上提出这个问题,获得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回答:一个回答说,音乐学既是文科又是理科,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另一个说音乐既不是文科也不是理科,而属于艺术。若要进一步探究這个问题,就要从概念上来界定何谓文科、理科,以及艺术与两者的关系,而大多数人可能就止步于此了。当代教育中学科的划分,更加深了真与美之间的隔阂。艺术院校单独设立和招生,使得其学生对文史传统和自然科学缺乏了解。科学家与音乐家似乎渐行渐远。殊不知在中西音乐的肇始处,对自然规律的理解与把握、对真的好奇可能才是关键。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约前575-前500)在发现“琴弦定律”的时候—在张力不变的情况下,弦的频率与其长度成反比—一定感受到了巨大的“惊异”:这个看似变动不居的世界一定是有其内在规律,而且人的耳朵居然可以听出来。这大概就是古希腊人的“天人合一”瞬间吧!于是他提出了“万物的本原是数”观点。音乐不仅不例外,而且恰是这一原理的极佳例证。这不就是“音乐是宇宙的语言”的先声吗?
虽然本书涉及的音乐史案例主要来自西方,但在中国乐理与“天理”原本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最早的音乐家可能是天文学家、历法学家。有学者提出假设,考古发现的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乐器贾湖骨笛,可能不仅仅是一种乐器,而是通过影高来测量节气的授历仪器。此外,中国古人历来也有“律历合一”的说法。《千字文》中提及“律吕调阳”,也就是认为可以使用音律来校准历法。而“葭管飞灰”(《后汉书·律历制》)的传说竟然神奇地残留于一些医书和古诗当中。对此虽然仍有争议,但它意味着可能存在着一条技术路径,即将物候和音律对应。美与真背后有着共同的“道”,只是被遗忘了。马慧元用她的文章一再提示出这一点。
音乐或许是过去两百多年中发生平民化、普及化最为显著的一个艺术门类。如果你是一个十八世纪的欧洲人,想要听高雅音乐的话,就要生活在维也纳、巴黎这样的大都市,才有机会去刚刚出现的音乐厅;或者你属于贵族阶层,有雄厚的财力来雇佣乐师,在自家庄园里为你演奏;对平民而言,最容易听到音乐的地方就是教堂了。在进行宗教仪式的过程中,教堂至少提供了唱诗和管风琴演奏。时至今日,任何一个人只要拥有智能手机或者电脑,就大致可以随时听到想得到的任何乐曲。然而这种“得来全不费工夫”也蕴含着一丝隐忧。
现代人的“消费主义”痼疾远远不止于体现在购买和消费行为中,也不仅仅体现为过度购买,而是“殖民”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费主义倾向于将几乎所有“交换”都降格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甚至自以为付出金钱就能获得世界上的一切。审美也有被异化为购买和消费的危险。很多人在付出金钱后,并不会真正投入自己的心智、心力和时间去进行赏析和钻研。一些洒金“乐迷”日益沦为了纸面“票友”。而马慧元的系列文章提示了另一种可能性,即在票友和乐迷之上,构建出了一个超越消费主义的新领域。我不知道如何来定义它—有乐迷的欣赏和投入,也兼具研究者的长情和敏锐,但又不用成为专业乐评人来养家糊口—姑且可以称之为“音乐考释者”。如借用本书中的一个词来说,那个位置恰是“一点五维”。
“一点五维”的尝试并非易事,它需要一种全新的语言。笔者曾问过大学里从事文论、美学与艺术哲学研究的同事,为什么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好像把绘画和雕塑作为案例的研究论文较多,而将音乐作为研究案例的相对少。他们均表示无从回答这个问题。我自己苦思冥想很久之后,初步得到了一个答案:学术研究的成果主要是论文和专著,它们都是用语言写的。将视觉艺术中的信息转换为语言是容易的—虽然其中也有无法转换的内容,但绝大部分图像是可以用语言加以描述的。因此在语言哲学中有所谓的“语言图像论”。而若要将声音—音乐—乐曲转化为语言,则会困难重重。你努力向一个从未听过某一首乐曲的人讲述,总觉得会词不达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曲调哼唱出来。换言之,语言和图像是同构的,而语言和音乐则缺乏这种同构性。音乐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在人类的五种基本感官中,嗅觉与味觉也有类似无法描述的特性。它们均具有第一人称的直接性和易逝性。于是,如何运用语言来讲述音乐,就成了一项极具挑战的工作。现今网络提供的所谓“多媒体”并没有解决而是绕开了这些困难。而像马慧元这样的作者则尝试对音乐进行“转译”“消化”甚至是“再阐释”,需要开创出一种独特的语言和文体。这也是一段在未勘之域中的勇敢旅程。无论这样的旅程终结于何处,阅读本书的读者一定会在真与美之间发现一群有血有肉、生趣盎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