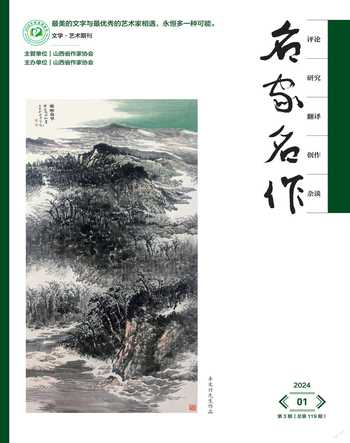空灵与真实:《齐物论》中的美学元素探析
[摘要] 从空灵与真实两个美学角度对庄子《齐物论》篇的内容进行美学探讨。《齐物论》对“物”“观”“无标准”进行了描述,构造了一个空灵的美学世界观;而对于万物世界、精神世界、变化的世界,庄子在《齐物论》中又给出了一个“真实”的美学诠释。《齐物论》中的美学元素包含着质朴无华的特征和深邃宏大的哲学精神,是先秦美学哲学中独特的一部分,至今仍然焕发出新的美学思考空间。
[关 键 词]《齐物论》;空灵;真实
一、空灵之美是《齐物论》的美学形象
(一)物的空灵美
“物”是庄子《齐物论》篇中的重要概念,包含着“物象”的形象意味与“万物”的抽象意味。从美学角度看,《齐物论》中的“物”并非单指感性的经验材料,而是更多地包含抽象的形而上学特质,也正是这一特质恣意流淌,呈现出《齐物论》全篇思想中闪烁的空灵之美。
不拘于“有形”的灵动性——是《齐物论》中对“物”独特的美学设定。这种灵动的美存在于物的天性之内,不拘泥于形态,使万物自身占有表达自身的可能性,即它的显现与美感不在于对客体产生某种效果。一切世界万物的发生都是瞬息万变无规定性的,物虽将自身局限于一定的物质形体中,却能依靠其本性中的“灵活”完全展露出“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的“天籁”之境。物通过这种本性的自由与空灵达到自身的不拘一格,每个个体的物在发挥自身灵动本性的同时就是对自身的终极关怀。于《齐物论》而言,这种物的灵动正是表现在它本质中潜藏的可能将本性偶然展露于外的可能。庄子将这种本质的灵动挥发成为一种绝对自由的状态,我们所说的物的空灵美,正是因为物之本性中蕴含的这种灵动——不拘于形态的意义,因此,物在本质上的灵动展现了自由的空灵美。
蜿蜒变化、流于无穷——形态上无时无刻的变化,是空灵之美得以流动的“准则”。如果说物的灵动是其本质中显露出的空灵,那么这种变化美必定是将本质展露出的美。变化之单纯的形态与变化过程的无定性包含了物尽善尽美的可能。比如《齐物论》中所说的孔窍“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滈者,叱者,吸者,叫者,濠者,宎者,咬者”就是极好的物之变化美。并且,物之变化不全在于其一定或是暂时的单纯形态美,而是变化的过程难以捉摸,在形态与形态之间游离,在本质与本质之内幻化,在我们难以捕捉的自然中,充满了美与美感之间的神秘与自由。这样在变化的不确定中使一切的形态都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性的尽善尽美,无论是哪个主体产生何种感受,都能在其中找到美的对象。空即在于变化的无对象,灵则是变化的无端倪,空灵便是在物的变化中尽善尽美,这种美存在于一切的变化间隙,与物的变化相辅相成。
物物而不物于物——突破规定性的“规则”,是《齐物论》中美学思维的精彩彰显。庄子并未将规定性限制于物之中,物只是一种呈现状态,更本质性的确定在于物自身把握自身,自身显示自身。《齐物论》中谈到言语的无定性,“今我则已有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一切判定都是有外在标准的,然而真正所要达到的空灵美,正是从怀疑一切客观标准开始,将这空灵的本性带入本性之中,怀疑一切,只将自身与天地相交。空灵的美正是要在怀疑思想的动力下才得以敞开,庄子通过这种本质与本质之间的交流,给物的灵动与变化留下极大的余地,使这种空灵美既包含世界图景,又在物的本性中留下了根基。
(二)天人相合的空灵美
“观”——人之于世界的美学认知方式——以天地万物为对象。对于“观”的空灵感,庄子提出了“以明”这一概念,他说“欲是其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大道之隐,则有真伪之辩,在否定与肯定之间此消彼长,与其接受这种杂乱,倒不如以灵显明,照彻纷扰。《齐物论》中认为世界的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似乎是必须的对立性,凡事物之展现都是自身的一切,正像前面所说的物之本性的空灵。因此,“观”之时,就无划分之说,而是“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我们应当抓住最初最真的“道”,而不是执着于事物种种变化的形态。庄子这种“以明”的观之境在于明本心,之于审美情趣,便是因任自然,即万物静观皆自得,大道于心,万物都随于道。与此,我们既未干扰物之自身对自身所设定的自由,却也为自我回归创造了契机。这种空灵的显现,与物不同,更多的是心的空与明。因此,空灵之于“观”,就是这种“以明”之“明”的展现。
人與世界之间的连接没有限制,是《齐物论》制造的无限与美妙的美学空间。《齐物论》中有言,“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尽善尽美,即在这种无规定性与无限性之中。这种观的无规定并非是让观者无视一切,而是“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庄子集释》),在无规定性的多样之中以求多样,更求本然。比如在说有无开始这一问题时,庄子就说到了有无的矛盾,“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庄子集释》)。如果连有无这种空灵性的对象都摒弃,那么庄子在这里所说的无规定性、无限制的空灵就是深刻意义上的空灵美,就像形而上的内容虽是无,却能包含一切。这种空灵美无疑是对美本身性质的逼近。
我们是否也应该在自身的本性之中求得这种实践原则,《齐物论》中的美绝不仅仅是感官或是抽象的,而是一种能让“观”者将超验的空灵感与经验的历史融合的桥梁,正如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庄子集注》),通过这种与世无争的“观”法,显现出来的美即是本质的美。而在这其中显示出的不仅是对观者自身的终极关怀,更是对世界万物从本原上的终极关怀,正是这种空灵性的不带物质追求的内修理念,使观者与万物在自身中达到和谐,在交融中完善自身。
(三)无标准的空灵美
《齐物论》的无标准首先“表现”出的即所有的显现都游于经验感官之上,把每一个主体的审美经验都放在形而上中,正如庄子说大小、寿夭有言:“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夭”(《庄子集释》)。对于日常之言语,《齐物论》中说道:“今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庄子集释》)有无是有,无无也是有,有与无相对依存,根本无定论、无标准。而对于开端和终结之说,《齐物论》的观点也是一样,有开始,有未曾开始的开始,无限推演,终点亦然。在审美时,体现出一种绝对的主观性。这种表现出的无标准的空灵美,一面充斥于天地之中,一面又令人把捉不定。《齐物论》所追求的并非那种大小、有无等的是与非,而是对天地万物之理囊括于胸,容藏于己,因任自然,不偏执一处,从内心的本质中把握这种空灵的美感。
这种“内在”的无标准反而成就了全篇的空灵之美。庄子思想中万物自身的无标准与主体内心的无标准一道展现出无标准的空灵美。在《齊物论》的空灵美中,我们不得不怀疑一切标准的可靠性,我们非要划定事物是非的那个标准本身意义何在?万物并不在于具有某种标准才具有某种特定的内涵,无物一定,万物本身就是独立于任何他物而自在的,自身凸显自身。李泽厚将这种审美意味说成是一种“高级的审美快乐”,是“一种忘我、同天一、超利害、无思虑”的“至乐”。任何个体在这种无标准中,能做到的就是将自身参与天地,掌握好身心的修为,“直至其所不知,至矣”(《庄子集释》),所至之处,即是界限之处,虽然界限是随着自身而在,但它的“在”是一定的。
二、真实之美是《齐物论》的美学内核
(一)物的真实美
纯粹的真性不在物之形,而在物之性。万物的真实并非是简单的物质上的“充实”,反而,我们可以认为其充实的基础一定是真实:将一种志向深入内化于心,使心在冥冥之中寻得中黄一点,“窈兮冥兮,其中有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再将这种“信”逐渐扩充,以至充实。在庄子《齐物论》中,庄子这样认为,有一个“真宰”,“可行其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庄子集释》)。不仅真宰整体的万物秩序,也真宰万物自身个体的每一部分,使万物自身都能成就自身,以完成这种本质上的真实美。一切事物有其是,有其不是,但“道通为一”,这个“一”就是最充实的真实,最纯元的完满,这不就是一种至善的美吗?美实际上并无确定的性质,在齐物论所给出的这种真实性中,万物自身等于自身。从内容上看,是一种饱和的、完满的自我充实,没有时间与空间的限定更是一种自由的状态,无所限制却又是实在的成全。其次,这种对物的真实性的鼓舞,不仅使美感成为对自然的全面表达。圣人并不划分是非,而是观察比照事物的本然,顺着事物自身而生发出“道”。自身完成对自身的成全。《齐物论》中的这种观点使物各自依照“以明”的环境从本质到外部都充斥着一种真实美,而对自然本身也是一种完全的表达,即本原的灵明通透持续地展现自身。
(二)精神世界的“真实”是《齐物论》美学元素的思想标杆
使物真实呈现的能力是《齐物论》美学中美感诞生的基础,而这种精神的淡泊与张力便是美的基本条件。古人向来追求真的境界,美学中所谓“静照”,俗语中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都是对精神真实美的追求。在《齐物论》中,这种精神的真实美具体就是包容万物并使之沾染人的性灵,后心物分离,又使万物自身独立凸显,自成境界。“精神的淡泊”更像是艺术中人的“心襟气象”。这种精神的真实并没有具体的形态,但是却能产生如陶渊明笔下“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深刻体悟,在胸中升起一种辽阔博大而事外致远的感受,这种精神的真实我们只能通过自身的判断,从本质上看具有更丰富的广阔性和深邃性。正如宗白华所说的那种“壮硕的艺术精神”,是一切充实“真力弥满”的基础,而将世界的壮阔“灿烂呈露于前”。由此看来,美不仅仅是一种升华或是释放,也是一种在本质内部的、深刻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关照。其次,这种精神的真实性还在于将美感体验放在对宇宙的深刻认识及对其本身尊重之上。我们必须为美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和自身对其内部性质完全的感知力。美之为美,正是每一个个体从美那里具有了潜于内部的深刻感,而自身作为命运的表达,本身又已经浓缩和提升了纷繁的生活。因此,这种精神的真实是纯净的,带有灵性的,不能单纯地将本性看作是感知某种具体幸福,而应该深入体察其鲜活的性情和真实的表现力,将这种对自然之真实的体验和深刻认识变成是对美本身尊重的一环。
(三)变化的真实造就真实之美的基本形态
庄子《齐物论》中是以不确定性作为一种动态变化的本质来表现美本身的不确定的。庄子认为,事物的一切都是变化不定的,可以将这种不确定作为一种全新的探寻美的方式。从《齐物论》的行文中看,从对物之天籁自然装填的“吾丧我”、万物形态与我之形态的无差别、大小等的齐一、“知止而求诸庸”,一直到最后的庄周梦蝶,都充斥着一种关于不确定变化的真实感悟。《齐物论》事实上并未对美的真实做出任何意义上的规定,但我想其对观者的美感体验一定是在抽象的形而上世界中诠释真实美的理念。《齐物论》中的这种真实美,全然以动态变化的本质存在着的,不论是在齐物思想理论上还是对“道”所追求的那种“敬以直内”的实践修养要求,对美的真实本质的发掘都在一定状态下拥有了自身独特的意义,也正是其不确定性本身的展露,美在《齐物论》的思想观念里是以其无定性对道的执着追寻作以生发和展现的基础。
三、结束语
在《齐物论》中,万物是不断生发、瞬息万变的,人之内心尊于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是无定准的,动静、有无都是变化作为一种空灵的美将真实的性质作以还原,这种真实即体现在主体精神之中。精神的淡泊与真实是自身成就自身这种真实美的重要支柱。在变化与精神中,诚然要达到“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置其滑涽,以隶相尊……参万岁而一成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庄子集释》),这种圣人的自我境界很难,但是《齐物论》中所提到的个体普遍的真实自我,是共有的,万物都是平等、一样的,拥有自身的可能性而互相蕴含于精纯质朴的真实之中。虽然我们各有差异,但这种真实美正是基于这样无限变化的源头而展开的,这样的“道通为一”就是庄子《齐物论》中真实博大之美的最终方向。
参考文献:
[1]包兆会.庄子生存论美学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北京大学哲学系教研室.中国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4]郭庆藩.庄子集释(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朱志荣.中国审美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李彤(1993—),女,汉族,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道家哲学、艺术学理论、书法理论等。
作者单位:西安外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