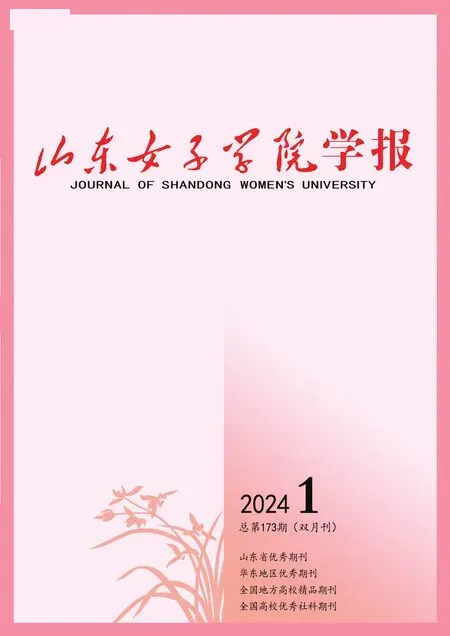女性批评的召唤
——以山尹新著《边缘处守望》为例
姜志鹏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63)
“批评”在各种理论语境中有其针对性的指涉,假如遵从萨义德的概括:“一是实用批评,可见于图书评论和文学报章杂志。二是学院式文学史,这是继十九世纪像经典研究、语文文献学和文化史这些专门研究之后产生的。三是文学鉴赏与阐释,虽然主要是学院式的……四是文学理论,这是一门比较新颖的学科。它作为学术界和普通人们的引人瞩目的讨论话题而出现在美国,在时间上晚于欧洲:例如,瓦尔特·本雅明和青年格奥尔格·卢卡契等人……”(1)[美]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页。,那么,山尹(原名王芳)的新著《边缘处守望》 属于哪一种批评范式?通读《边缘处守望》一书中的各类文章,我们发现其对这四种批评范式都有所体现:“《野草》观察”明显属于第一类,篇幅较长的作家论则可归为上述的第二类,单篇的作品书评显然放在第三类合适,当然山尹背后也储备着诸如女性主义、伦理学视角第四类的理论资源。山尹在其《边缘处守望》中实践了多种批评范式,并发出了“批评的召唤”。
一
《边缘处守望》的书名颇能让人联想到《麦田里的守望者》,平庸的智识喜欢将《麦田里的守望者》这类文艺作品压缩成一个类型化的指称,叫“残酷青春”。这种概括的“无赖”在于,残酷是否只有青春期的少年们才配拥有?在处于看似平庸的中年妇女时期的山尹那里就不够残酷吗?山尹面对平庸琐碎的家庭生活、蝇营狗苟的学院日常之外,还在以一个外国文学学者的错位身份持续不断地关注当代文学最前沿。比起少年人动辄要热血上头独自面对世界,中年人看透世界的平庸还要装作和平庸和睦相处的状态好像更勇敢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杰出在于:它是一个世事明了,知道人生注定是一场失败,但还愿意去说服自己去耐心完成这份失败的叙事。《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个“麦田守望者”,将那些随时会坠入虚无的孩子拦住。
正是在这个层面的对读,山尹为我们展示了过一种“文学生活”的可能性。
或许我们都对过一种“文学生活”这样的想法有点不适,在今天的语境下,人们总是很难相信这种生活真的存在,也很难相信它是值得过的。这样的判断并不奇怪,几乎每年都会有小说家、诗人或评论家站出来发出“文学已死”的宣言,这实际上是一种绝望和怨恨的复合体。绝望,是因为文学的每一个类别(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体裁)似乎都在同时经历着危机;怨恨,是因为当代作家和文学研究者都感到自己就像庞氏骗局中的最后一个投资者,“跟进”了文学这一可敬的事业,却发现它正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
当文学从业者对文学的信心和权威的衰落感到悲哀时,可以试着转向山尹,转向这本批评集。在她自己目前的职业生涯中,有传统的学术职务,她在中文院校教授外国文学课程,有着琢磨文学经典的深潜功力;她也为《野草》这样的地方性文学杂志撰写刊评,兼具在“文学前线”探索的经验。这本当代文学评论集分为“越地作家研究”“《野草》观察”“当代文坛一瞥”三辑,共35篇文章,21万字。其中大部分文章写于2011—2018年,有篇幅很长的作家论,比如海飞论、李郁葱论、斯继东论,有书评,也有对单个作品的评论;有对活跃在当代文坛、已经获得业内认可的作家如马炜、张楚、王咸、朱个、张悦然、周洁茹、东君、曹寇、王凯、杨遥、李浩等的评论;有对风头正健的青年才俊如文珍、陶丽群、唐棣等人的评论,也有对目前正在进入批评视野的“90后”新锐如梁豪、徐畅、温凯尔、刘菜等的评论,还有一部分评论针对的则是名副其实的文坛边缘作者。
山尹从其身处当代文学研究“边缘”的处境,去打捞去观察这个时代的样本,以免其沉入深渊。“所有的文本不论其艺术水准如何,都是历史、社会、意识形态和文本诸关系的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对于文化观察而言,都是有效的。”(2)山尹:《边缘处守望》,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她不仅长于追踪斯继东这样的逸才(文集中收录了《叙述的绝对必要性》 《双重牢笼与逃离的美学》 《赵四的人间漂流》 《逆位:回忆照亮的存在》 《因父之名,偕隐江南》5篇专论),也不吝啬对黑蓝这样的小众团体给出判断与意见。《麦田里的守望者》另一动人场景来自当霍尔顿在筋疲力尽游荡两天后,在过马路时感觉自己在无限下沉,他想到了自己的弟弟艾里。他在心里对弟弟说:亲爱的艾里,别让我消失,别让我消失,别让我消失。山尹的身处“边缘”守望的姿态也“没有消失”,它不是对沉默姿势的拥抱,而是以对“中心预设”的超出姿态,在边缘的视角下与时代照面,没在中心的裹挟下泥沙俱下,正如山尹在序言中的自白:“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将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向世界宣告自身曾经来过,生活过,写作过”(3)山尹:《边缘处守望》,第3页。。
也许具体到中国学术的话语谱系里,才可能锚定山尹的批评向度。在中国的写作语境里,首先,文学批评一方面具有专业性,比如文学批评或是书画之类的艺术批评,既要承诺给出评价判断,又要具备鉴赏品藻能力;另一方面又被自康德到海德格尔的德国哲学影响,这种自我审视的批评具有很深的批判意味,是一种二度的反思,所以这类批评往往会被划入认识论,甚至被归到形而上学中来,因为批评一旦涉及世事,那就不再是“批评”了,而是一种“功能”的溢出了。其实将文学批评作为志业的山尹时常要面对这种二律背反,“在中国,阅读研究……文学作家作品,目的是什么?价值何在?谁是主体,谁又是客体?”(4)山尹:《边缘处守望》,第1页。山尹一面对文本进行着世俗经验的“再描述”,一面又从超验层面在古今之际、中西之间的缝隙里作着自己真诚的努力。对那些爱欲与死亡的诉说早已浸透了她沉重的生命,她在精神和文字上也早已安静地去进行自己“边缘上的守望”了。
文学批评的从业者们还要时常面临“文化掮客”这样的指控。弗莱告诫了文学批评这种“边缘”而又扭曲的“身份认同”危机,“文学批评的对象是一种艺术,批评本身显然也是一种艺术。这话听起来,仿佛批评成了寄生于文学表现的一种形式,一种以业已存在的艺术为基础的艺术,是对创造力的间接模仿”(5)[加]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批评家们好像只能匍匐寄生在文学艺术的阴影之下。这个时代的批评也恰如山尹对一篇叫作《水源地》小说的评价:“过于依赖知识”,沦为“人对文化知识本身的展示欲”(6)山尹:《边缘处守望》,第125页。。很多时候评论家写下的仅仅是依附于文本的句子,而山尹的批评和她本人恰从这份焦虑中崭露,她身上带有的那种强烈的“对抗性”,“以一种相当霸道的读者心理来解读作品,似乎一个文本写出来,它仅余的姿态就是等待的姿态,等待着读者(无数个“我”)让它一次次地重生”(7)山尹:《边缘处守望》,第154页。。那种20世纪之前古典式的老派遗风,闪烁着女性主义能言善辩式的明晰,以及欲将整个文本竭泽而渔榨干式的阅读共同标记了山尹的批评风格。山尹的评论像是在当代文学前线处理的“文学新闻”,如其所指的“样本”在很多情况下实在是个不怎么样的隐喻,读者可能最多的感受是,“哦,又一个作家被琢磨过了”。但其文学批评中呈现出来的评论却没有那种急就章式的干瘪寡淡,她重新润色再塑了作者的“自我”,这在这本文学批评集中随处能够见到。这种漂亮节制的解说叙事,甚至会让人想到写作《阿克瑟尔的城堡》的威尔逊,下面这段选自《叙述的绝对必要性》有关作家斯继东的章节,是对其叙事才华的精彩概述:
在斯继东的身上,奇迹般地综合了一个信徒,一个虚无主义者。这种奇迹般的综合,既源自他的生命体验,也源自他对艺术的信仰。在他的小说里,叙述的冲动和情欲的冲动常常混合在一起,与存在相通。这一观念在《梁祝》中的四九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以叙述征服了银心,收获了生命中最酣畅的享受,在痛失所爱之后,他的生活再次回到了性与叙述:“我依然跟那些姐们做那事,但是做完那事后我却不让她们走,她们得留下来听我讲故事。”(8)山尹:《边缘处守望》,第16页。
正是在这里,马修·阿诺德关于文学性批评现代性身份的起点的论点才有机会被重新修正,对于“边缘”的文学批评来说,“死于荒野”不是唯一的命运,荒野应当是“希望之乡”(哈特曼语)。
二
综观《边缘处守望》一书,从调动的理论资源上看,支撑山尹批评事业的文学信条很大一部分受女性主义的影响,而她的批评质地显然来自“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女性主义这条支脉的漫衍,即对理论的使用更加谨慎,多凭借人文主义文学研究中主题学、性格刻画等传统批评概念,去探讨文本中女性生活和身体经验,并将其视为一系列表征。但在《艰难的破茧——评张悦然长篇小说〈茧〉》中倒是显示出法国学派的一些激进面相,以施虐—受虐这组病态心理切入了文本,进而旁涉了虚无主义、主体权力意志等命题。
女性主义在审视男性作家对女性的表征,思考文本和生活的权力关系,揭示被父权制遮蔽的观念这些方面,这种批评视角确实好得无与伦比,譬如山尹的《赵四的人间漂流——读斯继东的〈你为何心虚〉》,把“漂流”这一带有身体意味的能指当作一条诠释小径,重释了男性成长小说的女性版本。男性成长小说大都按照认清人生使命、怀抱热望、投身事业这样的一种程式书写,而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成长小说中记录的却是焦虑和自我否定。山尹说到赵四丈夫的背叛后,她“严厉谴责自己性欲中的身体”(9)山尹:《边缘处守望》,第23页。,她始终“对自我进行着严格的审判与否定”(10)山尹:《边缘处守望》,第24页。,最终在这种分裂的状态下,她完成了自我教育,“她需要的只是一个陌生男人,一种全新的刺激”。因此小说中的事件被解读为性别的强烈象征,这种女性问题意识也使山尹真正成为一个具有上乘品质文本穿透力的女性批评家。
山尹的女性主义视角尽管适于解剖男性作家的文本,但在处理女性作家文本时,她的批评叙事却显露出一种对回不去“起源”的乡愁式的虚弱,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柏拉图在《蒂迈欧》中对“chora”的界定,一种在语词之前和女性联系密切的语言状态。很多时候山尹似乎执着于将文本导向男女对峙的世界图景中,在《“古越国被废黜的公主”——若溪诗歌论》中,对其诗歌创作描绘出了以下愿景:“如果说在人类的思维模式里还有什么能够和父亲这一强大的形象抗衡的话,那么只能是母亲,尽管数千年的男权社会已经把原始的大地式的丰饶、多产的母亲形象压制在了底层,但是,这种压制从来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丰饶、多产的大地式的母亲,意味着宽容博大、无私奉献、辛勤哺育,同时也意味着硕果累累,所以,以地母为原型根底的诗,不容易虚无、软弱,相反,会拥有强大而坚韧的力量,我们能够期待浪漫的、青春的若溪走近大地母亲吗?”(11)山尹:《边缘处守望》,第94页。
在当代激进女性批评已经对男女二分的形而上学作出具体批判时,诸如克里斯蒂娃的《女性永远无法得到界定》(12)KRISTEVA,“Woman Can Never Be Defined”,in New French Feminisms,New York:Schocken Books,1981,PP.137-142.,西苏的《美杜莎之笑》 (TheLaughoftheMedusa)(13)[法]西苏:《美杜莎的笑声》,米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41页。,伊利格瑞的《此性非一》 (TheSexWhichIsNotOne)(14)[法]伊利格瑞:《此性非一》,李金梅译,中国台北:桂冠图书,2005年版,第1-51页。,更别说近些年来走得更远的朱迪斯·巴特勒,山尹似乎保守得更像一个“前现代人”。在面对朱个这样一个因细节著称的作者时,在《透明的暗夜——朱个创作简论》中,山尹对于“独自吃饭的人们”作了如此概括:“尽管都是‘独自吃饭的人’,仔细琢磨,却有高下之分。男性多数迷恋大男子主义,渴望控制、主动进攻,对现代社会的技术理性、消费意识形态缺乏警惕,对自身的不自由、无能缺乏先见,在真相来临之时,容易逃避责任,转移压力给女性。女性则多数对现代社会的本质有较清醒的认识,独立、勇敢,在双重压力——来自现代社会和来自男性的——之下,仍然渴望与他人建立真实的联系,时刻准备放弃自我中心,融入新型关系,或者更高的意志之中”(15)山尹:《边缘处守望》,第57页。。为了满足男性与女性压迫与反压迫这样带有意识形态教条化的叙述,叙事变成了一种可以推导的性学命题,文本本身作为一个丰富意涵的审美织体反而缺乏被关注,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阅读《边缘处守望》时,我们似乎能够察觉到山尹的两个面相:处理男性作家文本时的山尹,以及面对女性作家文本时的山尹。一个“成长”在男性统治世界的山尹,一个“撤退”回洞穴起源状态的山尹。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一度希望论证失去童贞的女人是否还有机会返回原先的处子状态,他的答案也很明了:上帝可以宽恕她,甚至可以施展奇迹赠予其处子温柔贤淑的气质,完美无缺的肉体。但即使是上帝也无法使未曾发生的事情发生,因为逆转时间规律有违上帝的本性。上帝基于以下无法违逆的逻辑原则:“p已经发生”与“p没有发生”不可能同时成立(排中律)。但阿奎那这种男性逻各斯是无法支配与统摄这本批评集所呈现出来的面相的,赫尔墨斯神话提示我们,文本之因果链状如螺旋,不断回复自身,“后”又会重新发生在“前”之前。“起源”会败坏现实的男性统治,而又成为一种改良世界的愿景,于此,这两个面相才能融贯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山尹的撤退与进入,克里斯蒂娃关于“chora”的重新读解才会显得更具有文本的实践意义,“以母亲为中心的被她标识为‘符号语言’的‘容纳处’(chora),或前语言、前恋母情结和未经系统化的意指过程。当我们在接受由父权控制的被她称之为‘象征语言’的句法顺序和逻辑语言时,这一过程受到了压制”(16)[美]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吴松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3页。。山尹的“撤退”依然可以视为对另一个世界的前瞻,她的意义在于去守望一个不同于当前世界尤其是不同于女性当前实际的世界。
三
现代以来的学院派批评普遍的一个倾向是通过牺牲文学话语本身的现实指涉力量来强调语言学意义上的修辞形式。在《边缘处守望》中,除了极少数山尹偏爱的作家,其倒是显得畸零地站在另一侧,她更愿意打量文学同现实的关系,于是“模仿论”这个几千年的老问题又重新装了一个“新灵魂”。
“我当然也能够感受到作品的美学特质,但一般不会把评论的终点放在这个层面,我常常从文学文本出发,走向自己感兴趣的文化观察与思考。”(17)山尹:《边缘处守望》,第154页。在很大程度上,以这种方式作为切入,山尹的文学批评施加了一种反向于自己的、区别于她极少能从文本中召唤出“审美感受力”的文学能力:不贸然将它们拖进审判的高光,感受其朝向世界的真诚的伦理力量。
“一方面,我把文学文本中的生活当成一个独立的世界来理解;另一方面,我又似乎并不承认有什么独立自足的文学文本,……如果更诚实一些,我会说读中国小说,很少让我产生追问文学本质的冲动,而是更多地让我产生对伦理与社会的思考。”(18)山尹:《边缘处守望》,第154页。面对这段话时,我们很容易面临两难的窘境,文本假如是一段阐释编码,读者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去遵守程序。一边是主观的“大跃进”,另一边是客观的亦步亦趋。这一问题导向了更大的理论语境——阅读在多大程度上被文本所控制?读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字里行间的潜在进行补充?山尹批评活动的考察给我们留下了有教益的思考,区别于卡勒对理想读者的“文学能力”的期待(这种结构主义诗学的文学能力表现为依赖后天习得方才生成的经验性阅读策略)(19)于雷:《何为文学能力》,《当代外国文学》,2022年第4期。,山尹给我们展现的多是与文本肉身撞击时的瞬间,用读到的死亡来温暖现时的生活,正如她说的“等待读者让它一次次重生”。这种文学能力是一种对文本伦理叙事的“再叙述”的能力。借助于审慎的生活经验和严肃的细节观察,以及横贯多个文本的主题学“俯瞰”,文本的场景便言简意赅地浮现上来。在谈论到她喜爱的作家王咸时,她说,“有评论说王咸的笔‘枯’,在我看来,王咸给出的实在是太多了,他的叙述者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同时表现出了一种异常的力量,他盯视着纷乱的人间,却保持着可以辨识的平静,因此,文本显得清澈透明,丝毫没有卡夫卡那种神秘的气息,即便是结尾处那一片草原,也有充足的心理学、社会学依据”(20)山尹:《边缘处守望》,第169页。。这几乎可以看作是山尹的夫子自道了,比如她写张楚笔下的“孤独”:“张楚写的是一群极其自我的人,或者说极其孤独的人。他们都是本能、欲望的奴隶,一根筋的行动派,能够约束他们的,也正是由于时空的广阔,世界的强大,他们的隐忍或‘不得不动’才常以悲剧结尾:自毁或者毁他”(21)山尹:《边缘处守望》,第261页。。她将伦理引入斯继东的“并置叙述”,“人物之间并没有共享多少精神资源,是孤独加孤独等于孤独。骨子里有离散的趋势,逻各斯被悬置了。这是一种激进的先锋姿态,内蕴彻底的虚无思想,却被让人亲切的生活细节、流畅可读的日常语言所隐藏……”(22)山尹:《边缘处守望》,第6页。叙事伦理的实践力量正是在于在现代性没有最高道德法官的生存处境之中,文学重新讲述了道德的可能性。
让我们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脉络,重思山尹的批评实践,这其实不是带有激进式的读者革命观。亚氏在《诗学》中确立了何为“模仿”,认为它是故事(muthos),是对行为的模仿,也即叙述而非描写。简言之,文学作品是对人类行为的再现,山尹强调的不是再现的对象或是模仿物,而是那些模仿者或再现者,“对我而言,我阅读,读的是人,双重意义上的人:作家文本中描绘的人,以及作家本人,而且我的着重点在后面……”(23)山尹:《边缘处守望》,第143页。通过再现的技术与其叙述的结构去重新叙述自己阅读的伦理故事,去观察记录模仿者们的心灵史和灵魂史。那么我们经过阅读时激起的情感,读后的沉思与交换,感同身受的努力,对于感受之外感情的重新发现与觉察,我们有理由确认,“作为一位普通的观察者,我其实更相信经由文本接近的现实,也保持着隐秘的信念:如果我们改变了文本,我们就会改变现实”(24)山尹:《边缘处守望》,第119页。。可以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山尹所相信的文学指涉现实的力量,一个消极的版本来自柏拉图《理想国》,他认为“模仿”具有颠覆性,会危及社会联系,诗人对城邦卫士的教育会有不良的影响,所以应该被驱逐出城邦。稍显积极的版本出自博尔赫斯的《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忒蒂乌斯》,好几代学者虚构想象出一个行星取代了一个真正的行星,故事末尾关于特隆的想象历史正在取代我们所知的历史,甚至连物理和数学定律都要更变。基于此,或许我们可以颠倒一下巴特关于“书是一个世界”的命题(巴特在《批评与真理》中认为批评家面对书同作家面对世界其话语条件是极类似的),“世界本身是一本书”,批评家也可以是真诚写作的作家。
阅读《边缘处守望》的部分乐趣正是来自于山尹这种真诚的文学能力。这种文学能力本身已经达成了一种文学成就,并且提示我们过一个好的文学生活是如何可能的。它不是来自山尹文化职务的特权,也不是对博学和智慧的专横宣扬,而是一种感性的表达,是个人心灵与世界、文本接触的记录。所有真诚的文学批评家都是如此,但在山尹那里似乎尤其如此,《边缘处守望》批评集收录的文章,既给读者带来重要的新作家的消息,也会力图教我们如何阅读困难的新作品。我们甚至能看到山尹私密的野心:对文学史进行论证式的重估。
如果山尹的文章不完全是文学批评,那是因为它们是更自主的东西:它们属于文学本身。就像诗歌一样,它们将作家的内心体验戏剧化;就像小说一样,它们对作家的社会和心理环境提供了主观的描述。像所有的文学作品一样,山尹的文章本身就是目的。假如用艾略特创造的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自发”(autotilic)的,就是批评是其永远不可能成为的东西。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山尹是在边缘处守望。她不向读者提供可能被组合成理论的结论或公式,她提供的是文学所遭遇的一种经验。
这种朝向世界的真诚力量,或多或少揭示了这个时代信仰的面相。她在《边缘处守望》自序中提醒道:“评论者偏居一隅,听从偶然性的支配,以论说因缘巧合进入视野的作品为乐。”创作者们总要面对这种偶然性。“平庸是人类文化史的基本事实,因此,热衷于日常性经验、反复书写痛感、疏离感和孤独感,可能表现的并不是作家对世界的判断,而是作家对世界的应激性反应”(25)山尹:《边缘处守望》,第2页。,但泥足深陷于琐碎的人们总会被细枝末节终结,“能量不足的作家则被琐碎的细节拖拽着踉跄前进”(26)山尹:《边缘处守望》,第44页。,具有真诚力量的人不会在这样的信仰中寻找避风港,而是会学习如何在不确定性中生活。我们知道世事洞明是有奖励的,但其代价则是可能会陷入深渊的凝视之中。不过,这正是这本文学批评集的召唤力量所在:拒绝被假象所安慰,也可能成为慰藉和力量的一个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