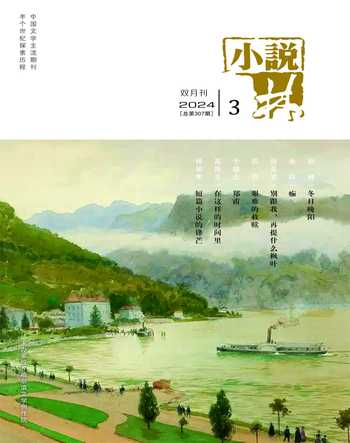短篇小说的锋芒
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次做文学的讲座,想来想去,能够讲一讲的还是中短篇小说的写作,最后确定讲短篇,讲短篇小说的锋芒。我会从几个经典短篇入手,当然它们也是我个人所偏爱的。
谈及这些作品之前,我会给每篇小说标注一个讨论的方向。真正好的小说,各方各面都达优秀,但我们在此还是要选取一个最精粹的方面,来方便识别这些小说的好中之好,找到它脱颖而出的理由。因为没做过类似的工作,所以这对我个人也是一次认真的小说梳理,来回顾当时我被它们打动的时刻。
我想到的第一个方向是细节。代表作家是美国小说家理查德·耶茨,我们就称耶茨吧。耶茨在国内最享盛名的短篇集,题为《十一种孤独》。这是一本我看了多遍的小说集,收录十二个短篇,每篇都很精彩,今天选取的是集子里的第一篇《南瓜灯博士》。故事不复杂,讲一个男孩是插班生,喜爱绘画,家庭条件不好,像所有心怀自卑走进青春期的男孩一样,他别扭、冷淡、不合作,用东北话说,是个格色的孩子。转学的第一天,他很早出现在教室,和新同学见面,被新老师介绍给大家。耶茨没有把笔墨用在描写他如何不适上,这是耶茨在这篇小说里第一次施展魔法的时刻——没写不适,没写心理活动,没写任何的不愉快,但读者都知道这个叫文森特的男孩不舒服了。如果他碰上的是一个冷淡教条的有经验的老师,也许这种不舒服还不那么叫人难挨,但他碰上的恰恰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年轻女老师。女老师当着全班问他,喜欢被怎么称呼?文森特说他希望被叫做文尼。女老师又问了一遍,她没有听清,可男孩的第二遍回答,在同学们的交头接耳中又一次被减弱了分贝,女老师反复叫着男孩不愿意被叫做的名字,好的文森特,好的,你会适应的文森特。耶茨在这里用了一个让人过目难忘的形容,他写男孩含糊不清地咕噜了一句什么,脸上笑容一闪就没了,刚好露出发绿的牙龈。
牙龈可能是绿色的吗?不太可能,牙龈可能看起来不那么嫩红,我们于是猜想,那是一种发青的笑容。尴尬的时候,人往往借笑掩盖,当这个男孩刚学会大人的作风,还不是个大人,于是他全力模仿,模仿不像,暴露了他的窘困——不单是心理上的,还有生理上的。通过前后文,我们确认了对男孩家境不好的判断,那么一个绿色的笑容是最好的佐证,他营养不良,更暗示了人物的性格。发青的,在狼狈时刻近乎野兽的笑容。这个孩子心思很重。女老师隐隐觉察到了这一点,她还不明白这种性格具体会带来什么,她天真而善良地当作是初来乍到的不适,为缓解这种不适,就像我们在面对身有残疾的人时,会刻意忽略他的缺陷,女老师刻意忽视文森特,不把他当作新来的成员,她继续进行惯例,即每周一由学生上台汇报,刚度过的周末都做了什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了班级的群像——孩子们有的会讲述得毫无逻辑,有的会编一点儿瞎话,我上学时也这么干过,孩子的想象总是丰沛,总想争取同龄人的好感,用冒险经历彰显勇气,用特立独行彰显个性。文森特冷冷地观察着别人,女老师则富有同情地观察着他。
在这段观察新生文森特的日子里,耶茨又来了一段很神的细节描写。站在女老师的视角,他这样说,课间时候,文森特独自一人待在教学楼附近的操场上,像运动员那样试着跑上几步,跳几下;然后又蹲下来,重新忙着系鞋带。在鞋带上忙活了五分钟后,他放弃了。转而抓起一把石子,开始朝几米外一个看不见的靶子飞快地扔着。在他想不起还有什么好做的时候,只得站在那里,手先是插在口袋,然后又拿出来搁在胯骨上,接着像个男人似的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我观察过多回人群之外的人,也做过很多回人群之外的人。如果你不想融入,就能保持松弛,可如果你想,但是不能,便会做出许多的小动作来化解寂寞,让别人但凡留意到你的每一眼,都看见你在做事,在被占据精力,仿佛根本没察觉到被忽视了的处境,你怡然自得。也许耶茨是个有着感受力天赋的作家,也许他经历过类似的场面,深刻地记住了。但为何他能如此生动的描绘这一细节,且激发强烈共鸣——答案更可能是,细节的准确。有时我们会读到那种细若发丝的描写,有时我们会觉得累赘,不知道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当细节太多,也是种过犹不及。出众的细节描写,永远细而准确,缺乏了任何一个标尺,都会流于平庸。就好像小说里女老师随后做过的那些努力一样,她不停地对文森特示好,却没有任何一次打动这个男孩的心,因她不知道文森特想要什么,平庸的小说家则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对人物的缺乏了解不能够被面面俱到所代替,相反,带来南辕北辙,将无法实现射击的精准。
现在,作为读者,我们已经知道文森特多不舒服了,可女老师还不知道,她还在做南辕北辙的努力。她不知道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更需要的是同龄男孩的佩服,而老师的同情让他更精确地体会到了自己的弱者身份,老师越是热情,他越要抗拒,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赢得关注。于是第二次汇报课上,文森特举起了脏兮兮的手,他走上讲台,看上去很自信,如果说有什么不妥的话,是他自信太过了。他编造了一个一听就能识别出谎言的周末经历,在谎言中,他表现得像个成年男人,撒谎去看了一场没看过的电影,他错把电影的名字讲成了南瓜灯博士。他讲父亲被人射穿了肩膀,无法开车,父亲问他你行吗文尼?他说,当然可以,他无师自通学会了开车,连妈妈也对他钦佩极了,我为你骄傲文尼,你一个人就完成了旅程。文森特自作聪明的汇报,收获了同学们的嘘声,他强撑着下了台,度过了一个更难熬的午休。随后女老师跟他私聊,温柔地鼓励他,如果以后能讲述自己的真实生活,大家会更喜欢你。她又一次忽略了人性的幽微,痛苦,是一个人的隐私。假装不痛苦,是一个人微茫的反抗。于是耶茨只能又提醒一次,他写文森特的反应,在从女老師面前走开后,他一个人到男厕所,吐了。跟着他转进一条小巷,在空空的水泥墙壁上,用粉笔写下他想得起来的,所有的脏话。
文森特的行为被同学报告给了女老师。女老师深感挫败,她第一次发觉了读者早就发觉的事实,她并不了解像文森特一类的孩子,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把文森特叫到面前,耶茨是这样形容的,一个神圣的时刻,一个有着拯救精神的教师,面对自己也无法了解的情况,孤注一掷,无的放矢地努力。看着我,她对男孩说,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漂亮过,脸颊微微泛红,眼睛闪亮,那是一种人陷入了自我感动时,才有的反应。女老师甜美的嘴有意识向下撇着。这是个多么闪光的细节。如果女老师只是甜美的,循循善诱地开导着男孩,女老师的性格将失去丰满,也让读者无法体会她的不够自信——甜美的嘴,有意识地向下撇着。她要时刻提醒自己的师长身份,更提醒文森特,我虽然原谅了你,但这是一次冒犯,我是你的老师,你不能用脏话去冒犯我。
这时她欣慰地看到文森特眼里噙着泪水。她和他掏心挖肺,讲了许多,看到了男孩的被感染,她自觉有所效果,问他,你能答应我记住这些吗,亲爱的?耶茨写道,亲爱的一词,就像她纤细的手随意伸出来,打在他穿着运动衫的肩膀上那般漫不经意。漫不经意,证明女老师此时此刻,已不再将文森特视为一个问题学生,她自信看到了他的悔过,看到自己教育的成绩,将一声亲爱的带来的文森特的反应,视为不见——当叫出亲爱的这个词时,他的头垂得更低了。
故事在追折中走向高潮,噙着泪水告别老师的文森特,在放学路上碰到两个男同学。他们问文森特,是不是被狠狠教训了一顿?文森特拒绝回答,直到在男孩们穷追不舍下冷不防冒出一句叫他的名字,告诉我们吧,文尼。耶茨写,这一次,这名字实在让他受不了。那是他一直希望被叫到的名字,被认可的身份,熟悉,安全,令他自在。男孩被这个称呼剥夺了抵抗力,断开和女老师刚刚保有的情感联系,他膝盖松软了,脚步缓慢下来,不急着回家,和两个同学一道,开始轻松闲聊地散步。他告诉他们,女老师有多么可怕地体罚了自己,他绘声绘色地讲着,当女老师偶然看到了这一幕时,后者惊喜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是一个完全正常、非常快乐的男孩,正被他的同龄人簇拥着,这场面无疑让女老师欣慰,她快乐地大笑。她情不自禁,虽然觉得自己还是搞不懂孩子的行事之道,但文森特的转变还是让她相信,是刚刚交了心的缘故。她加快脚步,超过他们身边,转身朝他们笑着,晚安,孩子们。剩下三个男孩在她离开后面面相觑——文森特难堪至极,他的谎言又一次在同龄人中被识破,带来了比上一次更恶劣的效果。刚还簇拥着他的男孩们倒退着走,鄙夷地看着他,就像文森特说有人开枪打他爸爸一样,他全是撒谎。男孩们用上一次文森特谎言里的南瓜灯博士称呼他,南瓜灯博士,你再也不会让我们信你说的,任何一个字。
这篇小说的结尾令人难忘。在许多个准确细节的铺垫后,耶茨用最后的准确细节达成了小说的绝杀,匕首般的短篇小说,结尾出鞘,锋芒毕露。文森特没有回家,他又回到了被女老师要求清洗过的那面墙壁跟前,被擦过的地方还是湿的,时间没过去多久,人的心理却已反复转折,再次掏出粉笔时的文森特,迎来他个性的巩固——不会再变了,也不会再被拯救。耶茨写道,文森特非常仔细地画一个人头,是侧面的,长而浓密的头发,他花了好长时间来画这张脸,直到画出他所画过的最漂亮的脸:精致的鼻子,微微张开的嘴唇,长睫毛的眼睛,线条优美像小鸟的翅膀。他停下来,以恋人般专注的神情欣赏这幅画作。然后他在嘴唇边上画了个大大的对话气球框,在框里,他写下中午写过的每一句骂人话,文森特如此愤怒,粉笔都折断在手里。接着他用很粗的线条,画了美丽的头部之下,一个女人的裸体,狂乱地画了隐私部位。故事结尾,画的下面,他写下了女老师的名字。
《南瓜灯博士》讲述了一个满是误会的故事,所有的误会都发生在文森特和女老师之间,而所有的明白都被读者看在眼里,有此对比,才更显力量,仿佛是悬悬欲坠的铡刀终于落地,准确,利落,一击必中,且让人长久惦记,在阅读心理上形成环绕,既想前因想后果,也想许多的过程。耶茨用准确的细节描写在受限的篇幅里,笼中起舞,贡献了难忘的故事,难忘的人物,难忘的心理以及难忘的思考。如果没有这些细节,人物的行为将变得荒诞,不合情理,人物的心理也将流于表面,支撑不起故事的起伏。细节的准确和语言的劲道一样,给短篇小说增色不少,都属于我想谈及的锋芒。
聊起短篇小说的语言,我想拿一个国内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家举例,举例的也是一则经典名篇,老舍的《断魂枪》。
我一直很欣赏老舍先生的语言功力,他的描写和对话,都那么见分寸,知情味儿,把日常用语炼化得极生动耐咂摸,绝不刁钻晦涩,也绝不流于凡俗。《断魂枪》是一篇经典,讨论它的文章很多,从时代背景到民族心理到文化的传承,讲小说语言的也有很多,落在文本上,可以说正是语言的魅力吸引读者先喜欢上了故事,再去探求故事外的思想。于是我们回到语言,先走进这个故事看一看。大家应该都有些了解了,我草草交代下大致的过程,和另外两篇小说不同,这篇我会在情节上少谈一些。主人公沙子龙是个使枪的老师傅,老师傅面临新环境,玩意儿都不叫人看重了,过去是走镖的,镖走不成,他不愿再在人前舞动过去让他声名大噪的一套枪法。可他的徒弟们还多借此生活,撂地卖艺,卖卖老师的名声,希望借此刺激老师出山,使一套枪法给大家看,东西真是好东西,总有一天会重放光彩。这天,沙子龙的大徒弟王三胜在街上耍手艺,老舍没写沙子龙如何如何厉害,到小说这里之前,我们都没看到沙子龙是怎么使枪的。王三胜先出场,先使了,老舍用了很利落的一段话写这次亮相,仿佛王三胜使枪时起的尘土都扬到了读者面前:
大刀靠了身,眼珠努出多高,脸上绷紧,胸脯子鼓出,像两块老桦木根子。一跺脚,刀横起,大红缨子在肩前摆动。削砍劈拨,蹲越闪转,手起风生,忽忽直响。忽然刀在右手心上旋转,身弯下去,四围鸦雀无声,只有缨铃轻叫。刀顺过来,猛的一个“跺泥”,身子直挺,比众人高着一头,黑塔似的。收了势:“诸位!”一手持刀,一手叉腰,看着四围。稀稀地扔下几个铜钱,他点点头。“诸位!”他等着,等着,地上依旧是那几个亮而削薄的銅钱,外层的人偷偷散去。他咽了口气:“没人懂!”他低声地说,可是大家都听见了。
读者也在心里低声地说,“你真懂。”自己跟自己说的话会震耳欲聋,我当时就这么跟自己说的,我不知道老舍先生对武术对卖艺生活是不是真那么了解入微,起码就这一段形容,我确信他懂,他让我一个外行看到了精彩的表演,看到了落拓的卖艺人落拓的心情,看到了无数的看客对表演的“也就那样”的反应,毫无留恋,除了给出的几个铜钱外,没有对这次表演特别的兴奋,人群是平静的,与之对照的是王三胜行云流水的一套枪法,人群越安静,就显出刚刚的精彩越落寞,刚刚那些行云流水的招式比之迟滞了的观众反应,也越显出连贯,快,太快了。我总是会对这段描写中许多个的动词着迷,动词就像语言里的骨头,骨头冒出来了,位置接对了,血肉可以依附生长,调动一段话——这一整个的生命体,跟着行动起来。大刀靠了身,眼珠努出来,脸上绷紧,一跺脚,刀横起,忽然刀在右手心上旋转,身弯下去,四围鸦雀无声,只有缨铃轻叫。为证明老舍先生炼字的功夫,语言劲道的魔力,现在我们把这段话换其他动词,不炼字,不收缩地形容一遍:
大刀在身上靠近了放,王三胜的眼睛突出,脸上毫无表情,十分严肃。他突然跺了一下脚,把刀横拿起来,又突然刀在他右手心上转过来,转过去,身体跟着下弯,四围谁也没出动静,只有红缨枪上的铃声,被轻轻带动着,响了起来。
这么写,大家都能看懂,一招一式知道你怎么比画的了,可更像打了一套太极,太清楚太衔接得住,就少了枪法的凌厉和卖艺人的神气。后面老舍又写了一段更精彩的打斗场面,讲王三胜面前冷落的人群里,站出个单薄的老人,老人也是练家子,认为王三胜枪使的不赖,有意跟他比画比画。在写老人是怎么连续打落王三胜两次枪的过程之前,老舍枪头一转,先写了老人的眼睛。对于这篇小说的语言劲道,在动作描写上我们已分析過,现在转到静态,我们转到老人的一双眼睛上。
老人小干巴个儿,披着件粗蓝布大衫,脸上窝窝瘪瘪,眼陷进去很深,嘴上几根细黄胡,肩上扛着条小黄草辫子,有筷子那么细,而绝对不像筷子那么直顺。王三胜可是看出这老家伙有功夫,脑门亮,眼睛亮——眼眶虽深,眼珠可黑得像两口小井,深深地闪着黑光。随着两人彼此观察,后面还有一句,写老头子的黑眼珠更深更小了,像两个香火头,随着面前的枪尖转,王三胜忽然觉得不舒服,那俩黑眼珠似乎要把枪尖吸进去!
老人和王三胜还没开始打斗,读者却觉得两人都已动了,连王三胜都觉得老人的眼睛黝黑深小,枪尖已经在被其吸动,这样的描写既摆明了老人的确深藏不露,是个高手,一面也写出了王三胜的心理,王三胜的败相。深不可测,是最让人产生接近恐惧的感受,如果对方是个精壮小伙,如果对方一脸的意满志得,都还不会那么害怕。最怕的就是平静,平静落在表面,暗地里山河涌动,眼珠本来就黑,居然能在注视中更深更小,像两个香火头,碰,就烫你烧你,香火,又隐含着规矩和宗师气派,我想不出比这更能表达人物身份和双方局面的外貌形容了。王三胜在这样的香火似的眼神前,资历是弱的,身手是弱的,心理也是弱的。他只有搬出更强大的宗师,来和香火相碰。落败了后,他气势汹汹带老人往沙子龙身边赶,师傅啊,你高低得出山了。沙子龙叫他烧水去。烧水是为了煮茶,煮茶是为了待客,王三胜焦躁要死,他领来的不是个客,沙子龙如果想把老人当作客人,便打不起来,王三胜深深失望。
老人也很失望,沙子龙越客气,他越不能再客气,客气来客气去,他的目的便要消散。老人再三要沙子龙跟他比一场,沙子龙不比,说身上早放了肉,懈松了,不比武。老人说出真实目的,那你教我那套枪。沙子龙笑,早忘干净了。哎你不行在这住几天呢,我带你吃吃逛逛,临走送你点儿盘缠。老人疑心沙子龙,看不起自己所以不传,他利落地飞檐走壁,打了一套在行的拳法,关于这套拳法的描写自是精彩,可我仍想提醒各位,到此,到小说即将结束,沙子龙的动作我们都还一个也没有看过。老人的这套拳法描写,是私以为动作描写里和水浒传多能平齐,毫无逊色的一段:
老人腿快,手飘洒,一个飞脚起去,小辫儿飘在空中,像从天上落下来一个风筝。快之中,每个架子都摆得稳、准、利落;来回六趟,把院子满都打到,走得圆,接得紧,身子在一处,而精神贯穿到四面八方。抱拳收势,身儿缩紧,好似满院乱飞的燕子忽然归了巢。
沙子龙站在台阶上点着头喊好,我们心里也不断叫着好,好到已经忘记了这人是来比武的,后面可能有一场殊死搏杀。用喜剧电影里的话说,气氛烘到这儿了,不热血沸腾好像不对。结局我们知道,沙子龙就是那个不一般的人,他说了,这套枪跟我入棺材。在送走了老者后,沙子龙也没去见徒弟们,徒弟们往后再也不敢到人前卖艺,人往往不那么容易理解避让,而容易看到退败,更愿意相信沙子龙是败了,不相信他压根没有打过。人们慢慢忘了沙子龙,剩下他自己关好了小门,一气呵成耍完六十四枪,望着满天群星,叹上口气,摸着凉滑的枪身,微微一笑,不传,不传。
沙子龙没有传枪,老舍先生却用许多作品传达了小说的语言劲道之美,传达如何炼出白话里头,血肉饱满筋骨凌厉的语言章法来。在短篇小说里,语言的简洁生动并非必不可少,但语言的简洁生动一定能助力短篇这一文体,突破藩篱,语之将尽,厚意无穷,从而为自己争取来更大的天地,也为读者,谋得最多的阅读自由。现在,我们可以说说今天的最后一篇小说了,放到最后,是因为前面说的细节也好,语言也罢,都和最后一个方向拆分不开,且归于它的统属。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说法,即短篇小说的匠心。在此,我先表达我的观点,在短篇这样的有限容量中,句子和情节的不设计不剪裁,才是不应该做到的。短篇小说需要更严密的设计,落在文本中,有时会让我们脱口而出,太匠气了,太规整了,太完美了。可每一股子匠气后头,都容纳了创作者的匠心,匠心需要独运,设计需要静思,如果有了静思和独运的匠心,我不觉得匠气是种批评,设计感在短篇小说中,恰恰是责任感的体现。
美国小说家罗恩拉什在国内出版的两部短篇小说集《炽焰燃烧》《美好的事物无法久存》都被编入上海译文的那套享有盛名的短篇经典系列中,且在其中广受好评。罗恩本人两次获得欧·亨利短篇小说奖,两度入围福克纳节选,凭借小说集《炽焰燃烧》荣获世界短篇小说最高奖——弗兰克·奥康纳短篇小说奖。要这样去介绍他,因罗恩在国内的名气不比前两位,但在国际上丝毫不逊,且仍在活跃,他本人是我非常喜爱的短篇小说家,对我的短篇写作影响很大,一本《炽焰燃烧》通红的封皮,摆在案头,都已经风吹日晒,发白了。我没经过专业的写作学习,罗恩的一些小说便被我视为教材,有时写作者自己寻找老师,认定能够受其教育,常是先被老师们的小说打动,被他们的理念打动,而后才在自己的写作中,发现了暗含的共鸣。说到匠心,我第一个想到罗恩的小说,《艰难时世》。可能因为罗恩描写的美国南方和东北也有隐隐的共鸣,那些美国南方文学,总能打动我。文字冷硬刚直,情感细腻暗沉,这些都于我个人喜爱的气质暗合。而最打动我的,还是罗恩小说里的设计感,像一个完满的圆,不疏漏更不庞杂,原原本本,极致的设计带来极致的天然。
小说讲了美国上世纪30年代萧条失业的大背景下一户南方人家,普通的几日生活。孩子们因为和父母的矛盾,更因受不了贫困的折磨,纷纷离去,剩下一对老夫妻留守在此,每日务农。主人公雅各布被妻子埃莱娜提醒,鸡舍里的鸡蛋数量总是不对。他们先是猜测被狗偷吃了,后来猜到周围人的头上,除了他俩,附近还有一家邻居。邻居哈特利一家养着一条老狗,哈特利一家非常冷淡,和谁也不来往,对于穷困,他们保持着让人无法理解的自尊,从不接受帮助。埃莱娜是个直性子的女人,她没听雅各布的劝阻,在看见哈特利带着狗经过她家时,直截了当问,哎你家的狗,是不是爱偷鸡蛋?哈特利没说什么,按小说里形容的,他就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他只是把狗叫到身边,从工装裤里掏出折刀,跟着单膝跪下,一只手薅住了狗的脖子,用刀割开了狗的气管。他一气呵成,在埃莱娜的惊讶里,把狗的尸体拖到路边。这是个狠角色,有些方面他不容置疑,心里有比死亡更不容越界的地方,你绝对不能怀疑一个人的自尊。事后,雅各布埋怨了妻子不该那么说话,可妻子也只是问问,只有同为男人的雅各布才知道,哈特利在眼下的艰难时世里,是怎么带领一家艰难地、无可诉苦地过着日子。
相比雅各布,埃莱娜作为女人,反而是粗糙的。她不觉得贫困是一种隐私,所以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回顾,埃莱娜对被她逼走了的两个孩子,从无心理上的保护,她觉得他们该和自己一样坦然接受,拥有韧性和耐力。这性格多么像我家里那些东北的女性长辈,她们都对生活有打不倒的信念,自己能够承受许多的摧毁,被锻炼出了比男人还刚硬的一面,却常在子女教育上,拔苗助长,失去了女性的耐心和宽谅。雅各布体谅妻子,也埋怨妻子,他把一切感情都埋藏起来,在艰难时世里,不问对错,选择和妻子一起面对,生活下去。他听说有些蛇也会偷吃鸡蛋的,且是整个吞下去,所以你看不到蛋皮散落在周围。他又是个心思深的男人,可以一面安抚妻子,一面自己想办法找到偷鸡蛋的人。他拿起一个鸡蛋,用鱼钩的倒刺在上面钻了一个小洞,缓缓把整个鱼钩放进鸡蛋里,接着把细线连在鸡窝后面的一根铁钉上。他做好了埋伏,等待这个埋伏。白天他和妻子聊了这件事,埃莱娜心不在焉做着针线活儿,夫妻俩和所有老两口儿一样,闲聊着过去。
“你今天早上说我赶跑了两个孩子。你说这话真是没良心。那两个孩子从没挨过一天的饿,衣服都补得妥妥当当,也都有鞋子和大衣穿。”
雅各布心里明白,自己不该再做纠缠,可哈特利用刀割开狗的气管的画面一直在他脑海里转。他说,你本可以更加宽容地对待他们。埃莱娜说,这个世界是个残酷的地方,孩子们需要了解这一点。雅各布说,世道很快就会好转,大萧条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但你对待孩子们的方式,影响一直都在。两人没有说服彼此,家不是一个能讲出道理的地方,但高明的小说家绝不会在短篇里浪费有限的篇幅给琐碎的争端,起码,我们看出来了夫妻俩的不同立场。这些立场就像引信,会烧去不同的火种,点燃不同的画面。他们都是有道理的,是眼下的艰难时世要求他们不能兼听则明,而必要保留个人的固执,成全每个人心中不同但必要坚持的一种活下去的信念。
雅各布的鱼钩住的凶手,是哈特利家的小女儿,雅各布发现她时,钓鱼线的另一头消失在她合拢的嘴巴里。雅各布让对方张嘴,看见鱼钩的倒刺深陷在小姑娘腮帮子的肉里,那一定很疼,她还只是个小姑娘,是更重的顾虑让她必须忍疼,她不能声张,让雅各布一家发现还好,如果她爸爸,哈特利发现了,难保那只狗的下场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雅各布没有声张,替姑娘把鱼钩取下来,并又给了她一个鸡蛋,问姑娘是不是从没带回过家,总是在这里就把蛋吃完。姑娘承认是这样。雅各布说,那就赶紧吃了它。可你不能再到这来,再来一次,你爸就会知道这件事,你明白吗?姑娘安静地吃完那颗鸡蛋,她张开嘴时,一缕鲜血流淌到下巴上。等姑娘吞下了最后一点兒鸡蛋壳时,雅各布说,别再回来。我会再放一个鱼钩到鸡蛋里,这一次鱼钩上不会再系着钓线。你会吞下那个鱼钩,钩子就会撕开你的肠子。回家后,雅各布告诉妻子,是一条蛇,一条蛇一直在偷吃他们的鸡蛋。他把蛇打死了,鸡蛋不会再丢失,睡吧。
罗恩写哈特利一家的存在,是设计,因为哈特利一家不受帮助,极为自尊,所以他们的女儿连偷鸡蛋也会把鸡蛋壳一起吃掉,所以偷鸡蛋即便被抓受伤,也不敢呼告。罗恩写夫妻俩对人情的不同处置,是设计,否则不会牵出埃莱娜一句问话,让哈特利狠心杀了陪伴多年的狗,不会引出雅各布对哈特利女儿的包庇和同情。三个成年人的三个性格,导致故事应该是这个样子,只能是这个样子,一切都衔接上,围绕对艰难时世的深刻领受,在此圆心,画出一个不太复杂,然而饱满合理的整圆。没有一个地方是多余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冗赘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偏狭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囫囵的,《艰难时世》这样的小说解答了短篇小说魅力所在:细节如何才能动人,因为准确;准确如何才能达成,关于设计;语言如何才能劲道,因为炼字;炼字如何才能炼成,也关于设计。短篇小说由设计始,由设计终,通篇都在谋篇,落点都在匠心。有的看法认为匠心便是匠气,而匠气不上台面,流于机械。这是不公平也不懂短篇小说的发言,它忽略了小说家的创造力,标秉天赋,而只要去写,会懂得天赋尤其需要规训。
短篇小说是非常迷人的一种题材,尤其这几年,呈现一种短篇小说热,也许和信息的碎片化有关,也许是大家重新发现了这一文体带着锁铐跳舞的浪漫。短篇非常讲求操作性,需要把现实进行剪辑整理和抽象,然后找到最有表现力的情节,组合成一个世界。希望借由我一点儿粗浅的认知,让大家更喜爱短篇小说,更有阅读短篇小说的热情,并能够观察到热情以外,千丝万缕织就它们的信息:碎片很重要,碎片是刀面,折射出不一样的锋芒,锋芒有时,就是核心。
谢谢。
作者简介:杨知寒,生于1994年,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当代》《花城》等,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作家奖等。出版小说集《一团坚冰》《黄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