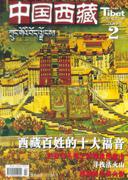在麦地卡当文书的日子
吴雨初

1976年进藏后,从自治区分配到藏北,再从地区分配到嘉黎县,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了一段时间。次年的一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同志到我们县检查工作。县里没有招待所,县委便让我腾出自己的房子,临时接待他。据说,热地书记一进屋便问,这是谁的家,陪同他的县委领导告诉他,是一位进藏不久的大学生。热地书记便对他们说,大学生进藏,不了解西藏基层的情况,应该让他们到区上去锻炼锻炼。虽然这不是一个特定的具体的指示,但等热地书记一离开嘉黎县,县委就再次把我分配到麦地卡区。
麦地卡,是嘉黎县、甚至也是藏北海拔最高的居民点,有的说是5400米,有的说是5600米,但肯定是在5000米以上。许多藏族干部到这里也很难适应。1959年平息叛乱时,这里是一个重要战区,叛乱者想凭藉这里的高海拔,与有着严重高原反应的解放军对抗,也确实有不少战士在这里丧生。我曾经在嘉黎区的烈士墓地拜谒过在这里牺牲的战士的坟墓。麦地卡距离我们的县城要骑5天马,或者坐一天汽车再骑半天马,算是距县城较远的一个区。
去往麦地卡的路上,有一座横跨麦地江——地图上叫野贡藏布江——的铁木桥,桥头有一个公路道班的土坯屋。来往的人们大都在这里等候着搭车,一头通往地区,一头通往县城。恐怕到现在为止,地县之间也没有定时的公共交通班车,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人们旅行只能四下打听车辆去向,然后求爹爹告奶奶似地搭车。我曾经有很多次在这里宿营。有一次我在这里等了整整三天,却没有搭上一辆车。道班的主人是一位长着大胡子的工人,他看见我这么一个孤苦的异族青年可怜兮兮的,便以道班工人的身份来帮我拦车,但道班工人的身份是拦不住车的。大胡子气得直用石块砸汽车,对着向他扬起尘土的汽车大骂:“亚古没都(不好)!”我那时真是很想当官,要是能当到一个副县级干部,也会有辆吉普车来接我的。虽然我后来当上的官要比那时想象的更大。
我是在1977年的冬天被派到麦地卡区委当文书的。知道区上是没有人可以理发的,在县里刮了一个大光头,戴上顶狐狸皮帽,裹着一件皮大衣,搭乘县车队的大卡车,在车顶上坐了大半天,然后在那个道班下车,请大胡子的道班工人给附近的公社捎上一个口信,请他们派一匹马来。送马的牧民告诉我说,公社说,我们就不派人送你了。这是公社的马,你骑到麦地卡,就把它放了,它自己就会回来。临了,那个牧民还留下一句让我挺寒心的话:“麦地卡的草再好,这马也是不会贪恋那地方的。”我不可能不感到一种委屈,我们一同进藏的同学中可能很少有像我这样独自“走马上任”的。
那天恰好逢上一场暴风雪。我骑着马穿行在不知厚度的雪幕当中,感觉越走便距离自己过去熟悉的生活越远,越不知道风雪后面是怎样一个世界。独自策马在风雪草原,不仅领略着孤独,而且更现实地领略着寒冷。更可怕的是,通往麦地卡的道路被积雪掩盖了,肆虐的风雪几乎让我迷失了方向,还能不时听到草原狼的嗥声。一种深深的恐惧控制着我。我知道,如果我今天果真迷了路,必定会冻死在草原上。于是,我只能使劲打着马,尽量行走在地势高点的地方,使自己的视野开阔一些。在一种绝望感和黑夜一同袭来的时候,我隐约发现了灯光!麦地卡,并没有拒绝我,但它的寒冷使我的手脚冻的麻木了,直到第二天也没有能够消除。
我的前任小杨——一个从河南农村招来的小青年,在这里干了近两年,熬尽了漫长的寂莫,因为我的到来接替而十分兴奋,因为他就调回县城了。在我到达的第二天,便急不可耐地骑着我的那匹马走了。
从此,麦地卡周围1000多平方公里的草原高地,只有我一个汉人。
一切都靠自己。我的前任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我自己去打水。小杨只告诉了我打水的方向和地点。我担着两只铁皮桶去才知道。那里根本没有我想象的水井和水流,只是一大片冰川而已,那里扔着几把铁锹铁镐,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凿出冰块来,再装进两只铁桶担回去,每走一步都过于沉重,都能最具体地感觉到5000米海拔对于人意味着什么,只有二三百米的路,居然气喘吁吁地走了半个多小时。
我这个人没有语言天赋。在区上工作的日子,虽然我也在努力地学习藏语文,区上藏族干部也或多或少地懂些汉语文,我们相互之间还是挺关照的,但毕竟独处的时间更多。与我相伴时间最多的,是区上那台电唱机兼收音机。这还是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中央代表团的赠礼,每个乡都有一台。不过,我们区的那台收音机已经磨损得相当厉害,加之这里的信号太弱,几乎没法用。我想了很多办法,反反复复地倒腾它,用一根铁丝把它的天线接到牛粪火炉的铁皮烟囱管上,终于使它能够发出微弱的声音了。正是透过这台充满杂音的收音机,我在麦地卡遥遥地感受着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
我从那里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感到其中的词汇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中,听到要求发展生产力和改善物质生活的呼声,听到批判我们曾经以为很革命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很想从中努力理解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走向,但仅从那里知道的信息真是太有限了。
麦地卡区的报纸,我们称它为“抱纸”。通常是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由区上到县里办事的人员捎来,那些迟到的报纸也往往是被用作生牛粪火的引火料,但对我却是最要紧的东西了,所有的报纸都要从第一版看到第四版,尽管那时候的新闻还是那么程式化。从地区到县城之间有一座雪山的阻隔,遇到大雪封山,往往几个月不能通邮。有一次,我一下子就收到了50多封信。区里的通讯员说,你一个人的信比我们全区的信还要多。我们区的财政助理每月都要到县城去一次,与县财政局结算账目,并领回我们区干部的工资。我委托他从我的工资中拿出50元——这几乎是半个月的工资,到县新华书店(其实就是一间平房)给我买书,至于买什么书,我说不清,说清了他也听不明白,便给书店的同志写了一张便条,凡是社科类和文学类的书都可以。于是,区财政助理便在他的马背上给我驮回了一纸箱书——有政治宣传的,有“文革”期间出的小说,让我最兴奋的,一是“文革”后最早出版的《李白诗选》,一是老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我在微弱的蜡烛光底下,读着老先生们的著作,感觉很是幸福。

有一天,我捧着的书突然出现了鲜红的血滴,开始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我自己的鼻血,等我抓起枕巾想极力压住,那鼻血把一条枕巾都湿透了。后来我找到区里唯一的卫生员——当时叫赤脚医生,她给了我一些药,并告诉我不要太紧张,流鼻血实际上也是一种高原反应。有许多次,强烈的高原反应让我鼻血滴流不止,把我吓坏了。后来的记忆力衰退,可能与那时有关。
在区委当文书,每个月的全部工作,就是开两次碰头会,根据两次碰头会的情况整理两期工作简报上报县委,也就是两天的时间。
西藏当时的体制是,县以下设区(相当于内地的乡),区以下设乡(相当于内地的大队),乡以下设生产队。麦地卡区一共有四个乡,乡干部都不是国家编制以内的,就是说他们不拿国家工资,而是挣工分,但区里每月给少量的津贴。每过半个月,乡干部就到区里集中一次,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简报仍然是老一套的三段式:政治学习、牧业生产、阶级斗争。开会的时候,我很狼狈,因为不懂藏话,就由桑美书记给翻译。如果不翻译,他们骂我,我也不知道。但那些乡干部都对我非常好,不会骂我。想想这1000多平方公里就我这唯一的汉人,至少也有一点新鲜感吧。而且,有了我这么一个汉人,会议开起来似乎也要更为认真严肃一些。
来区上开会的那些半脱产的乡干部们特别愿意住在我的屋里——县里没有招待所,区里就更甭提了。他们在我屋里的空地上,铺开自己的马被套,在我的炉子上烧茶,在我的锅里煮肉,我的生活其实跟牧民没有什么区别了。乡干部们用他们懂得极少的汉语词汇,而我则用我懂得极少的藏语词汇,别有一番趣味地交谈着。男人们的话题当然会说到女人,但我们这样的语言水平不可能谈到更为隐晦的内容,只能听懂乡干部们说他们乡有一位美女,“宗译”——即文书愿意的话可以把她娶过来。我也欣然凑趣——可以可以。乡干部却补充说:“但那是一个牧主的女儿。”最后引得大家哄然一乐。牧民之间是很重馈赠的。可惜我当时实在是没有东西可以相赠的。乡干部们来,总是给我带条羊腿什么的,我就把自己的家乡景德镇的瓷碗送给他们,最后我自己只好到商店买了几个塑料碗用。他们最喜欢的还是我从县城里带来的辣椒面,吃牛羊肉蘸点那东西很提味,我总是用信封一个个地装好,分赠给他们。
平日里,也常有牧民来找我帮忙,因为这个区也有一些牧民的孩子在拉萨、或者是在内地上学、当兵或者工作,总有些书信往来。因为邮政方面的需要,信封上最好是写两种文字,他们便找到我,让我给他们信封写上汉文地址。我十分乐意做这些事情,虽然写个信封实在用不着一个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但我在此时感到自己不是多余的,还能够为牧民做一些事。重要的是,可以从牧民的眼光中感受到一种民族间平和的友谊。
每个月我还要随着区委书记到一两个乡转转。住在牧民的黑色牛毛帐篷里,靠着中间那个泥土砌成的大火塘。早晨钻出马被套时,藏族阿妈或大嫂就把第一碗酥油茶递到了手上,晚上入睡前,她们又会让你喝上一碗自制的酸奶,说是这会睡得更好些。这时候,你怎么会想到他们的生活习惯——没有洗过手、或者是用一条脏毛巾擦过碗呢?在措那乡,有一位牧民为了款待我这个汉族客人,还将他家保存了不知多长时间的大米拿出来,但他家没有高压锅,那是做不熟米饭的,为了取得一定的压力,他想方设法用一把高腰细嘴的酥油茶壶来煮,虽然比一般的平锅略为好一些,但那米饭仍然只有五成熟。这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半熟的夹生饭其实更难吃。我为这位牧民的热情所感动。但此后其他牧民家,一旦发现他们有做米饭款待我的意图,我便赶紧声称,我已经是一个老牧民了,已经“吃不惯”米饭了。
麦地卡的夏天是很美的。没有事的时候,我会拿着一本书,跑到麦地江边的草滩上,一躺就是大半天。那里地阔天低,草原伸展到天际线,形象很特殊的云朵,像是固体物浮悬在半空中,远处的牧童的歌声让人真有一种童话的感觉。这个世界很大很大,却又很小很小。
那年冬天闹雪灾,我们麦地卡区的灾情相当严重。区机关的生活燃料供应原是附近牧民送来,我们付款的,这也算是牧民的一项收入。但雪灾一来,牧民自己的燃料都有问题,就难以保证给机关送来牛粪或者羊粪了。我们机关干部就只好到草场上铲开积雪,挖一些草皮来烧。雪灾中,我们到一些灾情严重的牧村去,看到一群群倒毙的牲畜,心里很不是滋味。听着受灾牧民的哭诉,也忍不住一阵阵悲伤。
1978年的一天,我接到《西藏文艺》编辑给我发来的电报,通知我参加一个文艺创作座谈会,我从县里骑了5天马到麦地卡区,再从麦地卡区骑了4天马到那曲,然后坐了1天车到拉萨,我赶到拉萨时,会议已经结束了。骑9天马,真是一种痛苦的事。我的尾椎骨处至今还留着在牧区骑马时磨破的伤痕。我穿着一身藏皮袍,带着一个牵马人——那个牵马人是一个1959年参加过叛乱的人。在路上,一开始我相当警惕,在那空旷无垠的草原,真有些怕他加害与我,所以总让他骑马走在前头。两天后,我发现他还是很老实的。路上借宿,都是我用半通不通的藏话先向当地的老百姓说,他再帮忙解释,然后,他就去忙着卸行囊、放马。就这样,我们两个牧民打扮的人经过长途奔波后进入了那曲镇——那可是我们40万平方公里的藏北地区最大的城镇了。有趣的,我到那曲镇后,打算到地区歌舞团去找那里的作曲家、也是我在江西师大的同学黄绵瑾去借宿。我敲错了一家的门(后来我认识他是一个藏族舞蹈演员),他打开门一看,看见两位陌生的牧民打扮的人牵着两匹喘着粗气的马,轰然把门又摔上,只甩出一句汉话:“老牧民!”
我被拒绝了,是因为我像个牧民。虽然同样都是藏族,他们拿着国家的工资,就自视高于牧民一等了。如果我真是一个牧民,而且又听懂了他的话,心里该作何感想?
后来我调到那曲地区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我的那些麦地卡“老乡”,到那曲还会来找他们曾经的文书。有一次,他们是赶着一大群驮牛到那曲来驮运粮食的。几个牧民在我家借宿,把他们赶来的四五十头驮牛都拴在我们文教局的院子里。第二天早上,他们走后,给满院子留下一堆堆牛粪,在灿烂的阳光下冒着腾腾的热气。我们局的藏汉族干部便七嘴八舌地指责我:“你这个老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