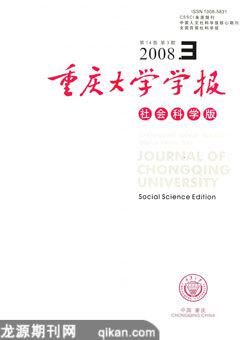从表象知识观到实践知识观
何 兵 王青青
摘要:近年来,库恩与逻辑经验主义的关系受到重新评估,有人据此提出库恩并不是革命家而是保守派,这涉及到如何看待库恩哲学贡献的问题。文章认为库恩的哲学贡献在于促成了研究科学视角的转换,即从作为表象的科学知识转向实践中的科学活动,而后库恩时代的科学研究者,包括科学知识建构论者和认知科学家,均比库恩本人更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许这正是库恩显得有些保守的原因。
关键词:表象;实践知识观;后达尔文康德主义
近年来,人们根据库恩后期的“语言学转向”,特别是他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批评态度,发现所谓的库恩革命更像是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某种修正。在一些人眼中,作为激进革命家出现在学术舞台上的库恩,其实是保守的改良派。库恩究竟是革命家,还是保守派?这个问题涉及到如何全面看待库恩的哲学贡献问题。笔者曾经撰文讨论过近年来对库恩的保守主义的解读。在此,笔者试图阐明的是库恩哲学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开启了对科学知识的实践理解,这正是当前科学哲学研究中最有影响的认知取向和社会学取向的源头。
一、从表象到实践的科学观
(一)重新评价逻辑实证主义
自逻辑实证主义衰落后,列举其各种罪状成为提出“新”哲学主张的惯常做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逻辑实证主义这种哲学取向不再被认为是具有威胁的哲学运动,因而它的价值与意义也被人们冷静地对待,人们不再简单批评逻辑实证主义的错误,而是通过细致的哲学史考察,分析其出现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弗里德曼在《重新评价逻辑实证主义》一文中认为,后实证主义哲学家错误地理解了逻辑实证主义运动的起源、动机和哲学目标。实际上,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并不是要提供认识论的基础主义,相反他们的哲学也不是基于某些先验的普遍原则,而是根据近来科学中的革命性进展重新界定其哲学任务,以取代传统的心理主义认识论。
赖欣巴赫严格区分“发现的范围”与“辩护的范围”,充分地体现了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哲学诉求。我们不能讲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研究范围的限制是一种错误,因为研究范围的转移体现的不过是哲学兴趣的转移。哈金明确提出,我们不能因为研究兴趣的不同,而指责对方错误,因为研究兴趣的转移,仅仅是把这类问题“搁置”(undoing)到一边。实际上,如果要坚持库恩的历史主义立场,借用库恩的术语,兴趣间是“不可通约的”,那么,我们最好不要指责说逻辑实证主义是一种错误的哲学运动。逻辑实证主义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的辩护问题,涉及到理论如何表象世界;而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的演变,涉及到知识的发现问题,即获得科学知识的理论表象过程,以及表象方式的转变。这是完全不同的研究视角。库恩的贡献,正在于促成了研究视角的转换。
(二)从实践维度解读库恩
约瑟夫·劳斯正确地看到了库恩工作的意义。他认为,“库恩著作中最具革命性的方面来自于他所强调的科学研究的实践维度,而这一点几乎被所有的哲学解读者所普遍忽视”。他指出,当库恩“要勾画出一种大异其趣的科学观,它能从研究活动本身的历史记载中浮现出来”时,这种写作努力实际上是将科学视为实践领域而不是陈述之网的最有影响的尝试。劳斯重新从实践的维度,把库恩的哲学解读为关于科学实践的哲学。
科学哲学通常被认为属于认识论的,它关乎科学知识,相关的哲学问题涉及到科学知识的目标、结构、来源、方法和辩护。而库恩本人似乎也并未清楚地区分认识论的和实践的科学概念,因此他的观点看起来是要提出另外一套认识论观点。但是劳斯建议,如果我们把描述科学的关键从科学活动的产物——科学知识转向科学活动本身,那么人们所熟悉的概念,诸如“常规科学”、“危机”、“革命”均会发生变化。
在库恩之前,人们关注的是作为表象的科学知识,而不是更能揭示科学本质的科学实践。库恩在《结构》中并未考虑为科学知识辩护,而是想告诉人们,科学家是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专业训练和研究经历使科学家相信他们正在做的:会得到什么,他们能够做什么。这些能力由于他们实践地掌握一个或几个范式而整合起来,具体的科学成就给可能的研究指向一个有希望的未来。范式不能理解为共同体成员接受的信念(甚至意会信念),而是概念化或介入特定情形的示范性方式。接受一个范式更像是获得并使用一系列技巧,而不是理解或相信一个陈述”。库恩后来用“discipline matrix”这个词取代“paradigm”,就在于强调“disciplihe”中的“训练”和“规训”的含义。决定某个人是否属于同一科学共同体,不在于他是否有相同的背景信念,而在于他是否从事共同的科学实践。反常与危机也可以解释为科学实践的危机,因为反常现象使科学家不能确定该如何进行研究:什么样的研究值得继续进行,什么样的背景假定值得依赖,什么样的概念和模型可以引导进一步的研究。劳斯因此认为“库恩危机所引起的最根本问题,不是信念的矛盾,而是实践的不连贯。革命取得成功,是由于恢复了研究的动力”。例如,伦琴x射线的发现,开辟一个新的实践领域,而20世纪40~50年代由于引入超高速离心机和电子显微镜,促成了经典细胞学向现代细胞生物学的转换。这些新的研究,都在先前研究没有陷入困境(危机)的情况下进行的。同样,科学进步不能理解为越来越逼近真理,而是通过革命“摆脱常规科学危机所带来的研究困境”。劳斯提出,库恩在哲学中导致的从科学知识到科学实践的转向,并不是让我们想科学应该如何,而是要我们哲学地思考科学。这实际上是要求自然地去描述科学实践,而不是提出什么规范性的原则。劳斯相信,把科学看成是实践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科学,以及我们应该从事什么样的科学。
因此,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库恩大量运用历史案例或历史分析的目的,并不是要去发现科学活动中的规律或规则(这是库恩在1969年后记中明确反对的),也不是重构科学的合理性,而是要去揭示科学活动的实践本质,而这正是库恩哲学革命的意义所在。可惜的是,注意到逻辑经验主义内在困难的新一代哲学家,虽然也开始从历史的视角理解科学,但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库恩工作的真正意义,在某些方面更像是传统的科学哲学。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仍然把注意力放到科学实践的产物——科学理论上。
二、表象知识观的局限
(一)重构历史的合理性
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等人的立场虽然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把科学的合理性建立在理论陈述对世界的表象关系上。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科学理论是一个一阶谓词逻辑构成的公理体系,理论陈述与经验对象之间具有某种对应关系,理论语言通过操作定义可还原为观察语言,最终还原为可靠的直接感官经验。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把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基础主义和还原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无论是用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还是劳丹
的研究传统,都不过是扩大了理论的范围:遭受评价的,不再是单个的理论陈述,而是理论的集合。这种扩大后的迪昂一奎因整体论,并没有改变新历史主义对理论表象的关注:评价理论进步是预言更多的经验内容(拉卡托斯)和更高的解题效率(劳丹)。这些新历史主义者仍然没有脱离以理论为中心的表象知识观。
表象知识观关心的是知识的辩护问题。表象的知识观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按柏拉图的理解,所有的知识都是对理念的不完善摹本,因此,如何恰当地表象理念,追求“真知识”成为认识论的主要目标。逻辑实证主义试图通过分析语言(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之间的关系,从方法论上逻辑重构科学知识,从而实现为科学知识辩护的目标。新历史主义者则从实证主义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开始关注特定科学实践的细节,他们开始从科学方法论的逻辑结构转向科学史的叙述结构。夏皮尔把科学史设想为形成自主研究域的过程,劳丹把科学史看成是问题及其解决的历史,图尔明则把历史看成是选择性地采纳概念的历史。
实际上,新历史主义者试图在历史的叙述结构中,重构科学发展的合理性,以避免归之于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关于科学变化的非理性主义和主观主义。为此,他们希望能在元方法论的层面,维持足够的科学合理性、客观性和进步的概念。例如在拉卡托斯那里,一个研究纲领的理论和本体论承诺的“硬核”在面临经验挑战时,通过辅助假说的“保护带”,总是得以保留;夏皮尔把“研究域”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作为评价意义变化的合理性基石;而劳丹为科学变化的网状模型抛弃了问题解决的可比较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家本体论的、方法论的和价值论的承诺均发生变化,但它们并不是同时发生。作为其结果,科学家的承诺中的任何因素中的变化皆可以通过寻求相对稳定的和共享的其他背景因素理性地予以辩护。
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新历史主义者,无论是从方法论的逻辑结构还是历史叙述的结构,无论考虑的是科学知识的真还是科学理论发展的合理性上,都涉及到理论与世界、语词与对象之间的表象关系,都是表象主义的知识观。表象知识观导致两个后果:一是表象的世界取代了生活世界;二是实践中的个体为先验的主体所取代。前者受到胡塞尔以来的哲学家的反对,刻板的科学家形象遭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无情揭露。
(二)对表象知识观的破除
库恩的《结构》革除了人们对科学形象的传统理解。与波兰尼注意到“默会知识”一样,库恩要我们关注实际的科学活动,要求在科学活动中去把握科学知识的本质。库恩的切入点是从作为“训练母体”(discipline matrix)的范式,即从一个新手成长为专家的社会化过程来看科学活动的特质。当然,作为一个前驱性的人物,我们发现库恩相比他的后继者,还不够彻底。实际上,库恩对科学知识的结构并不感兴趣,相反,他更关心形成科学知识的过程以及知识的传承。他采用历史个案研究分析方法,力图再现科学知识生产的历史过程。但是库恩的方法论立场与受他研究启发的后库恩科学研究者有所不同。后库恩科学研究者,如社会建构论者或认知科学家,虽然他们都采用了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但侧重点有所不同:或侧重于社会学的因素,分析科学知识中的社会成分;或侧重于从认知的角度考察形成科学知识的认知过程以及知识的认知结构。但在这些研究者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非常关注实践中的科学家个人。
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者首先打破了关于科学家的理想形象,在他们的眼中,科学家也是食人间烟火的凡夫俗子,他们在科学争论中运用劝说、修辞、权势等手段。科学知识同所有的其他知识形态一样,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而科学知识的内容也无法排除社会的因素。这种对科学的合理性、客观性持有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态度构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家行为的基本认识前提。虽然库恩本人一再否认他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联系并批评知识社会学者的强纲领立场,但科学知识社会学者仍然承认来自库恩的启示。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倾向受到传统科学哲学家的批评,但他们关心科学中的具体实践,通过对实验室和诊所进行人类学考察(最著名的是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谢廷娜的《制造知识》),分析科学知识的社会构建过程,揭示长期被掩盖的真相。这对我们理解科学活动的实质,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应该说,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者,自觉地破除表象的知识观,充分地利用库恩哲学的启示,把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和文化”。
三、后达尔文康德主义知识观
当然,表象的知识观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库恩本人在自1970年以来同新实在论者的论战中,也差点陷入到理论表象这一传统知识论的陷阱之中。库恩后期致力于语义不可通约性问题上,特别是晚年自称是“后达尔文新康德主义者”。但他考虑的仍然是理论如何表象世界的问题,只不过他是从分类结构的角度来讨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论者认为后期库恩走向了他早期反对的立场,是“错误的转向”。当然,库恩也注意到了表象知识观存在的问题,否认存在某个更接近实在的分类词典,坚持从进化论的角度来隐喻知识的进步,特别是把知识看成是某种生境(niche)内的信念,保留了在实践中把握科学本性的可能。
自20世纪80年代直至库恩去世,库恩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分类学的“词典”(1exicon)来替代备受争议的范式概念,并进一步区分了语言翻译与语言诠释,试图从语言学习的角度解决不可通约理论间的交流问题。实际上,后期库恩的哲学努力可以被看成是本体论的:不同的语言共同体拥有的分类词典,可以视作是自然和社会世界中某个部落(tribe)长期的产物,词典使对应的生活形式成为可能,并建构了这个共同体的可能世界。就像我们不能说哪种生活形式更为优越一样,我们也不能说哪个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更接近实在。要理解栖居于不同生境(niche)的共同体(部落)所用语言,不能求助于词典的翻译,而只能通过语言学习,进入到这个部落的生活场景,掌握其分类结构,从而熟悉其词典的用法,进而理解对方的语言。因此,后期库恩对不可通约性问题的解决,是通过语言学习实现的。
库恩承认他发展出了某种后达尔文康德主义立场。象康德的范畴一样,库恩的词典提供了据以经验的前提,但据此分类的词典,不象康德的范畴是固定不变的,它在从一个科学共同体向另一个科学共同体过渡时,可以发生变化,并因此为不同的语言共同体提供不同的“现象世界”。之所以称为是后达尔文的,就在于库恩的知识观是用进化论来隐喻的。在1969年《后记》中库恩已经用进化树来隐喻科学的进步,这与趋向真理的进步观,无疑要更少瑕疵。用库恩的话来说,“一个词典提供的存在于世界(be-ing-in-the-world)的方式不能用真/假来评价”。
因为每个词典都促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某些方式更适合某些目的,而有的方式又更合适于其他目的,但没有一种方式是因为真而被接受或因为假而被拒斥;没有一种方式被赋予了接近实在的世界的特权”。通过实践的介入,库恩避开了理论与实在的表象关系问题,表象知识观被彻底抛弃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库恩的后继者,可能比库恩本人更深刻地领会了《结构》的思想史意义。库恩的诠释者们,特别是社会建构论者和认知的科学哲学家们,从库恩的范式概念以及历史案例研究出发,注意到了实践中的科学语境远比作为科学实践产物的科学理论更值得关注。他们不再以理论作为讨论的中心而是以科学实践为话题,把人们关注的中心,从作为表象的科学知识转入到作为实践的科学活动。事实上,后期库恩所谈到的“理论”,不再是逻辑经验主义者强调的具有静态逻辑结构的与永恒真理相联的概念,而是与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境内的生活方式相关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真与假的评判变成好与差的比较。
因此,我们不能像伯德那样认为库恩后期的语言转向是一种“错误的转向”,也不能像一些论者那样把库恩理解为一个保守的改良派,而应把库恩的工作放到科学哲学发展的全景中予以理解,特别是从延续库恩所开创的或启发的研究路线上来看库恩后期工作的意义。我们可以不谈库恩是否终结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时代,倒是有理由声称库恩开启了一个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的新时代,而这个时代可以冠以“后库恩科学研究”。之所以用post-Kuhn这个词,主要是用于限定那些受到库恩著作启示的研究路线,特别是那些把科学看成是一种实践活动的研究。这些研究路线中当前较有影响的是建构论和认知科学。建构论者倾向于从社会的角度分析科学知识的构成,把利益、权力和磋商等因素纳入到科学知识之中。例如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强纲领”、人类学的实验室研究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与传统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知识社会学者不同,一些认知科学家开始利用心理学、神经生理学、人工智能学等认知科学的成果来分析形成科学知识的认知过程,揭示科学知识的认知本质,他们特别侧重对科学发现和概念变化的认知机制分析。对科学知识的认知研究,在20世纪末科学哲学的认知转向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特别是认知科学家们自觉地推进对库恩思想的认知分析,为我们理解库恩哲学革命的意义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