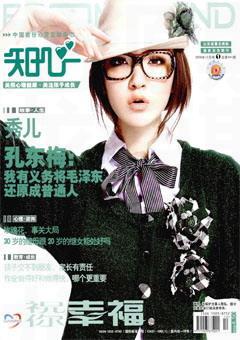孔东梅:我有义务将毛泽东还原成普通人
席淑君 乔 红
采访手记:
初次见到孔东梅,是在去台北参加第=次海峡两岸女企业家经贸论坛的飞机上,邻座的同行悄悄地让我转头看了看静坐在位置上的她。
她是做文化产业的,伟人毛泽东的外孙女的身份,注定了她在巾帼荟萃的女企业家中的与众不同。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她在台湾的影响力。
7月9日那天,论坛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开幕,蜂拥而至的台湾媒体一进会场,就不约而同地将镜头、麦克风对准我们的团长、全国妇联副主席黄晴宜,还有海尔总裁杨绵绵,澳门的何超琼,再有就是孔东梅了。大会议程进行着,台湾年轻的记者们焦急地等候在会场门口,我悄悄地问他们:最想采访的是什么?他们笑着回答说:人!那个毛泽东的外孙女!
他们私下议论:她长得好标致哦,同毛泽东是那么像!
他们想亲耳听到:她对台湾的感受如何?将来有没有与蒋家后代合作的可能?
台湾的媒体从业者一般很年轻,那段历史离他们很远很远了,可对毛泽东,他们却不陌生,此次与红色家庭的后代面对面,真是机会难得。
孔东梅始终微笑着回答台湾媒体的采访,她的聪慧与大方,她对台湾喜爱的真诚表达,征服了台湾媒体,她的访谈被刊登在次日的各大报纸上,就连台北普通的市民也对她津津乐道。
在台期间,我一直在观察孔东梅:女性们聚在一起,兴奋点总是很多,无论是在会场,在参观,还是安排的购物空隙,她总是低调地融入人群中,随和又沉稳,即便是在结束日程临行前安排的免税购物店里,女企业家们兴奋地疯狂采购,一掷千金,她也保持着理性的低调。
一路下来,孔东梅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也使我对这位年轻的伟人后代肃然起敬。于是,我决定采访她。
有了此次同行的经历,孔东梅没有拒绝,邀请我们到她在大山子798的菊香书屋见面。
798是京城有名的文化艺术中心之一,一路都是设计前卫新潮的艺术画店,挂着用毛体题写的不太扎眼的菊香书屋牌子还是被我们很快找到。
书屋所展卖的大多数是记载着中国历史的红色经典作品,但布局却时尚又现代,与名字很协调。“菊香书屋”曾是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生活过十几年的地方。一年前孔东梅把它“搬”进798艺术区,有了新的寓意。
三个小时的面对面,我们时而随着她的回忆跨越时空,回到那峥嵘岁月,领略开国元勋们为国家为民族的豪情与艰辛;时而随她回到上海那个非常岁月——4岁的她陪伴孤独的外婆生活的日子。毫无疑问,作为伟人的后代,东梅除了与生俱来的自豪感,更多的是压力和责任,而这种压力和责任,是如何继承先辈留下的精神财富,她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大家一条她所知道的真实的先辈们的道路。
采访后,又一次翻阅她的书。在《翻开我家老影集》那本书中她这样写道:在成长的岁月中,我歌过,我舞过,笑过,哭过。那个独自向隅、亦歌亦舞的小姑娘,似乎已经尘封在记忆深处,定格在小小的黑白照片中了。只是活到30岁之后,往事反而清晰起来,经历了这些年的风雨,我从没像现在这样理解外婆、了解妈妈、了解自己。于是一点点拾起记忆的碎片,拼凑成各种可能的形状,最终形成这本书,里面装的其实就是我们祖孙几代人的一些思索。
在《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中,她坦承,很多是借助别的书籍,如王行娟的《贺子珍的自述》,外加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才开始理解沉默的外婆。外婆勇敢无畏、敢于开创的奋斗精神固然可敬,而追求独立的人格更加难得。这样一位女中豪杰的命运却如此不幸,是不能单纯用性格、脾气来解释的。如果她不是频繁生育,或亲生骨肉没有夭折或散失;如果她没有身负重伤,或弹片被及时有效地取出,外婆怎会离开外公?她的后半生,同时也是外公的后半生都是另外的一种活法。
家史即是历史。同为女性,作为一位以女性视角关注社会和女性发展的媒体记者,我认同外界对她的作品是“在众多毛泽东出版物中最具特色和有份量的”评价,还有,她作品中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场景中的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故事,让我们再一次理性地看待当年的人和事,也明白了这个出生在外婆身边,在上海陪伴孤独的外婆生活到6岁才回到北京父母家中的外孙女,成年之后的思索;明白了生于70年代、有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现在仍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的中西文化交融背景的知识女性的历史感和祖孙三代女性有关婚姻、爱情、家庭的思考;读懂了经历大风大雨之后她的成熟与豁达,还有深藏在心灵深处的淡淡感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之际,我们推出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的访谈,一起缅怀历史,勉励前行。
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
1972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动荡期间,当怀孕的李敏向自己的父亲毛泽东征询意见,问他要不要把自己的第二个孩子生下来时,孩子的外公说:要,生活再困难,也是应该要这个孩子的。
后来,毛泽东看到孩子的照片,给她取名“东梅”,“东”是他名字里的一个字,“梅”是他平生的最爱。
不过,遗憾的是,直到毛泽东去世,孔东梅都没有亲眼见过外公,毛泽东也没亲眼见过这个和他一样下巴长了颗痣的外孙女。
记者:你对外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孔东梅:我对外公的第一印象,其实是在外公去世后,我7岁时和妈妈去天安门的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看到那么多人在哀悼外公,我第一次感到震撼。我才知道,我的外公是一个伟人。
后来,妈妈也会和我讲外公和她之间的故事,比如妈妈把外宾送来的面包吃了,外公就告诉她,中国的馒头也是中国的面包,馒头烤一烤,也很好吃的。小时候,妈妈常常给我烤馒头片吃。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走近你的外公的?
孔东梅:在去美国留学前,我对他的了解其实并不比同龄人多。2001年,我在美国收到了母亲写的书《我的父亲毛泽东》,书中提到家族的很多往事,我看后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我觉得自己作为毛家第三代人,有责任去还原过去的那些事,去寻访我外公和外婆独特的人生之旅。
而且,我始终认为,要了解中国的今天,必须了解外公那些新中国的开创者。为此,我去拜访过许多认识他的人,去过许多他所到的地方。
记者: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你是否同你的那些“洋同学”谈起过你的外公?
孔东梅:我去美国的时候,除了华人圈一些人知道我的身份外,我的同学都不知道我是毛泽东的外孙女。我在那里修的是国际政治,所以课堂上曾经讲到我的外公,那时的美国人对中国,对我的外公的了解非常有限,在他们印象中,中国还很封闭,很贫穷。我当时就站起来大声反驳,跟我的同学们讲外公领导革命前的中国,建国后的中国还有现在的中国,用事实去说服他们。
记者:有关你的外公毛泽东的书很多,那你所写的书和他们在视角上有哪些不同呢?
孔东梅:我读过许多描写外公的书,觉得对作为伟人的外公的描述已经足够多了,而我笔下的外公更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儿子,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一个感情丰富而不刻板的人。我的书里
记录着外公的初恋,收录着外公写给女儿的信,无论是从毛家后人还是从当代女性的双重视角出发,我都希望以朴素的心态将外公从一个伟人还原成一个普通人。
记者:现实生活中,你和你的家人会以怎样的方式纪念外公?
孔东梅:我现在遇到了困难,便会翻翻外公的书。记得我外公去世后,我们家设了个灵堂,一直保持了很多年,我爸爸妈妈一直都在祭奠外公,现在,在我们的新家里,我请当代艺术家创作了一幅外公的油画,还有一尊外公的雕塑,但它们都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有关外公的画作和雕塑,它们被赋予了现代元素,我觉得很有新意。
现在,每年的12月26日和9月9日外公诞辰和逝世的纪念日,妈妈和我都会去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献上一束鲜花,寄托我们的哀思。
记者:六十年前的十月一日,你的外公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他那带着湖南口音的洪亮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对于国庆六十周年,你以什么方式去纪念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
孔东梅:菊香书屋正在策划一本书,计划国庆前后推出,它是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暂定名为《毛泽东箴言》,是对毛泽东文集,选集的重新梳理,摘录,这也是我作为毛家后人献给国庆六十周年的一份礼物吧。
毛家的三代女性
2000年,从美国学成归国后,孔东梅在创业的繁忙之中,追寻外公外婆的足迹,挤出时间先后创作了三本书,她用自己手中的笔还原了外公风雨人生的同时,也记录下了毛家三代女性生活变迁的历程。
孔东梅生命时光的前6年一直在外婆贺子珍身边度过,她迄今还珍藏着外婆曾经穿过的两条裙子,孔东梅现在和母亲李敏生活在一起,她说她对文学的爱好源自母亲的熏陶。在她所著的书的扉页中,孔东梅写道献给——给予我生命和梦想的外婆和妈妈。
记者:小时候,你眼中的外婆是什么样的?
孔东梅:小的时候,外婆的身体不好,她长期在医院接受治疗。在我印象中,家中的外婆总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有时叉着腰独自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因为我当时很小,在家里,我们两个很少交流,总是沉默着。
不过,外婆对我一直特别照顾,她总是叮嘱工作人员给我做好吃的。外婆待人非常热情,对待老战友总是慷慨相助,每次有战友到上海,她都会去商店买上好多东西。她去世的时候,自己身边只有两千块钱,一台电视机和简单的衣物。
记者:你曾经在书中写道,“外公外婆的传奇,成为永久的爱情悲剧。”作为现代女性,你怎么看待他们之间的那段感情?
孔东梅:外公和外婆在一起的10年时间里,大小产加一起,孕育了10个孩子,生下来6个,有的夭折了,有的丢了,现在惟一存世的,只有我妈妈李敏一个人。
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女人来讲,她承受着多大的压力和痛苦?她尝遍了人生疾苦,失去了那么多,最后也没能跟我外公一起走完这一生。
记者:你的母亲李敏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孔东梅:她今年已经73岁了,身体还不错,过着深居简出、安详平和的晚年生活。“菊香书屋”做活动的时候,我们曾经请她来798看过。
记者:你的母亲经历了从延安到莫斯科、再到北京中南海一段特殊的历程,你是否想过写一本以她为主角的书?
孔东梅:我很想写一本关于妈妈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的书,妈妈曾经在那里度过了7年时光,而且不仅仅是她,还有很多老一代领导人的后代都曾经在那里学习生活过,我已经查阅了那里相关的档案材料。
记者:毛泽东外孙女的这个身份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面对这个身份,你感到更多的是压力还是什么?
孔东梅:作为名人之后,就一定要肩负一些东西。就像我的身上流淌着的毛家的血液一样,这些都是无从逃避的,而且压力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可能作为“毛家人”,别人会对我更加严格要求。就像我这次参加女企业家的活动去台湾,回来后,我上网就看到有网友说孔东梅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不该怎么怎么样。而且毛家的家风一直很严,我的母亲一直提醒我,“不要管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个背景,别人怎么生活你也一样”。
时尚的红色后人
2003年年底,为纪念毛泽东110周年诞辰,湖南卫视推出了电视系列片《东梅视界——毛泽东和他的亲属》,孔东梅担纲节目主持人。很多人也由此认识了毛泽东这个漂亮聪慧的外孙女。
虽然孔东梅自身并不喜欢镁光灯下的生活,也一直保持着低调,谦和,与时政界保持着距离,但她的一举一动,甚至是图书签售时她暗红色的脚指甲油都在吸引着媒体的关注。
记者:为什么你会选择做文化传媒产业,成立“菊香书屋”这家公司是出于什么考虑?
孔东梅:我受妈妈的影响,一直很喜欢文学,初中时几乎读完了所有可以找到的世界名著,高中参与校刊的出版,大学创办文学社……我喜欢自由,希望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我曾经幻想做海明威那样的作家。
通过自己从文化视角对外公的历史和中国红色文化的研究,在继承和延续家风的同时,我也希望能对他所代表的红色经典文化加以弘扬,让文化走向世界。
外国有句名言,没有文化追求的民族没有真正的前途,找不到自己根基的民族没有真正的力量。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对历史知之甚少,书屋招聘的“80后”,“90后”的年轻人不少都觉得毛泽东离他们很远。
记者:业余时间你喜欢做点什么?
孔东梅:我喜欢旅游,读书看电影,特别是那些老电影,像《雷锋》,《党的女儿》,《革命家庭》等等,我总是百看不厌。
记者:在现代女性中,你比较崇拜谁,或者说你比较欣赏什么类型的女性?
孔东梅:我崇拜的人很多,不过大概是两个类型:一种是特别富有爱心的,无私的女性,另一种就是非常有“斗志”的女性,比如希拉里。
我觉得现代女性在发展过程中,正面临着很多问题,诸如心理上的问题等等。我做文化产业有很大的空间去帮助她们。
记者:你理想中的另一半是什么样子?
孔东梅:首先,他一定要尊重女性,无论他事业上多么成功,如果他不懂得如何尊重女性,我觉得他都称不上是一个优秀的男性,我讨厌大男子主义,我相信缘分和感觉。作为女人,我觉得在事业之外,情感的归宿、家庭对我也格外重要。
编辑牛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