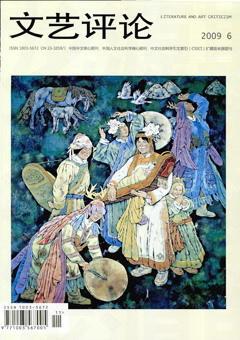20世纪后期西方文论对文学经典的解构
张红兵
在中外文学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所涌现的文学作品难以计数,它们层次各异,价值有别,能载人文学史、得以传承的。必定是其中的精品,甚至就是文学经典。可以这样说,文学史就是文学经典的历史。何为文学经典呢?虽然对文学经典的界定争议颇多,但文学经典,应该是文学史中优秀、杰出的、具有深邃精神内涵和超迈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正如刘勰所说:“三极彝训,其书日‘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意为:说明天、地、人的经久不变道理的书叫做“经”。“经”就是讲永久不变的根本道理,不可磨灭的伟大教诲。“经典”就是承载这种道理和教诲的各种典籍。所以。文学经典就具有统领一个民族甚至全人类精神走向的权威性,是体现文学史价值和走向的典范文本。中外各国文学史,在漫长的构建进程中,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文学经典系列,各国各个时代,都有一系列文学经典成为民众阅读的范本,为人们所敬仰。但是,20世纪中叶以后,文学经典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光环逐渐消退,越来越多的人对固有的文学经典产生了怀疑,进而怀疑承载文学经典的文学史。
为什么20世纪后期,人们解构文学经典的呼声日渐高涨呢?纵观中外文学史,文艺理论对文学的发展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印象。20世纪是文艺理论蓬勃发展的世纪。20世纪至今,诞生了几十种较有规模的文艺理论。这些文艺理论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学创作和文艺观念,进而影响着人们对文学经典的审视态度。20世纪后期的众多文艺理论的一个核心的特点便是对传统的冲击、反叛甚至颠覆。其中尤以解构主义为代表。在它的影响下。随后产生的几种文艺理论——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承继着反传统和冲击、颠覆权威的理论精髓,由此,它们全面地解构着中外文学史中的文学经典,冲击着人们固有的文学史观念。
一、解构主义对文学经典生成机制的质疑
解构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其创始人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所提出的解构主义理论,本是想以对语言结构的破坏,进而达到对社会等传统成规的解构。但解构主义理论一提出,就在哲学、文学、神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德里达认为。“解构”的意义在于涉及到惯例、权威、价值、中心有没有可能的问题。即德里达认为,权威、惯例、中心等,都是人为建构的,它并非天经地义、牢不可破,可以揭示其弱点,消解其权威和中心地位。德里达的这个主张,为解构主义奠定了反传统、消解权威的基调。
其次,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而提出反一元中心和二元对立的观点。解构主义对从柏拉图以来的以言语压制文字,言语占主导地位而文字居于无足轻重地位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提出了质疑,充分强调文字的重要地位。由此为契机。德里达进而认为,在传统哲学和社会中,人们有意识地建立起许多二元对立:真理/谬误、理性/感性、言语,文字、本质,现象、主体,客体、中心/边缘……这些成对的概念,两者并不平等,其中一方总是处于优势地位,另一方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对这种二元对立或一元中心的观点,德里达认为应该消解这些“中心主义”,要解构这些对立的等级。
再次,解构主义认为,文学文本并非意义恒定的客体,对文本意义的审视,不能以僵化、单一的视野对待它。“文学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指称意义可以被完全破译出来的明确的单元被人们接受”。即对文学文本应以多元的视野审视它,这样往往能挖掘出其隐含的意义和价值。
所以。解构主义的理论核心就是反权威、反传统、反封闭化、反模式化,解构也就具有颠覆、消解、推翻、重新审视的意味。在这种理论指向的影响下,使20世纪后期人们对许多传统、权威的事物产生了质疑。在文学领域,对以往固有的文学经典、文学史,产生了深深的质疑。人们明确质疑文学经典高高在上的权威性,进而质疑形成这种权威性的生成机制。
第一,对文学经典确立者的质疑。在文学史上,对于哪些作品为文学经典,哪些作品可以载入文学史册,这到底是由谁确定的呢?纵观中外文学史,担当此任的。主要是这样几类人:一是权威性的作家、批评家、理论家等。如贺拉斯等人对《荷马史诗》的推崇,金圣叹对《水浒传》、毛宗岗对《三国演义》、脂砚斋对《红楼梦》的评点,对于这些作品成为文学经典,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二是学术权威机构。这些机构在近现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17世纪法国推行文艺政策的法兰西学院,我国当代的文联、作协、文学研究所、大学等,都曾决定着近现代以来文学经典的确立。三是读者大众。如当代金庸的几部武侠小说被置于经典的高度,是与广大读者的热捧分不开的。当然读者大众的这种作用是非常有限的,金庸的例子,算是文学史上罕见的特例了。据此,文学经典实质上是由少数文学家、批评家等学术权威确定的。显然,这是缺乏足够民主的确立方式。少数的学术权威以其自身的学术地位以及政府赋予的权力,行使着特有的文化霸权。剥夺了广大读者大众在文学经典确立上的话语权。
第二,对文学经典确立标准的质疑。文学经典的确立是一项人为的活动,其确立标准很自然地具有主观性和时代性。如鲁迅认为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茅盾称《倪焕之》为“找鼎”之作……这些带有明显个人主观偏好的评价。曾遭致广泛质疑。而在不同时期,随着审美标准、欣赏趣味、政治要求等的变化,刈文学经典的框定也发生着变化。这就常常会出现某些作品在一个时期是经典。而在另一个时期却被打入另册的现象。如我们现今认为东晋诗歌的当然代表——陶渊明的诗歌。在唐之前,一直不为人们所重视,直到唐宋以后,其地位才迅速攀升,特别是经苏轼的推崇后,陶诗才在文学史中占据经典地位。而法国作家大仲马生前默默无闻,其《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当年被判为下里巴人而禁止登大雅之堂,直到20世纪,才在文学殿堂里被抬上经典的圣坛。正是由于文学经典标准具有这样的主观性和时代性,使文学经典常常缺乏足够的恒定性,所以那些已进入经典行列的文学作品,时刻具有被颠覆的可能性。
解构主义理论为人们审视文学经典,重评文学史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启迪。以致于人们借解构主义的理论之力,对文学经典的生成机制产生了全面质疑。而对文学经典形成进一步全面具体解构的,却是深受解构主义影响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正是这些理论,使人们在20世纪后期,形成了对文学经典的强大解构浪潮。
二、女权主义对文学经典的解构
女权主义文艺理论,是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结果。它兴起的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虽然其兴起时间与解构主义几乎一致,但解构主义对其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解构主义对二元对立的消解,对一元中心的反叛,对女权主义产生了明显影响。在女权主义批评家们看来,“女权批
评就是抵制理论,对抗现行规范和判断准则。”这显然承继了解构主义的衣钵,他们对绵延上千年的文学史一元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发Ⅲ了颠覆的呼声。
其实。在女权主义的理论渊源中,英国作家伍尔芙就具有反叛男性中心的文学史观思想。她明确指出了18世纪以来以阿弗拉·贝恩为代表的许多妇女作家长期遭到排斥和遗忘的事实。由此她提到:“妇女要当艺术家……不受鼓励,恰恰相反,她们受到冷遇、打击、训斥和劝告。”而女权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肖瓦尔特也曾指出:“直到19世纪末,女性作家的确被认为比她在文学领域内的父兄们低一等。如果她拒绝谦逊、自我贬低、顺从。拒绝以这样的形式呈现她的艺术作品……她将只能被忽视或者受到(有时是恶毒的)攻击。”于是她们明确地指出女性作家长期遭受的不公,充分肯定了前辈妇女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为妇女文学在文学史中争得一席之地。在此基础上,女权主义者提出了自己较为成熟的文学理论主张:一、对男性作家笔下歪曲妇女形象的现象提出批判:二、对文学史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发出挑战,重视女性作家的创作,重评文学史;三、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方式,关注女作家的创作状况等。
这几点理论主张掀起了重新审视文学经典,重评文学史的浪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作家、理论家,对传统的文学史中的文学经典重新审视。特别注重把文学史中被排斥和遗忘的妇女作家作品加以重新解读,充分认识其文学价值,对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做出正确评价。艾伦·莫尔斯在1976年出版的《文学妇女》中,逐个研究分析了18—20世纪欧美女作家简·奥斯汀、哈利耶特·比切·斯托、乔治·艾略特、夏洛蒂·勃朗特、薇拉·凯瑟等人的作品,充分认识她们创作中不同于男性作家的文学成就。认为她们是女性创作的先驱,她们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文学经典。理应载入文学史册。而英国女作家锡德妮·简尼特·卡普兰在1975年发表的《现代英国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一书中,认为从女作家的角度来审视,是能对文学史做出全新阐释的。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掀起了介绍、研究西方女权主义的热潮,大量的有关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专著、论文被翻译过来,不但使女权主义文艺理论成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热点,更对中国当代女性作家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女性作家的作品一直被边缘化,由于西方女权主义文论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起,众多女性作家的作品受到关注。张抗抗、王安忆、铁凝等人的女权主义创作,卫慧、棉棉等人的“躯体写作”,陈染、赵玫、林白、海男、徐坤等人的“个人化写作”。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如此众多的女性作家的创作受到如此重视。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女权主义文论思想深入人心的结果。女性作家们,要用写作去证明自己,正如法国女权主义作家、理论家埃莱娜·西苏说:“写作这一行为不但实现妇女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从而使她得以接近其原本力量。”而女性作家也借自己的作品向固有的文学经典发出挑战,争得在文学史中的话语权。
所以,女权主义文艺理论。冲击着固有的文学史,对以男性作家为主体的文学史发出抗议,对文学史中的文学经典进行解构,充分挖掘曾被埋没的女性作家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使文学经典的构成中,大大加重了妇女作家作品的比重,消解了文学经典构成中的男性霸权,让女性作家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三、后殖民主义对文学经典的解构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后殖民主义被视为解构主义的孪生兄弟,解构主义对后殖民主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文章中,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福柯等人的理论是他们频频引用的。他们承认,他们基本的批判策略都是解构主义的。那么,他们从解构主义那里吸收了什么呢?解构主义的解构传统,消解权威,否定终极意义,消解二元对立,反对一元中心的理论主张,成为了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支撑。后殖民主义把解构主义的这些理论主张具体落实为:对东方,西方、宗主国,殖民地、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文明,愚昧、开化,封闭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质疑。他们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的分类本身是虚假而不科学的,那么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一元中心更是荒谬的。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人物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对东方,西方这对概念进行了解构。“我从来没有感到我是在使两大对立的政治和文化方块之间的敌意增加,我一直在试图对这一对立的结构进行描述,试图减轻其可怕的后果——永久化。完全相反,如我前面所言,东方,西方的对立既是错误的,也是为人们所深恶痛绝的”。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欧洲文化霸权的产物,那么东方主义建构起了西方与东方、宗主国与殖民地的二元对立,其中西方或宗主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而“东方并不是实在的东方,它是被西方话语创造出来的他者,它是被西方话语想象性的虚构出来的谎言。”所以,后殖民主义的一个核心理论,就在于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也反对东方中心主义,拒绝用新的二元对立、一元中心来取代旧的二元对立、一元中心。即,东西方文化由冲突关系转化为文化互渗和对话的新型关系,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文化话语权力观。
后殖民主义对西方与东方、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对立关系的解构,对西方、宗主国的主导地位的消解,必然影响到对世界文学史的评价,必然影响世界文学经典的建构。20世纪中叶以前,英、法、美等国的文学占据着世界文学的主流地位。亚、非、拉美等国家的文学,常常是本国研究者眼中的宠儿,而不能为世界所公认。20世纪后期,随着后殖民主义的兴起,人们对世界文学史的审视视野,逐渐开阔。英美大多数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关注点一直是非洲文学,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使人们又把眼光盯向了东方。如诺贝尔文学奖是20世纪以来世界文学的最高奖项,从它设立至今,就经历了以欧洲为中心进而放眼全世界的过程。20世纪上半叶,“有人就把诺贝尔文学奖比作一只立锥旋转的陀螺,从它建立的那天起,一直以欧洲为中心在那里转个不停,欧洲各国的作家们,像走马灯似的轮流交替。一顶顶‘桂冠从欧洲这个国家作家头上换到另一个欧洲国家的作家头上,偶尔它也旋出去,在美洲、南美、亚洲光顾一下。即又迅速的旋了回去。”
确实,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诺贝尔文学奖,大多落在欧洲、北美国家作家头上。只有1913年印度的泰戈尔、1945年智利的女诗人米斯特拉尔是例外。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标准的调整,更由于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亚洲、非洲、南美的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66年以色列的阿格农、1967年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1968年日本的川端康成,连续3年非欧作家获奖,拉开了亚非拉作家频频获奖的帷幕。此后智利的聂鲁达、澳大利亚的怀特、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埃及的马哈福德、尼日利亚的索因卡、南非的内丁·
戈迪默、日本的大江健三郎等先后获奖。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国家的作家获得这项世界文学的最高奖项,这极大地提升了亚非拉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使更多的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亚非拉文学。进入到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
后殖民主义理论,消解了西方与东方对立中长期以来西方的绝对霸权地位。把一种全面、开放而平等的视野引入文学研究。在以往处于边缘地带的亚非拉文学中,发现了众多的文学英才,使他们的作品昂然成为世界文学经典,这不仅是对亚非拉文学地位的提升,更是对世界文学史格局的重构。
四、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的解构
20世纪60年代开始萌芽的文化研究,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解构主义理论的影响是明显的。解构主义要以对语言结构的破坏,来达到对许多传统领域的固有结构的破坏,由此,解构主义还认为在一个文本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统帅一切结构构成成分的中心,文本的中心和终极意义都是不存在的。“中心从来就没有自然的所在,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所在,而只是一种功能,一种非所在。”所以,以往文学研究、文学理论中,以文学为中心的固有模式,受到解构主义这种理论的冲击,于是,多学科、跨文化的视野被引进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应运而生。当前。文化研究仍然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是:对文化研究的学科界定。至今未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许多学者甚至认为文化研究就是跨学科、超学科甚至反学科的。虽然,由此为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的确立带来了难度。但“这种反学科的立场和态度,使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易于在被传统学科所忽视和压抑的边缘地带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所以,文化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重视大众文化、非精英文化,淡化文学经典、精英文化。即,文化研究超脱了文学研究只把目光停留于经典作品、精英作品的局限,打破了对文学经典的偏爱,把目光更多地对准文学经典以外的非文学经典。进而扩展到对大众文化的研究。
文化研究的这种审视观表明:仅靠对文学经典的研究,是不能全面而客观地把握各民族、各时代的文学所体现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的。而那此被排斥在经典大门之外的非文学经典、大众文化,往往蕴含着文学经典所缺乏的历史、文化和审美价值。正是基于此,文学经典越来越丧失其精神领域的贵族地位,越来越多的非文学经典、大众文化成为精神领域的新贵。20世纪后期以来。两种现象日渐明显:一是文学史上曾经被冷落的作家。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曾经被尘封的作品。却被赋予了经典的意义。
以中国而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钱钟书的《围城》、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金锁记》、徐志摩的诗歌等。都经历了建国后备受冷落,20世纪80年代起备受重视的过程。而在文学史上曾经商高在上的郭沫若、赵树理、李季等人的作品,现今,除了因其在特定环境下发挥了文学以外的作用而还在文学史中保留一席之地之外,大有淡出人们视野的趋势。二是大众文化由于其视觉的丰富性、娱乐性,越来越为人们所喜爱。流行音乐、通俗读物、影视、网络、广告等大众文化。猛烈地冲击着文学的领地,消解着人们对文学经典的热情。文学经典不但已失去了在人们心目中的令人崇敬的地位,而且许多人还以戏谑、调侃的态度对待文学经典,以至“戏说”、“大话”之风盛行。读者对《大话西游》、《烧烤三国》、《水煮三国》、《麻辣水浒》等作品的热捧,甚至大有超过对这几部经典原著的喜爱趋势,这让人们不得不哀叹文学经典在当下的命运。
2003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其著作《论文学》中断言:“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了。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当然,米勒的这个断言有其特定的语境,甚至有危言耸听之嫌,但是。他至少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文学已走向边缘化的境地。当今世界。不是没有文学,不是缺乏文学经典,而是在解构主义等理论的冲击下,人们消逝着对文学经典曾有的热情,更能理性地看待那曾让人崇拜的文学经典。况且,许多曾经关注文学经典的人,已经分流于影视、网络、酒吧、美容院等大众文化领域,他们在此消耗了太多的热情。现今的文学经典,大有成为明日黄花、少人问津之势。
现今文化研究这种理论仍在继续发展,它对文学经典的冲击和解构依然猛烈。文学经典的沉沦、文学的边缘化,就是文学发展到高潮后的自然回落。正是文化研究的冲击和解构,让文学经典从让人仰视的神坛走下,把文学带入了一种理性的发展轨道。否则,文学真的会走向终结。
综上所述,20世纪后期的几种重要的西方文艺理论,对曾经居于文学领域、文化领域权威地位的文学经典,形成了强大的解构之势。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这几种文艺理论,它们对文学经典的解构,启迪人们用多元化的视角关注文学,用开放的视野评价文学经典,因此形成了文学史和世界文学格局的重构,具有重大学术意义,令人弥足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