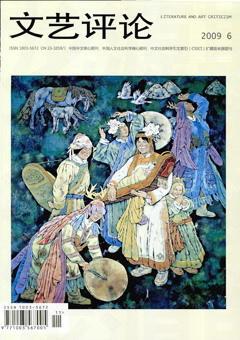全球化视野中的乡镇困境与贾樟柯的电影
马明高
有人说,贾樟柯发现了中国的乡镇。这话不假,贾樟柯通过他的电影,不仅为我们展现了独特而又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乡镇,而且更让我们窥见了全球现代化背景下的大中国。窥见了中国“三农”问题的真实图景以及在此图景下乡村城镇年轻一代的生存境况与命运变化。从《小武》中小镇上一个高中毕业后无业游民的生活,到《站台》里几个县城男女青年对现代生活的向往与迷茫,到《任逍遥》里几个矿中村工人子弟辍学后无事可做的困境与冲动,到《世界》里乡村青年打工者在“世界公园”的遭遇与命运变化,再到《三峡好人》中两对乡下人在大变迁中的三峡的情感寻找与失败人生。都可以体悟到贾樟柯电影的重心或主题。贾樟柯的电影与传统的农村题材影视剧不同,与传统的青春影视剧不同,他更多关注的是全球化与现代化下的中国乡村城镇的现实困境。关注的是乡村城镇中普通人物的世俗生活。正如他所说:“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他关注的是时代的变迁、以及变迁中普通人物的命运与心理,关注变迁人的一切的变化与趋向。从他的执著关注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贾樟柯宽阔的文化视野与对现实生活的分析和整合的强大能力。这一点,在整个农村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或者说整个影视界是非常少见的。
一、贾樟柯电影中乡镇复杂暧昧的生活与青年一代的生存困境
在贾樟柯的眼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有农业社会背景的人,所以他说:“我在拍电影的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我是一个有农业背景的人,我越来越坦然,不仅是我个人,对整个中国艺术来说,也应该承认农业背景。不承认这一点,可能做出来的东西就会和土地失去联系。”在贾樟柯的心目中,乡镇是中国最普遍的地理区域。也是跟乡村的纽带。通过乡镇可以拍到一个全面、完整的真实情况。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贾樟柯无论剧情故事片还是纪录片《东》、《无用》、《二十四城记》等中,都充满丰富的乡镇生活图景,都贯注着强烈的“乡愁”情感。被专家学者称之为“故里”意识。
我们发现贾樟柯电影中的乡村城镇与传统影视剧中的乡村城镇是不一样的。它不是田园的、温馨的、诗意的、安静的。它是复杂的、暧昧的、苦涩的、躁动不安的。在传统的农村题材影视剧中,乡镇的环境是安静的大自然,人际关系是温馨而充满亲情的。而贾樟柯电影中的乡镇一旦出现,就给你一种躁动不安的感觉。一种巨大的噪音,那些到处建设的敲敲打打的声音,那些乱七八糟的声音、或人声市声、或歌声音响,给你展现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捉摸不定的现实图景。这就是全球笃信资本与市场的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乡镇,这就是一个迅速变成为全球生产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世界工厂”中的乡村城镇。自然就成为一种深具中国特色的、各种各样拆迁的。正在消失和正在建设的现实,一种带有现代化进程渴求和躁动。付出代价和痛楚的现实。正是这种源于历史性和结构性的欲望,把中国乡镇的新一代一个又一个地送上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轨道。而作为人的个体性一旦和这种历史现实性相互冲突、相互胶着。就会产生种种人生真实的生存故事和强烈的精神震撼。《小武》、《站台》和《任逍遥》表现的是青年一代在乡镇、县城和矿区的人生痛楚故事,而《小山回家》、《世界》反映的是青年一代在大城市的角落里打工的人生痛楚故事,《三峡好人》则表现了乡下人寻觅爱情梦的破灭与酸楚。这一个个个体性在历史现实性中的种种挣扎和种种困境,让每一个观众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手指甲抓到肉里的心灵疼痛,一种抓出血来的心灵疼痛。
二、贾樟柯的电影是以人物在日常生活不确定的命运带动叙事进程,深入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
《小武》和《任逍遥》都是人生的一个切片。通过一个小偷的日常生活和两个矿区工人子弟的日常生活来叙事人生的无奈与伤感。《小武》里的主角是一个小偷。小偷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有他内心的生活。他也疼爱自己年老的父母,但他不愿意过黄土窑洞的生活,他要努力改变自己。他也因为自己过去的朋友看不起自己而难过。昔日一起买空卖空的朋友今日成了企业家还被电视台采访,他去参加人家的婚礼却被人家要划清界限。他也需要爱情。那个叫梅梅的歌厅小姐曾坐在他身旁安详的唱歌,曾靠在他的肩上安然入梦,曾陪他一起漫无边际地游荡。爱情总是捉摸不定,一会儿有一会儿无。突然梅梅给他特意买的呼机响了,他也因此被公安抓扣于街头。人们游走依旧,街上汽车摩托车喧闹依旧、市场上的叫卖和收音机电视机发出的歌声依旧,他却被拷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马路旁,把头深深地埋下去,去怀念梅梅留给他的那段真正哀愁的回忆。《任逍遥》也一样,彬彬和小济是两个小镇上矿工的子弟,刚刚19岁却无事可做。但也渴望有自己的情感天空,他们都愿意和矿区野模特巧巧在一起。为了自己的生活,他们只能铤而走险去抢劫银行……
如果说《小武》和《任逍遥》是人生的切片的话,那么《站台》就是人生的一个历程。县城文工团的崔明亮、张军都喜欢和团里的女演员尹瑞娟、钟萍在一起,关系微妙却从未相互表达。星期天,崔明亮、张军约尹瑞娟、钟萍看电影《流浪者》,恰巧碰到了尹父,尹父不愿意女儿和崔明亮在一起,大家不欢而散。张军请假前往广州看望姑妈,收到张军从广州寄来的明信片,望着画面上的高楼大厦,崔明亮彻夜难眠。尹瑞娟与崔明亮第一次约会于古城高高的城墙下,背后是牢固的城墙,脚下是冰冷的残雪,而希望却像天边很窄的一条线。张军去广州了,钟萍一个人在家里翻看歌谱,尹瑞娟来了,两个迷惘的女人背靠着窗户在逆光中闲聊吸烟。两个正值着青春年华的女人的惆怅和着闲散的时光飞逝,隐隐作痛的情怀在哀愁的时间中老去。文工团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排演了节目到乡村巡回演出,但尹父病了,瑞娟不能和崔明亮张军们一起远行。一对恋人不得不别离。钟萍与张军大胆的恋爱总是让周围的人看不惯,沉闷的氛围实在让钟萍受不了了,她对张军说她想大喊几声,张军说好,于是她蹲下来尖利地喊了几声,回应她的是山谷的回声,面对着的千年不变的老山深沟令他们绝望与空虚。后来钟萍就失踪不见了。文工团到小煤窑演出时,崔明亮看见表弟正在和矿主签定生死不管的合同,表弟追赶着远去的拖拉机,将五块钱交给明亮让他带给妹妹交学费。然后转身而去。表弟的沉稳与坚定让他感受到了残酷生存世界对青春的摧残与逼压。结婚了,崔明亮在沙发上熟睡,尹瑞娟抱着孩子在屋中踱步。茶壶响了,像火车的声音。这就是最美好的生命与最饱满的青春的一段历程。乡村城镇的青春少年破灭了理想,丢失了爱情,葬送了青春,最终又回到了苍凉的起点。影片就是这样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小人物命运一次又一次的不确定性,来深入挖掘卑微小人物面对迷惘苦闷现实的压抑与失落的内心情感。影片打动我们的正是这种真实的伤感与无奈,以及那种难以企及的脉脉温情。这伤感、这无奈、这温情是属于现
时代的大多数农村青年或农民工的,是诚心诚意的。是不吐不快的,而绝非那些“商业大片”的影像玩物。从贾樟柯的电影中。我们发现了与众不同的十分罕见的电影应具有的真实品质。他对当下中国乡村城镇社会的直面记录,对农村青年和农民工细腻而贴切的描绘,他对全球化下世态人情平静而高超的体察,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抚慰,还有心灵的震撼和精神的共鸣。这种既不媚俗又不媚雅的电影精神在目前的中国影视剧创作中是十分稀缺的。
三、贾樟柯的电影是对“回不去的故乡”的逼真描摹和对“没有故乡”时代的深刻批判
多少年前,夏多布里昂写的著名诗句“没有人从故乡来”,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谶语。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横扫着世界。要全球化就必须现代化。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我们的“故乡”已经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亿万农民离开土地惊世骇俗地涌向城市。惊天动地的大迁移让“故乡”山河破碎。“故乡”或者成为一个拆迁现场,或者被建上新城住进新人。“故乡”的历史诗意、田园风光早已淹没在现实的血污、挣扎和冷酷当中。一切都成为消费的文化扩展成为更大意义上全球化进程的核心之一。这些很快印证了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述:这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是一个除魅的时代,是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是一个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物欲主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价值观,主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这个社会成为一个“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个性生活的存在已经与宇宙失去了有机的意义,只剩下作为主体的“占有性的个人”对客体的大自然的赤裸裸的占有、征服的关系。在这样的价值观指导下,全球化更加有利人富裕的国家和富人们,而不是世界的大多数人。农民们只能成为“没有故乡”的人和“回不去故乡”的人。
贾樟柯的电影,一直都在探讨着人与故乡的冲突和决裂。《小山回家》是离开“故乡”的尴尬遭遇。《小武》则是留守“故乡”的无奈遭遇。但无论是外出的小山,还是留在家乡的小武,都还能保持笃定,因为“故乡”还可以回去,而自己与“故乡”的关系还没有断裂。从《站台》开始,“故乡”开始面临着破坏。县城里的文艺青年,比别人更敏锐地感受到了外面世界的变化,他们奋不顾身地投身到这种变化的世界里。无论工作、恋爱到全部生活,都在努力身体力行着新的价值观。但最后他们回来了。那个世界不属于他们,变化的世界将他们压榨后,将心灰意冷的他们弃之不顾。在《世界》里,他们就与“故乡”的关系全部断裂。《世界》里有三个“世界”:一个世界,就是离开乡村城镇进入北京的年轻打工者力图摆脱却如影随形的小世界。它真实属于现实世界,却贫穷困苦,作为田园风光和温馨情感的一点点特质正在剥落殆尽;第二个世界,就是这些乡镇打工者工作和生活的世界。这个世界光彩流溢,繁华多姿,却是个虚假的世界。是对真实世界的戏仿和嘲讽;第三个世界,就是乡镇打工者力所不及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现代化、全球化与消费性充斥的世界。这个世界冷漠、疏离、空旷寂寞。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渴望与追求,使得人与“故乡”在心灵、伦理和精神上已经全部断裂。
从《三峡好人》到《二十四城记》,贾樟柯用他的电影确凿无疑告诉我们“故乡”回不去了,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没有故乡”的时代。因为“故乡”不是被拆迁,就是被改造为新开发的商业楼盘。你即便回到“故乡”,也没有故人可以取暖,一切都已面目全非。《三峡好人》里有两个线索:山西的一个矿工16年前花钱买了一个老婆,第二年生了一个小孩后,公安解救了这个被拐卖的妇女,然后妇女就带着小孩回四川了。16年后,这个矿工孤身一人拎个包,踏过千山万水去找这个女人。这个女人16年里也没有嫁人。却跟着一个船老大跑船,过着一种尴尬的两人生活。矿工找到这个女人了,两人就决定结婚。她们的孩子已经大了,去东莞打工了;另一条线索是一个叫沈红的护士,她在山西工作,她丈夫却在三峡工作,好几年了,音信杳然。她从山西跑来寻找丈夫。但丈夫已经和另一个女人结婚了,她千里迢迢到奉节找丈夫,最后她跟丈夫见了面的时候,两个人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因为船马上就要开了,她跟丈夫说:“我来就是要告诉你,咱们离婚吧。”然后就坐船走了。贾樟柯把两个寻找爱人的故事放在正在拆迁和移民的三峡的大背景中来讲述。而且两个“找”爱人的故事正好颠倒过来了,能够保存感情的是一个非法的婚姻,而那个开始于自由恋爱的婚姻反而什么也留不下了。贾樟柯用自己的电影一直都在关注着“变化”这个主题。从《小武》到《世界》再到《三峡好人》,还有《无用》和《二十四城记》,变化渗透在所有的生活领域和感情方式之中,各种各样的叙事或纪录要素都在围绕着变化而展开。他在关注着时代的变迁,关注着变迁中人物的命运与内心世界的变化。他关注的目光是深切的,深情的,深入的,深深的尊重的。他纪录了我们这个变迁时代的重要痕迹和人们所感到揪心的东西。由此所产生的震撼给我们带来深深的感动。,“故乡”正在消失,婚姻、邻里、亲朋的关系也都在变异,寻找的东西也在变质。“找到”本身都成了自我否定,沈红对丈夫说“自己已经有人了”,丈夫问她是否想清楚了,她说“我决定了”,这是通过否定来保存自己感情的完整性,保存记忆中的“故乡”的完整性。矿工最后也做出了决定,是要回山西煤矿挣钱,赎回16年前的老婆。这一切都把我们这个变化的大时代的魔幻性荒诞性表达得极深。一切都是如此得离奇而乖戾。要想在这个离奇乖戾的世界里生存下去,就必须痛下决心,像矿工韩三明或护士沈红那样。与往日的一切断绝关系。或者以新人的姿态迎接新生活,就像《二十四城》中的第三代厂花娜娜,决心在已经成为“异乡”的“二十四城”里为自己的母亲买一套房子。这就是贾樟柯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面临的诱惑和必将经历的冲突和痛苦:乡村城镇和大都市之间。自身所处的小世界和外面庞大的世界之间,在冲撞、较量、压榨、抵抗,最终结果是“故乡”的沦陷败落,是那个全球化世界的大获全胜。我们与“故乡”之间的全部线索,全部联系都宣告断裂。我们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往日深切的、体戚相关的连带感,失去了相互间自由相连的热情与关怀。人仅仅成为琳琅满目的商品的消费工具,生活失去了意义,生命失掉了目标,我们的精神世界也会一天比一天荒废,枯萎……
贾樟柯就是这样的一位电影诗人,他不仅仅展现了迷失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人和我们的国家,而且也是在用自己的所有电影讲关于逝去的故事。逝去的青春、逝去的岁月,逝去的爱情……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逝去的。而逝去的东西是着不见的。而他正竭尽全力想让我们看见这些东西,铭记这些东西,并且重新审视和反省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