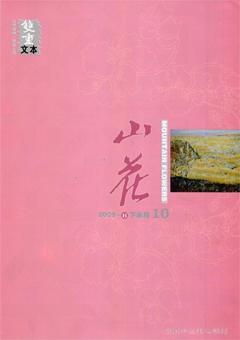论《兔子,跑吧》的家庭危机主题
“二战”后的美国文学作品中,“精神流浪”的美国人以及异化的主题占据了一定的主导地位。作品中的主人公以叛逆、逃跑行为对传统社会的种种道德规范提出质疑与反抗。约翰·厄普代克聚焦中产阶级的生活及生存状况,在兔子四部曲的第一部《兔子,跑吧》(1960)中成功地塑造了“兔子”哈里这个经典文学形象,展现了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精神贫瘠。本文将着重分析主人公在矛盾冲突中苦苦挣扎却无力解决,只能用“逃跑”来逃避的思想行为,旨在揭示小说中反映的普遍存在于美国当代社会的家庭危机主题。《兔子,跑吧》一出版就获好评如潮。评论家Richard Gilman称它为“一部关于美国生活的奇异寓言”、“一部小型史诗”。这部作品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生活和在这种“繁荣年代”里人们内心的空虚和苦闷。他把小说人物置于白人城镇或郊区,聚焦中产阶级的生活及生存状况,展现了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精神贫瘠。
“二战”后科学技术在美国突飞猛进,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并非都是正面的。一部分敏感的美国人对现实生活及个人的生存失去了信心,甚至无力解决家庭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技革命带给美国社会的另一个严重冲击就是破坏了家庭的稳定。本书的主人公哈里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土壤上产生的。
小说从始至终都是围绕解决哈里家庭危机的事件展开的。作品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受本能驱使从婚姻、责任的束缚下逃跑的年轻人“兔子”哈里这样一个经典文学形象。小说主人公哈里·安斯特朗(Harry Angstrom),是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小人物,26岁的他学生时代曾是个备受瞩目的篮球明星,但是结婚以后事业却一无所成。他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更无力处理家庭矛盾,因此他对自己的工作、婚姻和生活中一切都感到厌倦。
“兔子”这个绰号是因其打篮球时很敏捷而得名。“兔子”不仅是对哈里外貌特征的形象描绘,更是对他性格特征的贴切展示,暗示了哈里善于奔跑、驯服、弱小和善良的本性。他感觉灵敏,对客观世界和真善美丑都赋予直觉,但是对自己却从来没有过清醒的认识,他只会顺从本性,随心所欲。生活的压迫和强烈性欲驱使所引发的焦虑与恐惧占据了他的生活,他漫无目的地奔跑,认为唯有奔跑才是拯救自己的希望。正如他的英文名字所显示的,Harry意为困扰、焦虑,Angstrom,angst(fear)意为恐惧、焦虑、担心,而angstrom又释为“埃,物理学中表示一亿分之一米,一种用于测量波长的单位”。“兔子”只是千万中产阶级中的一个平凡普通的小人物,一个在理想和现实的裂缝中挣扎的小人物。他永远在追求着什么,也永远在逃避着什么,然而,多次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对他来说,现实生活的一切都是陷阱和罗网——婚姻、工作、信仰、性爱、夫妇之间的吵吵闹闹、分分合合,“兔子”时不时地感觉自己被困入罗网之中,一次又一次地逃跑。
哈里对自己的家庭和人生感到强烈不满,生活将各种各样的责任强加在他身上,他不得不扮演儿子、女婿、丈夫、父亲等多重角色。昔日体育场上的辉煌与现实中的一事无成形成强烈对比,更加使他找不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他感到自己的生活正在一天天地失去意义,因而梦想拯救自我,于是逃跑成了他拯救自我的工具。他从家中跑到露丝那儿,又从露丝那儿跑回来;从现实跑到理想,又从理想回到现实。如此反复奔走,精疲力竭却一无所得。哈里“跑-归-跑”这种似乎无止境的循环实际上是哈利一次又一次在理想和现实当中徘徊的结果。他对家庭抱着一种美好的幻想,然而残酷的现实让他陷入了一种“陷阱”般的困境。产生了“觉得自己掉进了陷阱”的幻觉。如果把“跑”看做是力图摆脱现实困境的一种努力,那么这种努力实际上却是失败的:哈里屡屡从家里跑开,但最终没有找到方向和归宿。与妓女露丝那看似美满甜蜜的爱巢却不能使他脱离“陷阱”,更没有让他找到梦想中的归宿。其实这打从一开始就有预兆:他离开家(陷阱)进入网状的公路,这时地图不但不能给他指引方向反而在他看来“浑然一体,成了一张网”,这些红杠杠、蓝杠杠以及星号组成的网,他被困在其中某个地方了。他的逃避只不过是从一张网逃到另一张。
哈里的行为在作者笔下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只会不断地逃跑的哈里是一个梦想与现实交锋中的“失败者”。他跑来跑去只能从篮球和性爱中才能得到一时的解脱。哈里在中学时代曾经是风光一时的校篮球队明星,当时的他风光十足,受人钦佩和尊重,有荣誉相随、美女相伴。小说《兔子,跑吧》的原型出现在厄普代克早些时候发表的短篇故事《秘藏的王牌》(Ace in the Hole)中:篮球明星弗雷德·安德森,“王牌”(Ace)是他的绰号。从英语字面上看,Ace的意思是一流运动员。弗雷德喜欢这一绰号,因为它能使他重温以前篮球场上的风光与荣誉。和他的原型一样,哈里也将篮球视为生活和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方面。队友们给他起绰号“兔子”正是因为他在球场上像兔子一样迅速、敏捷。打篮球时,“兔子”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奔跑、停球、传球、投篮,样样都做得那么出色、那么完美。值得注意的是,球场上大多数运动员都竭尽全力投篮得分,而哈里却不一样,他打球并不是为了得分——“你并不是像观众认为的那样为了去得分而奔跑,你是为了自己在跑。”对哈里来说,分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打球本身,因为只有这时他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证实自我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篮球场是哈里的天堂,他能从中找到自身的完美价值以及无拘无束的自我。哈里所祈求的自由、荣耀、完美与自我就是他一直苦苦寻觅的东西,是“它”的实质内容,而找到这一切(“它”)便成了他的梦想。
然而,昔日球场上的荣耀一去不复返,步入社会后,他体验到了一种从顶峰下滑的危机。平庸的生活,邋遢酗酒的妻子,一切无不让他失望透顶。下班回家的路上,哈里遇到一群玩球的男孩子,他情不自禁脱掉衣服参加进去。在奔跑触球的刹那间,他生命中那根僵死的神经被激活了,生命中的火焰被重新点燃,这是一次灵魂深处的悸动。哈里感觉一种莫名的力量从心底升腾,似乎又重温昔日的荣耀。“篮球”象征着哈利的年轻时代。往昔与现在的强力对比导致哈里始终不肯正面现实的后果,可以说,代表生命力的篮球和哈里的梦想天堂般的篮球场反而无法跟死气沉沉的家庭生活相融洽,甚至间接导致了哈利的离家出走。
造成哈里婚姻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性爱。对哈里来说,篮球场并不是他唯一的天堂,他还有另外一个天堂,即性爱。高中时,他在篮球场上的成功为他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正如哈里所回忆的,“他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走向她”。在与女朋友谈恋爱与做爱的过程中,他同样经历了一种胜利的感觉,这种感觉无异于他在球场上所经历的,而且时不时地,“这两种胜利在他脑海中合二为一”。所以可以说,哈里“胜利者的姿态”既是体育意义上的,又是性爱意义上的。打球与做爱之所以能合二为一,还因为二者都包含身体运动,而运动是哈里心中的灵丹妙药,是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这也是为什么他
始终不停地跑,因为他不满他所生活的20世纪50年代保守的社会环境、安稳的小城生活以及僵化的思维模式,他想通过跑、通过运动来改变这一切,来重新找到他自我,实现自身真正的价值。
26岁的哈里显然己不适合再靠打篮球度日,于是“成功的性爱便成了连接过去辉煌日子的唯一纽带”。换句话说,性爱取代了打球,或者说成了打球的另一种形式。篮球和性互为象征,性活动在哈里眼中更像一场篮球运动,他试图通过一次次的性活动来重温他骄傲的篮球技艺。哈里只能靠这点回忆来慰藉落寞空虚的心灵。正如打球不是为了得分,性爱也不是为了获得快感。哈利的欲望与其说是性欲上的,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性爱带给他的是超出肉体的超验感受,是灵魂的出窍,精神的超脱,是忘却世俗一切不如意的灵丹妙药。在露丝身上哈里觉得又重现了自我的辉煌,又变得自由与完美。而正是这一时刻哈里找到了渴望已久的“它”。
篮球与性爱给了哈里一时的解脱,却终究给不了他一世。从篮球与性爱中所能找到的自由与完美是暂时的,缥缈的,同时给他带来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家庭问题,出于对妻子和家庭的愧疚,他又一次次跑回家去。他理应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他理应与周围的人(至少是家人)达成和解,他理应为自己定出更为实际的目标,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哈里不愿做也做不到的。因此,这种当断不断的痛苦使得篮球与性爱演化为另一个无底的陷阱,一张无际的罗网把他牢牢困住。他想通过打球和性爱这个精神避难所来发现“真谛”,逃避现实,然而,却增添了人生的迷惘与困惑,他的逃跑没有给他本人带来解脱,甚至还导致了他女儿的夭折,加深了哈里这个小人物的悲剧色彩。
厄普代克也是个态度严肃的作家,笔下人物的行为也总代表着一种没有表白的观点。作者在一次演讲中曾对《兔子,跑吧》的创作意图做过一番说明:“确实,我在每本书中都描写了现实存在的压力和冲突,描写我们私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难看的瑕疵。社会上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各种问题,我认为我的书基于对这个事实的变态口味之上。在内心对生活的欲望与外部生活可能带来的满足之间,两者是无法妥协的。你希望永远活下去,永远富贵,你有无止境的欲望,无止境的自由,而社会又必须建立严格的限制,约束它的成员。在个人愿望与现实之间,两者根本没有办法调和。我写《兔子,跑吧》就是想说:没有解决的办法。这本小说主要写的是‘跑,在两者之间窜来窜去,直到最后,感到累了,精疲力尽了,然后死去。这个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小说结束,啥里仍在继续“跑啊,跑啊”,这种开放式结尾揭示了当代美国青年人的悲剧,作品对哈里的家庭危机主题的反映也正是作家对当代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家庭问题深刻忧虑的体现。
作者简介:
王蕾蕾(1981-),女,山东枣庄人,现工作于山东省枣庄学院,助教,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