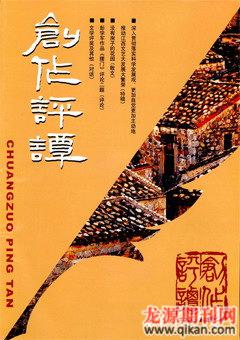画书人的故事
晓 禽
有写书人,有读书人,有猎书人,有贩书人……还有一种人,我称之为“画书人”。而我这组短文所写的,当然主要是那些给书画插图的人了。
但事实上,早期的一些书,的的确确是“画”出来的。中世纪的很多手抄本,就是名副其实的“手绘本”,花花绿绿,煞是晃眼。在印刷术尚未出现之前,书这样的产品完全是“纯手工打造”,不难想见其生产过程的多么繁琐、艰辛。我见过几幅图,表现的都是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早期的场景,第一幅就是一位正在工作的“画书人”,看样子应该是个教士。众所周知,在中世纪,像“识文断字”这样的手艺,完全被教士和贵族阶层所垄断,下里巴人是沾不上边的。后两幅分别是装订书和印刷书的场景,画面上的人物则明显是手艺人了,他们对自己手中所捣鼓的那些高文典册,多半一个字也不认识。但是,在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历史上,我们又怎能不记住他们挥汗如雨的身影呢。
直到维多利亚时代,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依然有人手工“画”书。不过比中世纪“画书人”更幸运的是,到这个时候,手绘书已经可以用印刷机大批量生产,恐怕再也难得有什么孤本了(除了原稿)。
言归正传,我这组短文主要还是写插图画家,特别是一些既写书又画书的“画书人”。至于人物的选取,完全没有规划,没有章法,逮着谁算谁。以图为主,文字顶多串个场子、跑个龙套什么的,不看也没关系。
这就算是个开场白吧。至于能写多少,自己心里也没底。信笔涂鸦,写到哪里算哪里,“不了了之”终归也是一种“了”法。就像小时候在长江边上放生,把牛往河滩上一赶,它爱上哪儿上哪儿,我自高卧江堤,看蓝天白云,听流水落花……
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
用罗塞蒂打头阵。总让人觉得有些不踏实。毕竟,罗塞蒂很难说是一个插图画家。前拉斐尔派兄弟会的哥儿几个,大多画过插图,我的印象里,罗塞蒂应该是画得少的。选择他打头阵。只能说是个人偏爱吧。他的诗人气质,丰富的细节,细腻的感觉,梦幻般的想象,再加上他与伊丽莎白·西德尔之间的凄美爱情,一切都是那么华丽而忧伤。
在罗塞蒂不多的插图经历中,有一件英国出版史上的盛事。他倒是有幸躬逢其盛。大约1855年前后,出版家爱德华·莫克森筹划给丁尼生出一卷四开本插图版诗集,作为对这位桂冠诗人30年诗歌创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这就是1857年问世的《诗集》,它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迷人的书之一。受邀为此书绘制插图的,正是前拉斐尔派的三位兄弟:罗塞蒂、米莱斯和亨特。
富有戏剧性的是,《诗集》出版第二年,出版人莫克森便归了道山。罗塞蒂的弟弟、文学评论家威廉·迈克尔·罗塞蒂说:“我甚至听到有人说是‘罗塞蒂害死了莫克森,不过我想,这只是个冷酷的玩笑,而不是严肃的事实。”此话从何讲起呢?原来,罗塞蒂对作品的要求非常苛刻,不但对画稿进行反复修改,而且还经常把刻好的木版打回重做,再加上——威廉说的——“我哥哥对自己分担的这份差事确实有点磨磨蹭蹭”,因此时间一拖再拖。还要经常返工,搞得莫克森焦头烂额,三天两头往罗塞蒂家跑,磨破嘴皮子也不硕事。所幸的是丁尼生对几位画家的工作完全不干涉(这一点不像狄更斯),因此这本书的55幅插图最后几乎都成了独立的艺术品,而不仅仅是对诗的图解。据说,丁尼生本人对这些插图也非常满意。
罗塞蒂本人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诗人之一,他妹妹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也是诗人,弗吉尼亚·沃尔夫甚至认为“在英国女诗人中,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应该排第一,她的歌唱有时像知更鸟,有时像夜莺。”1900年,伊丽莎白·卡里出版了一本《罗塞蒂兄妹》,详细记述了这对天才兄妹的生平和创作。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艺术界的教父级掌门人约翰·罗斯金认为:“在英国现代浪漫主义流派奠立的过程中”,罗塞蒂无疑是“最主要的智性力量”。插图画家、现代装饰艺术的先驱人物沃尔特·克雷恩在《书籍的装饰插图》一书中谈到罗塞蒂的插图作品时说:“它们的诗性想象,它们的丰富细节,色彩感,热情、神秘、浪漫的感觉,以及真挚的表达,都标志着一个新的纪元。”关于罗塞蒂及其家庭的传记资料,最权威的莫过于他弟弟威廉的两卷本《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此书出版于1895年,此时他的哥哥和姐姐都已去世十多年了,三兄妹中,威廉最长寿。他死于1919年,享年90岁。
约翰·弗拉克斯曼
弗拉克斯曼也很难说是个正儿八经的插图画家。他是个雕塑家,代表作品有《阿喀琉斯的盾牌》、《天使长米迦勒战胜撒旦》等。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是个瓷器装饰设计师,他曾是韦奇伍德手下的头牌设计师(可以说,是韦奇伍德首先发现了他的艺术才华),在现代欧洲瓷器收藏家的手里,他设计的作品大概已经成了稀世之珍吧。
弗拉克斯曼出身寒微。父亲在伦敦的科芬园新街开了一家小店,不过话说回来,跟艺术好歹也算是沾点边:他经营的是石膏模型。儿时的弗拉克斯曼身体很不好,成天趴在老爸店里的柜台后面看一本破旧的拉丁文书,这本破书是父亲花几个便士从一个旧书摊上淘来的。有一天,亨利·马修神父路过小店,被这个看书的小孩给吸引住了,得知他所读的书后。便说:“那不是适合你读的书,改日我给你带一两本书来吧。”马修先生给他带来的是《荷马》。就这样,希腊神话为年幼的弗拉克斯曼打开了一个浪漫而神奇的世界,那是他一生也做不完的梦。
15岁的时候,弗拉克斯曼成为皇家艺术院的一名学生,专业是雕塑。由于父亲的生意很是萧条,他不得不在父亲的店里做一些杂活。制作石膏模型什么的。正是在这个时候。韦奇伍德发现了他的艺术才华,邀请他加盟自己的公司,成为他手下首屈一指的设计师。27岁那年。弗拉克斯曼离开了父亲的家,在梭霍区的沃德街租了一间小房子和画室,并成了家,妻子名叫安妮·登曼,像他一样,也爱好诗歌和艺术。有一天,约书亚·雷诺兹(他是个单身汉)遇见了弗拉克斯曼,对他说:“哦,对了,弗拉克斯曼,我听说你结婚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要告诉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你算是彻底给毁了。”弗拉克斯曼回到家里,对妻子说:“安妮,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彻底给毁了。”“怎么了,约翰?出了什么事?在哪儿发生的?是谁干的?”“在教堂里发生的,是安妮·登曼干的。”他回答道。然后,他把雷诺兹的话原本托出,一一告诉了妻子。当然,弗拉克斯曼的事业没有因为结婚而给毁掉。相反,在妻子的大力支持下,他去了罗马(那年头,罗马可是艺术青年心目中的神殿),切身感受了古典艺术的熏陶;也是在妻子的扶持下。他一步一步艰难前行,终于进入艺术的殿堂——成为皇家艺术院院士。
中国读者对弗拉克斯曼应该比较熟悉(至少熟悉他的插图),人文社早年出版的那本《希腊的神话与传说》(古斯塔夫·施瓦布著),用的就是弗拉克斯曼为荷马史诗所画的插图。正是客居罗马期间,弗拉克斯曼
受黑尔·内勒夫人的委托,开始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绘制插图,这可以说是荷马史诗最重要的两个英文译本,译者非是别人,乃是鼎鼎大名的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弗拉克斯曼的插图,也以这两本书最负盛名。后来,弗拉克斯曼又为但丁和埃斯库罗斯的作品绘制过插图。
弗拉克斯曼的晚年生活得相当平静。1800年,他当选皇家艺术院院士。1820年。妻子安妮去世。罗马时期之后,弗拉克斯曼很少画插图,只为成廉·科伯用拉丁文翻译的弥尔顿的诗歌画过三幅,还有为《天路历程》画过一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为一篇中国故事《珠宝箱》画过一幅插图,这篇故事是他亲自为家人写的。但这几幅插图都没有发表过,如今怕是很难见到吧。
沃尔特·克兰
在雕版印刷的时代,一幅插图从画家的笔下出来,最后印刷到书页上,中间要经过一个重要的环节,这就是雕版。那年头,一个优秀的雕刻师是很受尊重的,在人们的心目中,也算是艺术家,而不是纯粹的手艺人。本文介绍的沃尔特·克兰,刚出道的时候干的就是这一营生。
沃尔特·克兰出生于英国的利物浦,父亲托马斯·克兰是一个肖像画家,但生意似乎不是很好,于是拖家带口在1851年迁居伦敦,希望那里能有更多的客户。但老托马斯看来时运不佳,在生意慢慢好起来的时候,竟撒手归了道山。小沃尔特在父亲去世后,便师从当时著名的雕刻师威廉·林顿,在他的店铺里当学徒,这对他此后的人生道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有很多名家的作品经他之手雕刻出来,像罗塞蒂、米莱斯及坦尼尔爵士等人。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早年的沃尔特受前拉斐尔派的影响甚深,并有幸成为约翰·罗斯金的弟子。
沃尔特·克兰是个名副其实的“画书人”,早年他画过很多儿童书,都是三色彩图,连文字也是手绘的,在当时独具一格,很受欢迎。他画的这些童书甚至登上了大雅之堂,在皇家学院和伦敦各大画廊展出。克兰为成人读物所画的插图当中,工程最为浩大的。大概要算是斯宾塞的长诗《仙后》了,全书共分六卷,一千五百多页,整页插图88幅,还有更多的扉页、题图、尾花及其他装饰,堪称是插图史上的一部大制作(本文的插图全都选自这本书)。但克兰并不纯粹是一个插图画家,他的艺术实践可谓五花八门,除了绘画之外,还包括石膏浮雕、瓷砖、彩绘玻璃、墙纸和纺织品图案。
除了威廉·林顿和约翰·罗斯金这两位恩师之外,另一个对克兰影响最大的人就是威廉·莫里斯。莫里斯是影响深远的“工艺美术运动”的旗手。罗斯金则是其理论教父,沃尔特·克兰自然是一员干将了。像莫里斯一样,克兰也是一个狂热的社会主义者。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同情巴黎公社,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除了埋头工作和热心政治之外,克兰还到处讲学,曾短时间担任过皇家艺术学院的领导人,他的讲稿后来被整理付梓,这就是1898年的《设计的基础》和1900年的《线与形》,可算是对工艺美术运动的理论贡献。
1914年12月,克兰妻子玛丽不幸葬身于一列火车的车轮之下。夫妇结婚44年,感情甚笃,妻子的去世对克兰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仅仅三个月之后,1915年3月14日,沃尔特·克兰也撒手人寰,追随亡妻而去了。
凯·尼尔森
凯·尼尔森是一个以画童话故事而闻名的插图画家,他出生于丹麦的一个艺术世家,父亲是达格玛剧院的经理,母亲是皇家剧院的名演员,家里几乎成了北欧戏剧界的沙龙,易卜生便是他家的常客。凯有位叔祖(拉塞姆斯·尼尔森教授),最开始是一位艺术家,最后却成了著名的医生。凯则刚好反过来。他最早学医,后来却成了艺术家。人生的无常莫测,大抵如此。
放弃医学事业之后,1904至1911年间,凯·尼尔森在巴黎学习艺术。师从让-保罗·劳伦斯,吕西安·西蒙,以及他的老乡克里斯蒂安·克罗格等人。他的聪明才智和独创性很快就在拉丁区得到了师傅和同伴们的认可。他最早的作品是黑白线描绘本《死亡之书》,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对那些过着波希米亚式生活的人颇有吸引力:青春的感伤,微笑背后的眼泪,快乐的梦想,绝望而孤独,死亡之爱的坟墓上散发着玫瑰的芬芳。一位英国出版商看到这些作品后,便请凯为童话故事配画插图,于是有了《12个跳舞的公主》。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尼尔森接下来的插图作品依次有《太阳的东边,月亮的西边》、《安徒生童话集》和《韩塞尔与葛雷特》及《格林兄弟的其他童话故事》,这四本书(有人戏称为尼尔森的“四大名著”)奠定了他在20世纪初叶插图界的地位,与埃德蒙·杜拉克、阿瑟·拉克姆鼎足而三,是20世纪初最重要的童话故事插图画家。
尼尔森所画的童话故事插图,想象奇特,天马行空,似梦似幻,如泣如诉;其笔法细腻,构图大胆,极富装饰感,这一点,明显有比亚兹莱的影响,同时不难看出日本浮世绘的影子(比亚兹莱也深受浮世绘的影响)。极具穿透力的线条则是他自己的,他的童话仙境不像拉克姆的那么阴郁,细腻而透明的色彩比杜拉克的更清澈。
1930年,尼尔森画的《红魔》出版,这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绘本。1939年,尼尔森在二战的阴影中背井离乡。前往加利福尼亚,为迪斯尼公司工作。但他的风格过于怪异,气质过于阴郁,与迪斯尼的甜美温情很不合拍,不久就丢了饭碗。晚年的尼尔森贫困潦倒,处境十分不堪。1957年,尼尔森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一年之后,相伴终身的妻子也随他而去。
阿瑟·拉克姆
20世纪初,多色套印技术的进步使得插图艺术进入了一个彩色时代,也迎来了它的又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插图界的“三剑客”(尼尔森、杜拉克和拉克姆)当中,年龄最长的是阿瑟·拉克姆。1904年,法国小伙子杜拉克漂洋过海到伦敦闯天下的时候,拉克姆正进入其事业的鼎盛时期。
阿瑟·拉克姆自己说:“我出生于伦敦。在那里上的学,并且,我一辈子都生活在那里。我在那里结婚,我的女儿在那里出生。我自己只有这么一个孩子,不过,我的父母却育有12个儿女,因此,我的孩提时代是在一个吵闹、快乐而忙乱的大家庭里度过的。那简直是一个工作和游戏的小社会。大到足以不依赖于外部的交往。”阿瑟的父亲在英国海事法庭工作,事业很成功,母亲是一位布料商的女儿。阿瑟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了绘画的天赋,他特别喜欢描画幻想中的奇异世界,夜里甚至会偷偷地把纸笔带到床上,趴在枕头上画。,但父亲似乎并不认为当艺术家是什么好行当,一心想让儿子步自己的后尘。18岁那年,父亲为他在威斯敏斯特火灾保险公司谋了一份职员的差事。业余时间他便去朗伯斯艺术学校学习绘画。
但枯燥乏味的职员工作毕竟不对阿瑟的口味,在绘画上小有成就之后,他便辞去了这份差事,作为插图记者先后为伦敦的几家杂志工作。他的第一本插图书是1893年出版的安东尼·霍普的《多利·戴尔洛格斯》,这之后,他的主要精力便集中在插图书上。他1890年代最成功的插图书是《英戈尔兹比传说故事集》和《莎士比亚故事集》,这两本书后来分别在1907年和1909年再版,增加了一些彩色插图。
1900年,《格林兄弟童话故事集》的出版,标志着阿瑟·拉克姆事业生涯中的一个真正的转折点。1914年5月,他写信给朋友说:“在很多方面,跟其他几套插图比起来,我更喜欢格林童话的插图。……它是我开始走向成功的第一本书。”1903年,36岁的阿瑟·拉克姆与肖像画家伊迪丝·斯塔基结婚,1908年。他们的唯一的孩子芭芭拉出生。在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中,芭芭拉提到拉克姆经常以自己作模特儿,叫她“弯下腰,想象自己正从地上捡起一只苹果”。或者,“试着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女巫”。
阿瑟·拉克姆的鼎盛时期是1905至1929年,他在此期间的重要作品有:《肯斯顿花园里的彼得潘》、《艾丽丝漫游仙境》、《英格兰童话故事》、《宴乐之神》、《睡谷传说》等。
1939年9月6日,阿瑟·拉克姆在萨里郡的家中去世,离他的72岁生日只差几天时间。《纽约时报》在讣告中说,拉克姆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插图画家之一,他有一本插图书,题为《魔幻的国度》。他创造了这个国度,并生活于其中。他是这个从未存在过、也永远不会存在的世界的组成部分。……魔师已去,魔幻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