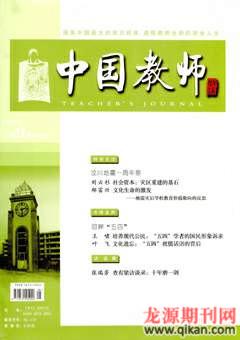文化生命的激发
郑富兴
“5•12”汶川大地震让四川西北地区遭受重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区的救援与重建让我们看到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生命赞歌与人性光辉。曾经以为市场经济导致了当代中国人的道德滑坡与精神危机,但是汶川大地震震垮了这些“认为”。教育是一种道德实践。我们开始反思过往的世事人情,反思学校的教育问题,其中包括学校教育价值取向的问题。反思当前关于学校教育价值取向的思考和看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重建灾区教育,重塑我国的学校教育实践。
一、抗震救灾中对待生命的矛盾态度
汶川大地震使数百万人的家园被毁,近十万人命丧无常。在救援过程中,对生命的珍视与关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准则。在初期的救援工作中,温家宝总理指示:最要紧的是抢救生命;我们要尽百倍努力,绝不要放松;废墟下哪怕还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抢救到底!这些救灾的指示或原则体现了生命的至高价值。在尽可能多地救人之后,国家又史无前例地为遇难同胞举行了3天国悼,降半旗致哀,体现了对这些身处偏远山区的普通民众生命的尊重。因此,珍视生命与关怀生命是地震之后生者感同身受的重要价值取向。
在抗震救灾中,我们看到了珍惜自己的生命与关怀自己的生命的人。他们坚信,个人的生命价值高于一切。他们认为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并认为对于别人的生命没有责任和义务去珍惜和关怀。
但是我们在抗震救灾中也看到了太多太多以生命拯救生命的人。有徒步急行军、乘冲锋艇逆流而上或从高空危险空降进入与世隔绝的灾区的军人;有冒着泥石流、山体滑坡危险抢修生命线的军人和工程人员;有至死用身体护住学生的教师;有用死换回孩子生存希望的父母;有不惧余震危险营救同学和老师的学生;有不怕瘟疫在酷暑下消毒的医疗工作者和士兵;有不畏余震,自发来援助的志愿者;等等。他们也珍惜自己的生命、关怀自己的生命,但灾难来临,他们首先珍惜的是他人的生命,关怀的是他人的生命。
二、一种民族精神角度的解释
这种对待生命的矛盾态度引出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为什么有人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挽救别人的生命?为什么有人不愿意这样做呢?一种合理的回答就是民族认同与民族精神。[1]
多难兴邦!汶川大地震激发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引爆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许多媒体都认为,震惊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灾难激发出了善良、勇敢、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在以往任何灾难中都未曾看到过像中国这样的举国动员的能力、勇往直前的决心和强大的团结互助的精神。[2]这种民族精神体现在各个方面:罕见的志愿者服务高潮,排长龙的献血、捐款、捐物,哀悼日里“汶川挺住、中国加油”的高呼,等等。而且这主要发生在被认为是自私、注重物质享受的年轻人身上。毋庸置疑他们身上仍然蕴藏着中国青年自古以来的爱国热忱。这种民族精神重视人的价值,其实就是重视生命的价值;这种民族精神就是不屈不挠、团结互助的精神,它的力量保护着这个民族里个体的生命,而这个民族也得以生生不息。
这次灾难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民族认同的力量。救援的军队、群众、医生、教师、学生、海外同胞都感受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这次抗震救灾中,通过媒体的文字、图片和视频的报道,全国人民形成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意识,一种“我是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感,感受到我们与“同胞”在一起。我们举全国之力来援救灾区的同胞,并支持他们的灾后重建:而灾区同胞也感到外边有人关心他们。于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鼓励帮助着他们,也鼓舞着他们继续新生活的信心与希望。
因此,共同的观念——“我们”,使得人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挽救别人的生命。我们都认识到了应珍视与关怀生命,同时我们珍视和关怀的是“我们”中的一员的生命,而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主义情感都是缘于这种对于“我们”的生命的珍视与关怀,于是,个体生命与民族精神统一在了这种生命彼此的共生与互助之中。
三、人的文化生命
正是因为这种民族精神和民族认同,使个体超越了自然生命观,也让人认识到,人的生命本质是一种文化生命。
生命是什么?这是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地说,生命是一种活动着的特定有机体,能够呼吸,需要搏动,需要探寻周围的世界。拥有这些自然生命的特征的人,同时拥有意识和思想,因而在生命扩张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每个人的生命扩展都需要考虑到他人也会有这样的思考和行动。于是,如何处理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理解生命的关键。于是,我们提出,人有自己特有的生命存在方式——类生命,一种“超自然生命的生命”。类生命是一种意义,一种关系。[3]超越自然生命意味着人类对于生命价值的考量不是基于动物式的趋利避害,而是基于一些制度要求、社会角色以及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精神信仰与道德习惯。这些因素是一种属于文化的内容。
文化生命是类生命的具体所指,是指个体的繁殖、延续、活动、生活。人生不是孤立的,而是运行于一定的文化场景之中。人是社会性动物,他们并非生来就有能使他们在特定栖息地生存的、严格复杂的行为模式,而是必须学习和发明种种办法以适应多种多样的环境——从寒带的冰天雪地,到没有人烟的荒原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的城市。这些世世代代传下来并不断经过修改的学来的生活方式就是“文化”。理解文化是理解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类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共同的文化,感到自己是同一群体的成员并对这一群体承担义务。[4]因此,人天生是一种文化存在物。遗世独立的生命关怀终究会使自己走向生命的衰竭。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能够创造文化,并以文化来塑造自己。人是离不开文化的。个体的自然生命通过文化成为了一种类生命,而文化则是人的自然生命的延伸,是人的另一种生命存在形态。
四、文化生命:个体价值与民族精神的融通
强调民族精神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体现。人们一般认为,民族主义具有狭隘性,因为它过于关注群体的生命、自由、权利而忽视个体的生命、自由、权利。批评者说,民族主义由于其强烈的情感色彩和鼓动性,因而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它可以自卫,维护尊严和权益,也可以杀人,去伤天害理。[5]就学校教育而言,正如英国学者约翰•怀特指出,如果国家缺乏对个人自由的信仰,那么,为国家的教育就是真正的为“国家”的教育,这很快会导向极权主义。这种思想就是强调“必须教育孩子们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一个并不存在的超个人的实体。实际上这是欺骗人的。为的是让人们相信存在着一个‘国家,国家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因此为了国家的利益要牺牲他们自己”。[6]
但是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我们青年一代乃至整个社会都陷入了民族精神危机之中。这种危机的表现大都为:青少年盲目崇拜西方,往往用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来评价中国的现实;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比较关注个人的物质利益和享受,缺乏艰苦创业和劳动创造的思想行为,民族自强力下降;淡忘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低估了中华古代文明,等等。[7]
从生命的角度来看,民族精神危机与民族主义批判两种判断都存在认识偏差。民族精神危机论者看到的是群体的精神生命的危机,而民族主义批判论者看到的是对个体生命的压制甚或摧残。这仍然是个体生命之间的价值衡量问题。民族精神危机论者强调,如果学校教育只是让学生认为生命高于一切,而且是个体的生命高于一切,那必然会培养出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而民族主义批判论者则强调民族主义产生的没有自我、牺牲个体生命的害己恶果,以及容易产生盲目、狂热、排外、哗众取宠等情绪,压倒理性的思考和判断。
文化生命能够给予备受批评的民族主义以灵魂和正当性。如前所述,文化的意义在于生命之间的交流互动。生命的相互救助、相依相伴成就了民族和文化的生命。这可以视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给了个体生命以保障和意义。在市场经济时代,我们逐渐疏远淡漠他人的生命,我们更关注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这些现代价值;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却感到生命的无意义、无价值,感受到生命的焦虑、迷茫甚至枯萎,因为自为的生命失去了文化赋予的意义。这次汶川大地震让我们开始关注生命的意义,其实就是关注民族、文化与个体生命的关系,认识到自为生命的无意义,意识到生命在文化与民族中才能获得提升,个体才能获得精神的力量,于是一种共同的文化——民族精神重新迸发出来。民族精神危机与民族主义批判其实并不矛盾,它们反映的是现代人追求自由与追求归属之间的一种张力。
文化不仅保护个体生命,而且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提供内容和意义。这种意义体现于文化生命在空间上的关系性和时间上的历史性。正如法国思想家居友所说:“生命不仅是营养,而且是生产和繁殖。”[8]生命力的过剩,不仅通过生育而扩散,而且能够控制智力、情感和意志并使之具有一种利他的性质。生命的活力在于与别的生命之间的交流,这是生命的特征之一。我们每个人都不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激发自己生命的活力,还要将生命敞开,向文化场域内的其他生命敞开。个体的生命是非常脆弱的,而文化的生命是强大的。生命之间的交流包括生命之间的互助。只有共同文化下的生命凝聚起来,才有可能抵御各种摧毁生命的灾难。个体生命的孤立容易使生命走向虚无,丧失意义,丧失生命发展的方向感,在没有交流中逐渐枯萎。
五、生命化教育主张的意义与局限
关怀生命是当前学校教育关注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生命化教育也成为了时髦的教育理念。这一理解把教育与生命的关系视为教育的根本问题:教育对于人类群体和个人而言都是一种本体性存在,它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教育的价值在于它对生命存在本身的意义,人类群体的发展和个体的生命发展是教育的最终追求,在这种追求中,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处于优先的地位;从教育价值的考虑到对教育目的、内容、形式和手段的选择上,都要关注生命本身。[9]生命化教育主张者认为,当前工具化、知识化、制度化的学校教育抑制了学生生命活力的勃发。这次地震中激发的生命意识和生命关怀将会更加肯定这一教育理念及其价值取向,促进其在实践中的贯彻实施。
教育是个体文化生命形成的重要途径。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人的文化生命。孔子认为,完美的人格理想是人的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的和谐统一。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里的“质”,指质地、质料,指人的自然状态或本性,即人的自然生命。“文”,指文采、华饰,实质上就是文化作用于人身而使之散发的特有的光彩和气质,即人的文化生命。每个具体的人都包含着两种生命——自然生命(质)和文化生命(文)。如果自然生命超过了文化生命,人就未免粗野;反之,如果文化生命超过了自然生命,人也未免浮夸。只有把这两种生命形式配合得很恰当,才是君子的典范。
对于文化生命,在教育学上存在着争议。比如,卢梭的自然主义思想就是主张自然生命优先于文化生命。而当前生命化教育对现行教育的批评,实际上就是指当前学校教育过程中强调文化生命超过了强调自然生命。这些争议乃至抨击在特定的时间和语境中是合理的,但都失之于把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相割裂甚或对立。
其实,人的自然生命已经具有文化色彩,纯粹的自然性已经很少了。按照儒家思想的说法,生命是文化的归宿和原点,文化只不过是生命作用于世界的创造物,只是生命的表现形式而已。儒家思想认为,文化发展的终极目标,即判断文化是否向最好的方向去发展,唯一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增强人的生命活动,弘扬人的生命精神,使文化生命与自然生命得到统一。当前人们支持的生命化教育主张,实质上就是要矫正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的关系。生命化教育就是激发学生的生命意识——这既有自然生命,也有文化生命。
文化生命肯定个体的自然生命,生命在文化中生长。个体自然生命依赖不同的文化要素保护自身不至于自我消亡。社会化本身就是一种人的“文”化,即个体对社会文化的内化。人类的婴儿在刚出生时是一个柔弱无能的有机体,一无所知,如果没有他人的帮助,至多只能生存几个小时。与其他动物的幼仔不同的是,婴儿后来的行为方式是学来的。如果没有掌握文化的内容,比如了解规范、价值标准、语言、技能、信仰,以及其他在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进行思考和行动的模式,那么个体或者无法在社会中生存,或者无法成为真正的人。在这个“文”化的过程中,文化中的一切都应该被使用。
六、激发文化生命:生命化教育的反思
就学校教育而言,生命化教育就是如何均衡地把握学生的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的关系,使得学生能够“文质彬彬”,既有生命的厚重与超越,也不失生命的激情与活力。这一点可以通过德国教育思想中的“教化”(Bildung)这一概念来理解。伽达默尔认为,就教育而言,教化的功能在于使人脱离人的自然存在的状态,而获得一种精神生命,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存在。因为人之为人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脱离了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而人之所以能够脱离了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就在于他在本质上具有精神与理性。因此,人按其本性就不是他应当是的东西,人之为人就需要教化。谁沉湎于个别性,谁就未受到教化。个体获得教化就是摆脱了他的特殊性而获得了普遍性的生命。通过教化和不断地自我教化,个体使自己的精神生命成为符合社会习俗的要求以及社会道德要求的人。[10]
教育激发文化生命意味着学校教育应该是学生个体生命体验与文化传统之间的主动对话过程。英国学者普林(Richard Pring)认为,教学的叙事可分为两个层面:(1)非个人层面,即在科学、历史或文学之中的叙事。(2)个人层面,指年轻人试图认识世界,寻求有价值的生活方式。教学正是在这两个叙事层面的联系中展开,即让学生与非个人层面的叙事建立联系,从而使学生通过一系列重要的人类活动和在与他人所言、所做和所为的联系中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寻找自己的价值。[11]民族历史上积累的文化传统在非个人叙事层面得到保存、发展和批评。人的文化生命就是在个人层面的叙事与非个人层面的叙事连接中逐渐形成的。个人层面就是个人真实的生命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层面的叙事是文化生命形成的起点和归宿。个人层面的叙事是个人的直接的生命体验,充满了激情和活力,而这正是文化生命的开始。通过与文化传统的对话,如学习了科学、历史或文学以及生活等内容,个体的文化生命逐渐形成、发展,最终这些非个人层面的内容通过学习成为学生个人的生命体验,成为个人层面叙事的内容。作为起点的直接生命体验更多是一种自然生命,充满了野性与激情,而作为终点的生命体验则是真正的文化生命了,当然,这一终点往往因人而异,因时不同,有的成为具有创造性的人,有的可能被文化的重负所压制而失去了生命的灵气与活力。而要避免那些不好的结果,就需要学校教育成为一种个体生命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平等对话。平等意味着让学生成为与文化传统对话的主体,使教学既立足于对传统的继承,通过对前人提出和思考过的问题的学习(表现为概念、思想、原则和理解的学习),认识世界和他人,又尊重年青一代在努力认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时产生的真实“声音”和真实的情感。这样的教育本身就充满了生命温情与历史关怀。
文化生命意味着个体生命蕴含了文化传统(包括民族精神),同时这些文化传统形式又提升了生命的存在并维系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怀生命与民族振兴的学校教育价值取向是统一在文化生命的激发之中的。因而,激发文化生命就成为学校教育新价值取向的一种可能选择。
参考文献:
[1]党的十六大将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对民族精神的一种时代解读。也有人依据传统哲学概括其丰富的内涵,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公无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厚德载物”、大丈夫气节,等等。
[2]郑永年.四川地震与中国民族精神的再现[EB/OL].联合早报,(2008-05-20)[2009-04-02].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6/forum_zp080520b.shtml.
[3]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1.
[4]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64.
[5]徐友渔.家乐福事件与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EB/OL].天益,(2008-05-13)[2009-04-02].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8791.
[6]约翰•怀特.再论教育目的[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126.
[7]李康平.当代青少年民族精神教育的几个问题[J].江西教育科研,1997,(5).
[8]居友.无义务无制裁的道德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03.
[9]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李家成.关怀生命:当代中国学校教育价值取向探[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10]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4.
[11]Pring,Richard.Education as a Moral Practice[J].The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2001,30(2).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王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