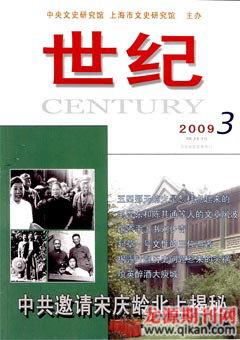起草一号文件的三位逝者
吴 镕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连续发起推动农村改革的五个一号文件,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文件是由中央领导布置,杜润生同志具体组织一个班子。正如万里所说:“我就抓了一个杜润生,他是邓子恢时代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实际经验多,也有理论水平,又比较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我就请他来起草会议文件,对文件作解释、说明。”“建立中共中央农村改革研究室,同时又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都是杜润生……它受中央委托起草政策性文件,协调各方面关系,实际上起着一定的综合性、指导性作用。”(《中国经验:改革开放30年高层决策回忆》)
杜润生是主笔无疑。但他谦虚地说,自己只是一个符号,关键是有一个团队。杜在其自述一书中开列了一批名单,包括至今佼佼者如王歧山、陈锡文、杜鹰等。我这里只想特别怀念和追忆三位默默的逝者,他们是起草一号文件的中坚力量:刘堪、林子力和张云千同志。
一枝幽兰
刘堪,1926年5月生于河北乐亭县农家,2008年12月25日在京逝世,享年82岁。他是一枝深谷中的幽兰。
牛年正月初六清晨,电波传来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何道峰君的短讯:“清晨6时梦醒,知刘堪君西归,推枕披衣,绕屋数匝。25年师友之谊,病榻执手相看泪眼事,历历在目,无以排解,致诗以伴君归。《品幽兰悼刘堪君》:一身正骨羞朝野,求真忍让八十年,不与桃李争晖露,留得清气满人间。”
读诗思人,不禁潸然泪下。
刘堪早年考入清华大学,即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7月在华北联合大学参加革命,辗转于河北石家庄、正定等地。同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至1952年2月,历任华北大学一部教务干事,俄文大队第二班学习辅导员,政治研究所教育干事。随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成立,刘任革大政治研究院组织教育科干事、教研室研究员、助教。1952年至1996年,历任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农村工作部四处干事,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理论教员,中共高级党校语文教研室及哲学教研室助教。1966年,调国家农林部政治部工作,历任政策研究室编辑组副组长、编刊组组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79年1月至1990年12月,历任国家农业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任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员等。1999年1月离休。
他是老革命,但最辉煌的一段经历,是到国家农委(后改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后,始终作为中央农研室主任杜润生同志最得力的助手,协助杜调查研究,运筹帷幄,连续为中央参与起草八十年代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和经济振兴。他带领调查组深入乡村农户,掌握第一手资料,跑遍了半个中国,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村情况和农民诉求,了如指掌。但他性格内向,默默耕耘,从不显山露水。外人只知有杜,无人知刘。其实他是一号文件的主要执笔者之一,是得杜老思想真传的第一人。他曾是学中文出身,文学素养极好。但起草文件从不用文学语言,而是十分严谨地采用科学语言。在实际工作中,协助杜老,协调折冲,博采众长。农村工作从一刀切、一个模式,到“可以,可以,也可以”,先多样化再逐步规范化,促成如此决策,刘堪是一大功臣。
我有幸作为地方上参与一号文件起草工程的“农民工”,得以亲炙刘堪的教诲。他循循善诱,严格要求而又温情体贴。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严密的逻辑思维,使我们得益匪浅。八十年代初,我根据江苏农村社队企业的探索,在《红旗》杂志上写了一篇《论以工补农》,后来湖南等地读者认为这有“一平二调”之嫌。刘堪帮我具体分析,认为在同一社区合作(集体)经济内部,付出等量劳动,但由于运用的生产工具不同,出现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加上当时工农产品剪刀差价等不合理因素,务农社员比务工的更辛苦而创造的价值却大大偏低,务工社员则无“露天工厂”的风险劳累而依靠先进工具创造较高价值。在务工务农社员之间,根据按劳分配原则,作一定的调剂,是体现了社区范围内的社会劳动公平和人际之间的社会公平。至于将务工收入购置农机具等补农措施,更是社区合作组织内部的调剂,不是“大跃进”时的共产风和一平二调。这些,在今天已是常识,而且从国家宏观范围内,都已明确要让工业反哺农业,实行以工补农、城乡统筹了。但在当时,是一场争论。相应的还有江苏提出的“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等等,也受到包括于光远同志在内的一些质疑。(客观上1985年农业减产,个别高层领导指责乡镇工业,说“无工不富”的声音太高了,乡镇工业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集体挤国营等等。)刘堪帮助我理清思路,写了答辩文章,把于文和我的小文都刊载在刘主编的中央农政室内刊《农村问题论坛》上。这一争论受到高层重视,总书记发话“不要再争了,这几年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刘堪教导我们的方法总是先讲原则、原理,再讲逻辑、方法,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基本点是从农民的心愿出发来看问题。不是指责农民“自发倾向”,而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起草一号文件,是“苦力的干活”。一般年初中央领导出题,紧接着深入农村调查,夏季汇报,理出头绪,然后再下去,到9月份左右上北京,开始与部门座谈、起草文件初稿,多次反复。12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当时号称“农民议会”(因为中国是没有农民协会和农民组织的,只能由农村干部作为代言人)。开会的过程也是一号文件争论、诞生的过程。最后由中央审发。这时,总是在万里、田纪云等同志领导和杜润生同志亲自掌握下,刘堪、张云千等一班人,日以继夜,反复琢磨,字字计较,那真是辛苦之极。有时,刘堪也会带领我们“放松放松”,带头游泳、健身。有一年还破天荒地让大家去了一趟承德看“外八庙”,当时是作为一个大享受了。那是刘堪发起的,让我们这些地方上来的“农民工”宽松一游。
1990年以后,中共中央农村政治研究室被撤销,许多农村研究者劳燕分飞。难能可贵的是,刘堪仍然作为杜润生同志的忠实助手,帮助杜老思考农村改革和发展,而且进一步从宏观上考虑中国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如何相匹配,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2008年7月18日,何康、陈锡文等一批农口新老同志,聚会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并为“九五老人”杜润生祝寿。刘已卧病,但还是作了长篇书面发言,回顾农村改革历程,并期待杜老百岁时再一起相聚。哪知天不假年,他却率先谢世。
前面说过,刘堪有一个传统,就是从不突出自己。他不写回忆录,不谈自己的经历。他总是说,我就是只会当当助手。他也几乎从来不写个人署名文章。他夫人对我多次说:“老刘这个人呀,内向。回家不多话。我看他对你们说的话比对我说的话多得多。回家从来不谈公事,只是埋头搞文件。”他晚年自谦为四平老人(平凡、平庸、平常、平和),但他的气质,风范,确实感染了我们一代人。
今年正月初六,收到何道峰君一诗后,我也不揣浅陋,步韵奉和:“辅佐杜老任朝野,赤心不移三十年。默默
耕耘世鲜知,巍巍风范留人间。”杜老在任上,他辅佐;杜老“下野”了,他仍知心相辅,实为难能可贵。患难识知己呀!
刘堪同志逝世前,他就遗嘱不写生平,不收花圈,一切从简,不准搞遗体告别之类。因此当时只有极少数同志知道,搞了一个极小规模的追思会。但是,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么一位农村改革的幕后先驱者之一。得知他逝世以后,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回良玉、李源潮、曾庆红等领导人分别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老农口同志更是纷纷表示悼念和哀思。幽兰刘堪也不虚此生了。
一只报春燕
经济学家林子力属林则徐后裔。1925年生于福建连江。他的贡献不自始于起草一号文件。1977年6月,他就与有林等同志著《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当年11月,中央电台连续全文播发,被当时人们称为十年浩劫后思想拨乱反正的“第一只报春燕”。它成为此后真理标准全国性大讨论的先导。
1980年,林子力调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兼理论组组长。凭借他深厚的理论素养,结合农村大包干的群众创造,他率先在起草文件时提出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这从过去把包产到户批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破天荒的理论突破,载入了第二个一号文件,即1983年1号文件。(当然,这里有集体的劳作,当时有吴象等的调查研究,有卢文等同志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农业合作化》引述语录,还有集体的讨论和争论,但这无损于林子力这只“报春燕”的大胆诊断。)
还有一个当时争论最激烈的雇工问题。广东人养鱼雇工,安徽傻子瓜子雇工,引起争议。杜润生派纪登奎(原任副总理,当时任农研室部级研究员)赴东欧考察,回来向我们作了一个小范围的报告,总的意思是说雇工现象是正常的。林子力从《资本论》中找到现为人所共知的小业主带徒弟、请帮手的计算模型。但他还是多调查,多思考,向中央写了报告,认为人的智商、能力不同,一部分人雇工,一部分人受雇,再自然不过。他对我们说,如果满世界都是博士,咱们都得饿死。人才是有层次的,有的人就当不了老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雇工现象有多样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可塑性。还开了政策口子:“除传统的变工、零工外,请帮工、带徒弟有学技术的成分,剩余价值小,可以不视为雇佣劳动。同时,雇佣劳动不等于雇佣劳动制度,为发展生产所必需,利大于弊,不妨允许,至少暂不取缔,以便为改革摸索经验。”如今,私营企业已大大发展,但当时作出那样的判断是理论和实践的又一创新。他还是最早赞扬浙江温州模式者之一,倡导市场经营,形成生产要素市场。
林子力在中央农研室是有名的大理论家。我们都愿意听他“吹”理论问题。农研室由杜润生主持过两次学术研讨会,一次是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舒尔茨教授,一次就是林子力讲社会主义经济论。
“报春燕”于2005年8月8日谢世,正好80岁。
一头老黄牛
中央农研室综合组组长张云千,在室里也是一位大哥。父亲是国家水利部副部长,但从未见他有什么高干子女的优越感,而是一位忠厚、内向的默默耕耘者,一头名副其实的“老黄牛”。与他接触,除了谈工作,就是谈文稿,从来未听他谈及自己的经历和成绩。同事们说他是头一个“工作狂”。对年青人总是循循善诱,埋头于文件的字斟句酌,还把道理剖析给大家听。从一号文件的执笔者来说,他实在是动笔最多、最勤的。每次在文件上修改的词句,写得工细,线条划得笔直,那时他已劳累有胃病,每次搞完一个一号文件,他都要吐一次血,病一场,才缓过劲来。这使我懂得了云千搞文件真正是呕心沥血,字字心血!
张云千勤于琢磨。每年一号文件也都会有些新名词。如今常见的什么机制、体制之类,那时是很新鲜的。一开始讲解文件中的新名词,农民也不大懂。我向云千反映中央文件要更通俗,朗朗上口,少用点新名词。他和杜老都笑笑说,如今总不能停止于“半部论语治天下”吧?时代变了,新的社会,新的改革,必然要有新的语言来表达,人们也会慢慢从见怪到接受和流行。当然,他们对农民创造的一些口号、顺口溜也很欣赏,有些经典语言被收入文件,如“无农不稳,无工不富,不商不活”等等。云千说,中国特色,混合经济,有许多非驴非马,杂交优势,产生许多特定的新名词。每一个中央文件的政策界定,常常是协调折冲、妥协的产物,要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特点,要分散决策以分散风险,不可一刀切。杜老、刘堪和张云千都一致倡导后来为人们称道的责任制“可以,可以,也可以”。正如云千笑眯眯、大包容的个性,也是深得杜老和刘堪之真传。
可是天不假年。云千劳累过度,刚刚年过七十,就撒手西去,成为农研室的早逝者。但他的身影和笑声,还长留于我们的心中。
(2009年2月7日于南京)
责任编辑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