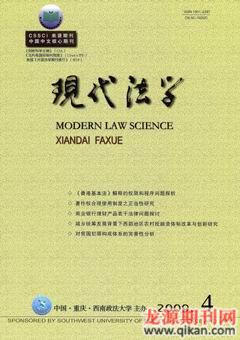论生态人的要点和意义
蔡守秋 吴贤静
摘 要:生态人是处于生态系统之中的人,是日常人,是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体现。生态人在人类生态系统中既可以是主体也可能成为客体。理性生态人是追求人与人和谐相处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构建生态人模式采用的是“主、客一体化的研究范式”及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论。生态人模式和理念的确立,可以为公民环境权的正当化、可实施化提供理论根据,为建设“五型社会”的法律夯实法理基础;有利于环境法与生态伦理接轨,增强环境资源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引入生态系统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促进环境资源法的生态化;有利于扩大法律调整对象的范围,促进当代法律和法学的进步和变革。
关键词: 生态人;法律人;主体;环境资源法
中图分类号:DF46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09.04.09
国外学者为了解决某些法律社会问题,服务于相应的目标,已经先后提出了道德人、阶级人、经济人、社会人、生态人等“法律人”(注:法学家在不同情况使用不同的“法律人”概念:一是指法律上的人,如自然人和法人;二是指法学上使用的“经济人”、“社会人”和“生态人”等概念;三是指法律工作者,如律师、法学研究人员等。本文的“法律人”是指法学家对人的本性和基本特征的一种认识模式,即法学上使用的“经济人”、“政治人”、“生态人”等概念。)的模式。其中影响最大的法律人模式主要有经济人、社会人和生态人。另外,以往的多数法学理论一般都将他们所主张的法律人称之为理性人,并且认为法律人都是法律或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即认为法律人都是主体人。笔者在《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简称《调整论》)一书中,曾对上述法律人的概念、特点和作用作过初步介绍。北京大学周旺生教授在2005年5月18日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中国法理学的若干迷点》演讲中也指出:“我想大家是知道人类通过法律调节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已经有了三种形态,这就是对经济人、社会人、生态人三种人的调整形态。”(注:参见北京大学周旺生教授在2005年5月18日晚在人民大学法学院所做的《中国法理学的若干迷点》演讲内容,引自中国法理网http://www.jus.cn/ShowArticle.asp?ArticleID=664。)本文主要研究生态人的要点和意义。
一、生态人的要点
目前学界对作为法律人的生态人的模式的理解,还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在《调整论》一书中曾对理性生态人的特点作过初步介绍,并认为,当代环境资源法中的法律关系主体或行为主体是“生态社会国家”、“生态城市”、“生态社区”和“生态人”,或者说,当代环境资源法的根本出发点是将法律主体定位为“生态人”。(注: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建立在‘一体化研究范式和‘生态人基础上的主体论和客体论”,第313页。)概括起来,生态人的内涵和要点如下:
(一)生态人是处于生态系统中的人
生态人是在人类生态系统中占有一定位置的人,既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人,也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人。生态学认为,生态系统是由生物及其环境所形成的统一整体,人类与其赖以生存发展的地球生物圈共同形成人类生态系统。人类生态系统既不是“主、客二分法”(Subject瞣bjet Dichotomy)所划定的人类社会,也不是“主、客二分法”所划定的自然界(注:按照“主、客二分法”的研究范式,世界可以划分人类社会(简称社会)和非人自然界(简称自然)两大部分,社会由人组成,是人与人的关系(简称社会关系)的总和;自然由自然物组成,是物与物的关系的总和。),人类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结合或综合。生态系统最基本的特征是它的整体性,生物与其环境统一的原理被称为生态学的第一原理,也是当前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环境与发展关系必须遵循的第一原理。大自然中的万物构成了地球上互相联系的生命之网。人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生命之网中的一个节点。现代生态学把自然界看作是生态系统,这是对生物界的新看法;把世界看作是“人—社会—自然”的人类生态系统,这是对世界的新看法。按照当代生态学理论,包括人在内的每一个物种都在人类生态系统中处于特定的地位即“生态位”,“万物各得其所”就是指每一种生物都有其理想的生态位。在生态系统中,每一种生物都彼此相生相克、相依相随,形成食物链和生态网。生态人既表明人在人类社会系统中的地位,也表明人在人类生态系统中的位置。目前有的法律政策性文件已经明确宣布,生态系统包括人,例如,1991年6月14日,8个北极地区国家在芬兰洛瓦奈密举行第一届北极部长会议,签订了《关于保护北极环境的宣言》,通过了《北极环境保护战略》。《北极环境保护战略》的目标是“保护北极生态系统,包括人类”。(注:参看王曦编著:《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页。)
生态人是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体现,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综合的体现。每一个具体的人、个体的人,既生活在“主、客二分法”所划定的人类社会之中,也生活在“主、客二分法”所划定的自然界中;既与其他人发生联系,也与自然(包括动物、植物、各种环境要素、各种自然资源及江河湖泊等生态系统)发生联系,人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
(二)生态人是日常人,生态人在人类生态系统中既可以是主体也可能成为客体
生态人不同于“经济人”、“社会人”和“主体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般的生态人并不是理性人,而理性的生态人才是理性人,无论是一般生态人还是理性生态人都既可以是主体也可能成为客体。“主体人”模式将人拔高或升华为比上帝还要高的、不可能成为作用对象或客体的“虚幻人”;而“生态人”模式将人从不可能成为作用对象或客体的“虚幻人”转变为存在于人类生态系统中的、既可以成为主客也可能成为客体的“真实人”。一方面,理性生态人是具有生态文明观和生态文化的进步人士,是从各种现实人中抽象出来的一种法律人理想模式;另一方面,生态人是可以观察、评价的具体人,是受自然生态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制约的、能力有限的人,是既可以成为主体也可以成为客体的普通人。生态人既要认识和作用于自然,也要认识和作用于其他人,还要认识和作用于自己。在人与人之间,人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些人既对别人发生认识和作用,也被别人认识和作用,即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互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状态;在人与自然之间,人既要认识和作用于自然,人也受自然的影响和作用,即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互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状态;在自身内部,生态人的思想与身体相互作用,生态人需要认识、作用和改造自己,即人本身既是主体和客体。生态人处于既可以作用别人或自然物也受别人或自然物作用的位置,它不像神和上帝那样可以摆脱任何限制、约束和控制,任何生态人都既可能成为作用和改造其他人和自然的主体,也可能成为被其他人和自然作用和改造的对象即客体。
生态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特征与当代哲学和行为科学中的人、主体和客体的概念十分相似。从发展的历史观看,主体和客体都是历史的范畴和发展变化着的。马克思指出:“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1]主体与客体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人既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动物、生态系统等自然物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主体,作为主体的人可以对象化,作为客体的动物和生态系统也可以非对象化。主体客体化或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是人类实践活动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们相互前提、互为媒介,人们就是通过这种运动形式不断解决着现实世界的矛盾(包括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2]。
例如,当我们说某人A发起(或实施)某种行为、拥有(或所有、使用、占有、享受)某种利益(或权利、权力、资格、事物)时,某人A是主体;当我们说某人B成为某种行为的作用对象或别人利益的载体时,某人B是客体。一个生态人既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主体和客体是对等而共存的关系。例如,某人A用刀打击某人B时,A是主体,B是客体,但B仍然是其被A侵犯的人身权的主体;当B还击A时,B是主体,A是客体,当A仍然是其所有物刀的主体。总之,主体和客体不再是区别生态人和其他自然物的概念和标志,而是表示生态人和其他自然物的关系状态的概念。
生态人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人或人的意志、人的精神,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人。生态人模式与当代社会学和哲学中的常人方法学中的人的模式十分相似,生态人就是日常人。当代社会学的一个重大进展是将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回归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人即日常人,而真正开始这一社会学思维方式革命的是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等社会学家提出的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注:“常人方法学的主要价值是在方法论上的贡献,并且是在方法论中最根本的问题──思维方式上实现了转变。……当代社会学的许多理论观点是在常人方法学实现的思维方式转变基础上建立的。常人方法学掀开了社会学理论的新篇章,它在社会学视野里实现了孔德希求的精神革命。因此,可以把常人方法学看做社会学史上的一个新里程碑,它是传统的现代社会学转向反传统的后现代社会学的重要标志”;“常人方法学开始的社会学思维方式变革,在当今已经演化成波澜壮阔的社会学理论革命,各种反传统的社会学理论风起云涌,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谱写了无数令人震撼的学术篇章。一部部别有洞天的振聋之作接踵而来,一篇篇另辟蹊径的发聩之说呼应而至。社会学进入了万紫千红、繁花似锦的春天,似乎到处都是新风景、新境界”。以上引自刘少杰著:《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1页。)“常人方法学把社会学看成常人的活动,迈开了社会学从神化转向人化的一步”;“常人方法学明确主张要用日常人或普通人处理日常生活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不仅社会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是日常生活,而且社会学本身也是一种日常活动,这个观点使社会学放弃了作为客体对立面的主体地位,社会学家及其社会学研究活动不再具有二元对立论思维方式中的那种主体性;他不仅仅是个在社会生活之中的观察者、反映者、辨析和评判者,一个构造者、整理者和实践者,而且更为重要的他还是一个在日常交往中的受动者,在其开展研究的过程中不断接受着来自对象主动作用的被作用者,是一个被研究对象能动地指向、理解和评价的对象”;“在常人方法学中,社会学(家)不再是绝对的主体,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常人。常人总是在具体条件中存在的,常人既是能动者又是受动者,既能思又被思,既他思又我思。”[3]常人或生态人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被传统的“科学”、政法、宗教、经济、哲学和法学遗忘的世界,因为这些文化形式或专业形式都是主题化的活动,都信奉“主、客二分法”的范式。而“日常生活世界或常人世界是真实的人的世界,这里没有科学世界、生产世界和其他主题化世界里的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关系,甚至也没有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主体与客体一样,都是在相互对立中才能界定、才能成立,不论哪一方,只要有一方的界定发生变化,另一方也必须随之变化。在常人方法学里,主体与客体都变成了人”[4]。
(三)理性生态人是追求人与人和谐相处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
如果说经济人模式的前提为或假定为——追求自身利益(主要指经济利益)是人身上最强大的动力,只有遵循这一动力,个人才会为社会的共同繁荣作出最大的贡献。那么理性生态人模式的前提或假定是:人既有自然性又有社会性,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每一个生态人都不能摆脱的基本关系,适当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实现生态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基础;每个生态人都有追求其自身幸福、自由和利益或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这里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但只有和谐的人与人的关系、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提供最大的利益;每个生态人只能通过自身与其他人的关系和自身与自然(环境资源)的关系求生存、求发展、求幸福、求最大的利益,或者说从自身与其他人的关系和自身与自然(环境资源)的关系中求发展求利益(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利益)、求幸福是人的不朽动力。正如古希腊罗马时期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所说的:“人生的目的就在于与自然和谐相处。”[5]“如果想获得幸福,一个人与他的环境之间就需要一种和谐的调整。”[6]
只有充分认识这一根本动力,个人才会为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最大的贡献;只有和谐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是人类生态系统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虽然生态人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总和,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生态人都天生具有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追求人与人和谐相处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理念和能力。生态人所固有的本性,仅仅为生态人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追求人与人和谐相处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了条件、可能和潜力,而要真正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则要求生态人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和生态维护能力,即要求生态人成为理性生态人。所谓“理性生态人”是指具有环境意识和环境法治观念,会计算环境利益,寻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最佳化、最大化的人;或者说,生态人是在不违反环境资源法律“游戏规则”的前提下追求“三种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和“三化”(一体化、最佳化、最大化)的人,追求当代人利益和后代人利益、人的利益和环境的利益“三化”(一体化、最佳化、最大化)的人,是按照环境资源法的游戏规则从事经济、社会和环境活动的人。这种以追求“三种效益”和“三化”为核心的理性生态人显然不同于仅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人的利益的“经济人”、“社会人”和“主体人”。理性生态人的人生的目的就在于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即追求和谐的人与人的关系、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理性生态人的行为的不朽动力;只要每个生态人都追求和谐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只要每个生态人都成为理性生态人,整个社会就会走向人与人和谐共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和谐社会。因此,生态人模式的形成,是对传统法律人的类型的扩充,如果说“个人”是法律的基点,“恶人”是法律的忧虑,“善人”是法律的乐观,“理性人”是法律的理想,“社会人”是法律的期望,那么“生态人”则是法律的必然,也是对“法律人”模式的完善。
(四)构建生态人模式,采用的是“主、客一体化的研究范式”及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的方法
迄今为此的经济人、社会人和主体人的法律人模式,基本上奉行的是“主、客二分法”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的特点是将人与物、社会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主体与客体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或者是夸大人、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和主体的决定作用,而贬低或轻视物、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客体的影响和作用。而生态人的法律模式奉行的是“主、客一体化” (subject-object integration)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的特点是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这两者联系起来、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虑。“主、客一体化”就是综合地(全面地、辩证地)考虑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即“既关注人,又关注自然,并且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既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又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将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和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结合起来”。无论是当代的环境资源学还是笔者的“调整论”,在对待法律人的生态人模式方面,既没有脱离对人的关注而是“以人为本”,也没有脱离对自然的关注而是“以自然为根” (注:法国作家加里在《天根》一书中指出:“大自然是人类生存之根,是所有生命的根”。引自[法]罗曼•加里(Gary Romain ,1914∽1980年)著,宋维洲,译:《天根》(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第五批),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罗曼•加里(原名罗曼•卡谢夫),法国著名作家,两届龚古尔奖获得者。在1956年,42岁的罗曼•加里就凭借长篇《天根》首获龚古尔奖。),并且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将“以人为本”和“以自然为根”同时运用到法律人模式即“生态人”之中。
在对理性生态人模式的构建上,环境资源法学基本上采用的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其基本思路如下:(1)从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以个人本位为基础进行人的抽象。首先分析具体的个人的特性,即每个人都是具有自然性的生命体,都有生物性、个人兴趣、爱好,都有追求幸福、自由和个人利益(自利性)的倾向。个人主义方法论不同于个人主义,它是以个人作为学科分析的基点或基本研究单位的一种研究方法论。古典自然法学派以个人主义为其哲学基础,强调个人作为社会基本元素的独立性以及对于社会而言的优先性,从而将其理论奠基于对个人地位、个人价值的肯定与弘扬上。关于个人主义方法论,┞芬•迪蒙曾将吉尔克关于自然法学所奉行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的要点简述如下:“与成文法相反,自然法并不包含社会的人,而只包含个人,每个人都是自给自足的,是上帝的代表,理性的沃土。……关于国家(和社会)构成的首要原则,是从没有任何社会政治依附的自主性的人的固有特性或品质中抽引或推导出来的。自然状态在逻辑上先于社会政治生活,它所考虑的惟有个人,而且逻辑的先在与历史的先在交织在一起,因此,自然状态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之中,人被设想成在社会或国家创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注:路易•迪蒙印度社会学文集,转引自: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个人主义方法论的要点是,首先将个人与社会、国家区分开来,个人是不依赖于任何政治社会而存在的自主性的生物,个人先于社会和国家而存在,社会与国家不过是人的创造物而不是人本身,“所有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和现实性”(注:引自汪和建著《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关于个人主义方法论,请参看胡玉鸿著:《法律方法导论》(《法学方法与法律人》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法律制度的建构及运作必须以个人的目的、需要和兴趣为依归。个人主义方法论强调以个人为前提,但并不否认个人与其他人或社会的联系,只是反对在强调社会(集体)时否定个人的独立性。(2)从整体主义方法论出发,确认每个人都必然生活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都必然与其他人和自然(环境资源等)发生联系即必然有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定每个人要求得其自身的生存发展(包括要追求自己的快乐、幸福和最大利益)的条件,即每个人都必须处理好与其他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与自然之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和发挥主体本身及其外部社会环境(即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即自然环境资源)的优势。整体主义方法论包括集体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同体主义方法,是对个人主义方法论的一种挑战和补充。它强调人是人类生态系统中的一种已被生态化、社会化了的元素,人只能作为生态人和社会人而存在。(3)将个人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结合起来,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联系起来,充分利用和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周围环境的客观条件,在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中求得个人的最大利益、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4)个人主要通过其行为影响、作用(包括建立、改变和改进)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法律是最有效力、效益和权威的行为规范,法律通过规制(规范和控制)生态人的行为,能够和可以调整好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生态人的意义
人性和人的模式,又称人的形象或人类形象,是包括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心理学、伦理学在内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是法理学或法哲学探索的主题之一。德国哲学人类学创始人M•舍勒(Max Scheler)在《论人的观点》一文中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哲学的中心问题应追溯到人是什么这个问题。”[7]
查士丁尼指出:“我们所适用的全部法律,或是关于人的法律,或是关于物的法律,或是关于诉讼的法律,首先要考察人,因为如果不了解作为法律对象的人,就不可能很好地了解法律。”[8]
法律是人的行为的社会规范,法学是一门以法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一向重视研究人的模式与人的行为、法律调整机制之间的关系。通过“人的模式”的建构,提炼出“法律人”的核心假定,被视为是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法律规范化的本质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出发点。
具体到生态人,笔者认为其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为建设“五型社会”的法律夯实法理基础
近几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党和国家确立了建设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循环经济型社会(简称“五型社会”)的国家建设目标。《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5年12月)强调指出:“加快构建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在内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弘扬环境文化,倡导生态文明”。2006年12月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37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必须“充分认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注:据新华网北京2006年12月26日电,“胡锦涛强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6/12-26/844423.shtml。)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9]。建设“五型社会”的崇高目标和艰巨任务,不仅表明党和政府已经将保护环境等人对自然的行为,从行为实践提高到文化、理论和伦理的高度;而且表明对包括法律体系建设、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制度在内的法律文化建设特别是环境法治文明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五型社会”的共同特点是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建设“五型社会”的法律的基本内容是改进和规范人对自然的行为、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2004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大会上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从法律上体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10]
2005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第二十二届世界法律大会的部分代表的讲话中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国家与国家的和平共处,都需要法治加以规范和维护。”(注:参见: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隆重开幕 胡锦涛会见大会代表并作重要讲话,《人民法院报》2005年9月6日第一版。)
为了建立健全适合于“五型社会”建设的法律体系,更加充分有效地发挥法律在建设“五型社会”中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形成并提倡生态人的法律人模式是十分必要的。健全的环境和生态法律制度不仅是生态文明的标志,而且是生态保护的最后屏障。而确立生态人的法律人模式,树立生态人的文明观念,必然对“五型社会”的法治建设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生态人较典型的思维方式是: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强调法治即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待人,以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同样强调法治即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待物,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包括人与自然建立伙伴关系、合作关系和生态治理关系(这里的治理关系包括治理和善治即英语中的governance和good governance)。生态人不仅考虑人的利益和人与人的关系,而且综合考虑人的利益与生态利益、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显然,相对于经济人、社会人和主体人的思维方式而言,生态人思维方式的角度更高、视野更远、心胸更广,因而更具有先进性;相对于基于经济人、社会人和主体人的法律而言,基于生态人的法律对“五型社会”建设更具有法律保障作用。在建设“五型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法律的基本作用是通过制定人的行为规则,规定人对其他人或人对自然(包括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可以做什么、应当做什么或不应当做什么,以此树立理想的人的形象,引导、促进和保障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促进和保障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法律上讲,适用于和谐社会的法律应该包括规范人对人的行为以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规范人对自然的行为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两个方面。环境友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人对环境友好,包括人对环境的态度友好和人对环境的行为友好这两个方面;从法律上讲,适用于环境友好社会的法律应该包括规定人对环境友好的基本理念和人对环境友好的行为规则这两个方面。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人对自然资源的珍惜、爱护和节约,包括人节约资源能源的品德和行为这两个方面;从法律上讲,适用于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法律应该包括规定节约资源能源的原则和节约资源能源的制度这两个方面。生态文明的基本特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互惠共利,包括生态文明的精神文明成果和物质文明成果两个方面;从法律上讲,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法律应该体现人对生态系统的文明观念和文明行为两个方面。法律只有根据生态人的法律人的模式,来规定“五型社会”建设中人的行为规范、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才能保障“五型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美国家,法律对经济人、社会人和生态人这三种人的调整是逐步出现的,对生态人的法律调整在1960年代之后才出现。当我国对生态人进行法律调整时,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对经济人和社会人进行法律调整方面已经取得大量的成功经验和教训,而中国连对经济人和社会人的法律调整还缺乏可以依据的完善法律,这无疑增加了我国用法律调整生态人的行为关系的难度。但是,我们不能沿着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法律“先保护经济人的利益、再保护社会人的利益、最后保护生态人的利益”的老路前进,当代中国的环境资源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中国在法治建设方面应该寻求新的出路,应该采用可持续的、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这就是在依法调整经济人、社会人和主体人的主动性的同时,高度重视生态人的法律调整,把对生态人的法律调整与对经济人、社会人的法律调整有机地结合起来,在重视以民法、商法为主体的私法建设和以社会保障法、经济法为主体的公法建设的同时突出环境资源法治或生态法治建设,形成建设和谐社会、环境友好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生态文明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充分发挥法律在促进和保障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
(二)与生态伦理接轨,增强环境资源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
如何看待人、人性以及设置什么样的法律人模式,对于立法者如何制定具有正当性(或合法性)的法律、执法者如何正确地适用法律、法学家如何理性地阐释法律,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在中国树立环境资源法律的权威、实行环境法治,首先要使人们相信包括生态人在内的环境法治的正当性,使人们信仰包括生态人及其环境正义、环境公平、环境安全、环境秩序、环境民主和环境效率等理念的环境资源法律。与生态伦理接轨,增强环境资源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为将中国的环境资源保护纳入法治轨道提供坚实的伦理基础。
目前中国已经制定一大批环境资源法律(注:到2006年,中国已经制定9部以防治环境污染为主的环境保护法律,13部以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和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自然资源法律,10部以自然保护、防止生态破坏和防治自然灾害为主要内容的法律,30部与环境资源法相关的法律,还有大量的环境资源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委行政规章和地方行政规章,仅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就有1600余件;已颁布800余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中国已参加《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50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先后与美国、日本等42个国家签署双边环境保护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与11个国家签署核安全合作双边协定或谅解备忘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已经形成环境法体系。但是,从国家和社会对政府环保工作和环境法律的要求和期望看,中国的环境质量并没因环境保护法数量的增多而成正比相应地得到改善。统计结果表明,随着环境法规数量的增加,环境污染恶化状况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有些地区环境污染程度不降反增。为什么我国政府制定了这么多环保法律、发起了这么多环保行动,仍然是“年年立法,年年污染,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污染速度”,有些地区仍然走不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继续恶化”即“越治越污染”的怪圈?为什么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等环保官员发出“环保部门立法虽多,管用的不多” 的感叹[11]?
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某些环境资源法律缺乏正当性和有效性。
正当性(人们往往将其译为“合法性”,英文是Legitimacy)是一个与“合法律性”相区别的概念。一般认为,正当性是指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能够让被统治者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使被统治者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正当性是人们对统治权力做出的价值判断,任何形式的权力,只有它被人们认为具有“正当”理由时才为人们所服从,从而具有正当性;正当性的核心是人们的自愿认同和支持。正当性不仅仅指法学意义上的符合法律规定或符合法律原则,而且主要指政治权力范畴上的权力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正当性(或合法性)与合法律性的区别在于:合法律性是指与国家法律的规定相一致或为现行法律所确认或保护,是从实证法规范上讲的,是一个法律解释问题,主要关注形式上的合法,其判断取决于执法者对法律与事实的认定;正当性(或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是否符合人民的意愿,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是否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和增进人民福祉,是从道德和价值角度进行的判断,不是实证法意义上的判断,主要关注实质上是否符合正义和公平的标准,其判断取决于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法律的正当性是指法律因其内在价值和外在效用而被人们认同和服从,法律的正当性也就是人们认同的法律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当代西方政治学家从各自的理论出发,定义了如下几种正当性(或合法性)概念,或形成了对正当性(或合法性)的如下解释理论:(1)通过伦理学解释的正当性(或合法性)概念,即把抽象的美德、善和正义作为正当性(或合法性)的基础或作为判断正当性(或合法性)的依据,认为一种统治或权力只要符合永恒的美德、善和正义就具有正当性(或合法性),采用的是抽象的伦理价值理念即伦理标准。“两千多年以来,自然法这一观念一直在思想与历史上,扮演着一个突出的角色。它被认为是对与错的终极标准,是正直的生活或‘合乎自然的生活之模范。它提供了人类自我反省的一个有力激素、既存制度的一块试金石、保守与革命的正当理由。”[12]
(2)通过社会学解释的正当性(或合法性)概念,即从经验和社会实际出发,认为正当性(或合法性)是同真理没有联系的经验现象,法律只要符合社会生活发展趋势和社会利益就是正当的(或合法的),只要现实生活中存在命令与服从的社会权力关系,并依据被统治者是否相信、是否赞同某种统治,来确认统治或权力的正当性(或合法性),采用的是社会经验标准。(3)通过法律实证主义解释的正当性(或合法性)概念,即根据现行法律判断统治或权力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实际上是将正当性(或合法性)等同于合法律性,采用的是法律形式标准。(4)通过价值与制度的统一来解释的正当性(或合法性)概念,又称现代规范民主理论的正当性(或合法性)概念,即从内在价值与外在形式相统一的角度解释统治或权力的正当性(或合法性),以社会成员(包括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交往、商谈、协商而达成的认同、承诺或接受作为统治或权力的基础,采用的是哈贝马斯提倡的社会化的交往理性标准。(注:哈贝马斯著,童世骏译:《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虽然上述四种方式都能为法律的正当性提供解释,但迄今广为应用的是从伦理学角度为法律的正当性提供依据,或者说伦理学是为法律提供正当性说明的理论基础之一,伦理道德是为法律提供正当性的基本方式之一。在西方国家,法律、道德与宗教并非同一种社会规范,但三者之间却有着天然的联系。“惯常的公式是,法律最终以道德为基础,道德最后建立于宗教之上。”[13]
道德是法律与宗教之间的桥梁,法律精神来自于宗教精神和道德精神,宗教和道德精神给予了法律以
灵魂,伦理道德往往成为评价法律正当性的标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以德育人也往往成为依法治国的基础。目前我国环境资源法所面临的正当性、有效性不足的问题,是“公地经济人”和“地球村生态人”的冲突,是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冲突,是灰色文明与绿色文明的冲突,是“主体人”与“客体物”的冲突。而在这些冲突中,缺乏生态伦理和环境道德则是使环境资源法律制度低效、无效和失效的一个内在原因;而生态人理念又与生态伦理和环境道德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当代生态伦理或环境道德就是生态人的伦理道德观,只要确认了生态人的法律人模式,也就为从生态伦理角度为环境资源法提供正当性依据奠定了基础。
在传统伦理学看来,伦理关系是人类社会内部成员特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近、现代西方伦理思想的主流不是人与自然和谐,而是人与自然的分立和对立,是人对自然的征服、掠夺和统治,“人是自然界的主宰者”。在这种传统的以人的经济利益为衡量标准的伦理观指导下,经济人、社会人和主体人可以正当、合法地用最直接、最便利的方式,无节制获取、肆意破坏自然资源来满足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需要,导致各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问题。也就是说,环境资源法仅仅依靠人对人的伦理、人对人的道德来维护其正当性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或有缺陷的,环境资源法要充分说明其正当性还需要寻求其他的伦理的支持,这就是生态伦理和环境道德。当代生态伦理学对传统伦理的主要发展是:不仅确认自然界对人的价值,而且确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不仅要求人们相互尊重,而且要求人们热爱自然、尊重生命;不仅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而且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不仅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而且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伦理,其中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既是当代生态伦理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生态伦理区别于其他伦理的一个重要特点。生态伦理的提出,对仅仅站在经济人、社会人和主体的角度去认识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人类主宰自然哲学”是一种时代反思,是在新的起点上的再认识。生态伦理为我们重新审视自然的价值,重新理解环境、自然资源和人类生态系统的伦理性质,重新定位人类生态系统内各利害相关体的关系等,推动环境资源保护工作和环境资源法制建设奠定了伦理基础。生态人是与当代生态伦理和环境道德一致的法律人模式。根据生态人模式,生态人是位于人类生态系统中的人,评价生态人的行为和法律的正当性的价值、伦理标准是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价值、生态伦理标准,它涉及人对自然的态度、行为和关系,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人追求其幸福和利益的必要条件,污染破坏环境资源就是污染破坏生态人的生态位、生存空间和生存条件。在生态人心目中,那些旨在保护和改善环境资源(包括动物、植物、物种和河流湖泊等生态系统)、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法律,不仅理所当然地具有正当性、合理性,而且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因为生态人不仅仅寻求符合人对人的价值、伦理和道德,它还寻求符合人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的价值、伦理和道德。由于得到了当代生态伦理、环境道德和生态文明观的支持,由于追求与生态伦理的接轨与协调,生态人的法律人模式就为环境资源管理、环境资源法律、环境资源执法的正当化,为增强环境资源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为将中国的环境资源保护纳入法治轨道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依据。正是由于生态人与生态伦理和环境道德的接轨,在法律中体现和采用生态人的法律模式,必然会大大增强环境资源法的正当性和有效性。
(三)为引入生态系统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奠定理论基础,促进环境资源法的生态化
随着生态学的广泛运用和生态运动的深入发展,当代环境资源法呈现出如下特点和发展趋势:环境资源法越来越重视对生态系统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运用,环境资源法正在向生态法的方向发展即环境资源法的生态化。所谓环境资源法的生态化,主要指“环境法律以当代生态学为理论基础,以建设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社会、环境友好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循环经济型社会为目标,越来越多地运用和体现生态系统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越来越重视用法律规范、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样一种变化或发展趋势。
生态法(注:根据有关资料,“生态法”是1970年代末以来在前苏联和俄罗斯法学界广泛使用的一个词汇。到1990年代俄罗斯出版了不少以“生态法”命名的著作、教材或论文,成立了诸如“俄罗斯联邦法院生态法和土地法研究室”等专门研究生态法的研究单位,以及诸如“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生态法律委员会”等政府机构。2002年1月10日公布施行的《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是使用“生态”术语最多的法律,是一部较多体现生态法思想和模式的环境保护基本法。)是反映当代生态学新理论、新理念,旨在保护和改善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和生态安全,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建设和谐社会、环境友好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生态文明,促进人与人和谐相处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障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法律规范和法律表现形式的总称。生态是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生态系统包括人,人是人类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环境是指围绕人的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和,自然资源是指能够被人类所利用的各种自然因素,环境与资源都不包括人,都是外在于人的物质世界。生态法与早期环境资源法在指导思想方面的最大区别是其贯彻生态本位观、生态整体主义观、综合生态系统观、生态基础制约或环境承载力有限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观,承认动植物、江河湖海等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当代环境危机、环境保护和生态运动的发展,使以经济人、社会人和主体人为对象的法律都暴露了其局限性,而产生了以生态人为对象的生态法。生态法的上述性质、特点和发展实践说明:经济人、社会人和主体的法律人模式,不能适应和满足生态法的需要;只有生态人才能适应和满足生态法的需要,才能推动生态法的发展。
目前我国学界提到的生态法的理论主要有:生态学;生态伦理(包括人类中心主义的、生物中心主义的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生态后现代主义;生态经济学;风险社会理论;生态系统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等。其中生态系统方法(the ecosystem approach,简称 EA)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Intergrated Ecosystem Management,简称IEM)是近年来在国际上广为推崇和流行的方法和理论,它既是生态法发展的主要成果和主要标志,也是对生态法的发展最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作用的具体理论。目前有不少环境法律已经确认生态系统方法的作用和地位。例如,1999年通过的《加拿大环境保护法》在其前言中强调“加拿大政府认可生态系统方法的重要性”;在第2条中强调,在本法的执行中,加拿大政府除应当遵守加拿大宪法和法律,还应当“实施考虑到生态系统的独特的和基本的特性的生态系统方法”。
我国从21世纪初开始引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探索创立一种跨越部门、行业和区域的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综合管理框架。2002年,中国政府与全球环境基金(注: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是关于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土地荒漠化的国际公约的资金机制。它通过其业务规划支持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国家水域、臭氧层损耗、土地退化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重点领域开展活动,取得全球效果。)签订的《中国/全球环境基金干旱生态系统土地退化防治伙伴关系》(PRC-GEF Partnership on Land Degradation in Dryland Ecosystems)文件,是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第十二个业务领域项目(GEF业务规划12即PRC-GEF—OP12)。该项目(PRC-GEF—OP12)的中心和重点是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旨在采用综合生态管理手段解决土地退化问题,所以该项目又称综合生态系统管理项目。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该项目的实施,成立了由财政部牵头、以国家11个部门(包括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林业局、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和中国科学院)为成员单位的项目指导委员会、项目协调办公室和项目执行办公室。该项目指导委员会、项目协调办公室和项目执行办公室与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内蒙、陕西等省(区)的政府达成承诺,要致力于提高项目省(区)的法规政策体系在防治土地退化方面的能力。这项法律改革作为中国可持续环境与自然资源法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采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和方法。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推进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特别是采取协调的、科学的、参与式的、适应性的管理方法来管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并使其法治化、制度化,以达到有
效防治土地退化的目标。该项目的实施标志着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已经在中国拉开序幕。2002年3月28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发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十五”计划》,已经将“生态系统方式的管理思想”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该计划在“指导原则”中强调“生态系统方式的管理思想。要树立大系统、大环境的观念,在搞好单要素保护的同时,强化区域 、流域多要素、多系统的综合管理和生态结构与功能的维护”。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首次指出:“按照区域生态系统管理方式,逐步理顺部门职责分工,增强环境监管的协调性、整体性。”这说明中国政府开始重视、提倡和推动生态系统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中共《十七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更将生态系统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提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当前,我国生态安全形势十分严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发展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这种形势将我国环境保护推进到一个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关键阶段,即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的新阶段。中国生态问题的整体性、复杂性和科学不确定性以及实现历史性转变的新要求,迫切需要生态系统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这样的新思想、新模式。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既是一种新的理念、原则,又是一种新的管理策略、方式和方法,是运用多学科知识、多种调整机制的综合方法框架。它具有综合性、可持续性、科学性、和谐性、灵活性的特点。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强调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主张生态保护应以维护生态系统结构的合理性、功能的良好性和生态过程的完整性为目标,对生态系统的诸要素采用系统的观点、进行统筹管理,从单要素管理向多要素综合管理转变,从行政区域向流域的系统管理转变,从对自然生态的统治和“善政”向“治理”和“良治”转变;要实现对生命系统与非生命系统的统一管理,生态监测与科研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将人类活动纳入生态系统的协调管理,综合管理土地、水、大气和生物资源,公平促进其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在环境监督管理体制、区域流域环境管理、环境友好社会和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方面,以生态系统方法为指导思想,采取协调的、科学的、参与式的、适用性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公平衡量、协调和分配各种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理顺区域内的环境管理体制,科学配置各政府管理部门的职责,可以调动各利益主体和广大公众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和促进环境管理机构职能和环境监管的综合性、协调性和整体性。生态系统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性质和特点表明,经济人、社会人和主体人的法律人模式,不能适应和满足生态系统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需要。例如,200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第V/6号决定即“生态系统方式”决定(COP 5 in Nairobi, Kenya; May 2000/Decision V/6),提出了有关生态系统办法的5项导则和12项原则即COP-5原则,其中原则一强调:“人类社会中不同群体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种类和方式多种多样”,“社会各有关部门的利益需要得到平等对待”,“同时也要确保子孙后代以及自然界的需要都得到充分代表”,“对于那些不能直接代表自己利益的利益相关者(比如子孙后代和自然界),必须确保它们由他人充分代表”。显然,经济人、社会人和主体人无法确保自然界的需要得到充分代表,对于不能直接代表自己利益的自然界无法确保它们由他人充分代表。只有生态人才能适应和满足生态系统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上述需要,才能关心作为生态共同体的自然界的需要得到充分代表,才能主动代表不能直接代表自己利益的自然界,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才能推动生态系统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发展。
(四)确立生态人的法律人模式,有利于促进当代法律和法学的进步和变革
第一,法律和法学在历史上的几次重大变革,主要是由法律主体的变革和法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引起的。确立生态人的法律人模式不仅涉及法律主体的变革,而且同时涉及法学研究范式的变革。生态人的法律人模式的确立是对主体人的法律人模式和“主、客二分法”的法学研究范式的反思和挑战。因此,确立生态人的法律人模式,对于促进当代法律的变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北京大学周旺生教授指出,从1960年代开始,在欧洲、美国、日本逐渐出现对生态人及其法律调整等问题加以研究的情形,并且这一情形随后在更大的范围逐渐展开和发展,进而直接影响各有关国家的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国家建设,法律上也因之出现了注重对生态人予以调整的新气象。(注:北京大学周旺生教授在2005年5月18日晚在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演讲《中国法理学的若干迷点》,引自中国法理网http://www.jus.cn/ShowArticle.asp?ArticleID=664。)
第二,法律调整对象和范围的扩大是法律和法学进步和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确立生态人的法律人模式有助于解决法律调整对象拓展的问题,即将法律只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法学理论拓展到法律既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又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学理论。经济人、社会人和主体人的“法律人”模式是:每一个具体的人、个体的人都只是与其他人相联系的社会人,人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即人的社会性的统一。根据上述法律人模式,既难于从理论上推出法律能够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结论,又不利于在建设“五型社会“的实践中发挥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作用。生态人的法律人模式是:每一个具体的人、个体的人,既生活在人类社会之中,也生活在自然界中,既与其他人发生联系,也与自然(包括环境资源)发生联系,人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每一个人都不能摆脱的基本关系,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实现人(甚至人类生态系统)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基础和基本保障。由此“生态人”的模式不仅可以从理论上推导出“法律既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又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结论,也有利于在建设“五型社会”的实践中发展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作用。法律是调整人的行为关系的规范,所谓行为关系即由人的行为所产生、形成的关系。人的行为可以分为人对人的行为和人对自然的行为,人对人的行为形成人与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的行为形成人与自然的关系;法律既可以规定人对人的行为,也可以规定人对自然的行为,因而法律既能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也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主要通过其行为影响、作用(包括建立、改变和改进)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法律是最有效力、效益和权威的行为规范,法律通过规制(规范和控制)具体个人的行为,能够和可以调整好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根据“生态人”的模式可以逻辑地推导出“法律既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又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结论,法律的基本作用就是与时俱进的调整好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
第三,公民环境权是环境资源法和环境诉讼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核心问题,而确立生态人的模式可以为明确公民环境权的性质和内容,为公民环境权的合法化、可实施化提供理论根据。一般认为,公民环境权是指公民有享用清洁适宜的环境的权利。由于环境的共享性、整体性和流动性特点,人们对环境的享用具有非独占性、非排他性、非占有性等特点,人与其环境形成人类生态系统,人与其环境的关系是一种生态关系而不是财产关系,这些特点使得公民环境权很难为传统私法所接受、很难利用传统的民法资源、很难受到民法的有效保护,或者说在公民环境权受到侵犯时没有可诉性。根据经济人、社会人和主体人的法律人模式,这些法律人只强调本体利益和人的社会性及人与人的关系,所以这些法律人的人格权都很难包括环境权的内容,即如果沿用上述法律人的模式和理论,将公民或自然人的环境权纳入上述法律人的人身权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但是,如果采用生态人的模式,将公民或自然人的环境权纳入生态人的人身权则是顺理成章的。根据生态人在人类生态系统中的地位,生态人既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人与人的联系,也强调人的自然性及人与自然的联系,自然可以被视为人身的延长或相当于人的手或脚,所以生态人的人格利益除了包括与其不能分离的生态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肖像、姓名、隐私等人格利益,还应该包括生态人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或生态系统,侵犯生态人的人格权除了对人身(包括身体的和心理的损害)的直接损害外,还包括对人的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直接损害,也就是说公民环境权可以视为生态人的人格权利。正如马克思明确指出的那样:“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14]
将自然界作为人的身体,意味着将自然作为生态人的人格利益。另外,人生活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应当享有适宜的生存环境,体现出其作为主体的尊严,而生活在被污染的、有害身心健康的、不具有美学价值的环境中的人,则不能被认为是有尊严的。基于这种生态人模式,在新一轮的《民法典》制定浪潮中,《乌克兰民法典》、《越南民法典》等法律中已经将自然人的环境利益作为人格利益予以保护,大陆法系国家的日本也倾向将公民环境权视为人格权,即认为:人的生存环境遭受破坏直接损害了人的环境权益,是对人(生态人)格权的侵害;环境权是生态人所固有的,为维护主体完整人格所必备的权利;在人与人结成的社会关系中,人享有自身的生存环境不被他人污染、破坏的权利;在人与自然结成生态关系中,人享有依靠其生态系统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污染和破坏同时损害人的社会地位和自然地位,没有安全、平衡、健康和适宜生活的环境,不仅那些基本人权,如公平、自由、幸福、生命及财产权统统无法实现,而且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可能受到威胁。在生态人看来,对人格利益进行现代扩展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环境问题发展到今天的迫切要求。只有在重视环境权的保护的条件下,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人才能真正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因此,确认生态人的法律人模式,对于解决公民环境权问题、推动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上)[M]第46卷(上),26
[2]李秀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83~84
[3]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6∽47
[4]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9
[5]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
[6]艾温•辛格我们的迷惘[M]郜元宝,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08
[7]蓝德曼哲学人类学[M]彭富春,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55
[8]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M]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11
[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2007-10-15(2))
[10]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讲话[N]人民日报,2004-09-16(2)
[11]郄建荣记者调查:环保部门立法多为何管用的不多[N]法制日报,2007-07-26
[12]登特列夫自然法[M]李日章,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1
[13]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154
[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G]//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5
The Ess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logical Man
CAI Shou瞦iu, WU Xian瞛ing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man means a man in the ecological system, who is an ordinary man, embodying an integration of social and natural elements of man. In the human ecological system ecological man may be either an actor or a recipient. A national ecological man seeks for harmonious coexistence with other men and with the nature. The model to ascertain ecological man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paradigm with subject and object integrated” and the methodology with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combined. The ascertainment of the model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notion of ecological man may supply a theory to justify the environmental right enjoyed by civilians, and lay a jurisprudence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the “five瞭yped society.” It conduces to combine ecological ethics with environmental law, increase the legitimacy and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 law, introduce ecological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management methods and encourage “ecologic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 law. Further, it will enlarge the regulation scope of the law and urge the advance and reform of modern law and jurisprudence.
Key Words:
ecological man; lawyer; subject; environmental resource law
本文责任编辑:曹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