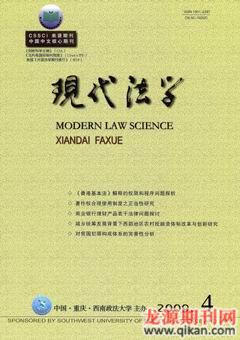身份犯的处罚根据论
摘 要:身份犯的处罚根据问题是身份犯理论研究的基础性范畴,它直接决定了身份犯具体问题的展开。发端于大陆法系刑法中的“义务违反说”、“法益侵害说”以及建立在二者基础之上的“综合说”都不能圆满地说明身份犯的处罚根据;我国学者关于此问题的个别看法也不无纰漏。以“身份法益侵害说”作为身份犯的处罚根据,则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关键词: 身份犯;处罚根据;身份法益
中图分类号:DF6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09.04.12
《刑法》分则缘何将有些犯罪主体限定在只能是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一部分人;又缘何在有特定身份者与无特定身份者都可以实施某一犯罪行为时只对有特定身份者进行加重或减轻处罚,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便是对身份犯的处罚根据之探究。有学者将之称为身份犯的本质或者规范本质[1]。
关于这一问题,在刑法理论较为发达且身份犯理论研究较为深入的大陆法系刑法学中研讨得较多且观点对立鲜明;而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则较少论述,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学者在研究所谓身份犯的问题时要么仅在犯罪构成主体要件部分作简要介绍,要么仅在共同犯罪部分稍带论及“身份与共同犯罪”问题,而并未将身份犯作为一个体系自足的、具有相对独立存在价值的理论范畴进行研究。这种理论研究现状的直接反映便是对身份犯处罚根据的不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身份犯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这从较早的有关身份犯的相关论述即可见一斑。好在近几年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对身份犯理论作了专门研究并提出了关于身份犯本质的相关看法,但是这种探讨还稍显粗浅。笔者将一一作出评介。
一、“义务违反说”及其检讨
该学说来源于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有个别国内学者坚持这一观点,其主要从违反义务的角度来解读身份犯的处罚根据。
首先,德国学者纳格勒(Nagler)、罗克辛(Roxin)等都是该说的坚决捍卫者[2]。
纳格勒试图以规范论为基础来探求违反限制性规范的身份犯之本质。在他看来,法秩序的本质是使个别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使个人的意思服从全体意思;所以,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被法纳入其调整范围,成为法的主体或客体,只有法要求他服从法,那么这个人才能违反法。在法的这一命题中,“被法要求服从的人”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认为,“被法要求服从的人”的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纯粹的实定法上的问题。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即在各个法律规范中,规定义务的法律命题是面向所有的国民呢?还是仅仅面向国民中的一部分?纳格勒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慎重的法律解释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在那个时代,对于如何限制课以义务的领域,存在着两种观点:第一,课以义务的领域应限于法规范所保护的法益可能由国民中的特别的集团的命令实现保护的场合;第二,课以义务的领域应限于法秩序因只对一定的人的集团的命令达到法益保护的场合。但纳格勒又认为,在第一种场合中,缺少一种契机,即不能达到保护法益的人,就不能直接赋予一定的义务;而在第二种场合,因为主张只有在法所要求的一定的人的集团服从的命题中才可以课以义务,所以也就放弃了原本对国民全体的命令[3]。
与此相应,德国学者罗克辛更直接地主张创设一种“义务犯”概念,以之取代“身份犯”。义务犯的主体是负有义务的“特别义务者”。只有该“特别义务者”才能够实施违反其所负特别义务的行为,其他一般人并无该义务可以违反,因而不能单独构成该义务犯的主体。
其次,日本也有部分学者持这种主张。有学者认为,在社会、法律等关于人的关系中对于满足身份犯的原因,要从具有承担特定义务的地位或资格的人犯罪这种角度来把握。即只有在有一定的身份可以构成纯正身份犯的情况下,违反了其身份所承担的特别义务,才能成为使犯罪成立的契机。不纯正身份犯是具有一定身份的人犯罪,因为违反比别人承担的更高一级的义务,而被加重刑罚的情况[4]。野村稔教授认为:“所谓身份犯,是指只有具有某种特定的身份才能构成犯罪,或者对于其刑罚予以加重或减轻的场合。这是因为由于一定的身份而负有特别的义务。”[5]
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学者认为纯正身份犯之本质系以具有一定身份者因其身份而负担特定义务,如公务员等,即以其在社会上或法律上因具有人的关系,取得其地位或资格,而负担特定义务[6]。
祖国大陆学者通常是从权利与义务的不可分性来论述主体的特殊身份的。一般这样表述:为什么法律要把特殊身份规定为某些犯罪的主体要件?因为刑法所要求的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莫不与法律上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密相关联。这些特定的身份赋予了有此身份者特定的职责即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的正确行使和这些义务的忠实履行,是维护统治阶级所要求的正常的社会关系和法律秩序所必需的。如果具有特定身份者不正确执行其身份所赋予的职责,而实施严重滥用其权利或者违背、不履行其义务的行为,则这种行为就严重破坏了统治阶级以刑法予以保护的重要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就具有了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危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法律秩序。而主体特定身份为什么能影响刑罚的轻重呢?因为刑事责任程度是立法者规定刑罚轻重的依据,而特定身份与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相关联[7]。
总的说来,从义务违反的角度来把握身份犯的处罚根据在德国刑法理论中似乎更具市场而且理由也较为充分。相应地,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主张及理由几乎与德国学者同出一辙,并无新意。而祖国学大陆者的相关论述表面上与大陆法系刑法学者主张相近,实则相差甚远。(注:传统刑法理论关于身份犯的义务违反性的主张似乎仅仅意在对身份的特征作出一种说明,其并不是在身份犯处罚根据(本质)的意义上使用,其表现之一便是在传统观点中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强奸罪的身份犯属性,这与其所言的义务违反性立场不相匹配。因为作为强奸罪特殊构成主体的男子无论如何不能说其具备何种义务,且因为其违反了何种义务而对之进行处罚——这也是大陆法系刑法学者主张将强奸罪排除在身份犯罪范围之外的原因所在。)
应当说,从义务违反的角度来寻求身份犯的处罚根据对于部分身份犯罪来说或许成立,但是并无普适效果。因为就整个《刑法》分则规范所规定的犯罪而言,大体可以分成两大阵营:大多数犯罪对主体构成并无特殊要求,只要主体达到相应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即可构成该罪;也有部分犯罪的成立或对之进行处罚以特定身份为必要。后一部分犯罪即为通常所研究的身份犯问题,之所以将这些犯罪统一起来进行一体研究无非是因为它们都具备“身份”这一共有特征。而“义务违反说”论者又试图将身份犯中的一部分犯罪再划分出来并认为仅有这些犯罪才是身份犯罪,将余下的那些其存在也与身份须臾不可分离的犯罪置入一般犯罪的阵营(主要是将一些具有自然身份的主体因无义务违反性的自然身份犯排除在了身份犯的范围之外)。这种研究方法不无疑问,因为就类型划分的近似性原则而言,毕竟论者所说的义务犯与被其排除在身份犯范围之外的自然身份犯都非一般人所能构成,因而更具有将其划分为统一类型进行研究的根据。
另外,对身份犯处罚根据的研究只是为了寻求作为整个身份犯理论支撑根基的原点,进而身份犯的所有相关问题都是以该原点出发并建立在此之上的。如此一来,作为身份犯处罚根据的探讨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着论者关于身份犯的其他理论问题之探讨和结论。最明显的例证便是有关身份犯的共同犯罪问题:根据纳格勒对真正身份犯的这种理解(义务违反性的主张——笔者注),无身份者不但不能成立共同正犯,而且也不能成立狭义的共犯(教唆犯和帮助犯);但是,纳格勒却认为真正身份犯情况下无身份者可以成立狭义的共犯。其论证如下:诚然,身份犯中的法益侵害只有对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才有可能;但是,无身份者通过与有身份者之有效侵害行为的结合,就消除了其在身份方面的障碍,从而使得其对真正身份犯之保护法益的侵害成为可能。从法益保护的观点来看,应当认为法秩序至少也第二次地禁止无身份者的加功行为。换言之,在真正身份犯中,无身份者承担的是“第二次的服从义务”。一方面主张义务犯论,另一方面则肯定所谓“第二次的服从义务”,这表明纳格勒的理论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正因为如此,纳格勒的义务犯论受到了包括迈耶(Mayer)在内的德国学者的批判[8]。可见,如果将身份犯的义务违反性贯彻到底,则无身份者根本无义务可以违反,从而导致无身份者无论如何都不能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犯罪,这便产生处罚上的漏洞和不合理性。纳格勒看到了这一弊端并试图加以解决,不得已而借用如何才能使无身份者“对真正身份犯之保护法益的侵害成为可能”这一法益侵害的概念来弥补漏洞和不合理现象,但这又违背了其义务违反性的立场。还有学者(如庄子邦雄、平野龙一)从违法性的实质的角度进行批判,该见解认为义务违反是违法性的实质,并且使一方面强调人的行为无价值,另一方面轻视结果无价值的见解成为前提,是不妥当的[9]。应当说这一批判也相当有力。
二、“法益侵害说”及其反思
很多学者试图从另一个进路对身份犯的处罚根据进行探讨,即身份犯所侵害的法益较之一般犯罪有所不同,此即身份犯之存在理由。具体而言,持此观点的学者又有不同主张:第一种主张可以称为“统一说”,也就是在探讨身份犯的处罚根据时并不区分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而是笼统的认为身份犯的处罚根据就是对特定法益之侵害。在纳格勒、罗克辛等学者试图从“对特别义务的侵害”方面来探求身份犯的实质的时候,另外一些学者却试图从另一方面来“捕捉”,那就是把身份犯和法益侵害联系到一起[2]93。这种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首推奥本海姆(Oppenheim),他曾经对典型的身份犯——公务员的犯罪加以详细、深入地探讨和研究,试图从保护对象那里寻求公务员犯罪的特征,这就是所谓的“特别保护对象理论”。奥本海姆认为,公务员犯罪的本质在于:公务员犯罪存在着公务员法益被侵害或者使之处于危险状态的切入点。公务员犯罪的法益侵害或者危险化状态,只能由公务的所有者即公务员进行。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担任公务,才能对这个公务施加影响。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教授也认为:法益侵害(与危险)是违法性的实质,特别是真正不作为犯,如果不是具有身份者,事实上也许不可能侵害法益,并认为这能给犯罪的成立以根据[9]149。
相应的,第二种主张就是“区别说”,该说尽管也是在法益侵害的范围内探寻身份犯的处罚根据,但它认为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应当区别对待。该说认为,关于真正身份犯,应当根据身份犯中的保护法益的观点来解决。真正身份犯,因为其身份,而且因为与法益的主体或者行为客体的关系,所以关于其行为的特别法益也是被保护的,仅有身份者由于其实行行为,侵害其特别的法益或者使其危险化是可能的。例如,《刑法》在关于泄漏秘密罪的规定中,认为仅有非身份者没有可能侵害他人的秘密的保护法益,因为对行为者要求一定的身份、具有那样的“地位、资格”,特别是也保护不泄漏他人的秘密的这种信赖。这样的信赖的法益,仅仅对有身份者可能保护。受贿罪中职务的公正及社会对它的信赖是保护法益,这种“信赖”仅仅是在与行为主体的地位或资格的关系中才可能受到保护,共犯者只有通过正犯者才可能侵害这样的法益。与此相反,在不真正身份犯中,对身份者比一般人较强地期待其避免犯罪。业务侵占罪中的“业务者”的身份,对身份者是特别强地期待其不侵害所占有的他人之物的。从而,对《日本刑法》第65条第2款的不真正身份犯的共犯,因为仅仅有身份的正犯才受强的期待,所以无身份者只能科处通常的刑罚[9]150。
笔者认为,尽管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都统一于“身份”这一特征之下,但是由于他们构成上的差异——一者身份的有无决定犯罪的成立与否;一者身份的存在不决定犯罪的成立与否但影响刑罚的轻重。鉴于这种构造上的差异,将二者分别予以考察的思路是可取的,当然这种分开考察并不能走得太远,否则将两个实质上迥异的概念统一在一个理论中进行研究的价值就值得怀疑了。因此,前述第一种观点表面上是对身份犯的处罚根据的判断,实质上仅仅论及的是纯正身份犯问题;而区别说的论点则是可取的,它既看到了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这样两种“身份犯”的共通性,又辨别了二者的细微差别。
三、“综合说”及其不足
所谓“综合说”,无非是将前述两种观点一同作为考察身份犯处罚根据的内容。一般是将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区别对待,进而得出不同种类身份犯的处罚根据是不同的结论。日本学者大塚仁在论述犯罪的本质时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论述:“犯罪,首先可以解释为把法益的侵害作为各个核心而构成。可是,根据刑罚法规,也不是没有作为义务的违反而把握的一面,例如,被侵害的法益尽管是同一的,在不真正身份犯中,身份者的行为比非身份者的行为处罚要重(例如,保护责任者的遗弃罪,《日本刑法》第218条的“场合”等),离开身份者的义务违反这一点,我认为就难以彻底理解;所以犯罪的本质,一方面基本上是对各类法益的侵害,同时,在一定范围内,一定义务的违反可以作为本源。”[10]国内也有部分学者与大塚教授的观点如出一辙,认为在离开特定的身份后刑法保护的法益就不可理解时,主体具备某种身份就意味着存在刑法保护的法益。这种身份是构成要件身份。……反之,在不具备该身份的人实施同样行为也构成犯罪、具备该身份就加重或减轻处罚的情况下,主体的身份意味着负有维护特定利益的义务或享受特定利益的权利,这种身份就是量刑身份[11]。
这种观点注意到了作为身份犯理论范畴之内的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二者构造上的差异,这一点是可取的。但是如前所述,它似乎将这种差异过分渲染而使得在实质上或处罚根据上二者几无任何共通之处,这样如果仅因为二者具备“身份”这一形式上的特征就将毫无关系的两个事物统一(实质上是机械地组合)到一个理论内进行研究的做法,其研究价值不无疑问。
四、国内学者的新锐见解及其剖析
正如前文所述,国内关于身份犯的传统观点几乎并未探及身份犯的处罚根据这样的实质性问题。直到最近几年有学者相继对身份犯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才将这一问题提上讨论日程。尽管学者的观点还存在可商榷之处,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体现了身份犯理论研究的日益深入和不断成熟。
有学者将身份犯的实质理解为三重法益论,认为身份犯的本质在于特定的义务主体侵害了法律所保护的特定的法益,身份犯的主体在违背自己特定义务侵害刑法所保护的特定法益的同时,也侵害了刑法所普遍保护的普通法益。在此,论者首先强调了主体的特定性,即身份犯的主体并非仅仅是普通公民,而是负有一定义务的特定的人;其次,强调了犯罪行为所侵害的法益的特定性,即这种法益必须是为法律所保护的特定的法益,它与犯罪主体的特定义务密切相关;再次,在强调身份犯侵害特定法益的同时,也强调身份犯所同时侵害的刑法所普遍保护的普通法益[2]98。
表面上看来,该种“三重法益”论较为全面,但它实质上不无问题。首先,论者所强调的前两重“法益”实际上是国外综合说的翻版,其不足之处已如前文所述,此处不赘述;其次,论者为了能够说明非身份者也能构成身份犯的共同犯罪,得出身份犯罪侵害法益的双重性质——既侵害了某种特殊法益又侵害了刑法所普遍保护的普通法益。笔者认为,该论者试图找出非身份者可以构成身份犯罪共犯的理由,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否则就会产生处罚上的漏洞。但是,他为此得出身份犯在侵犯特殊法益的同时又侵犯了普通法益的说法不无疑问。论者的大致思路是:特殊主体首先应该满足一般主体的条件,即特殊主体首先应该最起码是一般的人,只不过在一般的人的基础上,因为具备了刑法所规定的一定的条件而成为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即特殊主体。另外,身份犯所侵害的法益首先应该最起码是刑法所普遍保护的法益,应该满足普通法益的条件,只不过在普通法益的基础上,由于法律的规定与保护,因而成了特别法益[2]100。应当说这种思路在形式逻辑上大致是成立的,但也仅此而已,并无任何创意。因为作为身份犯主体要件之特殊主体的构成条件而言,固然需要首先具备一般主体所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还应当具备某些特殊身份要件。但是,从刑法规范的角度言之,我们在考察身份犯罪时应当评价的是已经具备了“一般主体要件+特殊身份要件”的特殊主体,并不需要再去考虑包含于其中的一般主体要件。例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窃取公共财物的应当构成贪污罪,但是我们并无必要认为行为人首先构成盗窃罪(一般主体实施的),只是由于主体具有特殊身份才构成贪污罪;而按照对于特殊主体的分析思路所得出的身份犯罪侵害法益的双重性质的结论也不可取。对身份犯罪而言,其所侵犯的是与主体特殊身份相关联的特殊法益,其与身份犯罪之成立并生。例如,受贿罪所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该特殊法益是身份犯罪成立的基础条件之一,那么作为受贿罪的身份犯同时侵犯的普通法益又是什么呢?对此,我们无从知晓。或许论者的初衷并非是要将身份犯所同时侵犯的“普通法益”实在化,其所要表达的在于,作为特殊法益也好、一般犯所侵害的其他一般法益也好,都统一在“法益”这一概念之下,这里所说的身份犯同时侵犯的普通法益仅指这一在更为抽象层次上的“法益”。但是,笔者认为,这样抽象性更高的“法益”概念与身份犯侵犯的特殊法益不应当在同一层次考虑——因为这样一来,是不是对于一般犯罪(例如盗窃罪)而言也侵犯了双重法益呢?因为盗窃罪侵犯的是他人公私财物所有权法益(一定意义上是不是也可以称之为“特殊”法益呢?因为该法益是相对于该罪名而“特殊”化的),同时也侵犯了作为该“特殊”法益上位概念的“普通法益”。这显然应当是论者所不赞成的。尤其值得说明的是:尽管在考察身份犯的处罚根据时不认为身份犯既侵犯了某种特殊法益也侵犯了普通法益,但是,这种理解在解决无身份者可以构成身份犯的共同犯罪问题上却并无障碍,具体理由参见后文论述。
也有学者从身份在对犯罪构成之各个构成要件的作用体现来论述身份犯的本质[1]33-41。论者认为,身份犯的本质只能从身份本身去找。身份犯作为以行为人的特定身份为标准而作的一种分类,其犯罪的本质以及犯罪构成的各个方面都有身份的烙印。也就是说,身份的触角已经伸进了身份犯构成的各个要件中,决定和影响着其犯罪构成的各个方面,这是刑法规定身份犯的原因之所在。具体而言,身份对身份犯之犯罪构成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犯罪主体方面来看,身份是身份犯之主体的构成要件之一;从犯罪客体方面来看,行为人的特定身份往往决定着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犯罪客体的性质;从犯罪的主观方面来看,身份往往决定着罪过的有无及其内容;从客观方面来看,身份决定着犯罪行为的性质及危害程度。
该种观点的思维进路似乎更为新颖,它不再纠缠于大陆法系学者提出的“义务违反”抑或“法益侵害”问题,而是独辟蹊径地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进行阐述。但是,究其实质,这种观点所要阐明的完全有别于传统理论所研究的身份犯的本质(处罚根据)问题,或者说二者并不是在同一层次上的探讨。身份犯的处罚根据意在说明《刑法》分则为何会划定部分犯罪的主体范围,仅将部分犯罪的主体局限于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份犯的本质意在研究“法律之前”的问题;而如论者所言,将身份犯的本质理解为对犯罪构成要件四个方面的作用,实则在探讨“法律之上”的问题,充其量可以称之为身份犯的“表现”或者说特征,而绝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欲探究的“本质”或者“处罚根据”问题。
五、“身份法益侵害说”之主张
通过对上述诸种学说的比较和分析,笔者认为,对身份犯处罚根据的探寻至少应当注意3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身份犯的处罚根据(本质)与我们通常所研究的犯罪的本质问题联系密切。犯罪的本质问题是刑法学中的基础性范畴,历来是刑法理论研究中的“必争之地”,因此关于该问题的学说和争论一直存在[12]。犯罪本质问题的研究无非就是为了解决刑法规范从形形色色的人的行为中挑选出一部分而将其规定为实定法上的犯罪之根据和理由,而这与我们研究身份犯的处罚根据在思路和目标上是基本一致的。对身份犯处罚根据的研究,其目的也是为了找寻将社会生活中的全部行为中筛选出部分而作为犯罪(包括只能由有身份者构成犯罪的纯正身份犯和身份只影响刑罚的不纯正身份犯)之根据和理由。基于此,我们绝不能孤立地研究身份犯的处罚根据问题,而应当结合犯罪本质问题进行研究。
其次,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的处罚根据应当有一个共通的联结点,只不过可以在此前提下有所区别。正如前文所言,在研究身份犯的处罚根据时,应当将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结合起来考察,这意味着不能以纯正身份犯的处罚根据取代身份犯的处罚根据问题;也意味着不能使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的处罚根据相去甚远,互无瓜葛。
再次,一般而言,对身份犯处罚根据的判断直接决定着身份犯相关问题的结论,尤其是身份犯的共同犯罪问题。身份犯的处罚根据是身份犯理论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也是身份犯理论的原点,身份犯之相关问题都建立在其上,对它的理解直接影响甚至决定身份犯相关问题的考量。因此,在考察身份犯之相关问题的时候,也应当顾及身份犯处罚根据的立场选择,而不能就事论事。
基于此,笔者主张“身份法益侵害”说。不过,由于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在构成上的不同,因此二者的处罚根据理应有所区别——纯正身份犯之特定身份决定身份法益的存在与否,而不纯正身份犯之特定身份决定着法益受到侵害的强度大小。具体而言:第一,纯正身份犯所要求的行为主体的特定身份与该罪所侵犯的特定法益相互印证并互相依存。行为主体所具有的特定身份与特殊法益(该特殊法益一般是通过身份犯的构成要件行为表现出来)相结合而决定了身份犯的存在。第二,就不纯正身份犯而言,其法益至少也应当与行为主体的特定身份相勾连,即行为主体特定身份的存在使得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受到侵害的可能性(或者说强度)有所增大或者减小。不纯正身份犯在犯罪构成上除了要求犯罪主体的特定身份之外,其他方面与该不纯正身份犯所对应之一般犯罪无异,①
因此,该特殊身份的具备并不决定(对应犯罪所侵害的)法益是否存在。但是,该不纯正身份犯在处罚上又有别于相对应的犯罪,这种处罚上的不同源自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受到侵害程度之差异,归根到底是受行为主体的特定身份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杜国强.身份犯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7-41.
[2] 杨辉忠.身份犯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88-92.
[3]大越义久.刑法解释之展开[M].东京:日本信山出版株式会社,1992:83.
[4]木村龟二.刑法学词典[M].顾肖荣,等,译.上海:上海翻译公司,1991:130-132.
[5]野村稔.刑法总论[M].全理其,何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94.
[6] 陈朴生,洪福增.刑法总则[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2:270.
[7] 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705-708;赵秉志.犯罪主体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291-293.
[8] 西田典之.新版共犯与身份[M].东京:成文堂,2003:138.
[9]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149.
[10] 大塚仁.注释刑法:第一编 总则[M].东京:青林书院,1978:122.
[11] 童伟华.犯罪构成原理 [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197.
[12] 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69-277;周光权.刑法学的向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92-218.
Justification for Punishment of Shenfenfan
WU Fei瞗ei
(National Prosecutors College of the PRC,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Justification for punishing of shenfenfan (offense the perpetrator of which is required to have a special statu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theories related to the offence and may immediately determine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arising out of or pertaining to the offense. Neither the failure瞭o瞗ulfill瞣bligation doctrine originating from the criminal law of continental law system nor the doctrine of violation of the interests and values protected by criminal law and the relevant comprehensive doctrine can adequately justify punishment of shenfenfan. Some arguments brought forward by Chinese scholars are also defective. In fact, punishment of shenfenfan should be justified based on the doctrine of violation of the interests and values related to status that are protected by criminal law.
Key Words:shenfenfan; justification for punishment; interests and values related to status that are protected by criminal law
本文责任编辑:梅传强
①
为了从构成要件的角度更好地认识不纯正身份犯同与其相对应的一般犯罪之间的关系,笔者提出了“主体的超过要素”这一概念。参见:吴飞飞.论纯正身份犯和不纯正身份犯的界分[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1):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