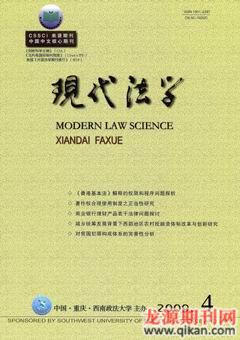网络表达的民主考量
陈伯礼 徐信贵
摘 要:网络表达具有增进民主和诱致秩序失范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它具有民主塑造功能,对催生公民意识、拓展民主广度、增进民主深度具有启迪意义;另一方面,网络表达在开启言论自由新时代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政府治理缺失的公共空间,产生了一些民主性隐忧,它可能引起公共秩序的紊乱、诱发多数暴政并导致政府在网络语境下的行为失态。为实现网络表达的当下治理进而推进有序民主,加强网民自律和完善网络法治成为必然选择。
关键词: 网络表达;自由;民主
中图分类号:DF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09.04.17
一、网络表达的民主塑造功能
(一)网络表达的个体平等性催生公民意识
1平等是民主的一个内在规定性
民主发源于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最初它是对政治体制的抽象性把握。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主的内涵不断丰富,它不再局限于表示一种政治体制,更多的则是指称制度之下的平等、自由的理念与现象,平等逐渐成为民主的一个内在规定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同类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中,大家就应享有平等的权利。”[1]孟德斯鸠认为:“在民主政治下,爱共和国就是爱民主政治;爱民主政治就是爱平等,在民主政治下,爱平等把人们的野心局限于一种愿望和一种快乐上。”[2] W•戈德温在其《有关政治正义和它对一般德行和幸福的影响之研究》中认为:民主是一种管理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认为是同样的人,谁也不比谁更多什么[3]。托克维尔认为:“所谓民主政治,我并不指涉共和国,而是一种社会状态,其中人人或多或少皆参与于公共事务。”[4]詹姆斯•博曼认为,“持续性不平等同民主协商具有不相容性,协商中的政治平等是判断民主合法性的批判性标准。”[5]
在传统东亚社会,平等价值并无植根之土壤,每当权利与权力两相冲突时,权利往往要败下阵来,握有权力者之力量总是异于常人,他们的话语分量也就大得多。许多例子表明,权力就意味着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的不平等,甚至于在理性与思想上也“应”高人一等,协商与对话只是空想,民主也就沦为空谈。在现代社会中,民主与平等是一对“孪生兄弟”。民主即是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参与国家治理,人们在公共事务的决策上需要进行协商与对话,而真正的协商与对话惟有在平等主体之间才能发生。民主作为一种共同参与机制意味着“特定参与者的物质利益、文化属性或伦理责任并不是预先的特权,决策结果依赖于参与者的行为而不是其以前的立场或其他特性。”(注:转引自杰克•耐特、詹姆斯•约翰森.协商民主要求怎样的政治平等[G]//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M].陈家刚,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212.)设若协商与对话的参与者中有人以先知自居或握有话语特权,则协商与对话不免落于形式,变成一种命令发布。
2网络表达使网民对“公民身份”产生心理认同
网络创设了一种政治影响力均等的可能性。“公共领域的由人为法律建立起来的平等性,只作为公民政治实践的形式上的条件,也就是在这法律规范底下,任何一位公民均有参与政治实践的平等。依阿伦特的解释,因为有这一形式上的平等,公民方有可能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其个体性。”[6]网络的开放性,以及BBS、论坛、博客等技术的成熟,让人们获得了一个个体平等的公共空间。网络就像一个过滤器,它滤掉了金钱、权力、容貌、年龄、种族等因素。在这个虚拟的纯净空间中,人与人不再有身份、地位的羁绊,不再有等级与贵贱之分,人们在网上发表某种意见时,他人对其见解的判断并不会受上述特征左右。人与人之间的表达机会趋向平等,大家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都有坚持和保留自己观点的权利。个体平等性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动力,使其真实想法的完全释放成为可能。公民通过网络收集、整理各种公共信息,并对政府决策、立法、司法、经济、道德、文化等公共事业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网络表达的匿名性使得任何一种言论成为强制干涉目标的可能性最小化了,它保证了网络表达者及言论能够得到平等地对待,人们的情感遵从对象由具体的人物转向道德和理性。网络表达者陈述的观点及其被认可并非依赖基于社会经济资源或政治权力的非对称性,而是依赖言论自身的合理性。网络表达并不排除自利性观点,然而,理性贯穿了网络表达的全过程,人们提出任何政策建议,为其辩护,都只能停靠在理性层面之上,这实际上就保证了任何人的合理声音能得到他人的倾听。当个体话语权和有效倾听得以融合之时,民主的进程无疑又更进了一步,因为主张现代民主,其实是预设了任何一种意见都应得到合理考虑的价值目标。
在这种个体平等的网络表达和有效倾听的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公民意识得到了培育和锻造。人们开始拥有一种成员归属感,对“公民”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司法等活动主体产生一种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逐渐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对国家命运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终极关怀,形成了一种缺失已久的公民意识。在现代社会,公民意识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石和本质内容。网络表达的个体平等性所催生的公民意识为民主制度的巩固提供了深层的精神与心理支撑,民主制度建构在广泛的社会基础之上,前景更为光明。
(二)网络表达拓展了民主广度
1民主的数量维度
民主广度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参与民主过程的主体数量。“民主的广度是数量问题,决定于受政策影响的社会成员中实际或可能参与决策的比率。用数字来衡量一种社会体制虽然不够精确,但在进行比较时,还是不失为一种有用的尺度。我们完全可以说,如其他情况相同,百分之九十的公民参加投票的选举所取得的结果比百分之六十的公民参加投票的选举要更为民主。”[7]“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广泛的政治参与是民主的本质要求,是现代政治系统良性运作的必要条件。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也是政治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8]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民主的养分来源,民主政治在公民的参与中获取持久的动力,从而有序运转起来。在民主社会中,公民的有效参与和持续热烈的讨论是决策民主性和合理性的实质保障,民主的价值在公民的政治参与中得以真正实现。可以说,没有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无所谓民主政治。
在东亚的传统社会中,大多数社会成员并非决策的参与者,对于民主没有太多的认同感。在东亚,“民主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产物,这种传统强调国家的养民与教民的作用,并以此作为公民行为的准则,而不是作为个人权利的保护者,对和谐和合作的强调优先于分歧与竞争。对秩序的维持和对等级结构的尊重被看作是核心的价值。”[9]由于受传统集权文化影响,今日东亚的一些
地区实行的是 “代议(表)制”的间接民主或行政集权民主制度。间接民主和行政集权民主的共同之处在于,决策参与者为社会全体之少数,实行的是“精英统治”,而大多数民众处于看客地位。(注:我们将此种称为“看客民主”,它与后面所述的“成员民主”(“权利民主”)相对应。)“看客民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民主真义相悖的,因为“看客民主”本身背离了民主政治的前提,即民众的广泛参与,社会成员若缺乏民主的实践和锻炼,其民主精神就得不到有效的培育,民主心理亦难以形成,民主政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民主机制的运行需要有一定的承载空间,公共空间的存在是扩大决策参与的必要条件。托克维尔认为,“民主政府的优点之一在于使政治权利的观念普及到了每个公民。”[10]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基础是社会自治,通过自治可以实现国家由权力私有型向社会公有型的转变。“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11]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机构运行的基础;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政治权利全民化始终停留于理论层面。社会规模的宏大性和社会成员的众多性带来的高昂民主成本,使许多国家对全民化的民主政治望而却步。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亦看到了民主的成本因素,他认为,“一般说来,民主政府就适宜于小国,贵族政府就适宜于中等国家,而君王政府则适宜于大国。”[12]大国、中等国家与小国相比,缺乏适合民主制度生存的公共空间,在此种情形下,倡导和推行直接民主所需要的高昂成本会使民主制度丧失其存在的内在根据。民主的生命力往往取决于良性互动的公共空间。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由于公共空间的缺失,民主制度的发展长期停留细枝末节的修补阶段,而未有大的变革。(注:直至20世纪90年代,为解决代议民主下许多人无法参与公共决策的问题,以约翰•罗尔斯、于根•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思想界开始倡导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论,实际上该理论的产生与网络的发展有密切关联。)
2网络空间和多元化的网络表达方式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
公共空间是介于国家与私人之间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领域,它是通向民主政治的必经之地。公共空间从早期的广场、剧院、音乐厅、茶馆、会场转到了网络论坛,网络技术的发展营造了政府和公众共同需要的、便捷、低成本、高效率的公共空间。这种新生成的公共空间打破了原有公共空间的组织界限和运作模式,给人们提供的一个便捷的自由表达意见的平台,开辟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新路径,人们由公共决策的看客转变为实际的参与者。这种新的民主操练空间使人们意识到自已对公共事务“居然”也有发言权,体认到一种成员归属,衍生出一种成员民主,抑或权利民主。
网络空间为公民的民主诉求提供了多元化的表达方式。电子邮件(E-mail)、电子公告板(BBS)、即时通讯工具(IM)、博客(BLOG)、播客(Podcast)、闪客(Flash)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主流方式。在“两会”期间,人们积极参加“网上议政”,利用电子邮件向全国人大或政协表达自己对一些公共议题的意见和建议,通过网络论坛了解国家的政治动向和公共议题,关注、参与论坛的讨论和调查。新华网去年“两会”期间做的“我有问题问总理”栏目得到了数千条回复,网民们对各种社会问题踊跃发表自己的看法。另外,许多网民也在自己的QQ工具、博客、播客中对自己关心的话题发表意见,并与其他网友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直接交流。丰富的网络表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们在以往政治生活中表达的缺憾,缓解了参与需求与传统民主制度构架之间的矛盾。网络中的表达和交流是自由的、自发的和松散的,“它的关键作用是形成公共舆论,并将其传达到制度性决策论坛如法庭和议会。”[13]网络成为民众表达见解和主张的主要阵地,公民借助网络表达利益、参与讨论从而影响政府决策。多元化和便捷化的网络表达为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可能,并有力地助推“草根”(注:草根(grass roots)一说,始于19世纪美国,彼时美国正浸于掏金狂潮,当时盛传,山脉土壤表层草根生长茂盛的地方,下面就蕴藏着黄金。后来“草根”一说引入社会学领域,“草根”就被赋予了“基层民众”的内涵。)民主的发展。
(三)网络表达增进了民主的深度
历史上曾经存在封建制度的历史意识在亚洲形成了一种与民主政治不太契合的心理沉积。东亚的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虽推翻了帝制,赋予国家各种形式的民主政体,但在民主的深层次上仍有不少缺憾。浸泡在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在政治生活上习惯于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缺少个体的自主、自我意识。政治生活对许多人来说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惟恐避之而不及,他们毕生的希望似乎就是能够永远被代表以免除他们政治思考的“痛苦”,这种希望之于现实生活就表现为强调对政治权威的绝对服从。民主社会理应是一种充满争论的、互动的社会,民主制度本身是一种竞争性表达的设计,而对权威的服从,意味着争论性与互动性的丧失,这虽不致民主制度的必然死亡,但至少将使民主在深度延展上处于休克状态。
1深度民主建构在信息公开之上
美国学者桑斯坦(注:此处的桑斯坦与本文参考文献[21]中的孙斯坦为同一人,为尊重译著原貌故在行文中按译者的翻译表述。)指出:“从民主的观点来看,有三个要点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去接触更多未经事先选择的题材、主题和立场,或有足够的接触,以产生一定程度的了解和好奇。二、共同经验的价值。三、去接触政策和原则的实质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各种立场。”[14]深度民主首先是建构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的,信息的不对称往往会产生权利落差。在现实生活中,信息占有的差别性往往成为权力不正当性的发生根据。“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15]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以其对公共事务的了解为前提。否则,人民将无法进行决策选择以及对政府实行有效监督。知情权之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知情权为人民自我治理之前提。在一个民主政府里,人民必须知悉政府的动态,如果人民连政治参与的基本信息都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则根本无从谈起。第二,知情权是监督公权力运作的良辅。自由主义的核心要义是公民要对公权力保持一种警惕性。社会治理需要公权力的运行,但这丝毫不表明人民就要臣服于公权力,因为任何拥有权力的人至少部分地怀有为他们自身利益而滥用权力的自然倾向。“美国学者艾莫生曾经尖锐地指出:政府所作的坏事……倘如事先让公众知道并交付讨论,它们大概不会发生,所以,我们要从一切事情都应该公开而不应该保密这一前提出发,然后才有必要产生某些例外。”[16]
现代网络传播技术解除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时空限制,穿过了原有的行政壁垒,引领人民进入自由和平等的网络王国。在这个王国之中,人们获取信息的机会在大体上是平等的。各种信息在网络上均留有痕迹,只要人们愿意就可搜寻获取。信息的自由获取让人们能够更多地、及时地了解经济和社会问题,使公民监督公权力行使与社会行为成为可能。网络中的信息流具有巨大的穿透力,任何打压报复均难以阻止网络信息的传播和公众舆论的形成,民众在网络王国中可以对各种事件和现象进行自由而真实地表达。网络传播媒介上存有许多公共议题栏目,网民参与议题基本上没有门槛限制,任何人均可对公共话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些信息呈现于在所有网民面前,供大家浏览。人们通过浏览网络信息了解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方面的最新信息,实现了经验和知识分享以及思维的开拓。网络信息与文化的动态传播性使其具有巨大的吐故纳新能力,从而促使网民在网络文化的争鸣性中重获了自主人格。网络表达的启发功能,是对民主深度挖掘的又一贡献。它以生动、直观的形式引导网民把提高科技水平同不断完善综合素质修养有机统一起来,使之在政治素养、民主意识和文化修养等方面达到一个较高的现代水准,进而有力地深化了民主。
2网络表达的互动性与监督性是深化民主的恒久力量
民主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与人民之间互动的流畅程度和民主的内在制约性。就民主的整合功能来说,集体行动者与个体行为者之间必须有一种沟通机制,公民与行政人员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互动是当代公共治理的基本标志。协商网络技术下信息传递的交互性使得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性大大提高,政府在网络发展的浪潮中也更新了自己的观念,改进了社会治理的方式。在最近几年里,各级政府都加快了政府门户网站的建设,(注: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通,中央政府网把互动交流作为4大基本功能区之一,在公开政府信息、提供公众服务的同时,互动性得到了更多体现;2005年浙江省天台县委、县政府建立了效能网,对老百姓提出的需求给予及时回应。)许多官员也转变了观念,以论坛、留言板、聊天室的方式与网民沟通,倾听网民建议。(注:2006年到2007年,江苏宿迁市80多名政府官员开通博客,倾听网民意见;2008年春节期间,广东省委书汪洋和省长黄华华发表了《致广东网民朋友的一封信》,表示愿意与网民就共同关心的话题“灌水”,对工作和决策中的不足之处,欢迎网民“拍砖”。)政府与网民之间的沟通、对话,改变了以往的相对封闭工作方式,公民与政府官员、选民与代表(议员)的直接对话变得简便易行,他们之间的互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间距被大大缩小了。依托网络这个公共平台,公众与政府之间可以实现良性互动,通过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意见交流或信息沟通,民众的意见得到了及时、充分地表达,政府也提高了对公众需求回应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这不仅使得政府的决策更符合民意和公共利益,提高了政府决策的可行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型的沟通方式形成了一种民主决策机制,保证了公众参与决策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制约性之于现代民主社会,往往表现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在民主社会中,民主与监督应该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可以说,监督是民主的延伸,是对民主制度的一种保护。“民主的成分越多,就意味着对权威的监督越多。”[17]长期以来的农耕文明塑造了传统政治社会封闭性,国家机关与社会民众之间缺少经常性的交流,重大国家信息坊间化,国家公务活动透明度低,社会成员参政议政的渠道不畅,政府活动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政府权力也就像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经常越过自己的权力范围,侵犯权利的领地。在当代社会,情势发生变更,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芸芸众生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使小小百姓也能形成巨大的舆论力量,监督政府的权力运作。网络信息传递的自由性带来了网络表达的繁荣,这既是公众参与的体现,更是一种监督力量。公民的意见经过网络的表达和整合功能,形成舆论并对政治决策过程产生影响。例如,在“华南虎”事件中,正是网民的“打虎运动”才使有关部门没有向错误的方向走得更远。网络表达具有强大的社会监督能力,它通过把政府置于大众目光之下,减少了国家侵犯公民权利的可能性,其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和监督功能推动着我国的宪政和民主进程。
二、网络表达的民主性隐忧
(一)网络表达诱致公共秩序紊乱
网络的去中心化和匿名制度,使人们获得了空前的言论自由。这一方面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可能使整个社会陷入紊乱与无序之中。网民在享受着网络表达自由的快感时,很容易忘记原初目的,淡化了自己责任意识。虚拟的空间对现实的解构,抹去了真实世界对伦理、道德、法律等一切社会文化的价值规范的界定,部分网民开始摆脱道德规范和法律观念的约束,将个人视为真理的惟一判断者。他们在网上放纵自己的言论与行为,对自己言行的后果则毫不顾忌。有的网民在网络上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例如网友“夏日追随”在《枣庄论坛》上发布谣言帖。(注:2005年11月,网民“夏日追随”在《枣庄论坛》上散布“有一伙犯罪分子,以专门挖肾卖钱的没有人性的手段,连续作了几起案件”的谣言帖,该帖在网络上迅速传开,并引起了社会恐慌,许多家长害怕自己的孩子出事,放弃工作,专门接送孩子上学。)有的网民无视他人的心里感受,在网络发表辱骂或诽谤他人言论。例如一名辽宁女孩因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玩不了游戏,竟对四川灾区人民发表长达了4分40秒的辱骂言论。有的网民则发布一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信息,破坏民族团结。还有的网民在网络上发布一些涉及他人隐私的信息或其它在道德上令人反感的内容。缺乏外在约束的网络表达导致一些网民的社会责任意识淡化和伦理道德失范,这种言论自由失去了其本身所蕴涵的民主价值,转化成了一种破坏性力量,冲击着整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就明智的、有益的讨论来说,某些秩序的规则是必需的。如果大家不接受探究和争论的合理程序,言论自由主失去了它的价值。” [18]和谐的社会秩序应当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追求的目标,它是任何个体利益可预期性的前提。因此,在倡导网络表达自由的同时,必须在个人自由与公共秩序之间寻找一个黄金分割点,以求得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保证网络表达的民主价值。
(二)网络表达的多数暴政倾向
民主就其内涵而言具有宽容性与妥协性,民主不仅意味着对“多数人的决定”的确认与保护,对于少数人与少数人的意见
的保护也是民主的必然要求。“在许多情况下,大众的共同意愿和一致意见是很难达成的,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持不同意见,若强制舆论一律,意志统一,对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就不会有宽容,而对少数人的宽容和保护恰恰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19]“多数与少数之间的自由讨论之所以对民主是必不可少的,就因为这是创造有利于多数和少数之间妥协气氛的一个途径;而妥协则是民主本性的组成部分。妥协的意思就是用这样一个规范来解决冲突,它既不完全符合一方的利益但也不完全违背另一方的利益。”[20]网络为普通公民开设了话语权,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这个公共空间发表自己意见,“孙志刚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厦门PX事件”等都充分显现了网络表达的宪政民主意蕴。然而网络言论有可能发生异化,小群体的意见常常走向极端化,使得网络表达呈现多数暴政倾向。“通常由于‘瀑布效应(cascade effect)(注:“瀑布效应”最初由英国学者R•亚当在观察尼斯湖瀑布后提出的。它是指当人们长时间注视向某一特定方向的运动之后,将产生特殊的运动后效的情形;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大多数投资者并非标准的金融投资者而是行为投资者,他们的行为不总是理性的,也并不总是风险回避的,因此金融市场中股价下跌会引发股市的新一轮下跌,这个过程多次重复,使得股价运行轨迹如同一条下泻的瀑布,这种现象被称为“瀑布效应”;本文中孙斯坦所指的“瀑布效应”与上述两种情形并不相同,它是指人们受周围人的影响后随波逐流的现象。)的作用——不管是由于信息的传播(无论是真是假),还是由于同一群体中其他人的压力——社会影响能够引导人们朝着特定的方向迅速发展。有时,瀑布效应具有很强的地方色彩,而且非常理性地引导某些特定群体的成员,使他们非常理性地相信或者去做其他群体中的成员觉得非常愚蠢或者更加糟糕的事情。”[21]在网络上,人们发表意见有时缺乏应有的理性,对许多不良社会现象声讨和遣责往往偏离理性的轨道,带有强烈的个人偏见。普通大众在特定的情况下通常会对这些错误的观点或看法产生认同感,形成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共鸣,这种共鸣往往会形成一种压力,迫使持不同意见者受制于这种非理性和情绪化的主流意见。“铜须门”、“辱师门”、“虐猫门”、“很黄很暴力”、“辽宁女事件”让人们不得不面对舆论强制和网络暴政这个沉重的课题。
民主以公共意见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然而民主内在驱动力是理性,多数人意见在形成过程中可能偏离理性与正义。“虐猫事件”发生后,网络舆论的集体讨伐,“铜须门”事件中网络舆论的一边倒的咒骂可以看出网络中的“正义”常常是以一种非正义的形式实现的。在“正义”的实现过程中,公民的权利遭受的无情的践踏,多数暴政的倾向显现无疑。在现代民主与法治社会,网络表达应多一些宽容,少一些强制。网络表达在实现言论自由的宪法价值之时,也应遵守法律的底线,不能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当一个社会视法律为无物时,暴政的噩梦也就为期不远了。网络上信息泛滥,真假难辨,缺乏自律的“口口相传”是滋生多数人暴政的温床。以简单武断的推理得出的结论在群体化的从众心里的推动下却成了所谓的“真理”。(注:学者周濂认为:就目前所前,广场政治的特性在网络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姿态和情绪永远都比理性和冷静要有魅力,网络表达已从“全民开讲”变成了“全民乱讲”,并很有可能到达“乱民全讲”境地。([2008-6-20]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0604/20/t20060420_6761288.shtml))任何人的言行必须与该“真理”保持一致,否则其他人就要群起而攻之。北京大学教授陈兴良对刘涌改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结果遭到网民的辱骂;央视的名嘴白岩因不赞成抵制家乐福,被网民称为“汉奸”、“卖国贼”;火炬手金晶只是说法国大部分民众是友好的,便被网民从“民族英雄”拖入“卖国贼”之列。当众口铄金抹杀百家争鸣时,“多数暴政”的乱象由生。“无视对多数权力加以限制,从长期来看,不仅会摧毁社会的繁荣及和平,而且还将摧毁民主本身。”[22] “现代自由民主的传统倾向于对多数人原则做出限制。例如,它不应被用来压制少数派,少数人的权利只应该在某个公认的标准内受到拒绝。如果少数人受到它的压制,那么多数人的意志就变成‘多数暴政,它是行政暴政的征兆。”[23]宪政和民主价值追求不仅仅意味着限制政府权力,也要规范民众权利行使,多数人的暴政并不比少数人的暴政正当多少,多数人的暴政破坏性更大,因为当多数人成为暴徒时,社会缺乏有效的对抗力量,一切只能听之任之。更为可怕的是,多数的暴政极易转化为少数人的专政。设若某一团体或个人掌握了所谓的主流话语权,形成了“权威意见”,网络民意就成为其推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工具。
(三)政府在网络民愤语境下的民主政治失态
网络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参政议政的公共空间,人们对于政府及其成员的行为可以自由评价,人们基于自身感受对政府的行为可能产生许多比较情绪化的言行。在网络民愤语境下,有的政府官员缺乏应有的淡定,对网络中涉及政府的情绪化言论产生一种敌对心理。他们往往以网络表达的非理性因素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有序发展为由对网络表达进行强力压制,有的地方甚至搞新时代的“文字狱”,最终诱发了一些不良公共事件。对网络世界中的言论,现代民主政府应秉持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正像政府不可以偏袒一种宗教信仰甚于其他宗教,在对其公民可能提倡的各种观点中,政府也必须持守中立。尽管政府对在公共空间中言论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可能施加‘内容中立的限制,但这些管制‘不可以受到对所要表达的观点的同情或敌视所影响。最高法院已经多次裁决,第一条修正案‘禁止政府对其公民强加一种官方的真理观或者偏爱的良善生活观,‘特别是,第一条修正案意味着政府没有权力因为信息、观念、主题或者内容而限制表达。”[24]
公民表达权是一项宪法性的权利,是现代民主的基本要素。网络民愤、民怨言论是一种典型的情绪化言论,情绪化的言论是基于现实状况的一种强烈的感情抒发,它虽然不必然代表理性,但具有内在的理性因素。“任何对情绪化反应的提及,都可以激起对煽动行为的担忧,但是情感本身应有其合理性,因为它常常源于信仰,比如,愤怒可能源于一个人遭受不公正待遇或者被冤枉的此类事情的信念。情感可以是道德判断的线索,从这一角度看,排除情绪化反应的任何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讨论规则都可能抑制/阻碍了阐述观点的特定方式,而且不可能保证观点的陈述力。”[25]公民对政府的情绪化言论往往是对政府工作的一种批评与建议,它通常源于客观现实,具有一定理性因子。在现实社会中,由民怨、民愤的监督力量引出的大案不少,例如上海首富周正毅案即导引于民愤。
现代民主政府的目的指向和平、安全与福利,其决策或行动的正当性基础即是公共意见,而公共意见的获取必须建立在认真听取任何一种意见基础之上。网络中的民愤言论即使具有非理性的因素,但是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意见,它是一种对政府及其成员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这种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无论其内容对错,政府不能剥夺这种意见的表达权,因为“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26]政府存在的目的决定其必须对网络民愤言论保有宽容的态度,即使民之所愤有所不当,政府也应采取疏导的政策,而不应对其进行压制。“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27]在任何社会,疏缓民愤、民怨的渠道是必不可少的。一味压制民众的言论自由,可能会在表面上形成了平静局面,然而“公共意见是决不会屈服于强制力的,”[28]民众转而将怨忿憋于心中,但久了终是会憋出毛病的,到一定的时候,就要形成猛烈的“井喷”。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如果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29]
当“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深入人心时,作为国家的主人的牢骚言论只要不损害公共秩序,就不应得到法律和社会的否定性评价。赞歌好听,牢骚逆耳。一个具有民主肚量的政府,不应该只允许人民对其赞美,而不允许人民发表任何反对意见或怨言。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社会的进步的推动者不是那些只会唱赞歌的顺民,而恰恰是敢于发脾气的民众。顺民具有很强的服从意识,他们所要做的是听从安排而不敢有所异议,这实际是对人类整体智慧的扼杀,是对主权在民理念的否定。那些对现实失望的民众,虽然他们的言论具有非理性因素,但他们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亦是现实之映射,在一定的价值预设下,透过这些现象服从性可以提纯出某些理性的成份,这恰是现代民主进程所需之现象因素。
三、民主政治下的网络表达的当下治理
绝对自由的人是疯子,绝对的民主是混乱。自由的舌头是现代民主的基本前提,然而舌头往往成为扼杀民主的工具。(注:荷兰哲学家斯宾诺沙曾说,“给我们太多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最难管制的东西,莫过于自己的舌头。”)当个体或某一团体的言论绝对化时,这种在言论主体眼中的所谓民主对于他人就意味着专政。进入网络社会后,民主政治获致发展之新契机,然而网络中的“羊群心理”由于催生、助长了网络暴力,使民主背离其原旨。透过网络暴力,不难发现人人平等的原则已被践踏,人与人之间建构在平等基础之上的道德义务和民主面相已荡然无存;因此,当下必须加强网络的道德自律和网络法治建设,以确保网络表达的民主价值和伦理意蕴。
(一)网络表达的内在限定性:网民自律
自由不是从来就有的,自律是享有自由的前提。在网络空间中,惟有伦理与道德倍受重视之时,网络表达的民主价值才能实现。“民主制下的公民必须不仅要积极地、非独断地参与对权威的批判,而且要通过慎议追求相互理解,而不是通过讨价还价或威胁,排他地追求个人利益。如果没有公民具备这些品德,自由主义就不能实现它的正义承诺,就的确可能会受制于非民主的和非自由主义的力量。”[30]重塑网络表达的伦理性与道德性关键在于自律。人是社会中之人,必须服膺于共同的行为准则,由这种行为准则衍生的义务首先是道德上的,然后才是法律上的。人们对一种社会义务的违反通常先是内心上的,然后表现于外在行为。外在的行为可以通过法律来约束,而内在心理则主要依靠个人自律。民主的原生力恰是民众的自觉意识,法律强制只是民众自觉意识的外在催化。民众之间的相互尊重,是实施民主政治的环境和必要风气,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与稳定来说,它是极为重要的。网民自律意味着网民之间存有一种民主制下的道德底线和人文主义的必要容忍,并且通过提供一种信任气氛和大众容忍的持久基础而使民主得以稳定;因此,网络表达所衍生的新型民主的发展关键在于倡导网民的个人自律。
自律即自己根据一定规范来约束自己。由于我们正处于网络时代的初期,网络社区中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网民对自己,网民与网民之间缺乏统一的、有效的道德评价标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物质受限于形态体积、精神亦有“约法三章”,网络也必须有道德公约。在“5.12”大地震后,全国网民倡议共同遵守《中国网民自律“十不”公约》,虽然该自律公约产生于特殊时期,但公约的产生显现了网民的自律意识和力量,昭示文明的、理性的、宽容的网络表达仍可期待。
另外,自律性的提高还需要适当的价值引导。自律是一种主观性的约束,人们在行为选择和道德判断时,极易受主观的价值标准支配。当前的网络社会的环境特殊性使得网民的主观价值标准模糊、道德失范、自律性弱化,因此,必须加强对网民的伦理道德教育,构建网络道德评价体系,提高网民的自律意识,使之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并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文明、理性、宽容的网络表达氛围。
(二)网络表达的外在限定性:网络法治
“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31]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或废除自由,而是保障自由和拓展民主,从而增进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自由设若不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不仅会增加民主机制的社会成本,而且易于走至民主的反向。诽谤个人、侵犯隐私行为、淫秽暴力文化不是网络表达的应有之义,而是网络技术带来的社会性的“负产品”。(注:负产品不同于副产品,本文使用“负产品”一词意图强调其负面作用。)但是如果网络个体的负民主行为得不到法律的应有规制,个体行为的危害结果就会转嫁于整个社会。网络暴力一旦泛滥,就会像洪水猛兽一样侵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正当秩序;因此,构建网络表达权利的法律边界实乃燃眉之事。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霍尔姆斯从言论的客观效果出发认为,“不论自由言论受到何等严格的保护,如果有人在剧场中诈称发生火灾造成巨大混乱,这种言论就不应受到保障。同样,发表具有暴力效果言论的人也不受保护。不论任何事件都应该考察言论是否在具有明确、即刻的危险中表达的或者其使用的语言具有这种性质。”[32]台湾学者刘清波先生认为:“言论自由应受到国家安全和社会公益所设之限制。”[33]张新宝教授则提出:“言论表达自由应受公权和私权两个方面的限制。公权的限制是指国家的限制,通常包括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国家保密法、新闻检查法律等的限制,而私权利限制主要是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限制。”[34]学者李忠认为:“言论自由具有两面性,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它既能消解社会的各种愤懑和不满,也能在特殊场合扰乱公共秩序,言论自由为恶的一面因现代通讯工具广泛的影响力而增强了限制的必要性。”[35]《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确规定表达自由为一种可扣减的权利。该《公约》第19条对“发表意见权利”作出了两项前提性规定:(1)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2)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第20条规定: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都应以法律加以禁止。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权利。”也就是说,网络表达权的行使不得损害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社会公益以及他人的合法权利。
上述应属网络表达的立法边界,然而在网络表达的司法边界的认定上却存在很大的困难。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标准不清。认定网络言论的有害性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而关于社会公益和公共秩序的概念界定上,学界争议较大。二是责任主体的不确定性。目前网络上实行的匿名制,因此,即使侵害行为发生,司法机关也不能确定侵权主体。另外,有害信息并非一目了然,转发者转发了此类信息之后的责任承担问题亦存有疑问。三是主体的责任能力的不确定性。在网络中,未成年人的数量不在少数,截止到2007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2.1亿人,其中未成年网民就有4 001万,未成人在网民的总数约占了20%,(注:数据来源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这样的比例在客观上使有关机关很难确定行为主体是否具有相应的责任能力。
针对上述难题,有学者认为通过加强网络监督立法方可解决。另有学者提出应加快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网络警察部队,(注:实际上在1999年安徽省就成立了我国的第一支网络警察部队,截止目前,我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建立了网络警察的专业队伍,网络警察制度虽运行多年,但并未能克服网络表达的弊端。)加强网络监管。还有学者认为应当实行网络实名制,以增强网民的责任意识。笔者认为,上述措施,对网络民主的有序化具有重要实际意义,然而这些措施亦可带来一些副作用。本文认为,要解决网络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应当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一是强化立法的精密性,为网络表达言论提供一个较为准确的定性标准,必要情况之下,可采用概括列举方式。以有害言论为例,首先对有害言论进行概括性的规定,然后通过列举有害言论的具体形态、形式使其范围具体化。二是当权利冲突标准不确定时,由法官裁量。在司法实践中,法律应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在综合考虑言论自由和其它利益的大小后,法官有权做出一个公正的选择。三是行业自治,责任自负。法律的内容总是落后于现实的,法律永远跟不上科技发展的脚步,对新科技带来的一些问题,法律总是缺少必要的规则内容。国家缺少治理新问题的法律规范,使国家的具体管理在逻辑上变得不可能。此时,有效的做法是倡导网络行为的自治,将网络行为中的风险性因素交给网络服务商。以诽谤言论为例,如果某网络服务商的网站上出现了诽谤言论,由于其未尽合理的管理义务,则须负相应的责任。
四、结语
网络技术的发展促使一种以网络为载体的自由表达模式得以形成,这种新型的表达模式对社会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据有关数据显示,有67.1%的人认为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官方了解民生、体察民意的重要途径,71.9%的人认为网络表达成了中国式民主的新通道。(注:数据来源于《中国青年报》社调研中心的调研统计,该中心曾通过益派市场咨询公司对2 874人进行了调查。)网络开辟了人们言论自由的新空间,网络表达成为民意表达的重要途径,通过网络表达人们实现着有效的政治参与,助推着中国的民主进程,因此必须要利用好、保护好网络表达。政府应该为网络表达提供制度性保障,加强网络法治建设,保障、引导和规范网络表达,保证网络表达的民主属性和法律维度,确保网络表达在民主法治轨道上运行。同时,开放的网络尤其需要克制、理性的表达,网民应提高自律意识,在行使网络表达权利时,遵从法律与道德的约束,确保网络成为一个实质意义上的民主、文明、自由的公共空间。当然,网络表达是民主的一个路径,在民主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形下,网络表达所衍生的网络民主并非是现代民主的替代品,而是推动民主制度变迁的“催化剂”,民主制度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386.
[2]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0.
[3]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M].黄华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9.
[4] 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107.
[5] 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M].黄相怀,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07.
[6] 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04.
[7] 卡尔•科恩.论民主[M].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3.
[8] 陶建钟.网络发展对政治参与的影响[J].社会科学,2002,(2):7.
[9] 萨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序11-12.
[10]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73.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82-383.
[12] 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83.
[13] Dryzek,John.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Beyond: Liberals, Critis, Contestation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128.
[14] 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黄维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18.
[15]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448.
[16] 唐禄盛,黄金华.知情权:人大代表行使监督权的前提[J].海南人大,2003,(11):35.
[17] 马克•E.沃伦.民主与信任[M].吴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
[18]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01.
[19] 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54.
[20] 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319-320.
[21] 凯斯•R.孙斯坦.设计民主:论宪法的作用[M].金朝武,刘会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7.
[22] 弗里德利希•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41.
[23] 迈克乐•罗斯金,等,著.政治科学(第6版)[M].林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71.
[24] 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M].曾纪茂,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84.
[25] 约翰•S.德雷泽克.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M].丁开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44-45.
[26] 约翰•密尔.论自由[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9-20.
[27] 国语.周语上.
[28] 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65.
[29] 萨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56.
[30] 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下)[M].刘莘,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528.
[31] 洛克.政府论(下)[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5.
[32] 刘迪.现代西方新闻法概述[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35.
[33] 刘清波.现代法学思潮[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163-164.
[34] 张新宝.名誉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92.
[35] 李忠.论言论自由的保护[J].法学论坛,2000,(2):19.
Democracy Issues Related to Network Expression
CHEN Bo-li, XU Xin-Gui
(School of law,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China)Abstract:
While improving democracy, network expression may have its adverse effect upon maintenance of social order. On the one hand, it may help people to breed a deeper consciousness of citizenship and develop a more acute sense of the scope and depth of democracy. On the other hand, while creating a new era of freedom of speech, it affords an ample space for the public over which the government cannot exercise complete control so as to have some democracy worries. It may disturb public order, induce the majority to exercise tyranny or cause the government to behave abnormally in the network context. To manage the network appropriately and establish an orderly democracy,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netizens” to be self瞕isciplined and rule of law of the network improved.
Key Words:network expression; freedom; democracy
本文责任编辑:张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