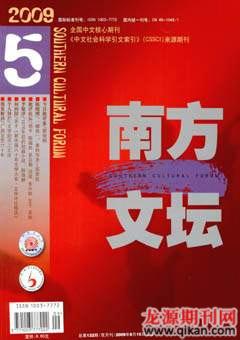吊诡的合谋:“美女作家”与大众文化
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内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社会形态出现明显的转型。它正从原来全盘政治化的专制形态逐步演变为经济优先、安定团结第一的商业化社会,一切向权看的革命时代被一切向钱看的小康时代所代替。同时也出现这样的新景象,即政治权力与知识精英与商业资本结成利益联盟,共同追名逐利,因此助长消费文化的发展而消解文化的精神内核。
我们无法回避这种政治背景以及与之合流的商业化消费主义价值观,由此形成的消费文化在世纪之交成为中国内地蓬勃发展的社会实践行为这样的事实,而且它实际上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暗许、鼓励和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政治革命的狂热已被金钱崇拜和性放纵所取代。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西方存在主义、现代主义、精神分析学等哲学、文学思潮进入中国,与当时人们的精神追求,关于个人主义、个性意识等等的思考一拍即合,形成呼应,那么,世纪末之后的拜金主义、物欲膨胀则成为一种流行而芜杂的社会风气。后现代哲学中“拆解”、“颠覆”、“重构”等中心词语被国人的政治冷漠、放纵欲望本能当做理论的依据。犬儒式的随遇而安、得过且过、日子无论如何都要过下去的“自贱”和身体的无灵魂化则演变为表演性的狂欢和实用主义的物质追逐。在这样的价值观与社会风气中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就是公共话语的虚假与及时行乐观念的结合。人们普遍丧失精神向上、人性向善的追求。“笑贫不笑娼”这类糟粕观念在要与世界接轨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新成为人们可以接纳的道德伦理。文化界面对这迅速变化且日渐陌生的现实场景,再度失语。而在商业大潮中所形成的消费市场使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物化、成为商业和消费景观。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当中国女性书写以“个人化写作”抵抗宏大叙事,以个人内心的真实话语反抗公共话语的虚伪,它们呈现一个隐秘而真实的内部世界,它们甚至是残缺、阴暗的,但对精神和心灵的审读、自省并没有一丝的放弃。这些作品的先锋性、内在价值及深度意义现在开始被忽略、被市俗化。商业操手更关注那些符合大众消费需求的东西。性别意识→性→女性的身体→美女……沿着这个方向寻找,于是,“美女文学”作为20世纪末中国文坛最为引人关注的女性文学群体,迅速将带有政治意义、精神意味的“身体语言”转化为与物质、欲望相联的“肉身叙事”。身体当然具有生理、本能的生物基础,但它也具有社会文化的维度,是历史、文化与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产品,它处于具体的文化氛围和现实动态空间中。如果说在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时期及改革开放初期,身体表达具有政治批判意味和颠覆特征,譬如说20世纪70年代末的港台流行歌曲及“奇装异服”一直到90年代的个人化书写,它们对一统的中心价值起到反叛的作用,并表达人们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以及进入80年代以后人们对灵魂的自我拯救与反思。这一切都是历史语境的产物。那么,从世纪末开始的中国内地消费主义本身已渐渐与主流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身体写作与美女文学作为美女经济的构成部分,是一个卖点,是围绕时尚与市场的商业文化消费,其社会功能不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性与颠覆性。这同样也是当下中国具体语境诞生的闹剧。
关于“美女文学”现象,青年学者邵燕君有专门的调查与研究:“所谓‘美女作家的创作群体最初在文坛集体亮相是通过‘70年代以后这样一个栏目。该栏目由《小说界》1996年第3期率先推出,随后,《山花》(1998年第1期)、《芙蓉》(1998年第4期)、《作家》(1998年第7期)、《长城》(1999年第1期)也先后推出相关栏目。在三四年的时间里,这些栏目共发表70篇小说,其中近七成是女作家的作品。……1999年以后,打造‘美女文学的‘主力已经从纯文学期刊转为图书出版业。……卫慧和棉棉是出书最火的作家。……其中《上海宝贝》一书的狂炒热卖(正版印刷11万册,网上点击逾14万次)使‘美女作家热达到高潮,并引发‘宝贝系列、‘粉领系列等仿制品的出现。‘70年代以后这一由纯文学期刊推出的文学潮流,经‘时尚女性文学,至此转变成畅快类型小说中的言情小说,乃至色情小说。”①
其时,笔者所供职的大型纯文学刊物《花城》杂志,在八九十年代作为中国内地纯文学原创作品的重镇,从1979年创刊以来几乎都有中国内地文学阶段性的代表作品占据头条。80年代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四大花旦”(《收获》、《花城》、《十月》、《当代》);一直到90年代,更成为王小波的作品、“个人化写作”的主要舞台,与《收获》、《钟山》一起被视为中国文坛的“三国鼎立”。面对市场经济中物欲横流的商业文化消费,文学作品也进入“肉身写作”、“隐私写作”,同行刊物及出版界纷纷推出“美女作家”甚至“美男作家”等等“新概念”,杂志同人还是以悲壮的坚守姿态打出刊物广告语:“《花城》——你最后的精神家园。”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的作品,甚至后来成为她们代表作的多篇小说,在《花城》这里却遭退稿。与市场博弈的结果,就是《花城》除了以原已成名的作家们的新作(如林白的《枕黄记》、《万物花开》等)继续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外,它已与喧闹的文学市场渐行渐远,显得落落寡欢。
作为纯文学作品最具价值和意义的艺术追求便是叙事艺术的探索。对汉文学语言的叙事建构和实验曾经在八九十年代使中国当代纯文学形成孤寂而高傲的文学景象,也显示出一种语言革命的激情。一直到“个人化写作”的女作家们那里,语言意义的艺术探索依然是她们不能放弃的尺度。
然而,与“美女文学”成为大众消费品一样,小说叙事的探索也基本消逝。“美女们”关于日常生活、身体细节的情欲叙述,足以迎来众多读者的眼球,满足人们猎奇和窥视的心理。
倪可小姐作为《上海宝贝》中的女主人公,她要炫耀的是老上海租界情调的咖啡、红酒、夏奈尔香水以及名牌内裤和与西方男人的床笫之欢。甚至同性恋,也由西方女人来共同完成。同时,倪可小姐也要听麦当娜的歌,谈论杜拉斯,住豪华公寓听肖邦……所以同为“70年代以后”的男性作家石康说得刻薄:
倪可一出场,便给人一个傻冒上海时尚女青年的感觉,她不求甚解地喜爱所谓反叛文化,十分虚荣,满脑子幻想,她的生活目的就是引人注目,这是所有小人物特有的感觉,十分可悲,但很好笑。……夏奈尔是倪可希望自己美丽而能出人头地的象征,而米勒则表现出倪可的文学抱负。当然,通过写作假反叛小说一举成名是很多时髦作家的共同心愿,一开头,卫慧只用三笔两笔就为她的主人公倪可勾勒出一个穿露腿装的咖啡店女侍者的形象,并说这个形象与上海这个城市关系密切。上海自有一种气氛,可以让一个在咖啡店端盘子的年轻姑娘产生十分荒唐的幻想,那么上海这座后殖民文化刚刚发芽的城市是如何培育这种恶俗的幻想的呢?
即便如此,倪可身上的这些标签,包括性描写,作为小说卖点,在世纪之交消费文化光怪陆离的中国内地,并不足以构成令人轰动的冲击波。它更主要是作者与出版商双方合作的生产与炒作的结果。从封面设计到签名售书活动,卫慧本人以身体的“行为艺术”引来青春男女里三层外三层充满期待和渴望的目光,并发出极度兴奋的欢呼和尖叫声。不是由于小说的内容,而是过于嚣张的促销手段,甚至在重庆的签售活动现场卫慧撩起上衣,说“让他们看看上海宝贝的乳房”。在印数一路飙升的同时,媒体及网络也骂声一片。该书的策划人,其身份既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著名批评家。这就难怪批评家们最初对此事的沉默了。直至2000年5月,由于读者举报,北京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认定该小说“是腐朽堕落和受西方文化毒害的典型”予以禁售。从一本畅销书演变为一个“禁书”事件,不仅在内地,就是西方媒体也被惊动了。卫慧因此成为一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新人类进入全球化的消费体系,并因此获得更大的名利。在这里,文学死了,身体写作成为新经济,也成为我们读解消费时代的中国文化现象的案例。
随着以启蒙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消解转向消费模式的大众文化,要看到中国内地消费主义的出现与西方发达国家是有本质不同的。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语境:一方面,大范围的中国农村地区处于只求温饱的前现代时期,大批农民工离开土地涌入都市,寻找生存空间同时沦为都市的底层阶层,他们与消费社会相距甚远;另一方面,城市里,尤其是沿海大都市则弥漫着消费主义的热情,其程度并不亚于欧美发达国家。在“拉动内需”的口号声中,GDP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危机四伏,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身体写作、美女文学诸如此类的概念既是转移大众文化注意力的重要方向,也成为开启新的消费可能的钥匙。
《文汇报》记者孙健敏曾经采访“下半身写作” 女诗人尹丽川。针对她发表的“当女人身体解放之后又该干什么”一文进行追问。尹丽川的回答是:
在当时,身体写作不仅是一种概念,还是一种方法。就是指口语化的写作。后来很快这对我就是一个常识了,我已经不需要再去强调它了。然后,我就需要去知道身体之后是什么。这可能只是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一种反复,但是必须要去经历这种反复。不过,这种东西在大众领域里是说不清楚的,传媒和大众理解的那种女人的挑衅还是指女人去脱光,我觉得这怎么构成一种挑衅呢,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而且现在也不需要什么勇气了,现在每个女作家、每个女人都可以做到,何况这背后还有那么大的名利的支撑。
身体景观化、物质化、符号化在现代消费体系里就是无限夸大身体的解放、身体的功能与欲望。这不仅是战略性的,也是一种策略。你可以利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强调女性身体的解放让女性找到一个自由表现的空间,强调“女性是自己身体的主人”,消费文化也可以利用这一点让女性被消费并成为消费本身。名利、权力、商业操纵、大众媒体共同建构身体拜物教。媚俗成为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内地文化的主要品质。
同样以坚守纯文学品质著称的老牌文学刊物《收获》(当时的主编是著名作家巴金,执行主编为巴金的女儿李小林)于2000年第1期推出上海青年女作家棉棉的长篇小说《糖》。尽管棉棉已经作为“70年代以后”的美女作家群中的一员在其他文学刊物发表过她的中短篇小说,但此次《糖》出现在《收获》杂志上,还是被文坛视为文学新人类登上高雅文学殿堂的标志。所以,与《上海宝贝》不一样的,就是批评家们(譬如陈思和)及作家们(譬如王朔、赵玫)开腔说话了,尽管争议依然很激烈,但《糖》显然获得比《上海宝贝》更高的文学评价。
这是一部关于坏女孩的小说:“我”辍学在家,爱吃甜蜜的巧克力,身边被不同年龄的男人包围(主要线索是与问题男孩赛宁的关系),毒品、迪厅、酒吧、性、吵架、艾滋病、同性恋、妓女、电邮、自虐、受虐……这些关键词组成生活的全部内容。及时行乐、放纵青春肉体、沉溺于痛苦与狂欢、只过今天,不问明天,没有未来和责任……身体已不再是灵魂的载体,而是否定精神、反思想的平台。通过赤裸的肉体将内在欲望呈露于世,并获得世俗社会的喝彩。正像作者自己在作品中说:“我要把所有的恐惧和垃圾吃下去,必须让所有的恐惧和垃圾在我这里变成糖。”
小说是在纯文学领域登场的,以一种嬉皮士和无所谓的姿态,并以很强的自传内容而产生巨大的冲击波。在棉棉的小说背后,藏着这个作者自己的故事:将近十年漂泊四方的岁月,三年海洛因生活,多次自杀未遂、车祸、酗酒、在夜总会做妈咪,无数身份不明、不断失踪的江湖朋友……棉棉自己告白:
我写的不是不健康的,只是非常规,不是很主流。我只是把自己的生活自然而然地写出来。我的小说,性不是主要目的,也不是有意地玩酷,描述失控的生活,不是为了刺激,因为这些我都经历过。我就把它写出来。我的缺点是我的惟美。我的问题是:是为了自由而失控,还是自由本身就是失控的?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文坛的急功近利风气与中国内地整个文化语境是一致的。一些纯文学作家退隐到书斋里孤绝坚守,更多的文学机构及写作者渴望利用消费文化的蓬勃发展分到一杯羹。
“用皮肤说话”是关于棉棉的《糖》使用频率最高的评论语。它更像一句令人想象无穷的广告语,引诱更多的人向它奔去。
与此同时,从新加坡留学归来的前媒体记者九丹出版被指为了“妓女小说”的《乌鸦》(2001年1月长江文艺出版社首版)。书中写了一个女留学生在异国他乡为了生存及获居留身份而“被迫”卖淫的故事。通奸、暴力、撒谎、偷盗、卖淫、谋杀等等,几乎所有人性中丑陋和恶的事物都从黑暗的地沟里捞出来。与棉棉一样,九丹也通过女主人公诉说:“我是个坏女人,可是我还能哭泣!”“坏”,作为一个定义,表面上是作者的“忏悔”,实际上是一个大肆张扬的卖点。2005年在上海召开的第四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传出信息,“中国的坏女孩写作”成为此次大会的一个专门议题。“与会专家认为,‘坏女孩作家群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但是性对于她们来讲,并不是真的‘性趣,而是用以追求名誉以及财富的工具。……‘身体写作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女性作家的品行或其作品优劣与否,更重要的是,它刺激起一大批写作者,尤其是年轻女性写作者的强烈名利欲,和‘一夜暴富的文化赌徒心理。” 按西方女性主义的观点,色情影像书刊是社会所规范的男性统治女性服从的性关系的肉感化、图解化、具体化。实际上是两性不平等关系的写实。而以“身体写作”为旗帜、并喊出“性解放”“张扬个性”口号,标榜反叛、标新立异的行为,这只是一个幌子。
诚然,“美女作家”们早就学会了中国式的“扛着红旗反红旗”的做法。当媒体、出版商、“红包”批评家(指在世纪末之后中国内地普遍出现的收取红包开会写评论的职业批评家)与作家们达成默契,从这些惊世骇俗的作品中提取“意义”“价值”时,女权主义、女性意识、性别立场也是被作为旗帜之一。而这种表面上反抗、骨子里媚俗、追逐利益与欲望的文本,把女性降低到生理性的,去思想化去灵魂化的情欲肉身,实际上是迎合商业社会男权要求对女性的规定。较之80年代王安忆、张抗抗、铁凝们的写作,她们并不关心“男子汉”们在哪里,不关心在这个社会里女性的地位、理想、家庭与职业矛盾等社会关系问题;而与90年代陈染、林白、海男等人的“个人化书写”相比,她们不再关心个人的情感冲突、自我个性意识,而只遵从内心滋长的某种欲望而欣喜若狂。其挖掘人性及女性心理的深度和广度、包括作为文学作品应有的想象力、驾驭语言的能力都是大幅地退缩。这是伪女性主义文学借助商品涌动的时代掀起的景观表演与狂欢。当这些美女作家们在媒体、网络互相攻击、吵架,鸡零狗碎地揭短甚至谩骂时,大众也开始无法忍受了。网上的一则评论语言尖刻:
在今天,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作家,她写的东西远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一、她会不会炒作自己;二、她漂不漂亮;三、她敢不敢写揭露自己的隐私;四、她是不是著名文化人的老婆(或情人)。
而作家阎连科则认为这些“美女作家”尽管彼此存在很大差异,
但有一点她们是相同的,她们的写作都代表着一个方向,那就是向传统和上一代作家的决绝与挑战。她们都最大限度地张扬了个人主义与私欲主义。在作家的写作过程中,他/她只代表人物自己,代表自己的思想、欲望与行为。而不像我们的许多作家那样,在写作中期望自己的人物代表一群人,一个阶层乃至一个民族。从这个角度中去说,《糖》和《乌鸦》与《凤凰》,也是相通的,一脉相承的。⑩
我们无法否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环境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事实。直至世纪之交,由消费主义、跨国资本、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意识形态等多重塑造的文化空间,呈现出斑驳陆离、盛世繁华的表象,充满广场音乐喷泉泡沫的狂欢,煽情的、欲望化的、瞬息万变的万花筒陈列在我们面前。文化价值危机犹如坍塌的山体,泥石流正在冲泻直坠。这似乎是一个肆行无忌的时代,话语混杂,“文化”一词成为万能标签,它过度的语义膨胀让人们很容易就迷醉于世俗社会的喧嚣与无主题欢乐之中。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曾经在《舞蹈的盲肠》一文中指出海外华文文学的唐人街语体及其盲肠命运,该文当时发表于《花城》杂志,在文学界有相当的反响。作为敏锐的文学预警者,他所指出的“盲肠命运”的事实,如今不仅仅存在于海外华文文学,更是眼前的图景存在。到处可见舞蹈的盲肠,又有多少盲肠能够切去?!
究竟是谁在操纵民众的欲望?谁把生活当成新闻报道,把新闻报道当做文化生产成果?谁在制造一系列文化传播事件?谁把文学艺术拿来作秀?它们之间所存在的互为消长的关系,正是这个转型时期的症候,也是需要拆解的新秘密。此时此刻,批评家的立场何在?
按照萨义德的说法:“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了提升生命,本质上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 而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犬儒主义横行其是。
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消费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当做消费品。消费身体、美女经济(色情经济)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在美女意识形态下,大众消费文化与文学艺术共谋,经过一整套社会文化生产机制的符号化与文本化生产、再生产,美女变成社会珍稀资源并具有商品交换价值。我们因此陷入价值观的歧途,价值杠秤早已失去准星。所以媚俗之后是媚雅,媚雅之后便是媚性。那种“笑贫不笑娼”的说法既消解了人的羞耻心,也消解了色情的社会毒素。
而在“美女文学”获得轰动效应并名利双收的同时,还有另一种同样获得大众欢呼和市场欢迎的女性写作,体现了这个时代中国内地文学妇女们又一个写作方向。那就是同样处于消费形态的商业化大潮中催生的都市言情小说。都市作为一种商业结构,它是市场存在的基础,也体现商业化的生存背景,并形成物质利益为主的都市文化意识。作为身居都市的女性作者,随着商业经济下发生演变的新的女性规范的出现及赋予妇女生活新的内容,她们的言说就是以占主流的都市职业女性的视角和立场来探寻都市女性的生活状态。身居都市的中国女性市民,绝大多数是职业女性。而女作家们所属的阶层应该是“白领阶层”,也就是所谓的“都市丽人”。这就是言情小说的主角。都市丽人们的故事也离不开全世界妇女同样的生存矛盾——家庭与事业,以及情感困惑——两性关系。而在这个由禁忌、压抑走向开放、经济繁荣的中国内地,转型期出现的冲突显然更加剧烈。同样,性别战争也成为小说的中心情节。但这种战争再不是两个人(男人和女人)的战争,也不是一个人的战争,构成言情小说的诱人之处更可能是三个人的战争(男人与他的妻子,还有婚外情人)。这就增加了言情的悬念及复杂性,因此也具有通俗小说的可读性。战争存在于两性之间,爱情却是缺席的。如果说80年代的女性写作弥漫着浪漫而不真实的爱情理想,在90年代女性“个人化书写”中质疑并追问爱情的意义,而美女作家们是言性不言爱,在言情小说中,更多的则是关于如何经营爱情经营婚姻的问题探讨。都市女性生存的准则、观念意识是如何在男权意识的笼罩之下获得生存的更大更自由空间。可以说,言情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充当都市妇女们的婚姻情感生活的导师。她们无情地撕下爱情这张美丽而无用的面罩,把两性之间的温情脉脉的真相揭开,那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是算计、伎俩、谎言构成的生活。言情小说的领军人物是曾被命名为“新写实主义”代表人物的池莉。《不谈爱情》、《烦恼人生》、《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你以为你是谁》、《生活秀》等等,是池莉的作品题目。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在池莉笔下,是猎人与猎物的关系,消费者与消费品的关系,唯一的纽带就是赤裸裸的性。所以不谈爱情才是女人能够不受伤害的保证。《来来往往》(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在中国内地多家电视台热播)中的林珠,作为第三者,也是新潮的、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她面对迟迟不能离婚的康伟业决不痴情:她卖掉康伟业赠送的高级住房,心安理得揣上五十万元远走他乡。没有爱,没有痛。回归世俗生活,脚踏现实大地。这是池莉给予商品化时代都市女性的指引方向。
不言情,可以说是处于权欲(权力控制与物欲膨胀)时代中国内地都市言情小说的主要特点。它实际上折射出整个社会情感匮乏、情感荒漠化的普遍现象。像徐坤的《爱你两周半》,干脆撕下情人面纱后面的权性交易,揭穿了电视台主持人于珊珊与京城地产大鳄顾跃进的赤裸裸的权性交易。都市里的男欢女爱,灯红酒绿,只有欲望的挣扎,并无诗意的留恋。
另一位都市言情小说家张欣,也已不再相信都市有什么纯情可言,不再相信爱情地老天荒:
爱情是一种感觉,无论多么伟大也仅能维持三五年,剩下的是感情、亲情、牵挂、依靠、合作、伙伴、撒气、说话、交流、暖脚等等,全是泛爱,不再是那种独特的感觉。所以,重要的是把日子过好,人有能力时才能顾及到自己所爱的人,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了。
不像池莉那样决绝,张欣会以一种都市浪漫者的遐想表达她面对商业都市里的男男女女情感故事的辛酸与矛盾心态。一方面是现代化都市里白领丽人的“经济独立”与“聪明能干”,另一方面是怕做花瓶被人瞧不起,做女强人没人看的担忧与无奈。男权意识作为传统观念与商业化进程并驾齐驱,构成大众与市场热烈拥抱的“都市言情”模式。较之美女作家们的嚣张与另类,都市言情写作更符合城市新富阶层的文化心态与价值伦理取向。所以,它们很快成为电视连续剧抢手的脚本。
不执著于深度,将灵魂的安妥问题落到实实在在的物化现实的空间,如何平衡现实与理想的关系是都市女性幸福与痛苦的根源。这是都市言情小说致力探寻的主题,其实也是对情感与精神价值最大的质疑。
物质渐渐成为统治人的精神的权威时,人本身也成为物的符号。物化的现实同时是人性异化的过程,所以诗意、爱情、理想等等只是一层虚饰的面纱。无论是美女作家,还是都市言情作家,她们骨子里不再肯定这些曾被视为人性光辉的形而上事物。女性的主体意识再度遮蔽,她们愿意汇入尘世的物质海洋,追逐现实层面的幸福感。这与中国特殊的语境特殊的社会结构是相一致的。学者徐贲认为:
当今中国的消费也正起到这种不良的作用。消费由它自己的领域扩展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一切人际活动和人际关系皆成为一种投资,一种资本,连公共生活领域(政治、司法、文艺、教育、医疗)也不例外。在中国,消费意识的发展是以公共生活的商品化和金钱为代价的,消费者身份理所当然地取代了公民身份。消费者主权意识并没有如一些市场经济推动者所预言的那样在中国顺利转变为公民主权意识,这种看上去是自由主义的消费文化其实是以非自由民主公民或者反自由民主公民政治为其特征的,它以取消人的最根本的一项自由为条件,那就是与他人共建关于存在价值的能动自由。
尽管商业化进程、全球化影响、消费主义共同促成大众文化的世俗化、粗鄙化,另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更多来自政治权力的优势。所以作为一种不是良性的、公平竞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权欲社会或者说权贵资本主义成为当代中国典型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说一套做一套”形成了当今中国犬儒文化的基本特点。
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语境下获得市场关注的美女文学及言情小说,意味着中国妇女主体意识在前进道路上的重新失陷。
【注释】
①邵燕君:《“美女文学”现象研究》,3—1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康:“卫慧《上海宝贝》批判”,http://www.xiaoshuo.com/
jsp/knowledge.jsp?id=15165&bid=0018576。
③卫慧声称,封面照片是她本人:“我请北京的化妆师李奇潞在我的皮肤上写下书名和作者名。”连广告词也是亲自设计的(“一部女性写给女性的身心体验小说”、“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一部发生在上海秘密花园的另类情爱小说”)。参见大卫:《卫慧:封面就是我》,载《南方都市报》2000年2月11日。
④⑨王珲:《她俩把“问题”解决了——卫慧和棉棉的吵架》,载《三联生活周刊》2000年5月15日。
⑤当代中国大陆一个诗歌流派。2000年7月,诗人沈浩波和杨黎、尹丽川等人一同发起创办《下半身》同人诗刊,以沈浩波的《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为宣言,改变中国先锋诗歌的走向。
⑥孙健敏:《从身体解放的尽头重新出发》,载《花城》杂志2004年第6期。
⑦小光:《迷茫的罂粟疯狂地开》,中华读书网http://www.booktide.com,2003年12月18日。
⑧浮蓉、季明:《西方学者:“身体写作”低俗,甚至发出“腐烂”气息》 ,http://new.xinhuanet.com /mrdx /2005-09/03/content_
3434398. htm。
⑩张者:《学者为美女作家“号脉”》,新华网http://news.xinhua. com /book /2003-03/04/content.756137.htm。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单德兴译,转引自爱德华•W.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2页“译者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张欣:《浮与缘》,见张欣中篇小说集《浮世缘——都市女性三重奏》,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徐贲:《“需要”在中国的政治转型和理论困境》,载《花城》杂志2006年第4期。
(林宋瑜,文学博士,花城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