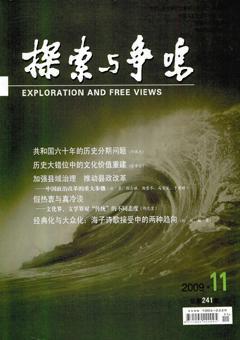加强县域治理 推动县政改革
自秦朝设郡县以来,中国就有“郡县治,天下安”之说。两千多年来,县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治理单位。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管县体制的逐步推开,县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地方治理单位在政权体系中日益被边缘化。当下,在基层民主渐趋成熟并逐步向上扩展,以及基层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县域治理的重要性已经凸显。县政改革能否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新的突破口,是考验实践者和研究者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本刊特邀几位专家学者就加强县域治理和推动县政改革发表自己的意见,以期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
——主持人杜运泉
国家化与地方性背景下的双向型县域治理改革
徐勇,襄樊学院“隆中学者”,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由于县域治理愈益重要,有关县域治理改革的论述也愈来愈多。但总的来看,与当年乡镇改革一样,主要限于就事论事,缺乏系统的学理性研究,结果是各说各话,各执一端,最后不了了之。政治学是一门制度学科,它要承担制度设计的使命,而进行制度设计时需要有足够的经验和学理支撑。我认为,讨论县域治理的改革和走向,需要将其放在国家化和地方性背景下考察。
人类历史是在活动空间一步步扩展中发展的,从早期的部落,到小型城邦国家,再到分散孤立的国家,直至近代以来的全球化。研究当下的县域治理或者说其他层级的治理,都离不开“全球化趋势、国家性建构、地方性复活、草根性成长”这四个关键词。
自近代以来,全球化便成为不可规避的大趋势。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论述了这一历史过程,认为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即“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现代民族国家有两个不可分割的特点:一是外部的主权独立,对外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二是内部的整体统一,由中央政府实行有效的统一治理。由此就有了对外争取独立、对内争取统一的国家化进程。即使是全球化浪潮不断超越国界,但人们至今还必须生活在国家这一“政治容器”之中,国家性建构并没有终结。
中国是一个早熟国家,即在西欧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时,中国就已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大型国家,因此,中国很早就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特质。但是,古代中国还不是现代国家,一是对外只有“天下”观而没有“世界整体”观,“有边陲无国界”,因此近代遭遇先崛起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侵略打击。二是内部的一体化程度低或者说是刚性的一体化。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地方和基层社会处于自治状态,中央集权只是一个与民众日常生活无关的外壳。这一外壳一旦被击碎,国家就陷入分裂和动乱。孙中山是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创立者。他深刻地反思了为什么作为人口最多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不堪一击,甚至有亡国灭种之忧的原因,这就是“一盘散沙”。他认为:“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因此,近代以来,中国就面临着双重任务:外争独立,内争统一。而这都需要建立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将原来散落于地方和社会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特别是中央。孙中山对现代国家设计时,将以县为基础的地方自治作为重要制度,但这一设想没有能够实现。其重要原因就是近代以来的中国未能建立中央能够有效管辖地方的体制,以完成国家内部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至今仍然有待完成,特别是还需要形成依靠统一的相互依赖的市场和文化网络建立起来的柔性一体化。所以,一个统一权威的中央政府还是必须的体制,地方接受中央统一领导的单一制仍然必要。
由于英美等国家率先成为现代国家,其地方自治体制也为后起国家所借鉴。但是,英美的历史传统不同,特别是美国,其中央权力是地方让渡的。地方权力是中央权力的基础,换言之,中央权力有地方权力作为其牢固的基础,为地方所让渡的中央权力有统一的领导权威。这说明地方自治有其特有的条件。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具备这一条件,往往是先有中央政权再有地方政权,因此这些国家大都采用的是中央统一领导的单一制。即使是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中央权力日益增长,地方权力日益式微,也成为一个趋势。这是因为,随着社会发展,对均等化的要求愈来愈高,如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公共福利的均等化等,而这必须依靠公共权力集中的中央政府来实现资源和财富的再分配。这就是20世纪以来,自上而下的权力一直延伸到每个社会成员的“权力垂直下沉”的过程。60年来,我国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体制,这对于社会动员、国家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一体制发挥作用的内容有所不同。前50年主要是管理,近10年则向服务转变,即统筹发展,实行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还得依靠这一体制。因此,中央自上而下的领导体制仍然必要,县级地方自治作为一项地方政治制度,不可轻易实行。
尽管国家化是近代以来的主题,但为什么近年来地方治理、地方自治又被广为重视呢?其重要背景是“地方性复活”和“草根性成长”。
历史的发展是辩证的。近代以来,那些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在不断加强中央权力,如英美;而那些实行单一制的国家,又在不断下放权力,如法国。但自20世纪以来,即使是不断加强中央权力的英国,也愈益重视地方和基层。如以往的政党政治主要集中于中央权力的获得,而现今更重视地方权力的执掌。其重要原因是地方性事务日益增多,民众与地方有效治理的关联性愈来愈强。随着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等国家统一性的建立,民众利益的实现与地方治理密切相关,大量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最终要依靠地方政府实施,地方的决策权和执行权增大。由此就出现了所谓的“地方性复活”。但这种地方性已不是传统封建时代相互割据的地方性,而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性。在“地方性复活”的过程中,是“草根性成长”。所谓“草根性”通常是指一般平民大众。这些人在以往的政治活动中是微不足道的“草民”,除了大选以外,对日常政治生活没有多少参与机会,其政治意愿主要被少数议员所“代表”。因此,在相当长时间里,民主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选举政治、议会政治。那么,随着“地方性复活”,民众的利益与地方治理日益相关,也为民众参与地方治理提供了契机。他们除了选举领导人以外,还通过不同的参与方式,共同讨论和决定其所面临的公共事务。地方治理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参与的程度。日常参与的协商性民主因此成为重要的民主形式。
60年来,我国的权力体系也处于一个双向过程,一方面是权力高度集中,一方面是权力下放。前30年代主要是集中,后30年主要是下放。与此同时,在集中过程中有下放,在下放过程中有集中。总体是集中,局部是下放。其重要原因是随着统一的现代国家的建构,“地方性复活”也日益突出。在传统中国,县官只是中央在地方的象征性权威,没有什么自主性。在计划经济时代,县级政府主要是执行。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的决策权力增大。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强县扩权的呼声日益强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有人提出“县级地方自治”的思路。以制度的方式而不是人为政策的方式提高县的地位,强化县的权力,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地方自治必须依托两个条件:一是国家一体化,即地方自治不可伤害中央自上而下的统一领导;二是草根性成长,即地方自治权的扩大要与民众参与扩大同步。没有前者,“地方性复活”很可能是传统的“割据式地方性”的复活;没有后者,“地方性复活”很可能是“土皇帝”式的地方性复活,这都无法达到地方的有效治理。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以县为基础的地方自治,由本县人治本县事,基本考虑是通过地方公众参与,实行民主政治。
根据以上分析,我以为,理想化的县域治理改革是双向型运作:一是中央权力适度向县级下放,使县级有更强的自主性,同时这种权力下放是整体性的,即权力下放与权力监督同步;二是民众对县域治理的适度参与,县域权力扩大不仅是扩大“县官”的权力,同时更是扩大“县民”的权利。可以将近些年成长发展的村民自治向县乡层级延伸,让县民通过县乡人大等制度化渠道更多地参与地方性治理。否则,草根民众可能就会通过非制度化的群体性事件来表达其意愿。同时,我国现有的制度资源还有很大的利用空间。我国地方政府体制事实上具有复合性特征,如法律规定,地方政府接受上级政府领导,同时又为本级人大所任命并接受其监督。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接受上级政府领导多,本级人大对政府的影响小。而本级人大正是民众参与地方治理的重要渠道。这一制度化的渠道还有继续发挥作用的余地。一般来说,当一种制度的生命力尚没有耗尽时,不可轻易替代。浙江等地的地方治理运用人大进行财政预算公开改革,便是地方治理改革的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