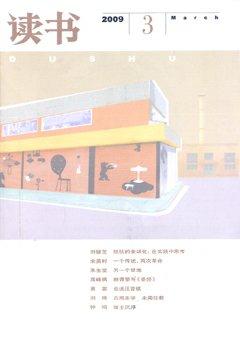搜读人间未见书(下)
王振忠
由于郑振铎的直接干预,间接导致了徽州文书的第一次大规模发现。前文述及,根据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指示,合肥、芜湖、屯溪和安庆四地成立古籍书店,专门负责收集、管理该四地发现的古籍。一九五六年十月,与韩世保关系密切的书商余庭光受命筹建屯溪古籍书店。屯溪古籍书店创办以后,首先对当地一百多名古书商贩加以摸底、登记和造册,加强了管理,其次是大量收购,抢救、保护和利用徽州古籍,他们还通过编印古籍书目发往各地,加强了与全国书店及收藏单位的联系。
余庭光一九三○年生于绩溪县城北门外,出身于一个传统的徽商之家。读完小学后,就到书店从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通过与韩世保的长期交往,古籍修养日渐提高。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的新华书店工作者,他曾奉命到北京新华书店总店参加业务学习。一九五八年,余庭光前往徽州祁门县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寻找古籍,起初颇感失望,因此处的废品虽然堆积如山,但全是各朝代遗留下来的契约、簿册之类,年代久远的可上溯到宋代。余庭光觉得这些纸品虽然不是古籍,但作为废品处理似乎有点可惜。最后,基于“不能空手回去”、“或许能够派上用场”和“即使没用也就是赔个运费”之类的想法,以八分钱一斤的价格将这些“废纸”装袋买回屯溪,一共装了整整三十只麻布袋。
正是由于余庭光的剑走偏锋,直接导致了徽州文书的第一次大规模发现。此后,这批原始的徽州文书,通过《屯溪古籍书店契约目录》流向全国各地,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轰动。徽州文书是徽州民众在日常生活、商业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原始档案,由于历史时期徽州社会的经济活动极为频繁,田产之推收过割,商业的锱铢计较,使得徽州人滋生出强烈的契约意识,再加上民间普遍的敬惜字纸的传统,使得这一带遗存下数量惊人的民间文书。徽州文书的数量极为庞大,种类也相当繁多。较之其他区域的民间文书而言,徽州文书所独具的优势在于——具有相当规模的同类文书前后接续、自成体系,而且,各类文书又可彼此补充、相互印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徽州文书被不少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大学研究机构收藏,这可以说是徽州文书第一次大规模的发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绍泉研究员的估计,已被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国内收藏机构收藏的徽州文书大约有二十万件(册)。而据余庭光的回忆,由他经手运出皖南的徽州文书、文献,倘以运输工具计,概算有数十部汽车之多。
余庭光收集徽州文书的举动,明显受到郑振铎的影响。一九五八年七月四日,郑振铎曾在北京,为古旧书工作人员训练班讲《古旧书籍的收购与发行工作》,“共讲了近四小时,听的人还感兴趣,加强了他们的信心,打破了他们的迷信”。前文提到,余庭光亦曾奉命到北京新华书店总店参加业务培训,是否聆听过郑氏的演讲不得而知。但一九五八年后,余庭光在郑振铎主编的《文物参考资料》上陆续发表《歙县发现明代洪武鱼鳞图册》、《徽州地区收集到万余件珍贵资料》等,将徽州契约文书的收集情况向外界作了报道。在郑振铎逝世之后,余庭光又发表《屯溪又发现一批古籍》的讯息。这篇刊载于《文物》一九五九年第四期的文章中专门提及:
安徽屯溪古籍书店继元刊本“邵氏谱”发现以后,最近又在歙县棉溪纸厂和私人藏书家中收集到一批稀见古籍,这批古书大部分都是明代刻本,共三十多种,有木刻版画、志书、医书及明人集子、词典等。明刊本饶安邓百拙编“花鸟争奇”,插图有十二幅之多,它是一本图文并茂,诗词赋曲皆收的文学作品,……在医学方面有明中叶刊本“回生外科医方”二卷,不著撰人。这本书的特点是:在每一单方前面都有一页完整的人体病位图……徽派版画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刻工细致精美,在这批书中也替我们保存了许多完美的版画,这是十分可贵的……
此处特别强调了徽派版画的价值,而这,明显是郑振铎的趣味所在。
数年前,余庭光还回忆,正当他悉心投入对徽州文书的收集,却正值全国展开轰轰烈烈的反右政治运动,这项工作遂受到政治气候的胁迫,“手脚放不开,思想有顾虑”,对于民国前的徽州文书、文献,只能粗线条地对集中地之收购站、造纸厂选择品相好的加以收购整理,对进入民国后的徽州文书,则一概不敢收购,生怕因此被戴上“复辟”的黑帽子(见胡成业:《徽州文书的“功臣”——余庭光先生》,载氏著《绩溪牛片羽》,二○○五)。其实,这样的困境,郑振铎的最后两年亦同样身陷其中……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郑振铎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殉职。因此,二○○八年是郑振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也是徽州文书第一次大规模发现的五十周年,我将一般人看来毫不相干的两件事相提并论,其实并不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郑振铎是个典型的读书人,从《郑振铎日记全编》来看,他几乎一辈子都与书打交道,隔三差五都要买书。每每买到好书,即得意忘形。在他的日记中,常常见到这样的文字:
灯下,披卷快读,浑忘门外是何世界!
浑忘晚餐未见矣!不仅眼饱,腹亦饱了,甚是高兴!……倚枕看书,不知何时入睡。
一九四九年后,郑振铎虽然身居高位,社会活动频繁,但公事之余,夜静更阑,他仍然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到去世前夕,当时因为正值中国的反右斗争,他才有所改变。
《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九期刊登了“文化部党组召开文物界反右派斗争座谈会”,题目是《辨明大是大非,驳斥右派谬论》,其下收录了一组文章,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宝钧、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等都有文章。郑振铎在同期上只发表了一篇比较学术的文章——《我国工艺美术的优良传统及其发展的道路》,这是在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该篇文章不在同期座谈会上的那一组文章之列。显然,他应当没有参加驳斥右派谬论的座谈会,可能是没有资格参加吧。
在那一组文章中,郭沫若在《我们坚持文物事业的正确方向》中,特别提到一些“右派分子”的说法:“土地改革时把民间藏书几乎烧光,等于秦始皇焚书。”土地改革,是新政权建立以来对于中国广大农村最为重要的一次改造,在此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根基也因而受到动摇。著名画家黄宾虹在《与郑初民》的信中提及:
乡邦文献,前三十年与公议有同编《歙故》之作,敝箧存稿不少,所收集元明清真迹及见闻所录,拟为付刊,未果。南北奔走,未尝一日去诸怀也。鄙人流亡出外,儿辈亦各守其职,不能有暇返里。即怀德堂住屋今如何,分配何人,亦杳无讯息可言。土革中敝居书籍等件,当如何久存保管为妥,自当考虑不致散佚为佳。宣歙文化书史散佚,殊为可惜,后之学者能就各乡各镇搜辑残余,保存本地公私收藏,传久垂远,即是人民幸福,不必集于一处一人之手。文物过目,随手笔载,见一幅考其姓氏里居、亲友交谊,踪迹行为,能得其详,虽片纸单辞,见之即录,不必拘拘于一族一姓也。乡村之中,各家族谱文词记载书画艺术之人,由本族后人笔述,先从个人努力分工开始,继集各乡汇为一编,可补古人府州县志之遗漏。
郑初民是安徽的文化干部,黄宾虹试探性地提出:自己在三十年前因与徽州史家许承尧(公)同编《歙故》(亦即后来由许氏单独完成的《歙事闲谭》),收集了不少皖南的乡土文献,后来因长年在外,这些资料都保存在歙县祖居潭渡村内,现在实行土地改革,他很关心这些乡土文献的命运。他询问郑初民,不清楚祖居怀德堂住屋现在的状况如何,分配给何人居住。他指出,尤其是那些乡土文献,应妥善保护。这是因为徽州文化博大精深,保存当地的公私收藏,“传久垂远,即是人民幸福”。这封书信,反映了土地改革之后黄宾虹对徽州乡土文献的看法。而在实际上,他的这种呼吁极为无力,完全被主流的声音所掩盖。在当时的气氛下,不仅地主的浮财纷纷被瓜分,而且,租册、账簿这样的徽州文书也作为“变天账”,被人们所掷弃。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句话当然没有问题。但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是传统时代所有中国人共同缔造的,除了下层民众的直接参与以及他们的辛勤劳作,为文化事业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之外,地主、文人士大夫在有闲有钱之余,也为文化之形成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因此,在摧毁旧政权的统治基础时,其实不能将孩子与脏水一同泼掉。但遗憾的是,不少地方都采取了一些焚琴煮鹤式的过激行为,政治教条也形成了僵化的思维模式,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郑振铎应当是注意到了土地改革过程中中国文物典籍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他也努力采取各种措施加以补救。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他到政协礼堂参加工作会议,“说了不少话,对于保护文物事,尤为慷慨激昂”。不过,很快的,他也受到了政治运动的波及。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四日,郑振铎在日记中写道:
在家理书。对所购各书,必须加以处理。要断然地不以“多”为贵。范围要有限定,不能见可欲心便乱了也。《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上,今天刊出了北大学生瞿秋白小组对我的《俗文学史》的批评,十分的尖锐。这是“一声大喝”,足以使我深刻地检查自己,并更努力地改造自己。是痛苦的,但也是一帖良药。
十天之后,也就是九月二十四日,他做了自我检讨:
八时,到部办公。八时半,到沈部长住宅,漫谈我的思想、工作作风等。先由我自己检查,说明自己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产生的典型的知识分子,有许多缺点。欢迎同志们多提意见,多帮助。发言者,有茅盾、吴仲超、王冶秋、徐光霄、刘芝明等同志,最后由钱俊瑞同志作总结发言。光霄和俊瑞二同志的话,极为尖锐,但也最击中要害。我表示愿意大力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改正自己的作风。十二时半,散。下午,整理自己的思想,下决心不再买书,并清理积欠,作为改造思想的基础。书籍亦是“物质基础”之一也。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书籍既是“物质基础”,那对“所购各书,必须加以处理”便极其顺理成章。从《郑振铎日记全编》来看,从这一天开始,到十月十六日日记结束,的确再未有过买书的记录。而再过两天,他就因飞机失事而去世……
平心而论,郑振铎之因公殉职固属不幸,但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来看,这对于他个人来说恐怕也是一种解脱。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郑振铎又是幸运的。
在一九五八年之前,作为新中国的高级文化干部,郑振铎除了公事(如出国访问、赴各地视察)外,跳舞、看戏、喝咖啡、喝白兰地、与书友叙谈、逛书店、在家看书,过的完全是传统文人的生活。他说“自己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产生的典型的知识分子”,这话倒真是大实话。难能可贵的是,一位身居高位的文化官员、知名学者,却能保持着读书人的本色,读书学习,著述不辍。他的许多著作叙次精当,阙疑征信,穷年累月,稿凡数易,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学者的严谨与执著。
我很难想象,一个一生酷爱书籍的人,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会放弃自己一生的最爱。也很难想象,即使他躲过了反右,是否逃得过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
或许是荣辱死生皆有定数,上天特别眷顾人间的这位读书种子,提前将之接往天堂,刻意让他看不到文物古籍惨遭劫难的“史无前例”?不然,以郑振铎的个性禀赋,他是否会在更为痛苦的状态下生活?……
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上述的疑问似乎早已有了答案。郑振铎殉职之后,茅盾在《悼郑振铎副部长》一文中指出:
他本来是铁路学校的学生,搞文学是由于爱好,完全是业余的;后来他搞古典文学、考古学,都是他自己摸索钻研的,因此,他不但走了弯路,也受了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的严重影响,……振铎在这方面,是很坦白的,他本来准备就自己的旧作(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作品)来个深刻的检讨,然而出国的任务使他把这件事稽延了,谁又料到“天夺其年”(请容许我用这句非马列主义的滥调)使他不能补过,我想他在九泉之下(再请容许我用这句迷信的滥调)是不会瞑目的。(《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八年第十二期)
历观往迹,备有明征。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不少人泛苦海之航,发自肺腑地希望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思想。沈雁冰认为,郑振铎生前对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作过深刻的检讨,在九泉之下应当也不会瞑目。由此应当可以想见,倘若没有因公殉职,等待郑振铎的必定是严酷的思想改造,这一点没有丝毫的疑问!
六十一年的生涯并不算长,但在郑振铎身后,却给学界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遗产。除了北京图书馆郑振铎藏书纪念馆中庋藏的二万种约十万册的珍贵典籍,除了他的那些话旧论文足为后世津梁,此外,郑氏临终前两年对抢救中国传统典籍的贡献,对于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尤其泽荫无涯。《文物》一九五九年第八期曾发布“文物工作报道”,说“中国书店收集到许多珍贵书刊”:
中国书店为了提供学术研究资料,半年来曾派出二三十个采购人员,分别到全国各大中城市和县镇,深入进行古旧书刊的采购工作,到目前为止,计其收购古旧书刊十余万部(册)。其中珍善本古籍约千余部(册),革命史料四五百种,而且有很多重要发现。……明弘治间陈氏刊印“大明律”三十卷,明刘惟谦等撰;万历间写刻本“顾仲方百咏图谱”上下二卷,附“雪篇”一卷,每叶图文各占一面,郑振铎先生生前曾云:“为访此书,遍寻京沪书林,十年不遇。”
中国书店抢救出来的这些重要古籍,与郑振铎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一九五八年第一次大规模发现的徽州文书,后来被有的学者称作是继甲骨文、秦汉简帛、敦煌文书和大内档案之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而这一发现,与郑振铎对徽州版画的长期关注密切相关。在版画研究方面,郑振铎有着强烈的学术使命感,独辟蹊径以待来者,数十年孜孜不倦的探索,使得“徽派版画”成为出版史研究、艺术史研究中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极大提高了中国版画在世界版画艺术史上的地位。
清初徽州人张潮曾经说过:“有工夫读书,谓之福;……有学问著述,谓之福。”(《幽梦影》)这是文人士大夫对“福”的一种诠释。而在我看来,作为读书人,有钱买书,有钱买得到好书,则是读书人之大幸!同时,书得其主,如宝剑终归英雄所佩,书借人传以不朽,也更是“书之幸运”!从这一点上来看,郑振铎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极为“幸”、“福”圆满的。
“搜读人间未见书”,对珍籍秘本的购藏与探究,成就了一代藏书家,也使郑振铎的名字与中国的徽派版画艺术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二○○八年深秋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