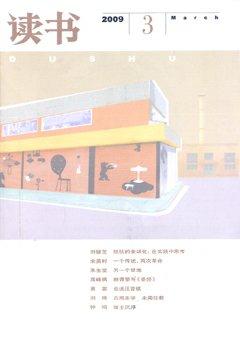寻找一种谈论方式
王际兵
《秦牧全集》出版了增订版(广东教育出版社二○○七年版),赫赫十二卷。作为一种文化的积累,这自然有积极的意义。可是,爱读这些文章的人实在不多了。这书只印行了两千套。
是写得不好吗?在建国十七年的散文作品中,秦牧的文字还是比较耐读的,能融知识性、趣味性和思想性于一炉。他善于从身边的事物、景物中发掘普遍联系,由知识阐发道理,引起联想,展开情思,从而把主观的意念与生活体验紧密结合起来。比起杨朔的造情煽情,刘白羽的政治宣传,秦牧倒是朴实、平易,更富有生活气息。像散文《海滩拾贝》,以贝壳为话题,串起形形色色的事物,把人引入海滩拾贝的情境之中,感悟渺小与伟大的统一。事、景、情、理浑然成为一个整体,不愧为一篇短文佳构。作者向来能出能入,收放自如,既有广阔的生活面、知识面,又能灵活地加以处理,可谓一位独具特色、颇见功力的散文作家。
是读者不喜爱散文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文学体裁就是长篇小说和散文。所谓文化散文、学者散文、小女人散文、新散文等等,术语概念层出不穷,随笔小品行销全国,甚至有人说现在是散文的时代。报纸杂志竞相登载,出版社大量结集出书。建国前的作家也相继被请出登场凑热闹,各式散文各式风格潮起云涌,蔚为大观。不读戏剧、不读诗歌、不读小说的大众读者为数不少,不读散文的却几乎没有。散文能够直接地说情、说事、说理,无疑为商业化快节奏化的生活供给了情感调剂、附庸风雅的资源,无形中成为文字消遣的一种时代体裁。
何以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既然作者的文笔不错,读者又爱读散文,为什么很少人读秦牧的作品,广而言之,很少人读建国十七年的作品?一般认为这是社会环境的变化使然。高度政治化的生活模式被改变了,人们的阅读兴趣阅读内容必然会转变。原来紧跟政治的读物已经被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社会读物所取代,可以阅读的范围越来越广,可以阅读的材料越来越多。这固然也是一个理由,但是吊诡的却是,与政治有关的东西并不缺少市场。李敖、顾准、王小波、章怡和等,他们的行情倒是十分可观。那些官场揭秘的小说,从地摊到网络都相当盛行。政治对于国人来说依然有很强的吸引力。由此可知,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谈论方式。如今大众不喜欢秦牧以及那一批人的作品,不是因为他们谈论了政治,而是因为他们“顺着说”的谈论方式。
就社会思想的发展而言,不喜欢“顺着说”是个提高。毕竟这种谈论方式比较容易,也缺乏创造力,用的人最多,也没有危险。本来它最需要谈论者的忠诚,可是“文革”时期的告密揭发,市场经济的尔虞我诈,使得诚信成了一种笑料,“顺着说”由此也成为过街老鼠。人们热衷其他的谈论方式也是合乎情理的。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顾准的日记等,便采用了“反着说”的方式。这需要勇气,也常常使作者的命运多舛,或者多舛的命运才造成如此的谈论。不过这几个作者都是幸运的,我们这个时代挖掘了他们,特别推崇这种言说的姿态。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等,则把事物提高到一个新的接受层面来观照,使用了“跳起来说”的方式,其中不可缺少的是见识。唯有见多识广,开掘深入,才能别开生面。至于从政治意识中“跑开去说”,养花种草、饮食男女、婚丧嫁娶、迎来送往、故居风情、师恩友谊等等,撰稿者众,观之者杂,报纸副刊、杂志文汇随处可见这类作品。从容不迫也好,激情难忘也好,感伤哀诉也好,只要是个人经验就可以下笔成文。好不好那要看是否有趣味了。张中行先生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流年碎影》,对老北大、民国旧人的记忆,打动了许多人。多种谈论方式的出现,是社会富有活力的表现。各种创造一般就存在于新的谈论方式当中,一个新的角度必然带来新的认知。
有了新的,旧的将何去何从?这是一个为人忽略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应不应该读一读秦牧,读一读建国十七年的作品,而且如何去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顺着说”提供了沟通的桥梁,也许从中读不出新奇,读不出勇气、见识和趣味,但是可以读出相互的信任和真诚。比如秦牧,一九四七年的集子《秦牧杂文》,充满了对权势压迫的愤恨,对善良、正义、劳动的向往等,这些情感并非日后的政治形势使然。后来他对劳动、对事物规律的热情,也不能说没有价值。事实上,有一些社会伦理从来是只能“顺着说”的。它们是人类建构自己的基石。王蒙的《青春万岁》固然幼稚,可哪个青少年又不幼稚呢?那种对信念的热情和执著对于青少年是大有裨益的。当今世界盛行的不确定性、多种可能性,正因为建立在确定性、必然性的基础上才有意义,没有常识也就没有创新,对常识认识得越清楚创新就越有可能。所以说,建国十七年的作品也有读一读的必要。当然,不必讳言那批作品的弊病,可这不是谈论方式本身出现了问题,而是如此谈论的人变得矫情了。同样,采用其他的谈论方式也会导致矫情的现象。李敖的“反着说”难免不夸夸其词。大骂别人“狗屁”之后,自诩“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尚且说是狂妄和故作姿态;可放言“光凭好文章,就足以使我不朽”,“把白话文写得气象万千,光芒万丈,这种中国功夫,是谁也抹杀不了的”,就无异于造神运动了。余秋雨的“跳起来说”逐渐演变为扯文化的虎皮做大衣,那些“跑开去说”的滥情、煽情的文字真是随处可见……这个社会从来不缺少媚俗者,媚权势之俗,媚功名之俗,媚金钱之俗,媚时尚之俗,媚欲望之俗。多少人一如昆德拉所说:“在美化的谎言之镜中照自己,并带着一种激动的满足感从镜中认出自己。”(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昆德拉说媚俗是艺术的敌人,想来又怎么不是生活的敌人?其实过去的问题不是“顺着说”造成的,而是媚俗造成的。通常人总想依附于某种力量来发言,从而显示自己的强大;而不是批判自己,在检讨我们的相对性中进步。有了靠山,也就有了乌托邦幻想,想象着一种历史的终结。在这些人看来,历史不再表现为具体情境,仅仅只是一些抽象的原则。因此媚俗的谈论都是虚张声势干巴巴的东西,当它出现的时候也就是死亡的时候。难怪有个说法,真理是不会形之于语言的,因为语言将把它搅得扑朔迷离,使它栽进慷慨陈词的泥潭,真理的伸张,只能通过把谎言引向荒谬。
想来,每一个举措,每一件事情,写作也罢,出版也罢,阅读也罢,都是谈论,都是使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在谈论。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我们不可能回避谈论的角度和立场,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角度和立场。比如对于秦牧及建国十七年的作品,可以挑选其中不那么矫情的文章结集成册推向大众,既能矫正人们的偏见,又能为阅读的选择、为精神的发展提供一种可能。如此说来,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体,我们的形象都是我们自己所建构的,事情并不必然这样,而是我们选择的谈论造成了这种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