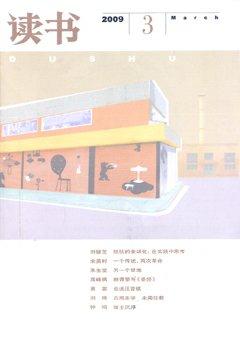上海的新娘与攻击的性格
张承志
两次旅行西班牙,我的背囊里都有堀田善卫的书。《西班牙断章》,还有《热情的去向》。对照着他的描写,我踏遍了安达卢西亚的处处古迹。那时我以为堀田善卫是一名专写西班牙或异国情调的作家,后来读了他的《在上海》,我才发觉,这又是一个中国通。
对鲁迅在一九三六年用日文写的、在日本尤其读者众多的《我要骗人》,堀田善卫尤有感触。
“单是自己一个人的过虑也说不定,要彼此看见和了解真实的心,……那固然是非常之好的,然而这样便宜事,恐怕世界上也很少有。这是可以悲哀的。……临末,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预感,算是一个答礼罢。”——在一九三六年当时,或在今日,能平然读过这文章的最后一行的,日本人也罢中国人也罢,恐怕是没有的。其间有血的历史……(《在上海》,121页,筑摩学术文库,一九九五年。引文为鲁迅自译的中文)
鲁迅的这段话,日文写得更加语感沉重。也许他的日本读者,对末句以血致礼的表达,读取了更多的信息?
其实鲁迅的预感,早已就是现实。五年前的“九一八事变”,已经把两国之间的险恶格局铸造完毕。预感的只是战火下次蔓延到哪儿——第二年,卢沟桥响起了日本全面侵华的炮声。
在日本知识分子中,可能唯有堀田善卫,彻底表白了一种——对中国的感情的苦恼。《在上海》的前言里,他的这段直抒胸臆,早就该被中国人讨论:
也即是说,所谓日本和中国、中国与日本一事,对什么文学或艺术之间关系等等提问,我总是说,有也罢没有也罢,那些不是我知道的东西。遇到了我它是这样的——不这么讲我无话可说:日本与中国的、在历史或未来、它的相交相关的方式,远不单是若国际问题那么冷淡的、外在的东西。与其说它是国内问题,莫若说它是我们一人一人的、内心和内在的问题。是我们文化自体的历史,不,甚至它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历史自身。这样,内在的问题其物,也就在它被称为问题的百色万端里,在最终,成了有最富攻击性格的东西。(《在上海·前言》)
这是罕见的披沥。就如鲁迅“以血”的添附,语言约束他难能尽吐心间的积郁。内心和内在的问题。它的执著,仿佛非要配上曲折三匝意犹未尽的、堀田善卫的长句!
或许这还是一个日语的表达丰富的例子。如此的曲折和直截,它于定音的最后一针见血,道出了日本人的中国情结:“最富攻击性格的东西!”不用说,即便排除政治的解释,单就一种感情的类型而言,这一表现,也足够令人震惊不已。
它是单向的,独属于日本人对中国的一方,而不能允许中国人对日本也照样情深意长。它是主观的,倔犟且稍有霸道,毫不在意对方可能还另有想法。它已经明言在先:它最富攻击的性格。
但这是一句真话。揣摩着它的真实感,对如此书写的堀田善卫,我摸索着对他尝试分析。对中国人来说,如此情感是陌生的,中国式的脑袋,装不下这么纠缠悖反的复杂性。保守的中国,使我们对他者的国度,思慕或敬远,总是自律越界的妄想。
它的过分,隐喻着施予对方的强迫。说到底仍不平等——既然被它深爱,那么作为对象的中国,已被夺去了拒绝的权利!
中国能够接受它么?否。深知这一点并为此而痛苦,便是堀田善卫的文学。虽然这痛苦的底色也印着文人的放纵——由母国强盛而被赋予的、占有的权利和主人的感觉。
唯因他是一个真挚的人,因着这种真挚,“最富攻击性格的东西”是可能弃留取舍、提炼珍藏的。真挚的证据同样留在文章里。《在上海》的如下一节,使我读得紧张。堀田善卫写道:
他在马路一边,眺望着一个盛装白纱的新娘子喜庆出门的场面。家人相送正在话别。这时,有三个戴着公用袖章的日本兵走来。其中一个突然分开人群,走到新娘子身边,一边伸出粗粗的手指,在那新娘子的脸颊上捅了几下,接着手又朝下,摸到了胸部和下腹……
他写道:霎时间,“我”只觉血涌头顶,不觉冲过马路,扑向那日本兵。结果“本来就无腕力、更一倍无谋的我”被日本兵打倒,拳脚交加。“我”的颧骨撞在水泥地上,旧病的肋膜被踢伤,最后,被新娘子的一家中国人扶起。
那个时候的新娘,恐怕过其一生,也不会忘记在那美好的登轿时分,被掀起婚纱、戳着脸颊,还摸弄了乳房和下腹的体验吧。哪怕那士兵也未必有过分的恶意——对于我,这已是一个出发点。(《在上海》,107页)
再没有别的文字,能比这一节解释得更贴切了:不顾一切扑向日本兵的“我”,深沉解说了堀田善卫痛苦剖白的、“内心和内在的问题”、“最富攻击性格的东西”。只是,那个被堀田宽容地说“也未必有过分的恶意”的士兵,他的“攻击性格”,也是滋生于这种放肆的、对中国的主人感觉!
而且他又是一个鲁迅的知音。
在俯拾满地的鲁迅议论中,这一小段可能捕捉鲁迅的文学特征最准确:
这改造社版的《大鲁迅全集》里,题作《社戏》的作品当时就为我喜爱。在十六年前的读书笔记上,我曾这么记着:“首先是,在鲁迅的(照片上),那双无言形容的、忧愁湿润的眼里,烙印着《故乡》和《社戏》的风景。既然已这么美好地描画了少年时代的回想,于是如《阿Q正传》、《呐喊》、《狂人日记》那般凄惨辛辣、令人毛骨然的现实,就必须要并列一旁。所以这两个系列表里一体,这两者,正是鲁迅的眼睛……”
在那以后经过了十六年,至今日我仍这么认为。(《在上海》,118—119页)
——话题一而再地涉及了鲁迅。
追究鲁迅逝后日本有过的鲁迅热,是一个深奥的命题。人们都知道,几乎鲁迅刚刚辞世,岩波书店的鲁迅全集便已出版。那时许多日本的名作家都在读鲁迅。堀田善卫,佐藤春夫,还是太宰治最富象征意味——他最终把鲁迅放置于自己小说中的“对席”。
然而我想,那个时期对鲁迅的接受与欣赏,藏着一直缄默的暗部。鲁迅对数千年吃人的中国礼教的控诉,鲁迅对中华民国蛮横暴政的倔犟抗议,鲁迅满纸晦涩黑暗悲哀的文笔,引诱了某种——同盟的一厢情愿。
一九三二年以后的鲁迅,择居上海,特立孤行,难与合作。他每日遣之笔端的、背景漆黑的描写和令人发的意象——诱导着多方的误读。
当日本国家加速侵略的步伐时,日本文人也向想象的鲁迅求索。这是国家发达携来的一种文学发达,就像日本的东洋学一样。鲁迅存在的暧昧,引诱了日本人的兴趣。
他们读得陶醉,自作多情。热烈且细致的、日本文人对鲁迅的偏重,最终显露了他们对中国复杂的估计不足。一条歧路,引出了一场相聚。他们在赞赏之中,误读了中国的异端。
中国的少数、中国的异端,古来依附着民族、家国与文化的大义。因此才有了皮之不存、毛其焉附的认识。
体察如此异端是困难的。
我对堀田善卫的在意,还因为他对西班牙的描写。
他走遍的西班牙的古今地点,我在十年间分做数次,也大都走遍了。最近(二○○八)刚补足了以前没去的马约卡群岛——堀田善卫就是在那座地中海的岛屿上,邂逅了一个受到同胞歧视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并慨叹人类的热情,常变做了排斥他人的狂热。
他从半岛的西北角徘徊到东南角,从圣地亚哥巡视到科尔多瓦,他的话题,从西班牙内战到穆斯林时代的辉煌,从建筑、美术到宗教、王室,涉及几乎所有西班牙问题。
与那些一下笔就歪向右派的写手不同,堀田善卫天生有着同情和正义的气质。他对宛如世界珍宝的科尔多瓦大清真寺的爱惜,对卡洛斯五世对这座大寺改建的“毒瘤”的尖锐讽刺,对圣地亚哥·德孔布斯特拉的狂热的反感,都使我惊奇和喜欢。他徘徊在格拉纳达红宫里,对着满壁的阿拉伯文字和花纹装饰吐露的人生感悟,使我深深感动:
在科尔多瓦或格拉纳达,我发觉自己总是被某种淡淡的悲哀感觉控制着。那悲哀,我想也许由两方面的东西组成。
一是每逢一事,总痛感自己文明享受能力的狭窄。
还有另一方面的感慨。那就是——无论从青春时代就与之相遇的西欧文明,还是采取与之竞争形式的亚非等国所谓第三世界文明——对它们的关心,混合着自己内在的、对美与艳的要求,这一切,难道要把流年六十的自己,领到最终为之迷恋的地方去么?……(《西班牙断章》,195页)
当我在他的书里发觉:因为缺乏一点阿拉伯语知识,他最终没能知晓阿兰布拉宫里满壁铭文的意思——我的遗憾无法形容。想象着他,我这么表达过:
而在堀田善卫的两本书里,我没有读到关于胜者铭文的段落。
我不太敢相信。
十数年时光孤注一掷,从巴斯克的小村到格拉纳达的阿尔巴辛、一连十几次住进西班牙,那样地倾倒于这个国度难道会不知道这句铭文?……若是真的就太可惜了。但字里行间的信息,又使我觉得这不是不可能的。
我心里浮起一种难以名状的同情。堀田善卫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不仅心怀正直,而且具有超人的敏感。……
……“痛感自己文明享受能力的狭窄”,“到最终为之迷恋的地方去”,他竟然这样剖白表露。在日本滞留时没有认识他真是遗憾。我理解他的每一个字,可惜在中国难得这样的朋友。在阿兰布拉的时间若是能与他共度,若是我们能谈谈对那句铭文的感受,该是多么好啊。(《鲜花的废墟》,新世界出版社,261页)
再打听时,得知他早已去世。如佐藤春夫一样,又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在反思自己一生之前,先期离开了我们。
仿佛我们从未有过交流。包括这些人:佐藤春夫之于唐宋古典、高桥和巳之于先秦刺客、堀田善卫之于上海、竹内好之于鲁迅——日本与中国的千丝万缕,使知识分子习惯了中国这一自己的文化资源,并陶醉于一种拥有者和享受者的自信。只是,用堀田善卫的话说,它带着一种“攻击的性格”。这种攻击或狂妄的性格,不意伤害了他者的人心,招致了拒绝。
零散记下的日本文学读后感,写到这里就该停下了。在结束对佐藤春夫、太宰治、堀田善卫的一鳞半爪的随笔时,还有什么该说的呢?
附在新潮社版《惜别》后面的、奥野健男的“解说”里,如下的一段追忆,写的简直不像日本:
太平洋战争时期对日本文学、对几乎所有的文学人都是痛苦的受难时期。在一种以军部为中心、包括一切国家权力、治安当局、情报部门、言论报国会、右翼团体以及全体庶民的狂热爱国的时代风潮的压迫之下,文学人丧失着自由灵魂与表现,随之萎缩。否,迎合当局和时代风潮进而从事御用文学的作家,自行投身军国皇国的狂信、为权势消化的文人,更已出现。昨天的文学伙伴,亲密编辑,都已变得没有信用。一个彼此猜疑的时代……
我读着恍如入梦,那一句句引人堕入冥思。历史的相错,环境的差异,不该如此逼真的类近。他们不是处在近代文学已然充分发达的时代么?难道不是经济的底盘,已然足够地刺激了文学的发育么?
文艺杂志纷纷废刊,统和于国策刊物。发表文学工作者的作品的舞台,极度地缩小了……残存唯有的发表作品的途径,是写成单行本。比起证照制度严峻的报刊,(单行本的)审查眼光稍显松弛。那些生不逢时又不写小说就活不下去的文学之虫、所谓执著与斗志旺盛的一些人,只能在不太出名的出版社,直接写了就出——用这种形式继续着文学活动……(《惜别·解说》,379—380页)
这描写的怎能是日本!……掩饰着心底的惊呼,一遍遍读着,我遐思疾飞,又噤口无语。
纠缠于纯文学的话题,是标榜高雅的习气。我只能说,恐怕中国文学还会长久缺乏——余裕充盈的“私小说”。恐怕还会有不少鲁迅式的——半纸心事半纸抗议的文字,呈着一副粗糙的样相。
纯文学的讨论以及艺术诸般,尚需缓行。一个民族要跋涉的文学路,尚要一步一步,数过他人不知的崎岖。中国大约仍是散文的国度。因为救国的老调,依然弹它不完; 因为命途多艰,小说的大潮尚未临近。使外人心仪的风花雪月,埋在文字的深奥,蓬勃尚待一些时日。
如果日本选择石原慎太郎,日本文学将堕落为帝国精神的粉饰。而中国文学选择什么呢?环顾左右,我们的文学,尚处在受辱的时代。
所以我想高呼: 且慢文学的浪言,先让我们立意自律。莫谈文学!唯谨慎对他人的冒犯,哪怕退守文学的敬远。
我们不想强求任何人,去认识中国文学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远较他们判断的更大。这不意味着居傲自诩。我只是说:文学的可能性,只在于依靠着他人想象不足的文明,只在于怀抱着激励永久的痛苦。
只是有时,当偶尔读到他们的美文,如佐藤春夫对石原的淋漓呵斥时,心中便难免升起一种不尽的遗憾。惜别——总是意味着强要的忘却。它留下了背影,长怀着创痛。又是堀田善卫写得出色:
若是能相互忘却,或者能学会这么做的话,我是想学的。于我而言,不快的事不愿说也不愿写,毋宁想,真的深深沉入缄默。但即便如此,还有叫做不可忘却的酸楚,它便是日本和中国交往的根本。我们互相握手时,在手掌和手掌之间,渗出的是血。(《在上海》,60页)
在贫瘠的大陆上,蹒跚独行着我们的文学。
如他们的揶揄,长旅中我们还背负沉重的枷锁、官僚的遮蔽,及失败的历史。但文学不是卑贱也不是虚妄;唯独对文学而言,过多的胜利和骄傲,会诱人步入危险的泥潭。我们自有前定的路;虽然举步维艰,我们不仅能求助于古典,而且能正视——纠正虚妄的傲慢。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