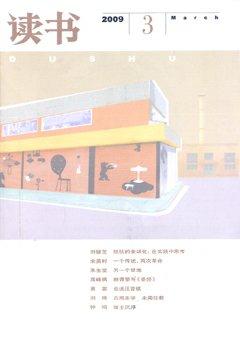古闻来学 未闻往教
刘 炜
一九三七年九月,淞沪会战失利,上海沦陷,日寇进逼杭州,马一浮(一八八三—— 一九六七)携外甥丁安期和弟子王星贤两家,共十五人,避寇南迁,辗转流离半年后,至浙江开化,再欲避难赣中而不得,处境十分困窘。马一浮迫不得已,写信求救于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时浙大已迁至江西泰和,希望竺能帮助觅车觅屋,转徙江西。竺可桢心领神会,不计前嫌,决定由浙大“收容”,聘马至浙大开设“国学讲座”(《竺可桢日记》第一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209页)。马于是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抵泰和,四月九日“国学讲座”开讲,讲稿题为《泰和会语》。一代大儒马一浮,终于结束三十年的隐居生活,出斋讲学于现代大学之内。
马一浮在一八九八年与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等同应绍兴县试,中榜首,为绍兴著名乡绅汤寿潜(后任民国浙江第一任都督、交通总长)激赏,招为东床。 一九○三年六月,应清政府驻美使馆聘,赴美国圣路易斯留学生监督公署任中文文牍,并兼任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秘书。一九○四年五月,离美赴日本,在日本停留半年后,十一月回国。此后,长期隐居杭州,闭门读书,不涉时事。
一九二一年,民国初立,蔡元培长教育部,邀马一浮往南京,担任教育部秘书长。马到职不足三周,便向蔡元培表示“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挂冠而去。马之辞职教育部,并非如他所说,而是在根本上不赞成蔡元培所推行的教育变革。多年以后,马回忆这段经历说:
南京临时政府收罗人望,拟以(汤寿潜)为交通总长,以蔡孑民长教育。蔡君邀余作秘书长,余至而废止读经、男女同学之部令已下,不能收回,与语亦不省。又劝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甄选宁缺毋滥,优给廪饩,供给中外图籍,延聘老师宿儒及外国学者若干人,分别指导。假以岁月,使于西洋文字精通一国,能为各体文词,兼通希腊、拉丁文,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国本初张,与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后,必有人材蔚然兴起,此非一国之幸,亦世界文化沟通之先声也。蔡君河汉吾言,但云时间尚早,遂成搁置,而余亦去。时方议定学制,欲尽用日本规制为蓝本,为荐叶左文、田毅侯为备参订,亦不能听。使通儒院之议见用,于今二十六年,中国岂复至于此?今则西人欲治中国学术者,文字隔碍,间事译,纰缪百出,乃至聘林语堂、胡适之往而讲学,岂非千里之谬耶?(《马一浮集》第三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1084页)
蔡元培教育变革的宗旨,在反对尊孔、废止读经,彻底摆脱传统儒学教育的影响,以日本教育体系为参照,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而马大概在一九○七年前后,就已确立了致力儒学的学术志向。因而他不但反对蔡元培的废止读经,还进一步建议创设通儒院,弘扬儒学,以培国本。但蔡元培的教育变革乃大势所趋,传统儒学教育终被废除,而现代学校教育通行全国。马欲以儒学兼济天下不得,只能回西湖以儒学独善其身,成就了近代中国的一位“隐士儒宗”。
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又一次想到马一浮,邀他往北大任教。马回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八字电文,拒绝了蔡的邀请。马的意思是说,中国教育的传统是学生来就老师受业,而不是现在这样老师去学校教授学生,其反对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在随后写给蔡的一封书信中,马详细说明了自己不能往北大任教的原因:
承欲以浮备讲太学,窃揽手书申喻之笃,良不敢以虚词逊谢。其所以不至者,盖为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撰。今学官所立,昭在令甲。师儒之守,当务适时。不贵遗世之德、虚玄之辩。若浮者,固不宜取焉。甚愧不能徇教,孤远伫之勤。幸值自由之世,人皆获求其志。委巷穷居,或免刑。亦将罄其愚虑,幽赞微言,稽之群伦,敬俟来哲。研悦方始,统类犹乏,以云博喻,实病未能。若使敷席而讲,则不及终篇而诟诤至矣。(《马一浮集》第二册, 453页)
一方面是“研悦方始,统类犹乏”,自己的学术思想(即马一浮的六艺论)还没有成熟;另一方面,则主要是现代学校教育一味趋新务时,遗弃传统儒学,与自己平日所学不合。所以宁愿“委巷穷居”、“幽赞微言”,继续做隐士、讲儒学。一说,蔡元培请马一浮,是到北大任文科学长,蔡元培请不到马一浮,改而邀请陈独秀,这才有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此说若属实,那么一九一七年的蔡元培邀请马一浮,倒颇具象征意味,它是近代中国知识阶层彻底抛弃传统儒学、全面接受现代新文化之前的最后一次深情回眸。
一九二九年八月,陈大齐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上任伊始,即力邀马一浮前往北大任教。又请马的好友邓伯成、邓叔成兄弟和马叙伦等人代为劝说。在回复马叙伦的信中,马详细说明了自己辞谢陈大齐的原因:
久谢人徒,遂成疏逖。迩者陈君百年以讲学见招,亦既电辞。未蒙省察,乃劳手书申譬,殊愧无以堪任。夫学有诸己,岂不欲转喻诸人。然义在应机,亦非一概。故道逢尹喜,始出五千;退老西河,乃传六艺。感然后应,信然后从。是知教化所由兴,不必尽在明堂辟雍也。今儒术方见绌于时,玄言亦非世所亟。乃欲与之扬周鲁之风,析夷夏之致,规改错,则教不由诚;称性而谈,则闻者恐卧。以是犹疑未敢遽应。虽菏敦勉之切,虑难仰称所期。与其不能解蔽于一时,吾宁俟悬解于千载耳。希为善谢陈君,别求浚哲,无以师儒责之固陋。(《马一浮集》第二册,455—456页)
马说,“夫学有诸己,岂不欲转喻诸人”,自己并非不想出斋讲学。但现代学校教育既已罢黜儒学,自己违背潮流以宣讲之,只怕闻者恐卧,不能应机。陈大齐心有不甘,一九三○年再次相邀,希望马能往北大担任研究院导师。这一次马亲自回信给陈说:
乌君来,奉惠书,不遗鄙远,以大学方拓研究院,欲使备员导师。但有牖启之责,初无讲论之劳。是所以待名儒显学,浮愚,何以当之。方今学子务求多闻,则义理非所尚。急于世用,则心性非所先。平生粗究始终,未尽玄微。耻为一往之谈,贵通天下之志。亦知语默道同,物我无间,酬机赴感,教所由兴。但恐无裨仁贤厉学之心,不副髦俊研几之望,是以未敢遂承,匪欲自隐其陋也。若谓孟荀亦预稷下之游,生肇并集逍遥之肆。备鸿都之礼乐,四裔犹愿来同;萃观听于桥门,严谷不容自远。处以学职,则余病未能,暂接清言,则犹或可逮。亦须干戈载戢,弦歌无虞。虽不设与皋比,将无辞于游履,但今殊未可必耳。此乃诚言,非为虚让。率尔奉答,诸维朗照,不宣。(《马一浮集》第二册,516页)
马说,现在的学生只求多闻博识和经世致用,儒家心性义理之学则非其所好,自己前去讲学,恐怕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对他们有所裨益。但在这封信里,马非常隐微地提出了一个新办法,就是像孟子、荀子往齐国稷下学宫和道生、僧肇往后秦逍遥园自由讲学一样,自己可以往北大与陈大齐等学者,相与论学,自由讲道。也就是说,自己可以往北大讲学,“暂接清言”,但须独立于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之外,不“处以学职”,不受其制约和束缚。但可惜的是,陈大齐似乎未能洞悉马的微言大义,没有按这一办法邀马前往北大讲学,错失了时机。
马一浮可以在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之外,往现代大学独立讲学的隐微想法,在一九三六年面对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时,非常明确而具体地表达出来。一九三六年四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到任不久,就得知马一浮乃杭州“瑰宝”。经人介绍后,两次登门拜访,希望马能至浙大讲国学。又托马的好友王子余代为劝说。马在回复王子余的信中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惠书具道竺君藕舫见期之意,久而未答。良以今时学校所以为教,非弟所知。而弟平日所讲,不在学校之科,亦非初学所能喻。诚恐格不入,未必有益,不如其已,非以距人自高也。今竺君复再三挽人来说,弟亦不敢轻量天下士,不复坚持初见。因谓若果有学生向学真切,在学校科目系统之外,自愿研究,到门请业,亦未尝不可。此实勉徇来教,不欲过拂竺君之意。昨竺君复枉过面谈,申述一切,欲改来学为往教。为体恤学生计,此层尚可通融。但竺君所望于弟者,谓但期指导学生,使略知国学门径。弟谓欲明学术流别,须导之以义理,始有绳墨可循,然后乃可求通天下之志。否则无星之秤,鲜有不差忒者。群言淆乱而无所折衷,实今日学子之大患也。若只泛言国学,譬之万宝全书、百货商店,虽多亦奚以为?且非弟之所能及也。此意竺君如以为然,能喻之学生,使有相当了解,然后乃可与议。否则圆凿方枘,不能收教学相长之效。与竺君相见两次,所谈未能尽意。在竺君或以为弟已肯定,然弟实疑而未敢自任。不欲令种子断绝,此天下学者所同然。虽有嘉谷,投之石田,亦不能发荣滋长。故讲即不辞,实恐解人难得。昔沈寐叟有言,今时少年未曾读过四书者,与吾辈言语不能相通。此言殊有意味。弟每与人言,引经语不能喻,则多方为之翻译。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处今日而讲学,其难实倍于古人。师严而后道尊,道尊而后民知敬学,亦难责之于今。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吾行吾素而已。竺君不以弟为迂阔,欲使诸生于学校科目之外更从弟学,大似教外别传,实为特殊办法。弟之所言,或恐未足副竺君之望、餍诸生之求。其能相契,亦未始非弟素愿。若无悦学用力之人,则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此当视诸生之资质如何,是否可与共学,非弟所能预必,非如普通教授有一定程序可计日而毕也。故讲论欲极自由,久暂亦无限制,乃可奉命,否则敬谢不敏。此意当先声明,并希代致竺君谅为荷。以左右与竺君相望之意甚诚,故坦直奉答,不敢有隐。(《马一浮集》第二册,517—519页)
马说,他可以接受竺可桢的邀请,往浙大讲国学,但是有条件。首先,自己的讲学应独立于学校科目系统之外;其次,自己的讲学,并非泛言国学,而是要讲儒家的义理之学。这其实是从体制和宗旨两方面,对自己的讲学做了规定,两方面都不同于现代学校教育。在现代学制之外讲儒学,乃马之“素愿”,他甚至还兴致勃勃地为竺校长代拟了《浙江大学特设国学讲习会之旨趣及办法》。但在随后的几次磋商中,竺可桢和浙大同人却对马讲学的名义和名称表示了反对。《竺可桢日记》记载了此事:
九点至青年路晤张圣征,应子梅之邀谈及马一浮事,适圣征之兄天汉亦在座。据张云一浮提出一方案,谓其所授课不能在普通学程以内,此点余可允许,当为外国的一种Seminar(研究班课程)。但一浮并欲学校称其谓国学大师,而其学程为国学研究会,则在座者均不赞同,余亦以为不可。大师之名有类佛号;名曰会,则必呈请党部,有种种麻烦矣。余允再与面洽。(《竺可桢日记》第一册,47页)
马坚持以“大师”,而非“教师”或“教授”的名义讲学。其讲学的名称为“国学讲习会”,而非一般的课程名称如“国学讲习”或“国学研究”。竺可桢等人认为,“大师”之名有似佛号,于现代学校不类,课程为“会”也非现代学校所有,须呈请政府批准。正如竺可桢虽然可以允许马所讲授不在普通学程之内,但以之相当于外国的一种Seminar(研究班课程),其实还是把马的讲学纳入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之内一样,竺可桢等人反对“大师”的名义和“讲习会”的名称,仍是不能接受马欲讲学于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之外的独立姿态。竺可桢建议马取消“国学讲习会”之“会”字,马则坚持己见,双方互不相让。在马看来,自己不能讲学浙大,“于弟毫无加损”(《马一浮集》第二册,519页);在竺可桢看来,自己“对于请马一浮,可称仁至义尽”(《竺可桢日记》第一册,48页)。
回到本文开头,马一浮和竺可桢的僵持,在一九三八年初打破。患难之中,马不再坚持“国学大师”的名义和“国学讲习会”的名称,接受“国学讲座”一名,竺则同意马讲学于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之外的要求,给予充分的讲论自由。在写给妻弟汤孝佶的信中,马说明了自己讲学浙大的原因:
所以来泰和之故,已具前书,又于答韦存书中亦详言之。左文亦颇以弟为不智,谓今日岂复尚有讲学之事。弟以为钧是人也,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其见接也犹若以礼,是可与也;若逆计其不可与而遂绝之,非所以待人之道。其词曰:可以避地,可以讲学。吾方行乎患难,是二者固其所由之道也。非以徇人而求食,乐则行之,忧则违之,不居学职,则去住在我;不列诸科,则讲论自由。羁旅之费取足而止,义可受也。彼中诸友以前年曾一度相要,颇能了解弟意,故待之以客礼,略如象山白鹿洞故事。来此匝月,亦颇相安。(《马一浮集》第二册,557页)
讲学于浙大,当然首先是为了避难,但讲学也的确是其心愿。而关键所在,还是浙大同人能待之以礼,他的讲学不居学职、不列诸科,不在学制系统之内,略似陆象山之讲学于白鹿洞。马之所以将其讲稿称之为“会语”,也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国学讲座”比作了宋明书院的讲会,“用明人讲学例,且示不在学官所立之科也”、“不在学校系统之内”也(《马一浮集》第二册,823、848页)。也就是说,马之所以讲学浙大,根本原因还是自己虽在现代大学之内,却又能超然独立于现代学校制度之外。但讲学浙大毕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避难,难免有“徇人而求食”之嫌。且身在大学之内,也难保不受学校制度的干扰。而自己讲儒家心性之学,似乎也激不起现代学子的兴趣。马写信给熊十力说:
古德云:“门庭施设,不如入理深谈。”弟今所言,但求契理,不必契机。佛说《华严》,声闻在座,如聋如哑。孔子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此虽圣人复起,直是不奈伊何。吾纵不惜眉毛拖地,入泥入草,曲垂方便,彼自辏泊不上,非吾咎也。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吾亦称性而谈斯已耳。且喜尊兄证明,言固不为一时而发。承告以方便善巧、曲顺来机之道,固亦将勉焉,冀饶益稍广。然此是弟所短也。弟在此大似生公聚石头说法。翠严青禅师坐下无一人,每日自击鼓上堂一次。人笑之曰:“公说与谁听?”青曰:“岂无天龙八部,汝自不见耳。”弟每赴讲,学生来听者不过十余人,诸教授来听者数亦相等,察其在坐时,亦颇凝神谛听,然讲过便了,无机会堪辨其领会深浅如何,以云兴趣,殊无可言。其间或竟无一个半个,吾讲亦自若。今人以散乱心求知识,并心外营,不知自己心性为何事。忽有人教伊向内体究,真似风马牛不相及。弟意总与提持向上,欲使其自知习气陷溺之非,而思自拔于流俗,方可与适道。此须熏习稍久,或渐有入处。今一暴十寒,一齐众楚,焉能为功。然彼不肯立志,是伊辜负自己。吾今所与言者,却不辜负大众,尽其在己而已。(《马一浮集》第二册,529页)
这一契理而不契机、似聚石头说法的尴尬寂寥场面,使马在浙大的讲学了无兴味。凡此种种,决定了马不可能长久滞留浙大。
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持“中国本位文化”说、大力提倡中国固有道德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有心恢复宋明书院的讲学传统。而当时在重庆政府部门任职的马一浮私淑弟子刘百闵(时任陈立夫秘书、中国文化服务社社长)、及门弟子寿毅成(时任官商合办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从旁赞议,希望能由自己的老师来创办书院,讲授中国传统文化。陈立夫、蒋介石等人对马一浮的大名早有所闻,亦极仰慕,于是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邀马入蜀办学。对马来说,跳出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直承宋明书院讲学的传统,自由而独立地讲习儒家义理之学,正是自己长久以来的心愿,虽然并不看好书院的创办,犹豫再三,但最终还是接受了邀请。经过半年的往复商讨后,马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八日离开浙江大学(时在广西宜山),乘交通部专车经贵阳至重庆,再转至四川乐山。又经过半年的筹备,复性书院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在四川乐山乌尤寺开讲,复性书院正式诞生。当然,马一浮在复性书院也远非称心如意,那一段不开心的往事,其实和上面所讲马一浮和现代学校教育反反复复的纠葛一样,颇有意味,不过那是另一篇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