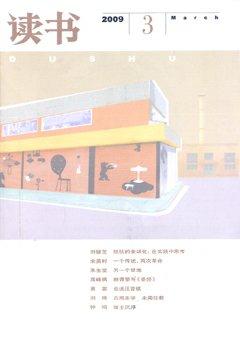蜗牛,不见得比鸟慢
钟 乔
多年以前,基于对亚洲民众戏剧的热衷追求,经常往返于台北——菲律宾之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从一位民众戏剧组织工作者的手边,拿到一本实务操作的小册子,前言是一则寓言,大抵是这么说的:
一个夏天的午后,林鸟不意间瞧见树下有一只缓缓爬动着的蜗牛。
林鸟便问蜗牛说:“我让您三个月时间,我们从这树下到森林外的另一棵大树下,看谁比谁先到达,您觉得如何?”
“我……我……”蜗牛一时答不上话来。
“怎么样,我是为您好,让您老先生赶得上时代的快速步伐啊!”
“好,要比就来比!什么时候开始?”一经刺激,蜗牛也鼓起勇气大声嚷嚷起来。
“就从现在开始啊!”小鸟于是跷起二郎腿,在林梢间找个舒服的姿势躺下身来。
这以后,小鸟便愈加悠闲地在林梢或玩耍、或休息,为的就是给林间的鸟兽虫蛾们,宣告自己即将得来的不费吹灰功夫的一场胜算。
三个月时间过去了!
就在距离相约时刻的前十五分钟,小鸟打了个哈欠,才从悠哉的睡梦中醒了过来,心想凭自己的飞翔速度,只要十分钟就可以抵达终点。那么,就飞去等候铁定懊恼地还在慢慢赶路的蜗牛吧!
小鸟不到十分钟时间,就飞到目的地了……没想到,令它懊恼的事才刚上场呢!因为,蜗牛早已躺在大树下等候小鸟的到来了!
“怎么可能……是你比我先到呢?”小鸟气急败坏地在大树间生着闷气地嚷嚷着。随后,扑着闷声不响的羽毛,一溜烟地从森林里消失了踪影。
如果说, 龟兔赛跑的寓言,是骄者反被自身的“傲慢”打败的话。蜗牛和林鸟的竞赛,却有更令民众戏剧工作者省思的地方。因为,就在这时,蜗牛说着,“可别小看我们了”。
“我们?怎么会是我们?”林间有声音这样问。
“是啊!是我们一群蜗牛们啊!”数以千只计的蜗牛们,一起轰轰然地大笑起来……
这时大伙儿才恍然大悟,原来在过去的这三个月时间里,蜗牛每逢寸步遇上另一只蜗牛,就要后者往前传递比赛的讯息,而后,再由后者传递讯息给另一个后者,从无间断,直到森林外大树下的那只蜗牛听到讯息为止。
为了这一整趟讯息的传递,大约耗去了蜗牛两个半月的时间。
因此,终点处大树下的这只蜗牛,已经在大树下等着小鸟的到来,足足有半个月之久的时间了!
故事说完了!但,寓言尚未结束哩!怎么说呢!
因为,这样的寓言故事,用来比喻小区民众戏剧的推展,有其恰到好处的地方。原因恰恰在于,发生于民众间的戏剧,并非单纯只为演员训练的艺术性而来。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剧场的互动机制,在人与人之间展开对话,并进而寻找到关切公共议题的可行性。民众不是抽象意义下各自存在的个体,而是相互联结的共同体。
同时,民众戏剧通常会较有意识地去面对处于弱势状态下、被称作“文化沉默”现象下的人们。这时,他们就不会是处于精神及物质皆居优渥状态的社会阶级。换个比喻,就像是寓言故事中那只自鸣得意的林鸟。不是林鸟。那么会是蜗牛!
的确,也不妨这样来指向。因为,蜗牛总是慢,总是在主流价值外踽踽而行。重要的是,一旦联结的时机到来,却也不会是等待着被施舍、被超越的对象。他们像通风报信的蜗牛,相互亲切地告知彼此的所需及拥有,让资源以“我们”的姿态具现在“个人”的独领风骚面前,并有技巧地赢得一场赛事。
要叙述“我们”,在实质的界面上,首先得去厘清的是:“我们”是一群没有经历过共识的培力,而排排站或排排坐在一起的人吗?当然不是。相反,“我们”是一群在视线上能彼此看见,在听觉上能相互听见,在身体的触觉上能相互触到体温的人们。
这样的人们,走进工作坊的空间,就成了民众剧场中的民众。民众在对话的场域中,认识到单向沟通的对待,是为了制造规训空间。如果,想从规训中出走,只有创造对话空间一途。
在这里,我们处理到一个核心问题。亦即:民众是在剧场中经由对话而联结的。但,对话经常被误读为相互矛盾的弥合。在思维的层次上,矛盾恰恰得经由对话而被揭发,才有可能在公共性面前往前推进一步。当然,对于大多数有过民众(或小区)剧场经验的人,包括参与者、组织者及辅导人在内,都一定心知肚明,这样的思维,通常在实践的层面上,是最具挑战性的一环。特别在为营造良好氛围的小区业务中,找到愿意参与的伙伴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若要揭发矛盾,岂不平添怨怼、伤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和气,不是吗!
因此,这是很难碰触,又似乎非得去碰触不可的事情。但,在时间中培养耐心,是必经的过程。
这个问题的原始出发点,还是得回到寓言中的蜗牛。当我们说,蜗牛比喻弱势者,便也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上,须要经由共同的力量去争取更多的平等。因而,蜗牛有别于蝴蝶。蝴蝶比较类似追求市民社会美好想象的小区产能者。在此,当然没有贬抑蝴蝶或张扬蜗牛的意思。只不过,就事实的层面而言,似乎也无法回避这样的判断。而恰恰也是在这样的判断下,我们发现,蝴蝶之间的对话,较多围绕着如何塑造芬芳空气,而蜗牛得为争一口气地活着而展开串联。这是他们对话的本质。对于模拟于蜗牛这样的小区或社群的民众,巴西教育哲学家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在《受压迫者教育学》一书中,精辟而深刻地说:“既然对话是对话者之间在共同进行反省与行动时的邂逅,当它向世界传达时,世界即成为它所欲改造与进行人性化的对象。”他说得太深了吗?在我看来,倒不是“深”不“深”的问题。而是这席话语因其思想的重量,恐会让蝴蝶无法展翅轻飘;至于蜗牛,则时时刻刻都不免是要扛着这样的重量,朝森林外的大树下缓缓地爬行与对话,否则,一个不小心,就要被鸟语花香给呛得失去了仅有的泥泞了!
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到底如何在小区的组织性或剧场的艺术性中,展开这样思想倾向性的对话呢?这其实是成人教育对民众剧场的一项挑战。
坦白地说,述说不难清楚;要命的在于,论及实践,则不比攀一座大山容易。理由仅仅在于,诚如弗雷勒所言:“对话是一种认知的方式。”因为,认知本身和问题意识的养成相关,而问题意识通常都隐藏在公共与私自生活的灰色地带,不经挖掘,不会轻易现形。
在小区剧场工作坊中出现的许许多多的案例,让我们有机会从民众身上学习到,如何从微观出发,去探讨具有公共面向的问题意识。这样的作为,是为了实现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举例而言,民众总会在脸上挂个问号,问道:“婆媳不和谐是问题吗?邻居之间有微词,是问题吗?”作为辅导人,首先,当然要接受这些都是问题。但,更要提醒,“这是切入问题的最好方法”。因为,我们就是要通过切身的问题,去找寻和小区公共议题相关的问题。所谓,知其然,再知其所以然。这是从一粒沙看世界的不二法门。当我们往前推进一步,将问题意识带到剧场中来,对话的认知方式又和身体的表述不可切割,那么,我们就得面对剧场和小区双重的问题了。
这些年来,在小区或社群主持民众戏剧工作坊的经验,让我有机会这样表述剧场与小区的对话关系。我的基本想法来自“empowerment”这个字眼。它一般被译作“培力”;但,也不妨翻译为“使能”。亦即,在对话式的教学工作坊中,充分实践双向交流的有机性,免于单向的上对下的灌输关系。教者使习者能,也从习者身上学到使自己能的各种可能性。
在此前提下,剧场或其他文化元素,不再仅仅为表现而存在。却以过程来呈现empowerment的重要性。重要的是,无论“培力”或“使能”,都需要一套方法,借由工作坊的操作,让参与者从个人的认知出发,和团体形成情感与知性的共识,而后,借由剧场的方式表达出来。
我们得以这样来想象,亦即,在小区或社群中,存在着一般的民众。如果,换作在剧场的空间中,这些民众也就是习惯于观看而不表达的观众。然而,经由组织关系的运作,民众(观众)走进了工作坊中,运用身体来厘清自身和别人的问题意识,并形成团体的共识。如此一来, 民众(观众)因着在工作坊中的相互对话,而走进了民众戏剧的美学空间中,进一步形成了戏剧的元素。这时,观众终于从观众席站了起来,迈向剧场并转化为演员。
巴西民众戏剧先行者波瓦(A.Boa),也是人称“被压迫者剧场”的创始人。形容观众从spectator转化为演员actor的过程中,得先作为一位“观演者”(spect—Actor)(即,英文中“观”和“演”的合字)。我想,这便是重视工作坊过程的对话机制。换言之,民众戏剧不单单仅为表演的艺术性而存在,如何形成表演的互动过程,是民众前来剧场相见的动机和目的。
总的说来,剧场作为一种社会论坛,如何在小区或社会弱势民众间展开身体与意识的对话,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而对话的产生,是为了揭示问题的本质,或者说,是在破除一元式教化的教习情境下,推进参与民众对问题意识的提升。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工作坊的方法论中,固然应免于因技巧化而失去有机的脉络。但,随时调整对话关系的有机性,却是保证能更有成效地呈现精神内涵的前提。
方法与脉络的辩证,通常出现于辅导者(facilitator)如何灵活运用沟通技巧,导引参与民众以最简单的方式厘清自身与伙伴间到底是处于哪一种状态中,是各说各话,还是强势(说者)对弱势(听者),或者相互对话。
应该不难理解,围绕着民众剧场与社会实践的关键议题,是剧场如何介入现实,而现实又如何介入剧场的辩证关系。此一辩证关系的建构,可以在以世界为中介的人与人的“对话”中找寻到切入点。从而,让“培力”或“使能”不再只是话语上的述说,而有实质上的意涵。
现在的重点是:对话的重要,是因应着行动者之间往返于行动——反应——再行动的辩证机制而来的。这其间,行动——反应的互动,其实持续处于流动状态中。就像剧场中的演员,永远在行动中寻找反应,又在反应中找到下一个行动的动机。如此,在民众剧场里,行动者是演员;在小区或社群中,行动者就是民众及组织工作者。只不过在民众剧场的范畴中,比较有系统地处理了观众如何穿过一条有方向性的路,从小区中被动的旁观者转化为主动的表达者。如果我们用剧场的空间思维来想象,就是从观众席到舞台的过程。这过程,在实务上,便是在工作坊的时空中发生的。
保罗·弗雷勒殷殷企盼,经由对话的开展,弱势者得以对世界重新命名。这是他在《受压迫者教育学》中,对于人性变革与改造的核心思维。
在这里,剧场推出了一个解放的空间,让民众在其间为自己的身体、情感、意识、想象“命名”。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空间中,却也铺陈着一趟从理论到实践的旅程。
许许多多的案例警示着我们,“命名”的旅程,在实务上,不免为民众、组织者和辅导人之间带来了焦虑感。通常,焦虑的发生,来自于组织者和辅导人善意地为民众彰显了“命名”的正当性或正义感。但,民众的需求,却是现实的问题如何被解决。这时,正义感非只失去了正当性,而且造成两造之间有形或无形的焦虑感,彼此拉扯,终至无法收拾。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澄清:“民众为个人或群体重新‘命名,终究是民众戏剧的动机和目的,可是,从动机到目的,有一趟转化的旅程,却是关键的要点。”就是在这样的旅程中,有了对话的发生。
是在这样的想法下罢!当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过后,曾经接到许多关心灾区心灵重建的大陆NGO工作者及民众戏剧团体的来信,殷切期盼“差事剧团”或我本人能够赴灾区主持民众戏剧工作坊,达成灾民心灵重建的目标。
会有这样的期盼,自然和台湾“九二一”大地震后,“差事剧团”在石岗和后来的“石岗妈妈剧团”开辟工作坊,并推动小区剧场的实现有关。
将民众戏剧作为一种疗伤的方法,实现在受灾难所侵袭的民众身上,除了热诚之外,亦深感责无旁贷。或许,也因为如此吧,对于如何与受灾民众重新为苦难的人与土地“命名”,却有了更多的省思。
在几次的座谈会上,我首先表达了对于将我和”差事剧团”的地震灾区工作坊视作某种典范的焦虑感。这么说,无非想表达作为辅导人的我们,自始至终,其实都只是灾难事件的“中间物”,亦即,并非以启蒙的姿态,为民众带来了如何非比寻常的结果或答案。这,非关谦虚,只是事实。
进一步,我表示,多年以来,虽然作为“差事剧团”一员的我,运用了民众戏剧在“石岗妈妈”身上展开了长久的对话。但,既是对话,就表示身为辅导人,不应也不恰当一直处于“代言”的位置。简言之,在相互对等的关系下,仅因提供这项经验,或许对于想前往四川震区进行文化实践的大陆朋友有些许参考作用,才有种种的发言。这发言的主体性,最终,还是要回到石岗妈妈或其他曾参与此一过程的民众本身。
最后,我以为,天灾导致人们流离失所,协力心灵重建自有其当下的必要与必然,只是,如果“必要”只因工作者有一项业务得去消化申请来的预算,长久下来,施舍的上对下关系不会被打破。如此一来,民众戏剧中强调的文化知识人与工农劳动者相互学习的情境,永不会被具现。再有,如果“必然”只是前去进行工作的辅导人一厢情愿的话,非止造成受灾者被“善意”所压迫,更容易让辅导人因无法收到立即的成效而陷入焦虑的状态中。
这样的表达,无非在述说着,“命名”是由组织者、辅导人与民众共同疏理出来的一条从论述到实践的旅程。如果将旅程比喻为河流,则其间充满着各式各样的激流和险滩,最终,在河的彼岸,长着一棵小区或社群的生命树,分别标示着:
代表着动机(或出发点)的树根,意味着现况如何的树干,象征着资源的树叶,以及具现着成效的果实。.
并且,彼此永远在询问着:
相聚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树根?)现况又如何?遇上的具体困难是什么?(树干长得如何?)有什么正面及负面的资源,如何善用及取舍?(树叶风貌如何?)如何评估具体成效?(果实累累或稀落、丰厚或病瘦?)
民众要在自身的探索与追究中,去找到共同发声的身体语言和声调,这是民众戏剧工作者的职志以及共同的明白和体会。面对这样的召唤,诚然责无旁贷,然则,更多的时候,于我而言,则不免是在职志的光明面前,因着自身精神性的软弱,又或常存对未来理想的既坚持又质疑的矛盾,而在灰暗中彷徨于无地。
当我彷徨,也必然因为目睹了在小区或社群中度过平凡岁月的民众,如何以蜗牛之身,继续相互的对话,而想起鲁迅在散文诗《野草》一文中所言: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这么说来,蜗牛也只有认识到和野草的休戚与共,才能最终寻到相互间对话的真谛!
果真如此,便也且以这样的思考和行动,继续着一趟从未抵临终站的旅程,毕竟,等在我们面前的,不会是一条平坦的路。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