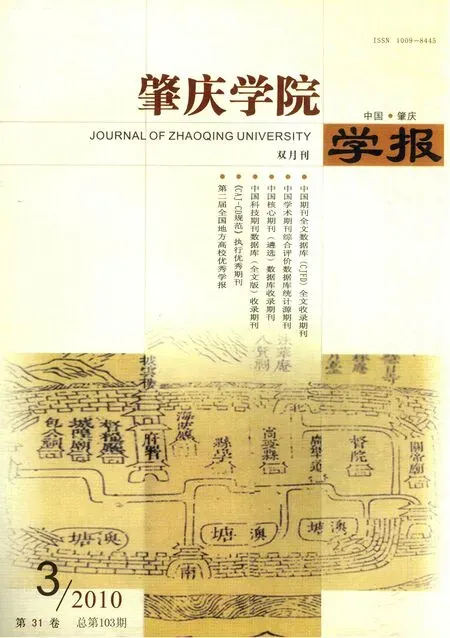关于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成败的政治原因分析
李自更
(肇庆学院旅游学院,广东肇庆526061)
关于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成败的政治原因分析
李自更
(肇庆学院旅游学院,广东肇庆526061)
日本封建二元政体、幕藩制、门阀和世袭制存在着缺陷,下层人士缺乏向上流动的渠道,导致中下级武士与豪商豪农联合起来,演变成为一股强大的推翻幕府统治的改革力量,进行明治维新,走上了强国之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及科举制相当完备,其强大生命力压制了社会改革力量的形成和发展,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维新派以其薄弱的力量,无法使戊戌变法在恶劣的国内政治环境下取得胜利。
明治维新;戊戌变法;维新派;政治制度
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是东亚近代史上的两次重要政治改革,对两国近代社会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19世纪中叶,日本面临着沦为殖民地的威胁。随着国内外矛盾的不断激化,以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为中坚力量的倒幕派联合各阶层力量,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推翻了幕府统治,实行资产阶级改革,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的情况与日本有诸多相似之处。1840年后,西方列强多次发动侵华战争,致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甲午战争的失败更把中国推向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历史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国提出新的理论和思想,救亡图存,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由此迅速兴起。可是,戊戌变法未能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拐点,却以失败告终。相似的改革为什么会出现成败不同的结局呢?学术界多从宏观层面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本文则力图从微观层面分析这两次资产阶级改革成败的政治原因,试图揭示影响日、中两国社会变革的规律性的内容。
一、封建二元政体、幕藩制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明治维新前,日本中央的政治体制是天皇—幕府封建二元政体。在这种体制中,幕府与天皇朝廷同时并存,幕府实质上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机构,幕府将军掌握着全国军政大权,凭借其政治、军事、经济等实力千方百计地限制天皇的权力。天皇掌管意识形态,只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朝廷名存实亡,但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天皇神授”在日本人心目中具有根深蒂固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天皇被认为是创造日本国家的神的子孙,具有超人的身份。”[1]163即使幕府将军也不得不承认天皇的权威及其存在。面对幕府的种种限制,失去了军政大权的天皇不甘心听从幕府的摆布,时刻伺机恢复至高无上的皇权。这是封建二元政体结构必然产生的矛盾和对立,并贯穿幕府统治的全过程。德川幕府末期,国内外矛盾不断激化,维新派利用了天皇与幕府的矛盾,以“尊王攘夷”的口号,把天皇作为团结倒幕势力的精神工具,使朝廷上下众多的倒幕力量汇集成为一个强大倒幕洪流,并以天皇的名义下达讨幕令,为实现武力倒幕取得合法的根据。天皇也希望通过维新派恢复他那至高无上的皇权。于是,维新派就与天皇形成了倒幕合力,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建立起明治新政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本主义改革,使日本迅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种独特的天皇—幕府封建二元政体结构,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一个因素之一。
在日本,幕府之下还存在着“藩”这样的地方割据势力。幕府将军是全国最高的统治者,下辖260多个大名藩主。由于幕府将军对各藩领地不拥有直接的行政权,各藩大名,尤其是“外样大名”虽受幕府的节制,但在自己的藩内却是封建的独裁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诸如设置‘藩厅’,管理行政,决定领地内的租税率,乃至设置关卡,征收赋税和拥有相应数量的武士军队等等。”[2]其中以长州、萨摩、土佐和肥前等四藩的实力最强,保持着封建割据的独立性,并与幕府有深刻的矛盾。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势力既彼此依赖,又相互对立,处于均衡状态,在一定的条件下,有转化为对抗的可能。这种割据对立的局面为维新势力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因此,当西方列强相继入侵,日本处于封建危机和民族危机的政治动荡时,革新的政治力量就有可能首先在一个藩内获得成功,作为取得全国胜利的据点。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中,长州和萨摩两藩就起了这样的作用,成为全国倒幕维新志士的集结地和大本营。
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与日本幕藩政体明显不同。中国自秦汉以来的政治结构是建立在地主经济基础之上的大一统官僚政治,君权至上。这是典型的政治全面控制的体制,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道德生活以及其他社会领域都纳入这个高度板结的体系中,任何游离于这个体系之外的因素都会被视为异端而被剿灭。这种中央集权制到清代发展到了极端,封建君主集军政等权力于一身,在中央增设军机处,地方建立督抚制,边疆设有理藩院,中央通过科举制度选任地方官吏。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统治网,致使革新力量很难独立地发展起来,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很难出现大的分化。在封建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大一统”天下,地方不可能独立于中央之外发展军事、政治力量。即使是晚清出现过的“湘军、淮军并不具备日本幕府末期的藩那样有比较牢固的统治地区和主从关系,而是寄生于清朝的统治机构,依靠外国势力的支持,因而不可能取代清王朝而制霸全国,创建新的国家机构。”[3]28在维护封建统治旧秩序这一根本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则和清廷是一致的。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封建专制统治仍然很强大,尽管腐朽但是仍然很顽固,不易被摧毁。因此中国维新派要冲破封建专制主义的罗网,进行政治上的革新,其所面临的阻力要比日本明治维新大得多。
二、两国官吏的选拔和任免机制不同
在日本,官吏的选拔和任免依靠门阀和世袭制。日本的武士属于封建统治阶级,但在其内部按照门第的高低又划分为20多个等级,幕府及各藩政府的职务,均依靠武士的等级身份分配,并可世袭。但政府的高级职位始终为大门阀世袭垄断,中下级武士始终被排斥在权力机构之外,这种僵化封闭的官吏选拔任免机制阻碍了封建政权机构吸收新鲜血液,以增强自己的活力;同时,也把下层人士,尤其是中下级武士往上流动的渠道堵死,“使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的中下级武士因无缘获取较高的职务,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并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1]456“门阀成了他们发号施令的资本,即使才华过人,如果不依靠门阀就不能施展其才能,也不能有所作为。在当时由于被这种势力所压制,全国已经找不到可以发挥智力的余地,一切事物都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到了德川氏的末期,社会人士已经开始产生了厌恶门阀的心情。”[4]中下级武士既是军事集团,又是政治集团,是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同时他们还是一个反封建的精英集团,有力的冲击和破坏着封建等级制度。
在中国,清政府主要通过科举制来选拔任免官吏,这种科举选官制具有他的合理的一面。首先科举选官制为网罗和起用人才开辟了道路,不仅把全国的精英分子集中到体制内,同时还形成了一条无形的思想锁链,把众多知识分子牢牢捆绑在传统秩序当中。其次,科举选官制也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以应试出仕的向上流动的渠道。虽然,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平民很少有读书的,更谈不上应试出仕,但科举制至少使他们向上流动具有了一种合法的可能性,事实上,也有一部分平民知识分子利用这种可能性步入仕途,成为统治阶级。由于这种制度具有很多的合理因素,“整个统治阶级都非常迷恋这种制度,热衷于维护这种制度”,[3]28封建统治政权就通过科举制度把全国各阶级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府,扩大了政权的阶级基础,调整了官僚机构,增强了它的“活力”。
此外,中国封建社会还有捐纳制度,即有钱者可以买官做,使一大批原来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的庶民地主、商人等得以跻身仕途。晚清政府渴望扩大财源,“通过捐纳制度造就的各种‘异途’出身的科举精英分子数量大增”[5],进一步扩大了清政府的阶级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可以不断地从其他社会阶级、阶层中汲取新鲜的力量以补充和更新自己,而其他阶级、阶层的成员由于存在着上升至统治阶级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与统治阶级的对立。这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和牢固性,难以在其内部形成强大的改革力量,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了强大的阻力。
三、两国社会改革的力量不同
社会改革的力量直接推动着社会改革的进行,是社会改革成败的关键。由于推动日、中两国进行社会改革的力量有着明显差别,从而影响到两国改革结局的不同。首先,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领袖具有政治家的谋略和才干,斗争经验丰富,在他们的领导下改革得以稳妥地进行。中国戊戌变法的主要领袖则缺乏谋略和才干,毫无政治斗争经验,难以领导维新变法走向成功。其次,日本明治维新得到了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及豪商豪农的支持,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上都强于中国。中国维新派力量单薄,缺少必要的社会基础。
(一)领袖的素质及其策略不同
领袖人物是否具有政治远见、执政经验,敢于和善于开展斗争,是改革成败的重要条件之一。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成员,如: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及伊藤博文等都是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精英分子,具有政治家的谋略和执政才干。明治维新前,他们就通过“藩政改革”掌握了西南诸藩的藩政,从中经历了改革风浪的考验,积累了政治斗争经验。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必须推翻幕府统治,夺取政权才能发展资本主义,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倒幕斗争中,他们善于利用形势,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包括农民武装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幕府。在建立和掌握了新政权的前提下,以五条誓言为施政方针,逐步改造了日本的政体。如:废藩置县、取消身份制、改革地税、发展实业和近代教育,最终实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全面开化。在改革过程中,他们采取强制和赎买相结合的方式,用十年时间,坚决、慎重及稳妥地解决了废藩置县和取消身份制等历史问题,大大减少了贵族反抗的激烈程度,保证了改革所必需的稳定的政治环境,使所颁布的政策得到较为顺利的实施。
中国维新派的主要领导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是些读书人,虽然有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却缺乏行政经验,疏于政务,黯于世事,缺乏韬略。维新初期,维新派只因名声不好,就把最具实力的李鸿章加以排斥,致使同情维新的李鸿章改投顽固派而成为维新的阻力。对于在改革中出现的阻力,维新派则乐观地认为“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6]251因此,混迹官场多年的顽固官僚们视之为“皆温雅辞章之士,鲜有老谋”,“不足畏也”。[6]467同时,维新派在未掌握实权的情况下,只求“全变”、“速变”。在短短的103天内,雪片般地颁布了110多道诏令,改革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企图在一夜之间把中国变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家。他们急于求成,不讲谋略,对统治阶级的各派别不加区别,全面打击,大裁大撤,废八股,改官制,触犯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以致“朝廷震撼,颇有民不聊生之戚”。[6]485维新派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反对势力,终因反对者众,支持者寡而失败。
(二)改革的主要力量不同
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力量是中下级武士、豪商豪农。这一改革的社会力量在明治维新前业已形成。
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既是武装集团,又是政治集团;中下级武士资产阶级化,有力地冲击和破坏着封建等级制度。德川幕府末期,森严的门阀制度使中下级武士深受政治压迫,而幕府和各藩财政状况的日益恶化,又使广大中下级武士陷入困境,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俸禄不保,生活无着。为谋求生路,许多武士从事副业生产或经营商业,进行具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活动。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影响和人民革命斗争的推动下,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和豪商豪农联合起来先后控制了长州和摩萨等藩的藩政,并且组织了近代化的武装力量。而许多不满幕府要求改变现状的藩主大名也纷纷归附,进一步增强了维新派的实力。他们利用了天皇与幕府的矛盾,联合天皇这个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在天皇的名义下,利用了当时反对幕府的人民力量,进行讨幕活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资产阶级化的豪商豪农,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受幕府的种种限制和打击,对幕府深抱不满,成为反对幕府的一支新生力量。如,在豪商白石正一郎的帮助下组织了第一支倒幕武装力量“奇兵队”,再如明治政权初期的财政则是靠三井、住友、小野等大商业资本作为经济支柱。显然,资产阶级化的豪商豪农是明治维新成功的社会基础。“明治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中下级武士之手,而背后的经济推动力则是三井、住友、鸿池、小野和安田之流的大商人的财力。”[7]所以,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和豪商豪农有力地推动着社会改革,是明治维新的主要力量。
中国维新派的力量却很薄弱,他们只是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从未掌握实权,清朝政权一直被保守势力牢牢掌握。他们只是在三年里创办了24个学会,19个学堂,8个报馆而已,根本就没考虑过,也没机会像日本维新派那样创建属于自己的军队,在危急时候只有寄希望于袁世凯这样的阴险小人。他们主要是从官僚和知识分子中寻求力量支持。在中央,希望联合以翁同为首的帝党来对抗以慈禧为核心的顽固势力。然而,翁同虽贵为军机大臣,但也无多大实权,慈禧一张旨谕,即将其革职回乡。在地方,他们也始终没有和地方实力派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没有获得像日本维新派那样在政治、经济上强大到足以与中央叫板的地方势力的支持,维新派所寄以希望的张之洞之流的地方实力派,在关键时候都站在维护封建传统的立场上,无不听从于慈禧的命令,共同扼杀维新力量。并且,维新变法缺乏支持革新的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维新变法时,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它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在一定程度上有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经济上有联系,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8]因此,中国资产阶级也不敢果敢地支持维新派,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同时中国维新派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毫无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不相信人民,害怕人民,不懂得也不敢利用当时反帝国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人民力量来冲破封建专制主义罗网,仅仅希望凭借光绪皇帝的谕旨条令来改变社会的面貌,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显然是幻想。当时,光绪皇帝受制于慈禧太后,未有实权。当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击时,维新派完全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
综上所述,日、中两国近代社会改革出现成败不同的结局,从政治层面上看主要由以下三个不同的政治因素所决定。首先,封建二元政体下的幕府将军与天皇、幕藩体制下的幕府将军与藩主大名之间的矛盾削弱了封建统治力量。在这种僵化而缺乏弹性的制度下,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和豪商豪农联合起来推翻了幕府统治,建立起明治新政权,进行资产阶级改革。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相当完备,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控制着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维新力量难以成长,戊戌变法就难以成功。其次,日本门阀和世袭制压制了中下层人士的才智,使中下层人士对现实产生了强烈不满,由此在日本封建体制内易于滋生出一个异己的力量。中国科举制既为清王朝统治不断输送“新鲜血液”,强固了其统治基础,又化解了社会中下层精英的不满情绪,从体制内很很难异化出一个反对封建统治的精英群体。再次,从改革的主导力量看,日本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和豪商豪农受到政治压迫,不满现状,但是他们具有在地方藩国执政的经验,策略得当,又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木户孝允、大久保利等人的领导下完成了资产阶级改革。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可能成为戊戌变法的社会基础,所以维新力量薄弱,而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主要领导人在领导能力上和策略运用上都存在着不足,所以戊戌变法无法成功。
[1]吴于廑,齐世荣.世界近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米余庆.明治维新[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2.
K304
A
1009-8445(2010)03-0042-05
2010-04-15;修改日期:2010-05-12
李自更(1965-),男,河南周口人,肇庆学院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