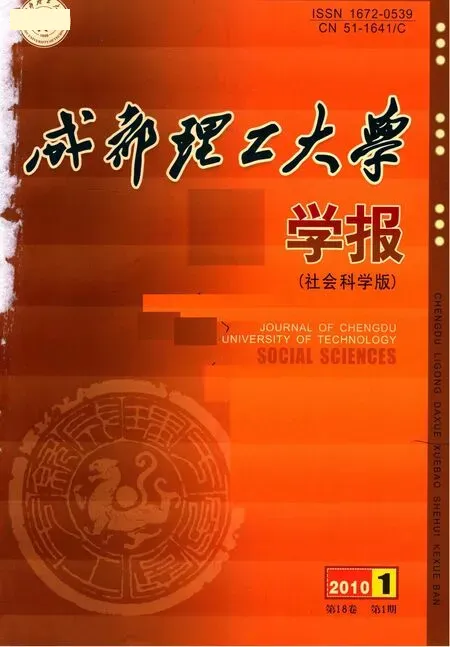论汉代辞赋“诗源观”的形成及其原因
许瑶丽
(成都理工大学 《学报(社科版)》编辑部,成都 610059)
论汉代辞赋“诗源观”的形成及其原因
许瑶丽
(成都理工大学 《学报(社科版)》编辑部,成都 610059)
汉代辞赋“诗源观”的确立经历了在“讽谏”功能上比附于《诗》到用论《诗》的标准评论辞赋,再到“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提出这样一个历程。究其原因,首先是汉代从帝王到士人的好赋风气需要寻求一个合符儒家思想的理由;其次,汉代政治思想的大一统,儒家正统思想的确立为辞赋提供了《诗》之“讽谏”论;最后,作赋者身份由言语侍从向儒家学者的转变也使辞赋“诗源观”的确立具有一种自觉性。在“诗源观”确立的同时,更符合辞赋自身特点的娱情说也依然存在。然而从辞赋发展史来看,“诗源观”并非客观之论。
辞赋;诗源观;形成;原因
中国文化有复古溯源的传统,而且“古”往往具有正面的意义。但对于“赋”,一方面大多都承认荀、宋的创体之功;另一方面又对宋玉颇多微辞,而宁愿把赋的起源追溯到“古诗”。正如王齐洲在《赋体起源和宋玉的文体创造》一文中指出的:“对一种文体构成要素的可能来源和文体的实际起源是否可以同等对待的问题”[1]51汉人对此纠缠不清。不仅汉代如此,历代学者也都对此都保持着适度的“糊涂”,故笔者拟在王齐洲先生所论基础上,进一步说明“赋者,古诗之流也”这一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并揭示此观念形成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
一、辞赋“诗源观”形成的历时梳理
汉代对辞赋并不严格区分,赋概言之则总包赋、辞,分言之则赋、辞有别。因此本文在论述时亦按此原则处理。汉代最早对辞赋作出评论的是刘安,《汉书·淮南王安传》载:“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刘安原文不可见,今可见最早者乃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评语: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这段评语首次将《离骚》与《诗》相比较,并指出《离骚》与《诗》在形态、精神上的一致性,而为历代论者所乐道。刘安称赞《离骚》的标准带有显著的儒家诗教色彩,“文约辞微”、“志洁行廉”可以说是典型的儒家文品、人品的范型。《汉书》载“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 ,亦二十余万言。”[2](卷四十四)观《淮南子》一书,亦多道家言,是知刘安非纯正的儒者。推原刘安之评语,当有迎合武帝之意。“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 ,昏暮然后罢。”[2](卷四十四)因此刘安对于武帝之喜好是比较了解的,既为受诏而作,当然会揣摩主上之意以附和之。那么此处对屈原及《离骚》的评价实际很可能代表的是作为大汉天子刘彻的观点。若此推论成立,由帝王暗示了的辞赋与《诗》之间的联系会被进一步的开掘和推广。
司马迁在《史记》中大段引用刘安《离骚传》,正说明司马迁对这种观念的接受。不仅如此,司马迁甚至进一步将《诗》的“讽谏”功能用于对辞赋的评价。《史记》中论及辞赋的语段主要有如下一些: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屈原贾生列传》)
“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司马相如列传》)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传第五十七。”(《太史公自序》)
“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贡生列传第二十四。”(《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将刘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这一评论深化、缩小为“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忽略了刘安对“盖自怨生”的创作动机的认识,而认为“讽谏”才是屈原创作《离骚》的根本目的。并据此批评宋玉、唐勒、景差等“终莫敢直谏”,是未能师承屈原的谏诤精神。而对于司马相如之赋,司马迁一方面肯定其与《诗》之讽谏精神一致,另一方面指责其赋“靡丽多夸”、“多虚辞滥说”,其批评与肯定的标准都是儒家的文艺观点。从司马迁对屈宋、司马相如的批评,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一个逻辑理路,即《诗》之“讽谏”是一切文艺活动的终极价值,所有作者在创作时应该明确地抱着这样的目标,观《史记》中其它论及文艺活动的语段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乃着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已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司马相如列传》)
板柱节点应进行冲切承载力的抗震验算,且应计入不平衡弯矩引起的冲切。为了防止强震作用下楼板脱落,穿过柱截面的板底两个方向的钢筋的受拉承载力应满足该层楼板重力荷载代表值作用下的柱轴力设计值,一般来讲,抗剪栓钉的抗冲切效果优于抗冲切钢筋。
“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滑稽列传》)
“优孟者,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滑稽列传》)
淳于髡、优孟的戏谑是以讽谏为目的的,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喻巴蜀檄》则不仅能“以风天子”,而且能“令百姓知天子之意”,这实际是对《诗》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生动解说。尽管班固批评司马迁的《史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2](卷六十二),但在对文艺的评价上,司马迁所坚持的的确是典型的儒家艺文观。
《汉书·司马迁传赞》云:“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2](卷六十二)扬雄不仅对司马迁的史才、史识非常叹服,而且对其衡文的标准也相当赞同,并提出“诗人之赋”这样的审美理想。扬雄最著名的赋学评论是《法言·吾子》中的一段对话: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则己,不己,吾恐不免于劝也。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蠧矣……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卷二)
扬雄的这段话包括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作赋不过是“雕虫篆刻”之类的末技,并不是什么值得用心的正事,这与司马相如与盛览谈论为赋之道时的自得大相径庭。第二,对自司马迁以来的“作赋以讽”的价值产生怀疑,这不是纯理论的思考,而是对前代以及自身作赋经历的深刻反思,“赋可以讽乎”这个问题是扬雄给自己提出的诘难。第三,扬雄认识到赋的风格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极敏锐的发现。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等赋作者,由于其辞人的身份和微末的地位,因而很难守持“则”,故而把辞赋引向了“丽淫”的状态。所以扬雄设想了一种理想的作者,即有“则”的“诗人”。他不仅仅用讽谏思想来改造辞赋,而且要用诗家的独立、风议精神来振起赋家。第四,对儒家不用赋的原因思索,虽然扬雄没有明确做出回答,但从整段对话我们还是不难发现他的未尽之辞。即使如贾谊、司马相如被认为是坚持了《诗》之“讽谏”精神的赋家,他们实际发生的讽谏效果也是绝不理想的。贾谊身怀异才,却抑郁而死;司马相如上《大人赋》以讽武帝之好神仙,而武帝反有“仟仟若仙”之感。而如宋玉、枚乘辈则完全混同于俳优,而成为士人羞谈的人物。孔门之不用赋,是因为“赋”根本不是一种可行的“讽谏”手段,而且作赋本身隐含着丧失士人人格独立性的危险,可能如枚、宋一般陷入迎合、取悦的境地,这与儒家“为王者师”的理想是相抵牾的。第五,“丽”是所有辞赋的共同特征,但“丽”又是一个不易把握的东西,稍不留心便有可能陷于“丽淫”,成为蠧害。
班固的辞赋批评主要反映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两都赋序》、《离骚序》等作品中,现择其与“诗源观”有较紧密关系的部分列于下: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卷三十)
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登高能赋”、“不歌而诵”是赋的传播方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体定义,况且“不歌而诵”的文体并不限于“赋”一种文体。“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这里有一系列的逻辑问题:为什么学诗之士,失志后不是以更具有抒情特质的诗来表达,而要作赋?“赋”又是什么样子?是由诗变来的吗?如果是,怎么变化的?赋与诗又有什么区别?班固显然无法解释这些逻辑上的失链,所以在《诗赋略》中它并没有明确提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观点,而是举出屈原及荀子作为“贤人失志”的例子。殊不知,在时间上从“周道寝坏”到荀、屈已是数百年,这其间的复杂过程岂可一笔带过?在“作赋以风”这一点上,班固继承了司马迁的观点,同时班固还吸收了扬雄的论点,并将司马相如与扬雄一起放入了“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者的行列。从这里可以看了班固不仅坚持了赋之讽谏的要求,而且较司马迁、扬雄更为严格、苛刻。在《两都赋序》中,班固写道: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夫夫董仲舒、宗正刘徳、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徳而尽忠孝。雍容揄扬,着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文选·两都赋序》卷一)
在这里,班固又玩了逻辑上的花样,直接提出“赋者,古诗之流也”,但并不对此观点进行逻辑证明,而是以大量的笔墨叙述汉代文治之盛。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对赋的功能的重新界定:“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徳而尽忠孝。”除前人所标举的“讽谕”之外,润色鸿业的功能被正式赋予辞赋,这既是对汉以来辞赋创作状况的客观总结,也是为赋之“劝而不止”的一种自我开脱。而且“颂美”的功能被突出地强调,“雍容揄扬,着于后嗣”实际就是指的“宣上德”之赋的特点,所以班固称赋为“抑亦雅颂之亚也”,这种提法将赋与诗之“颂”对应,加强了赋诗之间的联系。为了给汉代辞赋之盛找到了一个更官冕的评价,班固将大汉文章誉为“与三代同风”,并举出孔子删诗之事来证明汉赋兴盛的合理性。这可以算是从宏观的角度论证赋之诗源观。最后班固声明了作《两都赋》的目的为“极众人之所炫耀,折以今之法度”,其创作时已主动将“丽则”作为创作规范,故其文多议论、说理,刘勰称“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3](卷二)
今若屈原,露才扬已,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昏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议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楚辞章句》巻三《班孟坚序》)
上文出自班固《离骚序》,这是他以儒家文艺观对辞赋进行的一次文艺批评。他以《诗》之“哀而不伤”“明哲保身”来规范辞赋中情感的表达,使之不失法度。批评屈原对国君的大不敬态度,对同志者也有失温厚之道,而《离骚》文中的虚无之语则更非儒家经义所载。在此批评标准下,屈原自然只能算是“辞赋妙才”,而闪耀在屈作中的爱国思想、独立精神则荡然无存了,班固有取于屈原的也不过是其辞藻英华,叙述从容罢了。很明显,班固是在“诗者,古诗之流也”的理论前提下,全面采用儒家经义、思想来权衡、揣度屈原及其《离骚》,赋之诗源观进一步演化为全方位的诗教批评。其后王逸作《楚辞章句》批驳班固的观点,重新树立了屈原“进不隐谋,退不顾命”的忠贞品质。但从本质上看,班固与王逸在对辞赋与诗的关系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赋者,古诗之流也”是二人立论的共同理论基础。
自班固提出“赋者,古诗之流也”以后,赋之“诗源说”就逐渐成为最主流的看法,赋的批评也以《诗》为准则。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所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 ,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也。”[4](卷五十六)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3](卷二)白居易《赋赋》云 :“赋者 ,古诗之流也。始草创于荀宋 ,渐恢张于贾马。”[5](卷三十八)皆祖班固之说。
诗源说也使一部分赋作者,从“诗言志”精神中受到启发,并主动学习楚辞,开始在创作中融入抒情的成分,使赋逐渐从一味的夸饰浮华中走出来。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乃传统的宫殿赋,但作者较少关注于鲁灵光殿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而是更注重其真实状况的描写,较少虚饰夸张。正如其《序》云:“予客自南鄙,观艺于鲁,睹斯而眙曰:嗟乎!诗人之兴,感物而作,故奚斯颂僖歌,其路寝而功绩存乎辞,德音昭乎声。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匪赋匪颂,将何述焉 ,遂作赋。”[6](卷十一)作者遵循的是《诗》之“感物而作”,对鲁灵光殿的赞美也是有感而发。较之司马相如应需而作《上林赋》,枚皐、东方朔等应诏而为辞赋,王延寿此赋开启了一种新的创作类型,启发了赋向“感物而作”、发抒真情的方向发展。而“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匪赋匪颂,将何述焉。”则表明了不同于“风”与“化”的创作目的,而是注意到了赋颂的记载与传播的功能。
此外,东汉傅毅还在创作中大胆摒弃了“讽谏”论,其《舞赋序》借宋玉与襄王对话,指出“小大殊用,郑雅异宜。弛张之度,圣哲所施。是以《乐》记千戚之容,《雅》美蹲蹲之舞,《礼》设三爵之制,《颂》有醉归之歌。夫咸池六英,所以陈清庙,协神人也。郑卫之乐,所以娱密坐,接欢欣也。余日怡荡,非以风民也 ,其何害哉。”[6](卷十七)公然宣称郑声亦有其所宜施用之场合,从而肯定了帝王“余日怡荡”的合理性,这事实上是肯定了辞赋娱乐价值的合理性,赋的“讽谏”功能在创作中被搁置。傅毅这一观点无疑是更符合汉代辞赋创作状态的,在赋之“诗源说”盛行的当时,敢于如此标榜辞赋娱乐耳目的性质,实在是一种大胆的举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诗源说的虚弱。
二、辞赋“诗源观”形成的社会文化因素
1.汉代好赋之风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汉赋之兴与汉代社会的好赋之风密不可分。汉代建国者来自楚地,昔高祖刘邦为《大风歌》,慷慨伤怀,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吾魂魄犹乐思沛。”[7](卷八)故汉帝好楚风其来有自。汉武继位 ,颇好艺文,辞赋尤好之,司马相如因献《子虚》、《上林》而得位,朱买臣以诵楚辞为太中大夫。而汉初诸王如吴王濞、淮南王安、梁王更是招聚文士,造为辞赋。帝王不但喜听诵辞赋,而且亲自创作,《太平御览》引《汉武故事》云:“(汉武帝)好词赋,每所行幸及奇兽异物,辄命相如等赋之,上亦自作诗赋数百篇,下笔即成。”[8](卷八十八)帝王的倡导使得整个社会好赋、作赋之风弥盛。《东观汉记》云:“班固九岁能作赋颂,每随巡狩辄献赋颂”,直到东汉末的汉灵帝仍设鸿都门学以广献赋之路。辞赋甚至成了可以疗救疾病的药方,《汉书》载:“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王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 ,及所自造作 ,疾平。”[2](卷六十四下)班固《两都赋序》云:“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夫夫董仲舒、宗正刘徳、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徳而尽忠孝。雍容揄扬,着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6](卷一)辞赋成了整个政府各阶层的共同爱好,不仅专职的言语侍从“日月献纳”,连公卿大夫们也“时时间作”,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辞赋创造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指向,即为帝王而作,故班固谓“奏御者千有余篇”,所以,为辞赋的存在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非常必要。
2.汉代思想政治的大一统
汉代建立之初,由于实行分封制,诸王时有叛乱,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戸邑以封子弟 ,不行黜陟 ,而藩国自析。”[2](卷十四)至武帝时,汉朝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便逐步建立起来了。伴随政治大一统步伐的是思想领域的统一,汉武帝采董仲舒之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初以来思想界黄老、刑名、儒家等思想共存的局面消失了。《史记·儒林传》曰:“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向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 ,靡然向风矣。”[7](卷一百二十一)汉武帝时儒学之兴由此可见矣。一个时代指导思想的建立,必然伴随着其对各个具体领域的辐射。《史记·张汤传》载:“是时上方向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奏谳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着谳决法,廷尉,絜令扬主之明。”[7](卷一百二十二),张汤为了投主所好 ,在决狱时附会儒家经典的意旨,并时时注意扬主之明。这正是帝王与臣子在确立儒家思想统治地位中相互合作的一个典型,试想对于一代之文学的赋,岂可无人为之依经立义。
儒家思想中本不乏文艺批评思想,如“兴观群怨”说、文质彬彬之论、知人论世说等,比比皆是。《国语·周语上》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 ,是以事行而不悖。”[9](卷一)在儒家思想者眼中,诗、书、赋、诵等艺文形式,只是王权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其首要的功能是观政辅政,而艺文的审美价值往往是第二位,或完全被忽略的。汉代鲁、齐、韩三家解诗均尚“讽谏”之说,诗之讽谏功能对所有艺文都具有指导意义,武帝“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6](卷一)其艺术为政治服务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但同时,除汉末灵帝设鸿都门学,造为辞赋以外,辞赋在汉代并没有在官方政治系统中占有什么重要位置,换句话说,在统治者眼中,辞赋并不真正具有高尚的价值。但是汉代几乎全民参与的造赋运动必须找到一个合法的理由,这既是为帝王、卿相的爱好辞赋找理由,也是赋作者自己立身行事的需要。
3.汉代赋作者身份的变化
汉初赋家多为藩王所招聚,习染纵横游说之气。枚乘、邹阳、严忌、司马相如都曾客游诸王,《子虚赋》即司马相如为梁孝王所作。自武帝崇儒术、好艺文,天下学士,靡然风向,作赋者的身分由游士转变为宫廷言语侍从,司马相如是这种转变的代表人物。从《子虚赋》到《上林赋》,从美诸侯苑猎到美天子之狩证明了这种转变的发生。
在言语侍从中间,又可分为如枚皋、东方朔之类以言语调笑为能之士,和以润色鸿业、才高学优如司马相如、扬雄之辈。这种分化已然暗示了赋体未来的发展方向。相如虽以《子虚》、《上林》见知于武帝,但终其一身位不过郎官,《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其进仕宦,未尝有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7](卷一百一十七)按司马相如三度为郎 ,第一次还是“以赀为郎”,即出赀财买官为郎,是知其并非无意仕进,“未尝与公卿国家之事”才是他闲居的真正原因。在武帝眼中,他仍不过是一介言语侍从,与枚皐、东方朔等并无不同。而枚皐、东方朔对自己类同俳优的身份是有清醒认识的。《汉书》云:“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2](卷五十一)不通经术、以诙笑嫚戏取宠乎上的枚皋当然不可能获得武帝的尊重,更不可能被委以重职。东方朔《答客难》对身类俳优的状态有清醒、沉痛的认识,他说:“今则不然,圣帝徳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均平,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与不肖,何以异哉 ?”[2](卷六十五)大一统的政治格局限制了士人的发扬蹈厉,贤与不肖决于一人。不同于枚皋赋一味诙笑嫚戏,东方朔《答客难》时称《诗》、《书》,表现出相当的儒学修养。但即使是这样“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记,着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可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 ?。”[2](卷六十五)东方朔在牢骚之外 ,亦有一份清醒 ,除了“时异事异”的理由之外,东方朔亦看到了文士在大汉政权中的真实位置。“作赋以讽”不仅是文士给自己的一剂麻醉药,而且是帝王耽于享乐的挡箭牌。《汉书》载:“是时上颇好神仙,故褒对及之。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2](卷六十四下)“仁义讽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不过是汉宣帝的借口,而真实意图却是把赋当作音乐中的“郑卫之声”,其最大的价值在帝王眼里仍是娱乐,赋家仍不过是“倡优博奕”罢了。王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仟仟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长卿之赋,如言仙无实效;子云之颂,言奢有害。孝武岂有仟仟之气者 ,孝成岂有不觉之惑哉 ?”[10](卷十四)
当然东方朔非淳儒,因此既不为儒者所重,亦不为君王所用,其处境可以算作赋家向儒者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类型。在汉代众多的赋家中,扬雄算是第一个纯正的儒士,《汉书·扬雄传》称:“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2](卷八十七上)桓谭《新论》曰:“扬子云何人耶?答曰:才智开通,能入圣道,汉兴以来未有此也。”[8](卷四百三十二)扬雄也是对第一个对赋进行严厉批评和深刻反思的人。王齐洲指出:“汉赋作家在其创作实践中越来越感受到这一文体讽谏功能的丧失,所谓‘劝百讽一’,其结果是‘不免于劝’,赋作家们也逐渐沦为‘言语侍从之臣’,与倡优无异,这种文体的困惑和赋作家们的内在焦虑促使他们重新思考辞赋的有关问题。”[1]49如果说东方朔是以个体的骚怨来表达对赋家地位的不满,那么扬雄则是站在整个赋家群体的位置上思考赋在汉代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所以刘勰《时序篇》所云:“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3](卷九)我们看到 ,汉代的赋家由纵横游说之士到言语侍臣,再到服膺儒术的经生,正是这种身份的变化,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只在形式上比附诗经,并不能真正使赋有补于政治教化,只有从赋作者自身修养上改变其俳优身分才能实现赋的讽谕功能。故扬雄将赋分为“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试图以诗人的讽谏精神代替辞人之赋对帝王需求的一味顺应。但扬雄还是置身于汉代政治之外的,这可以从《解嘲》中看出,“向使上世之士,处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亷,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髙得待诏 ,下触闻罢 ,又安得青紫。”[11](卷四)扬雄是现实政治的失意者,他不是以策试或孝廉等正统取士方式进入政治的,他依然是被汉成帝以言语侍从看待的人。而班固则作为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正统儒家的双重身分,代表汉代政治与士人双方利益,对赋的功能意义进行整合,在“讽谏”之外,增加了赋的“颂美”功能,使赋的“丽靡”具有了“美盛德之形容”的高尚用意。在班固的时代,大一统的政治与思想已相当稳固,儒家士人成为政权、思想的积极维护者和建构者,他们通过经学与政权产生了深刻的同一感,同时经学也向其它领域辐射,典型的例子就是班固无视逻辑论证中的诸多空白,大胆将赋指为“古诗之流”。这不仅是由于帝王好赋不已,而且也因为赋家多为儒者,献纳双方都需要一个最天经地义的理由。
三、辞赋“诗源观”并非客观之论
很明显,对于赋的功能,赋家与作为主要读者的帝王在认识上表面上是一致的,但在实质上,帝王把辞赋当作消遣娱乐,把赋家视同俳优。而赋家却希望借辞赋展示自己的才华见识,指望借赋能对政治产生影响。正是读者与作者对赋功能认识上的偏离,使赋的“讽谏”论流于空谈,而“赋者,古诗之流”的说法,最终不过是赋家一厢情愿的攀附而已。赋从起源上就根植下的“媚上取宠”的本性,使它在汉代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格局下,更加的变本加厉,形成了无以复加的华丽外观。
从比附《诗》的讽谏功能到直接将赋的起源回溯到《诗》,是汉代辞赋“诗源观”形成的逻辑理路,而汉人的好赋之风、政治思想的大一统以及辞赋作者身份的转变则是“诗源观”形成的内在原因。在辞赋“诗源观”形成的过程中,一直都伴随着对辞赋的批评与反思。从司马迁的“虚辞滥说”、“靡丽多夸”,到扬雄的“童子雕虫篆刻”、“辞人之赋丽以淫”,再到班固的“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辞赋之“丽”一直都是众矢之的,“丽”的价值总是从属于“用”的。王充《论衡·定贤篇》曰:“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10](卷二十七)“定是非”、“辩然否”作为衡量文章的标准是第一位的,而文之锦绣、眇深是无足重轻的。至汉末蔡邕则在进呈汉灵帝的《陈政要七事》中明确指出:“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奕,非以为教化取士之本。”[12](卷二)不但将赋的地位等同于“博奕”,而且明确指出辞赋非教化取士之本,不能用于“匡国理政”,这实际上否定了赋的讽谏功能,并进尔否定了班固的诗源说。如果撇开其功利性的偏颇,应该说这样的认识是真正理性的认识,较之班固之论更切近实际。但在汉以至后来的正统认识中,这种观点却并不被采纳,相反倒是班固的诗源说成为主流,这实际上是由历代基本相似的政治思想文化环境所决定的。
以上对于汉代辞赋“诗源观”形成过程及原因的分析表明,“赋者,古诗之流也”并非一个客观的关于文学发展的论断,而是基于特定政治、历史境遇下的趋附之论。因此在探究辞赋的形成与发源时,过分的重视班固此说的价值是并不恰当的,关于辞赋的起源的探讨应该更加注重早期辞赋形成与发展的客观环境,关于此点笔者《论“读者期待”与先秦赋之繁寡情》[13]一文有详细论述。
[1]王齐洲.赋体的起源与宋玉的文体创造?——兼论汉代赋论家的赋体探源[J].湖北大学学报,2002,(01).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欧阳询.艺文类聚[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白居易.白氏长庆集[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6]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
[8]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9]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0]王充.论衡[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扬雄.扬雄集校注[M].张震泽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2]蔡邕.蔡中郎集[M].四库全书本[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
[13]许瑶丽.论“读者期待”与先秦赋之繁采寡情[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11):188-192.
On Formation and Reasons of Idea That Fu Is Derived from Shi Jing
XU Yao-li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engdu 610059,China)
The setup of idea that Fu is derived fromShi Jingexperienced a comp licated course that firstly Fu is thought to have the same function of advising as the poem has,then the criterion onShi Jingwas be used to remark Fu,at last the idea was be puts forward by BAN Gu clearly.The reasons for thismainly are follow ing three:firstly,both emperors and scholars enjoy Fu in Han Dynasty,w hich needs a reasonable p retext that acco rdsw ith the Confucianism,secondly the unification of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Han Dynasty and the setup of Confucianism p rovided the view of advising often used in remarkingShi Jing,finally the w riters of Fu changed their positions from attendants to Confucian,thus they wanted to give Fu lofty status.Meanwhile the idea that Fu is caused by the demandsof entertainment is still alive in Han Dynasty.However acco rding to the developing histo ry of Fu and Ci,the idea that Fu is derived fromShi Jingis no t an impersonal conclusion.
Fu;the idea that Fu is derived fromShi Jing;formation;reason
I206.2
A
1672-0539(2010)01-073-07
2009-11-10
许瑶丽(1975-),女,四川简阳人,编辑,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