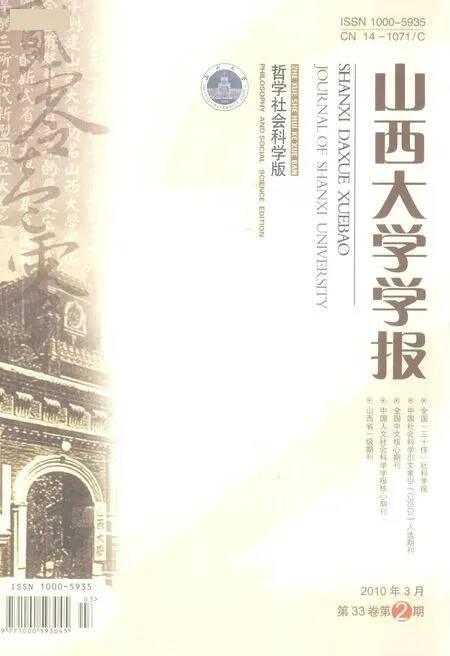试论陕西当代小说创作的地域文化特色
郭 萌,赵学勇
(1.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2.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 710054)
试论陕西当代小说创作的地域文化特色
郭 萌1,2,赵学勇1
(1.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2;2.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 710054)
陕北黄土高原、关中平原、陕南山地三大地理板块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陕西作家深受其影响,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创作风格。陕北文学以路遥为代表,深受生存文化影响,形成了宏阔大气、粗犷奔放的创作风格;关中文学以陈忠实为代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形成了含蓄蕴藉、内敛深沉的创作风格;陕南文学以贾平凹为代表,深受秦汉文化和荆楚文化影响,形成了或质朴厚重、或自然朴素、或神秘鬼魅、或虚无缥缈的创作风格。
陕西当代文学;地域文化;生存文化;儒家文化;荆楚文化
陕西地理风貌的差异,形成了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陕北黄土高原、关中平原、陕南山地三大地理板块。地域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促成了陕西三种不同的地域文化,而陕西作家的创作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较大,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关于陕西三地的文学艺术特点,贾平凹有着深刻的见地:“陕北,原为黄土堆积,大块结构,起伏连绵,给人以粗犷、古拙之感觉,这一点,单从山川河流所致而产生的风土人情、又以此折射反映出的山曲民歌来看,陕北民歌的旋律起伏不大而舒缓悠远。相反,陕南山岭拔地而起,弯弯有奇崖,崖崖有清流,春夏秋冬之分明,朝夕阴晴之变化,使其山歌忽起忽落,委婉幻变。而关中,一马平川,褐黄凝重,地间划一的渭河,亘于天边的地平线,其产生的秦腔必是慷慨激昂之律了。于是,势必产生了以路遥为代表的陕北作家特色,以陈忠实为代表的关中作家特色,以王蓬为代表的陕南作家特色。”[1]其实,贾平凹本人的文学创作,就体现了陕南相应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 陕北文化与路遥的创作
陕北黄土高原位于黄河中游,西部是陇东、宁夏,东部为黄河、晋西大峡谷,北接毛乌素大沙漠和蒙古草原,处于黄土高原向蒙古草原过渡地带。再加上年降水量极少,属于中温带半干旱气候类型,因此,人们选择了适宜生存的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长期大规模的砍伐森林使这里日益荒漠化,形成了山荒岭秃、沟壑纵横的地表特征。
土地的贫瘠、气候的干旱、生活的艰辛,使陕北文化带有鲜明的生存文化特征,这种特征决定了路遥的创作无法超越对现实生存苦难的关注。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对现实生存苦难的真切感受决定了路遥从文学创作初始,就时刻关注着陕北人民苦难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沉浮。不管是路遥还是他笔下的人物,在面对苦难时所表现出的粗犷豪放、豁达洒脱的人生态度透露出了陕北人特有的文化姿态。路遥是从陕北高原一个自然环境极为恶劣也极为贫困的山村走出来的,饥饿是他成长过程中最刻骨铭心的体验。为了生存,七岁时他被过继给了伯父,这无疑使他遭受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生活的困顿使他形成了“内向忧郁的性格、倔强刚毅的气质,形成了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品格。”[2]“要有所收获,达到目标,就应当对自己残酷一点”[3],路遥常将人生道路上的坎坷理解为人生的必修课,把痛苦理解为走向成熟的最好课程,他小说中的人物大都经受了苦难的洗礼,从而演绎出一幕幕震撼心灵的悲剧。从马健强、高加林到孙少安、孙少平,面对苦难,他们不但没有退缩、屈服,反而表现出了更加顽强的生命意志和生存毅力。以孙少平为例,在县城上中学时,每餐只能吃两个焦黑的高粱面馍,五分钱的清水煮萝卜也是一种奢望。“每天从下午两点到吃饭这一段时间,饥饿使他两眼冒花,天旋地转,思维完全不存在了,两条打战的腿,只能机械地蠕动”。但就在这种极度的痛苦之中,他还萌发了要求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的决心和勇气。孙少平赤手空拳地走出双水村,到黄原县当揽工汉挣钱。为了拿“高工资”,他宁愿干小工行里最苦的活儿——把浇过水的湿砖头,用手一块一块往楼上扔。他用自己一双粗糙的手、一副健壮的身体,靠出卖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全家人的开支以及妹妹兰香的学费。当一天的劳动结束后,他会很满足地在微弱的灯光下看书,在书的世界里获取感人的魅力与力量。路遥的苦难意识具有陕北黄土地的传统文化精神,即在苦难的磨砺中主动地建构高尚的人格和追求理想的人生。英国美学家斯马特 (N.Smart)指出:“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4]从孙少平等路遥笔下众多的人物形象身上,我们不难感受到这种在生命的抗争冲动中所展现的悲剧美,也不难体会出路遥小说中洋溢着的青春的激情和苦涩的浪漫诗意。
陕北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因而儒家文化对这里的渗透相对缓慢而微弱。加之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冲突、碰撞与重组,使这里的文化具有古老性和原初性。首先,它保留了人类原初古老的人性美和人情美。黄土高原上古老传统中的人性、人情以奇异的力量,融化着巨大的人生苦难,消释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隔阂。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就像这块土地一样具有承受一切压力的博大胸怀、不被困难所征服的强悍性格和坚韧挺拔的生命意志。他们崇奉的一些最基本的人生原则,如诚实、质朴、忍苦、善良、重亲情等,以及相应的生存方式、风土人情、言语习惯等,都非常自然地化入了路遥的创作之中。《平凡的世界》中孙玉厚的家庭生活是黄土高原上千千万万个农民家庭的缩影。孙玉厚自幼丧父,是他帮母亲把年幼的弟弟拉扯成人。为给弟弟娶媳妇,他背上了多年还不清的债。当弟媳提出分家时,他让出了祖居的窑洞,带着母亲和一家人借居在别人家的破旧窑洞里多年却毫无怨言。孙玉厚的长子孙少安继承了父辈的善良与厚道,成为家庭生活中传统伦理感情和人生义务的承担者,为了弟、妹的前程,不惜自己辍学,与父亲一起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即使是对那些否定性的人物,路遥也都以极大的宽容和爱心去关注他们。老谋深算的乡村政治家田福堂、不务正业的二流子王满银、无是非观与正义感的投机分子孙玉亭等,作者没有把他们漫画化,而是充分发掘出他们性格中的复杂内涵。因为“从感情上说,广大的‘农村人’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而不是优越地只顾指责甚至嘲弄他们。”[5]作者充分地表现出他对黄土以及农民的深厚而复杂的思想感情,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在作品中,对黄土、对农民,他灌注的浓烈的情感和深沉的同情,构成他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这种浓烈的情感色调贯穿在他的几乎全部创作活动之中,是沸腾在他作品中的血液。”[6]此外,这种原初古老的文化还不可避免地具有浪漫精神和诗性气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路遥对故事情节的安排和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在创作过程中,路遥基本上能够对叙事进行理性控制,但那种热烈的感情会时时冲破理性的框架,从而影响了他对文本中有关爱情的情节设计。在《平凡的世界》中,省委副书记的女儿、省报记者田晓霞,医学院学生金秀先后爱上了煤矿工人孙少平,尽管这样的爱情不太符合现实生活逻辑,经不起理性的推敲,缺乏可信性,但却充满了浪漫气息和诗性气质。爱之痛苦与生之艰难,是路遥小说一以贯之的两大主题。对于孙少平与田晓霞、孙少安与田润叶、田润叶与李向前的爱情,虽然作者赞美其“使荒芜变为繁荣”的爱之伟大,但却设计了或生离死别或香销玉殒的无言结局,以遗憾和悲情再一次彰显了爱情的浪漫诗意。此外,在叙述过程中,路遥常常情不自禁地站出来,对笔下的人物和事件进行一番充满激情的议论,即使在景物描写中,也是情景交融,夹叙夹议。路遥小说的宏阔大气、粗犷奔放的创作风格和热情、浪漫、极富感染力的审美效果,彰显了其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背景。
二 关中文化与陈忠实的创作
关中平原西起宝鸡,东迄潼关,东北有黄河、渭河蜿蜒于中部,南有秦岭山脉阻隔,位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又称渭河平原。这里土地肥沃,降雨丰沛,自然条件优越,适于农耕生产。关中处于四关之内,东西南北分别有潼关、散关、武关和萧关,四塞强固,一马平川,既利耕作,也便交通。“秦中自古帝王都”,黄帝在此发祥,周天朝奠基于此,秦皇、汉武的霸业,大唐盛世的辉煌均成就于这片灵山俊土。因此有人赞叹:“大部分令后人自豪的中国历史,都放在这片厚土上了。”[7]由于长期处于政治文化核心区域,使得这里的农耕文化积淀深厚。
适宜农耕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关中文化洋溢着以农为本、固守土地、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在《白鹿原》中,成家、生子、置地、盖房,是本色农民的人生渴求,也是白嘉轩早期的人生理想和心理追求。在连着死了六房媳妇、家产几乎荡尽的情况下,他以三年之力重振家业并且人丁兴旺。这种文化气质也同样体现在陈忠实的文学创作中。多年以来,陈忠实一直关注农民,以书写农民的遭遇、命运与心态为己任,创作题材始终没有离开土地和生活于土地上的农民。北宋时哲学家张载和其弟子创立了“关学”。“关学”重“礼”、爱“仁”,最重要的是以“仁人”的标准“为生民立道”,即是界定人应走的路、应循的理,也就是指什么是人,做人的标准是什么。要想使人达到“仁心”的标准,就必须用“礼”来规范社会、规范人心,把它作为贯通社会的道德规范,社会才能通畅顺达。白嘉轩在作品中是以关学实践者的姿态出现的。自始至终,白嘉轩都对政治有一种天然的疏离,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内省与仁爱之上。纵观他的一生,可谓忧患重重,年轻时曾发起过“交农事件”、大革命时期被游街示众、中年忍受了被土匪致残、儿子违逆、痛失爱女……在这般诸多的具体细节里,白嘉轩一步步地完成其人格进阶,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皆在他整个人生的肌理中展示了各自的本体意义,因此他重修礼堂、制定《乡约》、开办学馆、修塔镇“邪”,甚至自残祈雨,将“仁义白鹿原村”的美名发扬下去。在这里,“仁义”的原则作为关学思想治世之要旨,已不仅仅是一条个人修养的准则,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基因,在作者的眼中,正是这种基因在不断地传承着中国文化。然而,儒家仁义救世理想的颓败,堵塞了传统文化的回归之路,也使白鹿原成为一个缺少灵魂寄托的精神荒原。如果说白嘉轩是作为关中儒学的实践者出现的,那么关中最后的大儒朱先生则是作为精神领袖、圣人和作者的理想人格的化身出现的,白嘉轩的种种仁义之举也都是直接受到朱先生的影响产生的。朱先生有着全面的知识结构,天文地理、农业耕种,尤其是传统的孔孟儒学,他无不精通。他又是一个道德的完人,始终主张以“仁义”压抑和限制人的各种私欲,从来都是与人为善,为人排忧解难,传统的儒家文化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白嘉轩的精神之父,他为白鹿村制定了《乡约》。《乡约》包括了“德业相劝”、“迷失相规”、“礼俗相交”……可以说这是以“仁”、“德”为核心的纲领性文约。《乡约》是对白鹿村的思想风范、礼俗准则、行为举止和仪态仪表的规定,如果遵循着传统关系这条线索追溯上去,便会发现朱先生制定的《乡约》实际上是关学大儒吕大钧在继承了张载“尊礼贵德”、“仁人”等思想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
《白鹿原》中“游于西原”的白鹿是一个充满地域文化特征的象征意象。鹿是华夏文化模态的最早原型之一,白鹿的艺术形象是构成整个作品的灵魂,“白鹿”精魂在作品中贯穿始终,“它是‘关中儒学’与作者内在心性的统一,象征着圣洁完美的非功利性人格”[8]。关中儒学以强调经世致用为指归,白鹿原的命名,四吕庵的御赐匾额,白鹿书院的挂牌,白嘉轩的画图,朱先生的解语,无不传达出作者对“经世致用”的认同。史书记载,“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雍州之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9]。可见,刚烈不屈的个性和敦厚质实的民风自古有之。“关学”的广泛传播和深入渗透,加剧了关中文化务实、功利的特点。在《白鹿原》中,白嘉轩生活的目标和乐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尽可能多地占有土地,为了以劣地换取鹿子霖家的几亩水田,白嘉轩用尽了心机。自走上文坛以来,陈忠实一直致力于表现他所熟悉的关中农民及其乡土生活,不追求时髦,甘于寂寞,终于写就巨著,体现了关中文化的务实特点;而他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意义,对《白鹿原》“死后可以拿来当枕头”的接受效果的预期,则体现了其功利性的一面。
关中平原在北面的黄土高原和南面的秦岭山脉的挤压下形成了一个狭窄的区域,这种独特的地理形态决定了人的思想观念的短视和保守。对土地的崇拜和相对殷实的生活,使关中人形成了安土恋家、重在守成的心理倾向。“走不出去,没有出息”是《白鹿原》一书中反复探讨的一个话题,关中文化中的保守理念异常强大,“冲不出去”是关中人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前面提到,陈忠实一以贯之的关中农民及其乡土生活的创作题材体现了其务实的特点,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似乎也体现了其保守、缺乏创新精神的心理倾向。关中文化由于长期存在于政治中心区域而带有权威性和正统性,儒家文化的理性色彩、秩序感和对现世的关注给生活于此的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处世方式以极大的影响。具体地说,儒家文化以乡约、族规等形式渗透于关中人的深层文化心理,制约着人们的风俗习尚和日常生活,具有无形的规范和威慑作用。尽管在客观上具有保障社会秩序和稳定人民生活的积极意义,但其保守、狭隘和由此带来的对人的价值的否定和对人性的毁灭却是不言而喻的。白嘉轩是儒家文化中宗法家族文化理想人格的具现,他时刻以乡约、族规对生活于白鹿原上的人们的言行举止加以规范,既保障着地方的秩序与稳定,又不时流露出残酷和戕害人性的一面。独特的地域文化影响着陈忠实的创作风格,他不似路遥那么热烈、直率,而是含蓄蕴藉、内敛深沉,能够极有分寸地以理性驾驭自己的感情,叙述风格客观沉稳,不动声色。
三 陕南文化与贾平凹的创作
商州居于关中和陕南间的秦岭南麓,属于过渡地带,是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之地。这里群山环抱,丹江水交错纵横,属亚热带湿润气候,雨量充足,气温较高。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此处既有关中的古朴、浑厚,又有江汉的清雅、灵秀,俱得秦楚文化的厚积。从历史角度看,秦汉文化即汉唐文化,古朴、粗犷,楚文化柔媚清丽,兼具巫文化的奇幻神秘。因此,“贾平凹有着文秀温雅的南国气质,也具备关中人厚道的一面。商山丹水培育了他诗人的气质,经黑龙口流入的关中民俗也制约着他的情思。”[10]
贾平凹倾心勾画了陕南商州的古老地域风情。他总是迷恋着故乡,他的人格理想和审美追求深深蕴涵着以陕南山地为特征的地域文化色彩,“社会的反复无常的运动,家庭的反应链锁的遭遇,构成了我是是非非,灾灾难难的童年、少年生活,培养了一颗羞涩的、委屈的甚至孤独的灵魂,慰藉这颗灵魂安宁的,在其漫长的二十年里,是门前那重重叠叠的山石和山石之上圆圆的明月。这是我那时读得很有滋味的两本书。好多人情事态和妙事,都是从那儿获知的。山石和明月一直在影响着我的生活,在我舞笔弄墨挤在文学这个小道上后,它们又在左右我的创作。”[11]他从商州汲取了丰富的艺术养料,自然人文景观和社会风尚给了他商州文化的基因。在以商州为题材的创作中,又有两种创作倾向,分别体现了楚文化和秦文化对他的影响。一种是早期以乡土人情人性的美好来消解生存困境的创作。贾平凹自言童年家境很贫穷,加之反复无常的社会运动和家庭接连不断的不幸遭遇,使得童年的苦难成为其对乡土最初最深切的记忆。然而,当作家提笔回忆商州时,无论是山石明月、清泉小溪还是山村屯落、袅袅炊烟,一切无不饱含灵韵,充满温情诗意。尽管作家对乡民的悲苦生活感同身受,但他却有意掩饰其闭塞落后而谱写淳朴民风,以田园牧歌式的描写有意淡化生存困境而美化、渲染人性的善良。另一种是对乡土阴暗、丑恶的揭露和批判。对苦难的记忆和农村真实生存状况的难以逃避,使得贾平凹的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作为一个富有时代感和使命感的作家,贾平凹以滞重的笔调呈现了乡土阴暗、丑恶的一面。在《山镇夜店》《年关夜景》《二月杏》《浮躁》《高老庄》《怀念狼》等作品中,作者怀着无限的痛惜之情呈现了乡民麻木、愚昧、落后、保守、自私、残忍的一面。贾平凹也书写城市悬浮状态中精神的无根漂泊和心灵的焦虑苦闷。《废都》记录了西京“四大名人”沉溺于色欲、物欲,过着蝇营狗苟、精神无着的生活。作家繁复细致地描摹庄之蝶名人光环笼罩下的日常生活的忙碌,主旨恰在于热闹生活背后的心底荒凉,“废都”意象投射出了都市人精神的荒芜和颓废。
三省交界之地,意味着中原文化、秦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融,因而商州文化具有多元性和丰富性,这在贾平凹的文本中也得到了体现。贾平凹早年迷恋商州世界,然而,当他走出商州、奔赴西京后,又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八百里秦川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良好的生活条件、发达的文化事业,使得贾平凹深深地体味到了秦人勤劳、朴实、内向的个性特征和其自然任性、知足安分的人生态度以及喜平淡、重实际、少玄想的生活模式,于是他在《鸡窝洼人家》《小月前本》《浮躁》等作品中以质朴厚重的笔调竭力凸现农耕文明下儒家文化“持中贵和”的人生理想,展现秦汉文化环境下秦人乐守天年、豪爽大气但又封闭保守的生活。楚文化中道家的老庄思想对贾平凹的影响极大,道家道法自然、抱素含朴的意念在其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道家言“大地有大美而不言”,贾平凹描写商州的系列作品在思想内涵上充满了道家的哲理玄想,在艺术风格上追求自然朴素、简单平易,在审美倾向上钟情道家的飘逸潇洒。《商州初录》首先展示出商州的自然之美,作品中作者深情地把商州称作是块美丽富饶而充满野情野味的神秘地方,这里的树细而高大,向着天空拥挤,炊烟也被拉成一条直线,山的悬崖险峻处树木皆怪,枝叶错综,白云忽聚忽散,幽幽冥冥,有水则晶莹似玻璃,清澈见底,这样有韵致的如诗如画的描写背后是作者对返璞归真境界的体味。《古堡》中对老道士这一人物的有意安排,体现着道家文化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叠印。《废都》中庄周梦蝶的典故不仅直接化作了主人公的名字,而且贯穿其中的老庄哲学思想,使整篇小说弥漫着道家遁世的消极、颓废、虚无。商州奇妙无比的八景十观,广泛存在的深厚的巫文化,以及众多神异的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构成了商州文化的神秘感。这不仅为贾平凹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题材,而且强化了他作品中的地域文化色彩,也直接导致了其文本独具神秘色彩和鬼魅风格。此外,贾平凹还吸收佛学思想进入作品。就佛教而言,它源自印度,后传入中国,与中国儒学结合,产生禅宗。佛重妙悟、讲虚无,常常在神秘莫测、虚无缥缈之中体现人生无常、生死轮回。贾平凹的写作潜隐着对佛家教义的宣扬,对生命存在的玄思。代表性小说《浮躁》可以说是非常写实的作品,但其中也设置了许多混茫之笔,文中不静岗和尚实质上代表了一种佛家文化精神,作者借用和尚的禅宗之学阐释世上之事皆空,各自养性才能成佛,又何必卷入纷繁的斗争之中。最能体现贾平凹佛学思想的小说是《白夜》,开篇便出现了再生人死而复生的故事,典型地体现了佛家生死轮回的观念。目连戏是指以目连救母为题材的戏曲剧目,目连救母的故事本就来自佛经,贾平凹在作品中反复铺排目连戏的内容,表现出他对佛家文化的浓厚兴趣。作品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平常就是道,最平凡的时候是最高的,真正仙佛的境界是在最平常的事物上”的思想,显现的是佛家的虚无观。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地域文化特色蕴涵着丰富的民俗学、宗教学、哲学,其中沉积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他的地域小说亦儒亦道亦佛,既能得儒之质朴、浑厚,又采道之清秀、俊雅,亦获佛之神秘、虚无。
[1]贾平凹.朋友——王蓬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131.
[2]陈思广.理解路遥——重读《路遥文集》[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5):55.
[3]路 遥.路遥文集:二[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379.
[4]斯马特.悲剧[M]//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06.
[5]路 遥.路遥文集: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67.
[6]李 勇.路遥论[J].小说评论,1986(5):74.
[7]樊 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M].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53.
[8]曹 赟,龚举善.《白鹿原》审美意象的文化解读[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3):106.
[9]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M].上海:上海书店,1986: 3.
[10]费秉勋.贾平凹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9.
[11]贾平凹.贾平凹文集:七 [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359.
On the Features of Regional Culture in ShaanxiM odern Novel Creation
GUO Meng1,2,ZHAO Xue-yong1
(1.College of Language and L iterature,Shaanxi Nor m al University,Xi’an710062,China; 2.College of Hum 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710054,China)
The three geographical plates,Northern Shaanxi Loess Plateau,Central Shaanxi Plain and Southern Shaanxi Hilly Area;have different features of regional culture.Influenced by them,the writers of Shaanxi have for med three different creation styles.LU Yao,who represents the Northern Shaanxi literature,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survival culture,thus forming a grand,bold and unrestrained creation style.Much influenced by Confucian culture,CHEN Zhongshi,as a representative of central Shaanxi literature,has developed a reserved and restrained creation style.J I A Pingwa,the representative of Southern Shaanxi literature,is influenced byQin-Han and Jing-Chu culture,hence evolving a creation style,which is either si mple and steady,or natural and simple,ormysterious and supernatural,or illusory.
Shaanxi contemporary literature;regional culture;survival culture;Confucian culture;The Jing and Chu culture
book=37,ebook=197
I207.425
A
1000-5935(2010)02-0037-05
(责任编辑 郭庆华)
2009-12-10
西安科技大学科研培育基金项目 (200706)
郭 萌 (1979-),女,陕西榆林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赵学勇 (1953-),男,陕西乾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