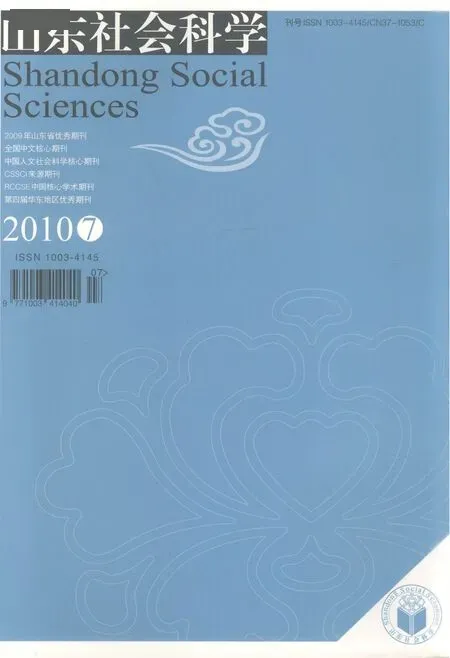道家语言观探析*
李 婧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道家语言观探析*
李 婧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道家哲学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历代的文人骚客都为其深刻的思想、奇幻的语言所征服。正是由于道家哲人运用独特的语言方式来言说思想,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语言观。
道家语言观;道不可言;言不尽意;立象尽意;批判;自然;诗化
一、道家语言观的内在理路
(一 )道不可言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道”的本义原指行进的路线,《说文解字》:“道,所行道也。”随着中国古代哲学思维的繁荣发展,“道”在本原意义上逐渐地向抽象的方向升华了。它不仅作为一个具象的概念存在,而且延伸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即泛指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法则和规律。如《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为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最早把“道”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提出来的是道家哲学的创始人老子。此后,“道”便成为道家哲学最基本也是最高的范畴,整个道家哲学都围绕着“道”展开。道家所谓的“道”含有宇宙本源和普遍规律双重意义。“道”作为宇宙本源,是一种不依赖于任何事物而独立存在的,“自本自根”,“生天生地”的“东西”。换言之,在道家哲学中“道”是一种“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老子·25章》以下所引《老子》只注篇名)“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21章)“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庄子·大宗师》以下所引《庄子》只注篇名)由此可知,“道”作为宇宙的本源是一种先天地而生的,弥漫四方,无始无终,浑然一体的“物”。但“道”又不是普通的一“物”,它还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也正因为它不是普通的一“物”,它才是不可名言的,因此老子才说“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14章)。
在道家哲学中,“道”与“言”的问题是道家语言观的核心问题。这里所谓的“道”是道家之“大道”、“常道”。先秦典籍中,多用“言”来表示言说和语言,用“名”来表示称谓和概念。老子讲道不可名,他在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章)可道之道,可名之名皆不是常道、常名。王弼注曰:“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老子》1章注)能够说出来的道和名都是可识可见有形象的具体事物,只能是“道”的具体表现,而不是“道”本体。之所以说“道不可道”是因为在老子看来“道”具有博大、幽深、玄远、恍惚 (或惚恍)等特征,道的特征决定了它不可能与任何具体事物相对称。庄子继承了老子的“道不可名”,进而发展为“道不可言”。庄子认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知北游》)妄图用语言表达“道”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种对“道”的言说,都会像“昭氏鼓琴”一样“有成与亏”(《齐物论》)。因为“道”“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论者,谓之冥冥,所以论道而非道也”。(《齐物论》)“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齐物论》)如果“道”被听到、见到,被形容出来、表现出来,那就不是真正的“道”了。庄子因此感叹道:“夫道,窅然难言哉!”(《齐物论》)王弼认为“道”“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老子指略》),他发展了老子“道常无名”(三十二章)的思想,明确等“无”于“道”,“道者,无之称也”(《论语释疑·述尔》),他将“无”看作事物的本体,它无形,无名,但又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因此不可言传,“故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指略》)
从语源学上来考察,我们发现“道”本身就是一种“言”。在先秦文献中,“道”除了在哲学文本中的形而上的意义外,其最基本的语义之一就是指言说。“道可道,非常道”(1章)中第二个“道”就是言说的意思。作为形而上的“道”与言说意的“道”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道”,“道”是使一切存在者得以存在的根源和依据。万物之所以是其所是就在于我们能够言说它们。万物只有当其被“道”(言说)出来时,才成为面向于人的存在。然而,正因为“道”本身也是“言”,所以“道不可言”,因为任何言都不能言说它本身,就像造物主可以创造一切,但却不可能创造他自己一样。
老、庄都认为“本体和‘道’是无限的、是大全,是超越一切的绝对,而有限的名和言自然就无法言说它,称谓它”①王中江:《道家形而上学》,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1年版,第 48页。,所以“道隐无名”(41章),“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齐物论》)但是他们要谈论“道”就不能不给它一个名称,因此他们又反复强调“道”其实是不能够命名,也不可言说的,称之为“道”并谈论它,只是强为之名。故老子说:“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25章)名“道”为“大”(无所不包)是不得已的事情。王弼说得好:“名以定形,混成无形,不可得而定,”(《老子》25章注)事实上是不该命名的,如今勉强给它立个名,只是权宜之计,为了一时的方便。还因为“道”难以言说,无法规定,为了对“玄之又玄 ”的“道 ”说上几句,老子用“希 ”、“夷 ”、“微 ”来指“道 ”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触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 ”。(14章 )庄子称“道 ”为“一 ”、“周 ”、“遍 ”、“咸 ”,说“通天下一气耳 ”(《知北游 》)“周、遍、咸三者 ,异名同实 ,其指一也 ”。 (《知北游 》)王弼训“道 ”为“无 ”,“无名 ,则是其名也 ”(《老子 》二十一章注)不管是“大”、“一”,还是“常”、“无”这些对“道”的不定称谓和言说都是强名、强言。
(二 )言不尽意
其实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章)就已经透露出“言不尽意”的观点,庄子在继承老子观点的基础上对言意关系做了深入探讨,进一步论述了“言不尽意”②出自《周易·系辞》,庄子中虽无此言,但通篇都在讲这个意思。。
庄子怀疑语言本身,认为语言并不能表达事物的真相,不能把握客观事物,“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齐物论》)“言”是有对象的,就是其“所言者”,但这个“所言者”却是未定的,而如果用“言”把“所言者”表达出来,那么“所言者”便成了固定的东西,也就不是“所言者”了。庄子所说的“言不尽意”主要指“道”之难尽,认为语言只能表达有形有色可以被经验的具体事物,对于无始无终、浑然一体、无形无色的“道”是无法言说的,言说出来就等而下之了。“可言可意,言而愈疏”(《则阳》)越是用语言来表达,离“道”就越远。这是为了突出“道”的特征,而不是否定语言的功能。庄子又云:“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物的粗疏、精微部分可以分别用语言表达、用心神体会,至于语言所不能议论,心神所不能传达的,那就不期限于粗疏精微了,指出语言功能的局限性。在《老子指略》中,王弼以“无”释“道”,认为言不尽“无”,因为最高规定性的“无”很难以某一具体的存在来完整地解释它,“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概”。如果强行言说它,就会“言之者失其常,名之者离其真”。
怎样解决“言不尽意”的矛盾呢?庄子不同于老子的“不言”,而是开辟了一条超越语言把握“道”的途径,并进一步揭示出言意关系中,言为实、意为虚,言为用、意为本,两者之间是一种工具和目的的关系。“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庄子的观点鲜明地表现出语言只是表达意念的工具,认为“言”的目的在“得意”,但“言”是不能尽意的,如果沉溺于“言”反而不能真正“得意”,必须“忘言”才能“得意”。这里的“忘言”是要求我们在语言文字之外去寻找丰富的意蕴,由此庄子找到了解决言意矛盾的办法,告诉我们“言”虽不能尽“意”,但是“言”可以成为通向“意”的桥梁。
(三 )立象尽意
《周易·系辞》和《庄子》都认为“言不尽意”,但不同于庄子的“得意忘言”说,为了解决言意矛盾,《周易》将“象”融入言意关系中,提出了“立象尽意”的观点。“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周易·系辞上》)
魏晋玄学家王弼在整合儒道两家语言观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老、庄的语言观,成功地把“立象尽意”和“得意忘言”融合在一起,对言意关系进行了精彩的阐释,阐明了言生于象,象生于意,立言尽象,立象尽意这样一个言、象、意关系,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玄学方法。王弼对言意关系的论述主要是在他对《周易》的注释过程中阐发的。他在《周易略例·明象》篇中论述道:“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则所存者乃非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者,则所存者乃非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忘言者乃得象者也。”他既肯定了言能尽象,象能尽意,因此可以由言观象,由象观意;同时又指出,言只是象之蹄,象只是意之筌,要想真正得意就必须超越言、象,由个别进入一般。他强调尽管言能尽象,象能尽意,但言并不就是象,象并不就是意。
至于如何克服语言和意义之间的矛盾,即如何通过言、象来洞悉圣人之意,王弼在深刻揭示语言局限性的同时,提出了“忘言”、“忘象”的方法,认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周易略例·明象》)从象上可以体察到意,从言上可以体察到象,而这种体察的前提是忘言和忘象,只有忘掉了言,才能真正得到象,忘掉了象,才能真正得到意。虽然这里的“言”是指《周易》的卦爻辞,“象”是指卦象,“意”是指圣人作卦的意义,然而正像章学诚说,“易象通于诗之比兴”(《文史通义·易较》),后来文艺理论中讲的“象”或“意象”,就是从“易象”发展而来的。王弼的论述其实已经超越了卦象、卦意,他所说的“象”并不是形象,而是指“意象”,这种言、象、意的关系与文学作品中讲的语言、形象、思想的关系是相通的。
二、道家语言观的基本特征
(一)批判语言的倾向
春秋战国之世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社会政治动荡不安,思想极度开放,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学术氛围。“名实”关系问题是哲学中认识论的首要问题,从“名”与“实”的角度来观照这一时期,一方面是旧“名”未去而新“实”已生;另一方面是新“名”已立,而旧“实”仍在,出现了“名实相怨”的矛盾现象(《管子·宙和》)。“名实”问题成为当时诸子百家竞相讨论的问题,各派学者莫衷一是,辩言争胜,互相攻击。孔子在政治上主张“正名”,强调“名实相符”;墨子提出“取实予名”的理论;韩非子提出“循名而责实”的主张。儒、墨和辩者们的言说方式的特征就是要区分出是非彼此、坚白同异,执着于固定的名实关系进行争辩。在老庄看来,这种名言之辩最有害于对“道”的探求,因此批判名言之辩。
在“名实”关系问题上,老子提出了“无名”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章)、“道常无名”(32章),既然“常道”是不可说不可名的,那么体道的圣人如何把握“道”?在老子看来,主体要进入一种物我同一的境界,“致虚极,守静笃”(16章)、“涤除玄览”(10章),才能真正地得道,而不是无休止的论辩。对老子的“无名、有名”关系解释的最为精到的,要数王弼。“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所宗也”(《老子指略》)。庄子对儒墨言辩争胜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在宥》),他讥讽惠施等人“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终”(《齐物论》),批评名辩家“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乎?而杨墨是已。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骈拇》)。庄子认识到这种执着于是非彼此和名实关系的言说方式是对“道”的一种遮蔽和亏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齐物论》)因此,庄子提出“辩不若默”、“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则阳》)言谈是不能够圆满周遍的,议论总有界限,而“道”是没有界限的,有限的言论不能表达无限的“道”,只有超然域外的合乎自然本性的“大言”才是通往“道”的坦途。
(二)自然语言的理想
道家主张“道不可言”,认为“言不尽意”,怀疑语言的能力,揭露语言对“道之本真造成的遮蔽,而事实证明,美的完整性确实丧失在语言中。任何人、任何言语包括“道”或“大”都不可能把“可以为天下母”的恍惚之美表达出来。然而,道家对于不可言的“道”不是弃之不言,而是否定一种“言”(俗言)的方式,而代之以另一种“言”(无言)的方式,这种通过言显示出的“无言”即是自然语言。
老庄之言是本真之言,是语言的自然流露。老庄都讲天道自然无为,老子主张圣人应行“不言之教”(43章),做到“润物细无声”,以求“无为”,他提倡“希言自然”(23章),听任万物自然的变化。老子还提出“贵言 ”(十七章 ),“善言 ,无瑕谪 ”(二十七章 ),“希言 ”、“贵言 ”、“善言 ”都是少说话 ,实质上都是“无言 ”、“不言”。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言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寓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天道》)。庄子认为天地万物与我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一”,既然只有这个“一”,就不容“一”之外还有一个“言”,否则“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用乎!无适焉,因是已”(《齐物论》)。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四十一章),“希声”即无声,或者说是听不见声音。王弼理解为“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声者,非大音也”(《老子指略》)。与之相类,庄子提出“天乐”,是一种“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的音乐,它无声无形却又无处不在,令人“无言而心说”(《天运》)。
道家主张的“无言”、“不言”不等于不说话,而是要顺从万物的自然本性,主张一种真正的言说——自然语言。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吾以观复。”(16章)通过保持主体的虚静来体会“道”的奥妙。不言的真正含义在老子那里是指对作为宇宙本体之“道”,只能保持静观,不能说或多说。老子还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5章)在多言时就蒙蔽了体道的智慧,要守中就要“绝圣弃智”、“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庄子要求主体“外物”、“外生死”、“离形去智”而达到“心斋”、“坐忘”的精神境界,如此才能在静观中体道。总之,道家认为要把握不可道、不可名的“常道”,就必须让言向道开放,即自道自言,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在语言中让语言本身即语言之本质向我们道说”①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海德格尔选集》(下),三联书店 1996年版,第 1093页。。
(三)诗化语言的风格
由于道家有超然的处世哲学,齐物的关照方式,崇尚自然的审美理想,因此,反映在文学上其语言观必定有着独特的风貌,是一种诗化语言。
道家哲学的基本范畴“道”具有博大、玄远、混成无形等混整性的特征,因此,“道”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审美本体要想体悟“道”,只有“致虚极,守静笃”(16章),达到“心斋”、“坐忘”的精神境界,对作为宇宙本体的“道”只能保持静观,不能说或多说,要“无言”。但是,要让人们明白不可言说的“道”就不可避免地要谈论它。于是,与“道”的混整性特征相适应,道家先哲们便寻求一种诗化的表达方式,使“道”变得既可以显见、可以言说,又不至于太多地破坏它的丰富性和混整性。老子称“道”为“恍惚”、“惚恍”,庄子用“象罔”、“浑沌”来说明“道”,老、庄都用这种模糊性的诗化语言来解释“道”,强化了语言对“道”的混整性和非认知性的审美特性的描述。“老、庄道言的模糊性正是力图保持语言对道的无限开放性,只有这样才能使道成为贯穿古今、与物宛转的‘常道’、‘大道’”②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 1991年版,第 766页。。
老子散文用语极其朴实简短,却富有哲理,五千言纵横排荡,给人一种浑沦、恍惚的审美感受;运用形象的比喻,贴切恰当的说理,“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8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78章),以水作比喻,揭示柔能克刚的深刻道理;运用鲜明的对比,用正言若反的语言形式说明不可用传统语言形式说明的道理。“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2章),“大巧若拙,大辩若讷”(45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41章),“明道若昧,讲道若退,夷道若颣”(41章),阐述了天地万物之间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庄子寓言广泛运用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是隐喻、象征之言,即诗化语言。庄子对自己作品的表现方法和目的这样总结:“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纵恣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天下》)由此,庄子将自己的哲学语言归结为三种类型:寓言、重言、卮言。庄子采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方式,以丰富的想象,以虚构的方式凭空想象许多子虚乌有的人物和故事,如《逍遥游》中以九万里高飞的鲲鹏和蓬间的小雀作比,以朝菌、蟪蛄、冥灵、大椿作比,说明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的道理。运用极其夸张的手法创造出许多奇特的人物形象,并使形象含有深刻的意蕴。如《天地》篇黄帝遗失并寻找玄珠的寓言中虚构了知、离朱、象罔等几个奇特的人物,在《庄子》中这些形象名称并非是逻辑意义上的概念,而是诗学意义上的隐喻或象征。“知”是智慧的象征,“离朱”是明察秋毫的目力的象征,“象罔”是无形无相的超感觉的存在的象征。
I299
A
1003—4145[2010]07—0138—04
2010-05-10
李 婧 (1980-),女,山东莱州人,山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汝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