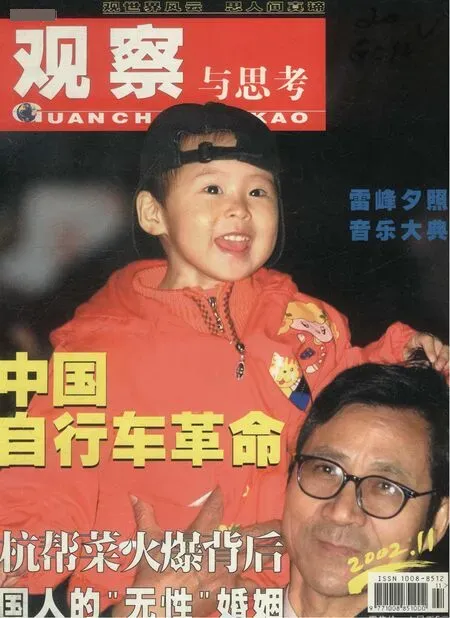我怎么写《周作人传》
■止 庵
我怎么写《周作人传》
■止 庵
我很喜欢读传记,但买这类书的时候,凡带有不注明出处的对话或“他想……”的,比如大名鼎鼎的欧文·斯通写的那些,我一律不要。这就是我对所谓“传记文学”的态度。自己动手写传记了,当然要守这规矩,我在《周作人传》序言中说:“我曾强调不能将‘传记’与‘传记小说’混为一谈。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这一底线不可移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
“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小则添加,大则编造,均系钱氏所云“想当然耳”。既是想象,就不能当作事实来写,其间没有合理不合理之分。友人谢其章尝云,所见三种周作人传,都写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晚周作人在家中被捕一事。其中拙著引述了一句话:“当军警用枪械对着周命令周就逮时,周还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注明出自一九八二年《文化文料》第三期所载张琦翔《周作人投敌的前前后后》一文。另外两种用的是同一材料,但其一写作:“当枪口对准周作人要他就范时,他只站起来嘟囔着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就跟着军警走了。”其一写作:“当军警的枪口对着他要他就范时,他嘟囔着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谢君问:“周作人的‘站起来’和‘嘟囔’,有出处吗?”此等“添笔”,无非搀杂进一种主观倾向性而已。
“传记文学”,换个名目就是“演义”。其弊害即如章学诚《丙辰札记》所批评,“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以假充真,进而以假乱真。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说是“容易招人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如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也是学者,而他有一个诗的题目叫‘落凤坡吊庞士元’,这‘落凤坡’只有《三国演义》上有,别无根据,王渔洋却被它闹昏了。”
我曾写文章说,传记写作,以下几点均系要事:(一)材料;(二)观念;(三)切入角度与剪裁;(四)文笔。盖后三项皆以第一项为基础,而这正是我写《周作人传》的困难之处。我在序言中说:“虽然陆续有《周作人研究资料》、《回望周作人》之类书籍面世,周氏的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匮乏。日记迄未完整印行,一也;书信很少搜集整理,二也;档案材料不曾公布,三也;当年的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还没汇编出版,四也;后来的回忆文章缺乏核实订正,五也。”这里且略作解释。
我写《周作人传》,有关一九三九年元旦遇刺事件,最初引用的是《知堂回想录》中所说;后来在虞山平衡编《作家书简》(上海万象图书馆一九四九年二月)中看到周作人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致陶亢德信影印件,言及此事,内容虽出入不大,却有当下记载与后来回忆之别,于是趁重印的机会,换用了这一材料。至于周作人所得来信,《回望周作人》丛书之《致周作人》一册,收录三百余通。周氏家属处尚存约两万通,据说正在整理,如能出版,将大有益于周氏生平研究。
其他中国作家的情况,其实相去不远。鲁迅也许是例外,因为早已成立了几处纪念馆、博物馆,还有不少专门的研究者,但是就迄今为止公表出来的生平材料来看,离写成迈耶斯和萨维诺那样水准的传记作品差得还远,说来我们也的确从来没有一部内容详备的《鲁迅传》。
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