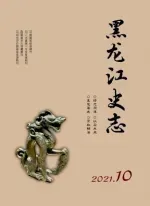周恩来在哈脱险真相(上)
赵 力
9月初,我家来了三位陌生的客人:蔡衍夫妇和蔡喆,他们是双城民国名流蔡时杰的亲孙子,给我带来了许多蔡运升手稿,以及其他资料,请求我帮助他们把祖父营救周恩来在哈脱险的这段历史弄清楚。蔡时杰,本名蔡运启,字文珊,号铁痴,黑龙江双城人。伪满州国经济部大臣蔡运升的三弟,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与周恩来是同班同寝的学友。
关于这段历史的第一版本
据我所知,关于这一段历史事件最早见诸于报刊的版本,是发表在《哈尔滨日报》1982年8月3日第三版的《周恩来路经哈埠的一件险事》,作者的笔名叫“夫山”,即哈尔滨市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张福山先生。后来,他又以真名张福山在《新晚报》1985年11月5日第三版发表了《周恩来在哈的一次脱险》,内容大致相同。
《周恩来路经哈埠的一件险事》全文是: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会前,六大代表都要去莫斯科。当时在上海的六大代表走的路线是东北,经过大连,哈尔滨到满洲里过境。为怕路上出问题,代表分三批走。周恩来同志是第二批,六月初由上海乘船到了大连。周恩来同志改乘火车后坐的是四等车,这种车又黑又脏,检票员和警兵看到周恩来同志的打扮、言谈举止与众不同,便产生怀疑,一路上注意盯梢。本来周恩来要在哈尔滨下车的,由于苗头不对,周恩来灵机一动提前在双城站下了车,直奔蔡时杰的住处。蔡时杰是周恩来的南开同学,关系甚好。周恩来说明情况要蔡时杰帮助。蔡时杰急忙打电话给在哈尔滨他大哥蔡运升(当时任滨江道尹兼铁路交涉局长)那里当秘书兼科长的徐达九(笔者注:应为“徐逵九”,下同)。叫他速来双城一起商量办法。徐是周恩来留日时的好朋友。当时蔡和徐都劝周恩来暂时在双城住上一两个月,等过了危险再走。周恩来却若无其事地说:“不行,那要误事的。”徐达九主张用交涉局的名义专门挂一辆车来护送,周恩来认为这样目标太大不妥当。最后蔡时杰和徐达九商量找一找蔡运升想想办法。于是决定让徐达九马上返回哈尔滨找蔡运升,回哈后,徐达九向蔡运升说明了周恩来和蔡时杰以及自己的关系,希望设法帮助。蔡运升考虑了一会,然后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徐达九给周恩来办个护照,就说是蔡运升的亲属病重,要赴满洲里求一位汉医治病。又派两个可靠的警卫护送,搀扶上车,坐头等车,包一个车厢。检票员来,叫周恩来装病,票由警卫拿着,以防检票员查问。万一出事,一个在车上守着,一个打电报给蔡运升。按着这个办法,周恩来顺利到达满洲里,安全过境。蔡时杰和徐达九当时并不知道周恩来到什么地方去,他们是从友谊出发,尽到朋友之责,把周恩来同志送走的。
这篇文章刊登后的第三年,即1984年1月11日《黑龙江日报》第四版,刊载了署名王俊杰的文章《周恩来同志早年三次来哈尔滨》,作者特别注明,该文“系在访问徐逵九、邓洁民的女儿邓育英之后,又参阅叶祖孚的文章等而写成的”。对这段历史描写更加细腻:
周恩来同志为了预防万一,到了长春,周恩来同志在伯父家停留一、两天,但他仍不放心,在双城就下了车,来到南开的同学和好友蔡时杰家。蔡时杰的大哥叫蔡运升,在哈尔滨任滨江道尹兼铁路交涉局长。
周恩来同志把一路上碰到的特务盘查跟踪,和蔡时杰说了一遍。蔡时杰便马上从双城往哈尔滨给徐逵九打了电话,让徐马上来一趟。徐逵九当时任滨江道尹公署的秘书兼内务科长,会英、德、日三国语言,公署的外交活动均由他去办,受到蔡运升的重视。徐接电话后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便向蔡道尹告了假,登上火车到双城,一看是翔宇(当时对周恩来同志的尊称)来了,喜出望外,他们在日本东京留学时都是很要好的朋友,而徐逵九正是听了周恩来同志的劝告,才报考了日本帝国大学经济系的。他们对周恩来同志为人正派、人品好、学识渊博、才思敏捷,都很佩服。
如今周恩来遇险,他们挽留他住一、两个月,风声过去再走,并说,蔡家是保险的。周恩来同志说那会误事的,执意不肯。徐逵九和蔡时杰商量后,当天晚上回到哈尔滨,迅即找到蔡道尹,报告说,蔡时杰的好朋友周翔宇从关内要到满洲里去,一路遭到军警特务的盘问跟踪,才到双城;并赞扬周恩来是前途有望的人物,不能让他受害。蔡道尹听后,考虑了十来分钟说:“……你办个护照就说是我的亲属病重,需到满洲里求一位汉医,他有偏方能治这种病,途中希各军警放行遵办。”他寻思一会又说:“另外派两个卫兵护送,搀着他上车,要坐头等车,包一个单间车厢,送到满洲里,车上有人查问叫他装病不要讲话,一切由两个守卫照料。万一出事,一个在车上守着他,一个打电报给我,到时候我有办法。我看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徐逵九又考虑为确保安全不走露风声,九派蔡道尹的两名卫士担任护送。就这样,徐逵九又去双城,和蔡时杰搀扶周恩来同志上了火车。到了哈尔滨站,徐和蔡下车时,又一再嘱咐两名卫士一路好生照顾。
关于这段故事,还有更加绘声绘色的描写,而信息来源,基本出自徐逵九先生。
这个生动的故事,有几个很容易发现的破绽:
1.地点不对:据蔡时杰的女儿蔡迪、儿子蔡兴瑞回忆,蔡时杰留学日本归国后不久(1925年前),便举家搬到哈尔滨花园街居住,直到1935年前后才搬回双城。
2. 时间不对:1928年,周恩来两次途经哈尔滨,根本没遇到危险。这个问题留在下面分析。
3.情节有悖常理:蔡运升一生谨慎,不能不明白帮助周恩来的利害。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样凶险的事情,他怎么可能不与自己亲弟弟密谋,而与部下商量呢?一旦走漏风声,那将是什么后果!
徐逵九,本名徐鸿渐,曾用名渐九,吉林省永吉县人。1912年吉林一高中毕业后,以官费赴日留学,1919年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1923年,毕业回国,经蔡时杰介绍,到蔡运升手下任秘书兼科长。日本侵占东北后,徐逵九在伪满政府做官,历任抚顺市副市长、铁岭市市长。1941年,因在教职员讲习班上公开宣传反日,逮捕下狱。据他的一位亲属说,他回忆这段往事时,已年逾70岁。
这个一家之言,一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广为流传,不断地演绎,许多人都信以为真。
邓颖超讲述脱险经过
《周恩来同志早年三次来哈尔滨》一文,据说引起了邓颖超的质疑,她身边的工作人员高振普说:“邓颖超听了《周恩来三次到哈尔滨》的文章后说:‘文章中所说的三次到哈尔滨的过程,有两次我不清楚。1928年去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这一次,我是作为列席代表与恩来一道去的。写这一段经过的人(指徐逵九)我是没听说过,更不相识。他写的这个过程有点像传奇小说,与事实相差太多。’”
1985年8月14日,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一文。原文是:
1982年夏,我翻阅一本《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书中有一段以《机智的周恩来》为题的文章,内容是描述1928年恩来同志和我在大连遇险事件。嗣后,我又看到过几份资料也提到此事。因作者并非当事人,都是别人对他们说的,内容并不完全。1980年《八小时以外》杂志登了一篇文章,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有些情节是作者推测的。总之,他们所写的情节不很准确和完全。我是亲身经历了那次事件的两个人之一。虽然恩来同志于60年代初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简要地讲过此事,但听到的人并不多。现在,既然有几个刊物先后发表过,我想将它的整个经过和真实的情况公诸于众是必要的。
1928年,我们党要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由于中国的环境不可能在国内召开,故决定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党的“六大”代表,将分批出发,经大连、哈尔滨这条路线赴苏。
……船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我和恩来同志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可能引起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 (实际我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恩来同志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恩来同志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恩来同志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的盘问,恩来同志泰然沉着的一一作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
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时并没有涉及到我,可我总觉得他一人去不好,当时我表示一同去,恩来大怒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这时他告诉警厅负责人,让他们帮我找旅馆,并把我送到旅馆先住下。于是我与恩来同志分开了。我住进旅馆,等候恩来同志回来。他是凶是吉很难预测。当时,我的心情是着急、忧虑不安,如坐针毡,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分秒如年了,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表面上还是沉着、镇定,装着泰然无事的样子。大约两小时后,恩来同志来到我的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我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我立即烧毁。我马上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后来,我们还是有说有笑的去楼下餐厅用餐。
恩来同志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为我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但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嗅!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似乎没有什么人跟踪我们了。住进旅馆,恩来同志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认出是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我们回家了。为什么未直接去哈尔滨而绕道吉林呢?我们怕日本警察厅去查问伯父有王某的外甥没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惊扰了伯父。我们仍然没有脱离侵华日本军人和奉系军阀控制的地区,随时可能被捕。另一方面,当时的形势,蒋介石占领南京以后,继续经山东夺取东北,咄咄逼进,使在华北、东北一带奉系军阀和日军认为共产党失败了,主要对付国民党,对我们有所放松,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利的,但也不能麻痹。所以,我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我和恩来商定,他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他三弟陪我赶到哈尔滨会合。这是我第一次当了周家的媳妇啊。
我们从上海出发到达哈尔滨,一路上的险境,由于恩来同志的机智、镇定、沉着,泰然无事的对付敌人的盘问,终于脱险了。可是,我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我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因此,我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同志,一连数日都没有接到,真是有点着急,但还是继续去车站,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他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我们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次大会。
邓颖超是和周恩来一起出国的,对这段经历说得十分清楚,文中只字未提徐逵九,更没有周恩来在哈尔滨脱遇险的事。
接待站负责人的回忆
《哈尔滨市志》大事记中,1928年4月条下:“中共中央派龚饮冰、何松亭、杨之华等来哈建立交通站,负责护送各地去莫斯科参加‘六大’的代表。至5月末,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颖超、罗章龙、李文宜等全国各地代表40余人先后经哈赴苏参加中共‘六大’。”当年为了保证六大代表的安全,中共中央委托中共哈尔滨县委在哈尔滨设立了秘密接待站,使周恩来等40余名代表从满洲里过境,顺利到达了莫斯科。中共哈尔滨县委由李纪渊负责接待站的工作。此外,还有阮节庵、沈光慈和小白。秘密接待站设在哈尔滨道里区外国四道街(现红专街)14号阮节庵、沈光慈夫妇的住所。同时,党中央还派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到哈协助哈尔滨县委完成护送任务。
在《哈尔滨党史资料》第一辑(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辑,1987出版)收录的杨之华《在哈尔滨护送“六大”代表的回忆》一文中,杨之华回忆说:当时东北的白色恐怖也很厉害,特别是大连,在日本人占领下盘查得很严,许多六大代表在大连都遭到盘查和扣押。同我一起走的有三位代表,有李文宜(罗亦农的爱人),还有两位男同志,一个是四川人,另一个是湖北人。我们到达大连也受到了盘查。敌人扣押了我们一天,反复地追问我们的来历。当时我们很紧张,惟恐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最后,敌人问我们是不是贩卖人口的(因为当时我带着我7岁的女儿),我才放了心。我说:“她是我的女儿,你们不信,可以验血型。”敌人信以为真放了我们。到了哈尔滨,我带着孩子住在道里江滨公园附近的一个同志家里。这家只有夫妇两人。这时候,因为哈尔滨地下党组织做护送六大代表的工作有困难,组织上就临时决定我留在哈尔滨帮助做这个工作,因为我带着孩子便于掩护。当时哈尔滨负责护送六大代表工作的交通联络员,是一个汉语讲得很流利的朝鲜族同志和一些其他同志。每个代表抵哈后,都是由朝鲜族同志通知我,然后我到公园或其他事先约好的地点和代表接头,并找个地方住下,对外就说我和来人是“夫妻”。当时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和检查,我和每个来的代表住的地点并不总是一个地方,有时在道里区,有时在道外区,但大部分是住在同事家里。记得那是个平房(或许是一楼),代表睡在里面床上,我和女儿睡在地板上。我住在这里,平时是不上街的,因为口音不对,怕出去惹麻烦,所以当时吃饭都是由同志给买回来吃。有时买饭不及时,我女儿就饿得直哭。在哈尔滨,护送六大代表的工作我只是临时做了一个多月,整个工作,哈尔滨地下党的同志做了许多。1928年5月,我最后一个离开哈尔滨,6月份到达莫斯科时,会议已经快要召开了。
中共“六大”结束后,中央又派龚饮冰等人在哈尔滨设立交通站。据龚饮冰在《回忆接待“六大”代表》中介绍,周恩来等代表路经哈尔滨时,决定暂住几天,进行休整和烘干文件。当时,周恩来住在天津南开同学吴玉如家里。吴玉如,安徽省泾县人,滨江道尹马忠骏的女婿,铁路交涉局秘书,住马忠骏私邸,1982年在天津逝世。据吴玉如回忆,周恩来曾两度住在他家里,第一次留宿交涉局的后院里;还有一次,“恩来是临时住在我家,当时好像秋天”。楚图南回忆说:“到1928年秋,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开会,代表们来去都经过哈尔滨,由组织介绍,分别住在同志们的家里。代表回来时,通过绥芬河昼伏夜行,到哈尔滨后,住在我家的是王德三。住别家的还有总理和罗章龙等人。他们昼伏夜行,路上又逢大雨,衣服都淋湿了,文件都是被捆在裤带里,也都湿了。”
上述都是亲历者的回忆,且都在邓颖超发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之前,言之凿凿,王俊杰《周恩来同志早年三次来哈尔滨》所言,与这些亲历者的回忆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周恩来参加“六大”往返两次哈尔滨,皆没遇险,更无脱险之事。
可见,邓颖超的回忆符合历史真实,不可置疑。张福山、王俊杰二位先生根据徐逵九的一家之言,而写的这段故事,缺乏必须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