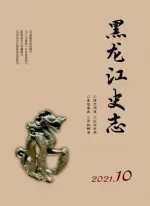贞观政治人治与法理相混合的意蕴
王 曼
(华北电力大学 河北 保定 073001)
自主张“人性善”的儒家思想成为诸子百家中的显学并取得支配地位后,其应用在政治生活中就自然而然的使政治思路倾向于人治,“人性善”是从单纯的道德维度上讲的,本身隐含着对法理理念和法律制度的排斥,所以在中国一直倡导的是“贤人政治”或“圣人政治”,缺乏运用西方分权政治和权力制衡体制的文化土壤和政治环境。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虽然皇帝有时对官僚采取“分而治之”的方法,并且设立御史监察制度,但是这只是政治上运用的权力牵扯的手段,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封建社会“治世”中,贞观之治最具有代表性,这与唐太宗超越当时政治传统的治国理念是分不开的。唐太宗不仅成功的继承了世代传承的贤人德治的人治传统,而且在治理国家过程中还初步具有了法理治国的理念并实现了制度上的突破。
一、中国的人治传统与清官意识
“长幼有序、贵贱有别”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如同今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样天经地义且深入人心,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伦理道德体系决定了权威统治的合法性,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阶层以合法的形式存在更使得中国封建社会成为典型的身份社会,在这种体制下集所有的权力于一身的皇权更具有至高无上性和不可约束性,从“八议”、“请”、“减”、“赎”、“免”到“官当”,尤其是“十恶”这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无一不是对具有“高贵身份”的贵族和官僚阶层享有减免处罚这一特权的合法保护,在不平等制度和皇权统治的前提下,权力在本质上和根本制度上是不受约束的,这样,权力与法律产生了根本的矛盾,当皇帝为明君时,便可以守法奉法,如唐太宗;当皇帝昏庸或专横跋扈时,皇权下设的机构、组织以及臣子除了苦谏也别无其他良策。唐太宗即是这样贤明的君主,他实行仁政、减轻刑罚并且带头守法,以身作则。他率先垂范,在他统治下的中国,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贪污、腐败、渎职和滥用职权的现象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贞观王朝是历史上少有的没有贪污的王朝,太宗成为百姓心中名副其实的清官,尤为可贵的是,唐太宗是以身示范和制定比较科学的制度来预防贪污,他并没有用严酷的刑罚来警告和惩戒贪污,在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没有贪污的欲念,而贪污的官吏更没有藏身之处,明朝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酷刑,但明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实属罕见。统治者自身的德行和制度的约束与保障才是政治清明的根本,民间流传着包公、海瑞等清正廉洁的官员的传说,实际上是反映着中国百姓普遍的且一致的政治期望——他们同样渴望廉洁、公正、透明的政治和管理,只是把这种希望和理想寄托于人治。百姓总是依靠清官来替自己做主,却从来没有主张自己参与政治。这种传统的清官意识也是有良知的官员自律的政治目标,因为没有制度的保障和约束。这种自上而下的、在官员中和百姓中普遍存在的清官意识,无论他们有没有意识到,都是对政府权力的崇拜,而这种政府权力又是不受限制的,因而这种崇拜是错误的、盲目的。这是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政治上的直接反应。马克思在分析路易·波拿巴时期的法国小农社会时曾指出: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由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1]
二、西方的法治传统与分权学说
纵观西方历史,还在神权统治时期,就出现了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这一观念经过历史的传承和发展,成为西方政治统治的核心理念和传统。西方法律思想发源于古希腊,这也是法治观念的诞生地。苏格拉底认为遵守法律是公民的美德,城邦的法律是人类幸福的标志;柏拉图在他晚年时期曾讲过: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2]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说: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即使有时国政仍需仪仗某些人的智慧(人治),总得限制这些人们只能在应用法律上运用其智慧,让这种高级权力成为法律监护官的权力。[3]这更为清晰的反应了他对于法治的崇尚。古希腊人认为在公共事务中遵守法律,是因为法律的精神让他们心服。古罗马的西塞罗继承了希腊人的法制观念并且更为明确的指出:法律是最高的理性,从自然产生出来的,指导应当做的事,禁止不应当做的事。[4]因此,法律必须要高于权力,而权力必须从属于法律,因为“法律统治执政官,所以执政官统治人民,并且我们真正可以说,执政官乃是会说话的法律,而法律乃是不会说话的执政官。”[5]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传统,西方在17世纪就产生了分权政治的思想,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政府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分权理论初步形成,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立法权属于议会,行政权属于国王,对外权包括外交与结盟,也为国王所行使。洛克之后,法国的孟德斯鸠指出,只有法治,才会有宽和的政府,才可能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他进一步发展了分权理论,提出了著名的三权分立学说,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且各自独立,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执掌,既能限制各自的权力大小和权力范围,又可以相互制约以维持权力的平衡。英裔美国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托马斯·潘恩明确且尖锐的表达了其法律至上的观点,他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6]19世纪,英国宪法学家戴西指出:任何人不能因从事法律不禁止的行为而受罚,特权或无限官僚权力与法治相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官吏和人民受到法律同等制约,排斥政府行为享有特殊豁免权;每个人的权利不是宪法的产物而是宪法所赖以建立的基础。[7]
三、贞观治国在理念上的突破
在以儒家德治为统治阶级治国主导思想的封建王朝,唐太宗十分重视法治。作为一代明君,唐太宗继承和发展了“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思想,他说:“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他发自内心的表示: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在告诫太子诸王要守法时说:“君主发号施令,为世作法……威者,所以治人也。”唐太宗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太宗多次减轻刑罚,废除肉刑,这充分体现了儒家的仁爱思想。法律制定出来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资治通鉴》有载:贞观元年,敕令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廕,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8]唐朝法律的主要形式是律、令、格、式,《唐六典》有载: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为止邪,式以轨物程式。据此推定,令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指令,是君主专权的体现,法与令冲突的实质是法律与皇权的对峙。法律的信条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而皇权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权力,具有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唐太宗在皇权与法律发生碰撞之时能够如此以法律来约束自己,实为可贵,这表明,太宗虽然实行仁政,但并不是同以往帝王一样将之作为礼仪规范,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将仁义爱民的政策制度化了,初步具有了依法办事的理念。
在守法方面,唐太宗多次表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大法,不可因私废法。”史载,庞相寿因贪污被撤职,太宗念旧情想给他官复原职,魏征上奏:“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太宗欣然纳之,曰:“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9]法治的核心是权力服从法律,唐太宗遵守法律,不庇故旧,开启了官吏奉法而守的先风,成为历代帝王的典范。
在执法方面,太宗强调:“人有所犯,一断于律。”[10]裴仁轨私自役使门夫,太宗“欲斩之”,按照法律“诸监临之官,私役使所监临……以所受监临财务论”[11],罪不至死。监察御史李察佑指出:“法者,陛下与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独有也。今仁轨轻罪而抵极刑,臣恐人无所措手足。”[12]太宗不仅收回了成命,而且提升了李察佑。法律的普适性使得人们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做出预期的法律评价和判断,进而得出该行为可为或者不可为,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如果法外执行,就会导致徇私枉法、草菅人命,太宗援法定罪蕴含着现代罪刑法定原则的因素,这在封建社会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贞观治国在制度上的突破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分权的目的在于避免独裁者的产生,古代的皇帝以及地方官员均集立法、行政、司法权于一身,极易造成权力的滥用。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权力如此集中又没有相应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因此中国历史上的专权和腐败屡禁不止。然而,贞观年间首次使用了制约权力的制度和国家部门。三省六部制度始创于隋代,发展到贞观时期,在唐太宗的运作下发挥了其初创者不曾料想的作用。三省分别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六部分别为吏部、礼部、兵部、度支(后改为民部)、都官(后改为刑部)和工部。中书省掌握行政大权,负责发布命令;门下省负责审查命令、签署奏章,有封驳之权;尚书省负责执行命令。一个新的政令的形成,先由各位宰相在中书省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给皇帝,准请批示,皇帝批准后形成诏书,在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到门下省进行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有权拒绝“副署”,依照法律,诏书缺少“副署”就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审查副署后的诏书才能生效为国家的正式法令,然后由中书省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交由尚书省执行。最为可贵的是,唐太宗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经过如此严格的程序审查然后发布,以防止他心情不好或心血来潮时作出的不慎重决定。这种运作方式的特点是部门之间分工明确,在权力运用上能够相互制约,有效防止了权力的过分集中和专权。这种政治模式非常类似于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西方开始于17世纪的三权分立制度,一千多年前李世民就应用在了中国政治体制中。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 677-678 页.
[2]柏拉图.法律篇[M].上海:上海出版社,2002.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转引自刘绍贤《欧美政治思想史》第93-94页.
[5]应克复.西方民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应克复.西方民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7]应克复.西方民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8]《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9]《资治通鉴·唐纪八》.
[10][11][12]《资治通鉴》卷一九二.